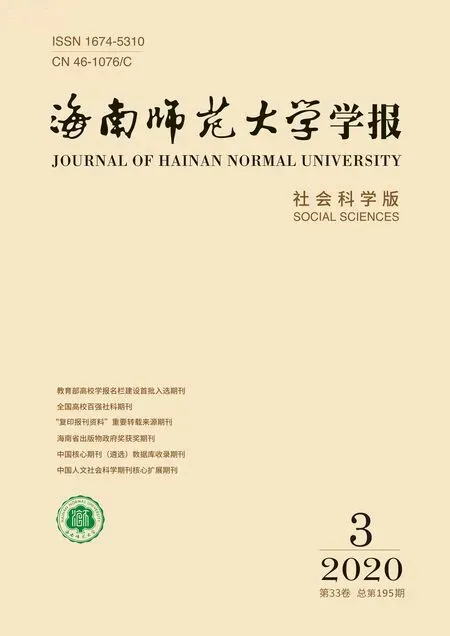新诗的道路与现代文学丰富性的挖掘
——李怡教授访谈
马雪琳,李 怡
(1.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马雪琳(以下简称“马”):李老师,在您早期的文学研究中,致力于现代新诗研究。1994年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可谓一次比较集中性的成果展示。从1994年的第一版、1999年的再版到2006年的台湾新版,再到2007年的增订版,每一次您都对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我想不单单是新诗这个话题有无限的延展性,这本著作对您来说也具有特殊的情感,那不断的修订、补充与再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您的学术研究又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怡(以下简称“李”):对我来说,这本书确实很重要,因为我始终在寻找一个最准确的表达中国新诗古今关系的方式。这本书出版后影响比较大,它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新诗古今关系的著作,过去没有那么详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大家也都比较留意。但是,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对这本书的评价中有这样一个观点:20世纪80年代太强调外国诗歌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好像使中国诗歌走上了邪路,只有回归传统,新诗才能找到一条路。这个观点让我很警觉:是不是我这本书给读者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要为中国新诗发展指出一条路,而这条路是批判向西方学习而倡导中国新诗回归传统。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根本不是我的本意,实质上中国新诗永远都应该在一个开放的姿态下。我想说明,不管如何学习西方,都不能忽视骨子里依然有中国自身诗歌传统影响的事实。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种清算20世纪80年代西化传统的倾向,其实我的追求和这个倾向没有关系,但可能被人误读。我不愿意被人误读,不愿意被人认为是一个中国新诗发展的保守主义者,我的整个论述的中心都不是说中国新诗只有回归传统才有路,其实书中有提到回归传统并不是一条值得炫耀的路,不要产生误解,但是当时有的读者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都觉得是在谈古今关系,而且把我的事实描述解读为价值观的倡导,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不断地修订,其实就是不断地要让我的这个思想凸显出来,而且后来我还在最新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导论》里加了一段,专门论述有关对传统的不同理解。传统只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这只是一种理解,中国新诗自身也构成了传统,并且从中国诗歌史的事实来看,一味只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实质上阻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到最后更是这样。我在书中有意把穆旦加进去了,因为穆旦恰恰是一个反传统的诗人,加入穆旦就是想证明我所说的“传统”含义是很丰富的,所以你说的总趋势就是这个趋势,让读者更完整地体会到我的思想和含义,所以我主要想表达这个意思。
马:您刚才提到在最新的版本中把穆旦加进去了。我还注意到在1999年的版本中,您在《前记》中引用了穆旦在1941年创作的《赞美》,包括在《后记》中,您以穆旦的一首诗作为结尾,而且我还记得您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也是穆旦。那么穆旦对您的新诗研究有什么特殊影响吗?
李: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穆旦的创作出现在中国新诗普遍被人很挑剔的时候,这时期学界一般对中国新诗成就的评价都不高,有很多批评之词,那么这里就让人产生对中国新诗这条道路的怀疑。就像郑敏在1995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中认为20世纪中国新诗,路都走错了,从胡适开始就走错了。我们要证明这条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走错了,就必然要找几个成功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研究穆旦的人很少,穆旦是我很早发现的新诗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一直是我心目当中中国新诗的方向之一,至少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我当时是带着这种可能性来写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所以当然就不会包含对这个方向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穆旦是我心目当中中国新诗发展的灯塔,有他在前方照亮我们,至少周围显得不那么黑暗 ,我们也不那么沮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马:在中国新诗作家里,除了穆旦非常优秀,您认为还有没有其他的诗人和穆旦一样值得我们关注?
李:冯至的诗作和艾青解放前直到抗战时期的诗作,我觉得都有可供挖掘的空间。穆旦、冯至、艾青以及中国新诗派当中一些诗人的一些观点。我说一些,指的不是他们每一首诗都很好,也包括七月派某些诗人的探索,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马:根据您前面的论述,我发现您对传统一直很关注,包括您刚提到中国诗歌传统不仅仅是古典诗歌传统。您的老师王富仁老师认为传统是一个浑融的整体,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来说,不仅有古典诗歌的传统还有西方诗歌的传统。那么对于传统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古典诗歌传统?对于现代诗歌创作而言,我们能够从古典诗歌传统中获得什么样的经验?
李:其实任何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很多基因。这个基因包括历史的记忆,一方面,历史的记忆作为一种知识性的存在,我们从小学习了很多唐诗宋词,构成我们知识积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知识性的基因和历史记忆,就像一个人的胃一样,有对原初的唤起你审美快感的记忆的特别嗜好。就好比你的外祖母或者你的母亲做的饭一样,当你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吃到这些饭菜的口味,不需要任何理由,就会在一瞬间产生一种特别的心切感和应和感。那么,我们从小读到的古典诗歌带给我们的意象和境界,当有一天忽然出现的时候,也会对你的心里产生一个召唤。所以古典传统永远是我们非常内在的一种温馨以及让我们感觉到蕴藉的审美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古典诗歌传统给我们的深层影响。当然,反过来说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论到,相对历史的记忆不是放在空中随手就可以抓来,要等待机遇,同时对个人来说还需要付出努力。艾略特讲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发展的辩证法,看着是属于我们的古老东西,但是却需要我们重新发挥努力才能把它挖掘出来。艾略特这句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代表了传统既是存在的又是在流动当中存在的,不是僵死不变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也许我们通过一种艰苦的努力可以唤起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唤起的记忆和历史本来的存在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觉得艾略特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继承古老的传统绝不是一个懒惰的行为,不像别的学习,我躺在那里就降临在我身上了。它是需要我们付出,而且是相当的付出,才能得到精髓。所以说继承传统也需要我们的创造力,没有创造力连传统也继承不了。艾略特这么一说,就把历史复杂的几重关系放在了我们面前,我觉得这值得现代的每一位新诗人认真思考。我们今天往往造成误解,以为继承传统就等于保守,就等于把古人的诗拿来放到现代诗歌的追求当中,怎么放得进去呢?只有努力,只有创造才能放得进去。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与回归、创造与民族文化复兴,是一个相互可以通达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很复杂的,这样问题就变得丰富了。
马:您在《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这本书中反复强调“走向……本体”“回到……本身”(1)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这个主张的提出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找寻到了另一种可能。这与您近些年提倡的“文学的民国机制”(2)“文学的民国机制”倡导从民国的经济形态、法律制度、教育等不同角度进入历史,重新梳理文学发展和意义。参见李怡:《“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有相似之处,您主张文学研究应当回到历史现场,把文学放到“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语境中分析,要从之前强调的“现代性”“二十世纪”等宏大概括中解放出来。那么在我们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传统/现代”的关系?
纵析嘉兴女弹词的兴起,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评弹演绎的核心区域苏州对女档的排斥与限制,使相当部分女艺人向浙沪流动,而毗邻沪上的嘉湖则成了重要的中转地区。二是浙江作为“浙系”润余社的演绎场域,是光裕社势力的“盲区”,对女档相对包容,使女档在浙江迅速开辟出市场。因此,名不见经传的王燕语夫妻才能在乌镇一鸣惊人,而醉疑仙等艺人的早期演出也主要游历在嘉湖一带。第三,嘉兴地近上海,受上海的都市化意识形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性别囿限,培育出了对异性身体的审美时尚。
李:我觉得不要太被这两个词束缚住,传统也好,现代也好,都存在于我们对于人生和艺术的非常新鲜、富于创造力的发现当中。一个诗人进行创作,是要发现前人没有发现过的新趣味、新的语言形态,只要有能力发现别人没有抵达的艺术深层程度,传统和现代尽在其中。“传统/现代”是理论家解释文学现象时用的词语,绝对不能成为指导诗人创作的理论。对于诗人而言,他只需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不要管什么地方是传统,什么地方是现代,不要用这个词束缚诗歌创作。在诗歌创作中,把这两个词遗忘最干净的人,是最传统的也是最现代的。相反,把这两个词当作前提,当作一个帽子,天天来思考,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传统与现代最终活在人的创造力当中。对创造者的呼唤和实际使用某种理论范式研究文学作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这种理论和那种理论都是一种假设,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不应该空洞地论述一个很大的抽象理论框架,文学的鲜活性和创造力是很重要的。
马: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背后实际上是不同思想、文化的对抗与磨合。进一步看,现代文学研究不单纯是纯粹文学的研究,而是要把它放入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认识,这样许多文学问题才能够得到更好的阐释。您曾提到过,文化是任何一个现代中国艺术家都无法逾越的关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艰难的理性对话是磨砺和塑造每一位现代中国艺术家的心灵的炼狱。那么您认为现代文化与文学之间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对话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不断在发生的过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是文学的精神生产,最终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同时,文化也部分地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状况,甚至他的情感倾向,所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警惕文化决定论。也就是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文学也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当中产生。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决定论,反对文化决定论就意味着我们虽然承认文化已经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会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动性、可变量就是人的主观性和主体性。实际上,当人的主观性和主体性发生改变的时候,文化也才能随之改变,否则文化就永远是凝固的,谈不上有自身的变化,所以说文化可以影响文学,但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文学,不能彻底地规范文学,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人的主动性始终是最重要的。
马:我了解到您在很早以前进行过戏剧、诗歌的创作,但是后来您转到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上。根据您刚才所说,相对于理论,诗人的创造力很重要,同时人的主动性始终也很重要,那么在今后您还会进行相关创作吗?
李:短期之内不会。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批评或者研究的思维方式,主要的生活状态已经在这里了。但是我早期的创作很重要,让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什么是重要的,所以说一个理论家首先是要所谓“理解之同情”。对历史境遇的理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理解作家与众不同的创作姿态,一定要理解作家在创作当中最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最拨动心弦的,否则说的都是外行话,说的是与作家创作无关的话。我的创作经历帮助我更多地理解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但是短期之内我主要还是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过没有这个经历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在研究当中更多地理解创作的独特姿态,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他们。
马:您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最近几年提倡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而感知作家的文学创作。您之前也去过日本,走访郭沫若曾到过的医院,寻找鲁迅在仙台生活的足迹。这种研究方法,您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吗?
李:我到那里主要是唤起一种感受,为了想象郭沫若,能够尽可能地还原郭沫若的某些心态,不完全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性。到那里是寻找感性,寻求与他的共振点,这点很重要。我觉得文学地理学强调地理,最终也是在特定的空间当中寻找文学的感受,而不是说进行纯客观的理性研究,这不是主要目的。换句话说只有找到了感觉,才能进行理性的研究,是这样一个关系。
马:看来地域性的发掘,不仅对文学阐释非常重要,对文学批评者来说也非常重要。在您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中,强调地域性文学和学派的个性,背后其实包含的是您对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的主张。最近“地方路径”的提出,我觉得更多的是强调地域和国家之间的共通性,那这两者之间有何种联系?“地方路径”这种研究方式最后的落脚点是什么?
李: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以前的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学是在一个国家共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现代化首先是从少数先进地区、发达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首先开始的,然后他们的发展就像投入湖里边的涟漪一样,由中心向周边进行扩散,后边的是后发达城市,区域是作为后发达城市对于先进文化的一种接收和反应,并且逐渐向更不发达的城市和区域扩展。这个思路实际上忽略了区域和城市独特的个性。那么今天提出地方路径,实质上是提出另外一个思路。实际上,地方和城市也在不断地展开自己,他们也有改善自己、改变自己,去进行现代性追求的这么一种可能性和道路。那么,通过他们的发展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整体的一个特征,形成了一个总体的中国性,所以中国性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中当然有先进或者发达的外来文化向其他地区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但是也有这些地区自身发展的过程,两者构成了一个对流,并且在不断的交流当中构成了地方和中国的现代化。“地方路径”这种研究方式最后的落脚点是丰富我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各种可能性、各种特点的认识,是把过去被我们忽略、遮蔽的一些特点重新展现出来。比如说现代化,不只是只有一种道路或者一种模式,它可能有很多潜在的道路和模式,我想这些模式未来会成为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马:关于您之前提倡的“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一方面深化了对区域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回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去阐释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路径。到今天“地方路径”的提出,从地方看中国,形成地方和国家、民族的对话,来阐释地方文学的全国性启示意义。这是否是“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的深化?其中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我分别提出了几个概念:第一个是“文学的民国机制”,第二个是“大文学史观”(3)“大文学史观”作为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强调回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中,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参见李怡:《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建构现代大文学史观》,《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第三个就是“地方路径”。当然,这些概念的提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我自身的思考,以及思想逐渐发展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文学的民国机制”强调回到国家历史形态,尊重历史的丰富性,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可以说,正是这种还原导致我们能够更切实地认识现代文学在不同区域的不同的个性。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呈现文学的丰富多彩,“地方路径”是对于“文学的民国机制”的深化。同时“大文学史观”是我们观察问题的视野和方法论。所以说这几个概念是有机的,都是对我们现代文学的一种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内在规律的深入把握。
马:对不同地域现代文学个性展现状况的重视,让我想到近年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倡将新疆的地缘位置凸显出来,其经济贸易、文化等都面临着新挑战。在过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其他一些地域,尤其是偏远地域的文化往往会被忽视。在新疆地缘位置凸显的今天,面对新疆这样有着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多民族地域,我们可以以一种什么方式进入新疆文学的发现和研究,以及新疆文学如何与其他地域文学进行互动?
李:关于新疆的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现在我还没有太多的资格发表评论。因为我自己没有研究过,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最近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地方路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地方路径”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北京上海开始,没有北京上海就没有地方,其实这个话既对也不对。对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确受到少数中心城市的影响,不对之处在于所有中心城市的影响,都不能替代各个不同地方自我发展的轨迹,实际上这两条道路是同时存在的。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这往往是每个地方文化和文学发展的真正内在动力。我强调“地方路径”就是要把这两个力量结合起来,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我认为过去纯粹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阐释,应该逐渐地和强调地方作用的姿态并存,而且后者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最近我有一系列的文章谈中国文学的地方路径问题,并且组织专栏谈论,我觉得提倡重新发现地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转向。但是发现地方不是猎奇般的展示,比如新疆哪些作家别人还不知道今天要让大家知道,不是这个含义。发现新疆或者发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反过来说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能够重新发现中国,这就改变了过去把地方作为极其特殊的文化加以叙述的方式,转为强调地方和整个国家、民族处于不间断的对话中,在地方发现了中国,在中国又印证了地方,是在这样的层面上的新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这就超越了文学地理学的观念,是强调地方的深层次内容,或者说更广大意义上的凸显,我把这种研究叫做“地方路径”研究。以后对包括新疆地区在内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有必要引入,新疆作为中国的地方路径所产生的意义在哪里,换句话说,要思考和归纳新疆作为方法有何意义。过去强调中国作为方法的意义,今天是将新疆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并加以总结和提升。从地方看中国,看出中华文化独特发展的一条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文学的全国性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