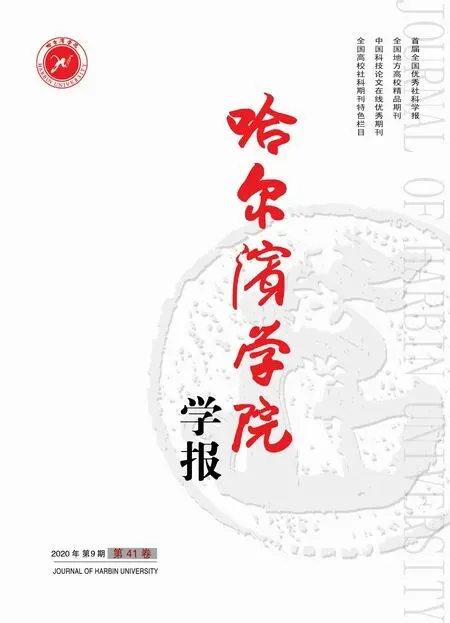刘言史著述考
高贤达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唐诗人刘言史实为一颗被埋没的耀眼诗星,皮日休称其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1](P39)严羽《沧浪诗话》称:“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2](P163)然刘言史在两唐书中无传,其生平事迹散见于皮日休《刘枣强碑》和辛文房《唐才子传》两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厘清。笔者曾就其字号、家世、生卒年、籍贯、仕历问题行文予以考辨。[3]此外,诗人的著述、思想、交游、行迹等也是其生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择其一对刘言史的著述情况进行梳理。
一、刘言史诗歌散佚情况考辨
刘言史的著述情况,历代古文献中载述如下。皮日休《刘枣强碑》称:“所有歌诗千首。”[1](P39)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称:“刘言史,歌诗六卷。”[4](P1615)郑樵《通志二十略》称:“刘言史歌诗,六卷。”[5](P1775)脱脱等《宋史·艺文志》称:“刘言史诗,十卷。”[6](P5340)辛文房《唐才子传》称:“有歌诗六卷,今传。”[7](P257)这是目前能见的公家、私家著述中关于刘言史著述情况的记载。下面我们试作简要分析:
皮日休是晚唐人,在时间上距离刘言史最近,按照常理,皮日休的说法应最可信。他在《刘枣强碑》中说:“邑人刘永,高士也。尝述先生之道业,尝咏先生之歌诗,且叹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岁之后,埋灭而不闻,与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当刊焉。’日休曰:‘存既摭宝,录之何愧!’呜呼!先生之官,卑不称其德,宜加私谥。然枣强之号,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为《刘枣强碑》。”[1](P40)由此可知,刘枣强碑文的内容是借刘永之口,由皮日休“录”成。文中有“述先生之道,咏先生之歌”的话,看来,高士刘永颇喜爱刘言史的诗歌,经常玩味赏读。既然皮日休假刘永之口成此碑文,可见其本人或直接、或间接阅览过、闻听过刘言史的诗歌是一定的。皮日休评价刘言史诗:“彫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美丽恢赡。”[1](P39)如果不是亲自读过刘言史的全部诗歌,不会有此全面、深入、精辟的见解,皮日休称刘言史“歌诗千首”的说法绝非妄论。
刘言史的诗歌存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卷”,郑樵《通志二十略》也著录“六卷”。在时间上,郑樵晚于欧阳修、宋祁,显然,郑樵的“六卷”说承袭《新唐书·艺文志》而来。至《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十卷”,由宋至元,由“六卷”变为“十卷”,表面上看刘言史诗歌的数量有所扩大,实际上,按照皮日休“所有歌诗千首”的说法,无论是《新唐书·艺文志》中“六卷”容纳千首诗,或是《宋史·艺文志》中“十卷”容纳千首诗都是可能的,只不过是史志目录分类略有差异而已。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略早于《宋史》,书中称“有歌诗六卷,今传”,“六卷”的说法亦承袭前贤而来,也可以旁证《宋史·艺文志》中“十卷”的说法并非数量上的增加。“今传”二字表明辛文房时依然能见到刘言史的六卷诗歌。按此论断,由皮日休至辛文房,即从晚唐五代经宋至元,刘言史诗歌至少保存六卷千首的存量,然事实并非如此。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中选录刘言史诗歌十三题十四首,分别为:《竹里梅》《春过赵墟有作》《初下东周赠孟郊》《过春秋峡》《长门怨》《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送婆罗门归本国》《潇湘游》《放萤怨》《观绳伎》《买花谣》《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乐府新词》(二首)。[8](P694-698)计有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北宋末期人。今检视《全唐诗》所收录刘言史诗歌,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选录的十四首诗歌在内容上不出《全唐诗》的范围。
南宋洪迈编纂《万首唐人绝句》,其中辑录刘言史五言绝句二首:卷二十一《立秋》;卷二十五《别落花》。七言绝句五十七首,其中卷二十八,五首:《长门怨》《乐府》(二首)、《过春秋峡》《竹里梅》;卷七十二,五首:《登甘露台》《夜泊润州江口》《看山木瓜花》(二首)、《题十三弟竹园》;卷七十五,四十七首:《乐府杂词》(三首)、《岁暮题杨录事江亭》《冬日峡中旅泊》《泊花石浦》《闻崔倚旅葬》《赋蕃子牧马》《牧马泉》《越井台望》《扶病春亭》《赠童尼》《读故友于君集》《病僧》(二首)、《右军墨池》《送僧归山》《题源分竹亭》《山寺看樱桃花题僧壁》《伤清江上人》《山寺看海榴花》《赠成炼师》(四首)、《上巳日陪襄阳李尚书宴光风亭》《奉酬》《病中客散复言怀》《处州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寻花》《赠陈长史妓》《题王况故居》《偶题》《恸柳论》《夜入简子古城》《桂江中题香顶台》《僧檐前独竹咏》《送人随姊夫任云安令》《山中喜崔补阙见寻》《偶题》(二首)、《嘉兴社日》《席上赠李尹》《弼公院问病》《惜花》《代胡僧留别》《桂江逢王使君旅梓归》。其中,七言绝句卷二十八《乐府》(二首)与卷七十五《乐府杂词》(三首)中有二首重出,按此,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计得刘言史诗五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五十五首,总数为五十七首。[9]
在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基础上,明代赵宦光、黄习远对《万首唐人绝句》进行了重新编定。重新编定的目的,除了理顺“洪本”混乱的体例外,同时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对“洪本”中一部分诗人的绝句进行了增补。检“赵黄本”《万首唐人绝句》,其中收刘言史五言绝句二首:《别落花》《立秋》;七言绝句四十七题五十六首(诗题略),其中,《乐府杂词》重出二首,得五十四首,总数五十六首。[10](P591-597)对比“洪本”“赵黄本”《万首唐人绝句》,其中收录刘言史诗歌情况有如下区别:(1)诗题变更。诗《上巳日陪襄阳李尚书宴光风亭》易为《上巳陪李尚书》,诗《病中客散复言怀》易为《病中客散后言怀》,诗《处州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易为《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2)疑诗未录。如《奉酬》,关于本诗的作者问题,下文还要提及,姑且不论。可见,除上述细微差别外,“洪本”“赵黄本”《万首唐人绝句》所收刘言史绝句诗,在内容、数量上完全一致。并且,检视《全唐诗》所收刘言史诗歌,“洪本”“赵黄本”辑录刘言史绝句诗在内容、数量上也不出《全唐诗》的范围。
清代刘云纷编《中唐刘言史诗》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集部·总集类·存目四》有《八刘唐人诗集》八卷(内府藏本)称:“淮阴刘青夕选,不著其名。前有康熙癸未李翰熙序,称青夕尝有唐诗十三家之刻。又辑为此本。凡刘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八人,皆《全唐诗》所已具。且既以家数区分,而版心又标曰中唐诗晚唐诗,体例亦殊未协也。”[11](P1774)刘青夕即刘云纷,根据李翰熙的序可知,刘氏所编之书体例混乱,其中所收刘言史诗依旧不出《全唐诗》的范围。序中言“皆《全唐诗》所已具”,表明较《全唐诗》,刘氏书晚出。《八刘唐人诗集》已佚,仅存目,刘云纷编选此书的目的或因所举唐代诗人与己同为“刘”姓。
综上所述,关于刘言史诗歌的散佚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晚唐五代至宋代计有功编《唐诗纪事》,在此期间刘言史诗歌出现严重散佚;自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至明代赵宦光、黄习远重新编定时,刘言史绝句诗除了辑得五十七首(或五十六,《奉酬》诗存疑)外,未见其他佚作;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言:“有歌诗六卷,今传”,“六卷”的诗歌存量与“今传”的说法均不符合历史真实;清代刘云纷编《八刘唐人诗集》,通过李翰熙的序可知,自《全唐诗》以后,也未见刘言史的诗歌佚作。
二、现存刘言史诗中的几个问题
清代彭定求等《全唐诗》中收录刘言史诗歌一卷,计得六十九题八十首,[12](P5321-5332)这是目前能见的刘言史的全部作品。检视这些诗篇,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释疑,下面试作简单辨析。
(一)《全唐诗》卷首语疑问
《全唐诗》卷四百六十八“刘言史”目下称:“刘言史,邯郸人,与李贺同时。歌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能比。亦与孟郊友善。初客镇冀,王武俊奏为枣强令,辞疾不受,人因称为刘枣强。后客汉南,李夷简署司空掾,寻卒。歌诗六卷,今编一卷。”[12](P5321)
文中涉及刘言史著述情况的表述为“歌诗六卷,今编一卷”,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这句话有歧义。既然称“歌诗六卷”,又何言“今编一卷?”不免使人怀疑有“择取”的可能。事实上,《全唐诗》是唐代诗歌的汇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来完成,其编撰宗旨以追求完备详赡为目标,断然不会有择取的可能(其中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悖的作品除外)。并且,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到清代康熙年间,刘言史的诗歌仅存一卷八十首的数量,所以,“卷首语”的表述语义指向不明。
(二)《奉酬》《嘉兴社日》《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释疑
现存刘言史的诗中,有三首值得商榷:一是《奉酬》,本诗又题李翱作,题名为《奉酬刘言史宴光风亭》。从诗题上看,本诗属于李翱的可能性较大。二是《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本诗又题王言史作,误。按,《全唐诗》中作者并无王言史,应是“刘”讹作“王”。三是《嘉兴社日》。本诗又题李商隐作,诗云:
消渴天涯寄病身,临邛知我是何人。今年社日分馀肉,不值陈平又不均。[12](P5331)
首句“消渴天涯寄病身”可以作为本诗属于刘言史的一个旁证。“天涯”指诗人一生漂泊四方,“病身”指诗人身患“消渴”病,也泛指身体状态差。无疑,这两点都与刘言史的人生暗合。一方面,刘言史行迹极广,据不完全统计,其一生到过的地方有岭南、洛阳、茅山、潇湘、潞州、长安、邯郸、润州、处州等,这与“天涯”的提法相应;另一方面,刘言史一生贫病常伴左右,试看下面的诗句:
老性容茶少,羸肌与簟疏。/那将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虫借光影强疏稀发着纶巾,舍杖空行试病身。/华发离披卧满头,暗虫衰草入乡愁。金榜荣名俱失尽,病身为庶更投魑。/欲令居士身无病,直待众生苦尽时。信陵门馆下,多病有归思。[12](P5322-5332)
这些例证说明诗人一生贫病交加,与“病身”的提法相应。清代冯浩称:“徐笺本据《岁时杂咏》收《嘉兴社日》七绝,而曰亦见《刘言史集》。考《全唐诗》小序,刘言史邯郸人,初客镇冀,后客汉南,其集中有润州、处州之作,则当经嘉兴矣。义山虽有江东之游,未知至嘉兴否?且诸集本皆不载也。”[13](P2010)由此可知,除了《岁时杂咏》将此诗归为李商隐作,历代李商隐诗集中并未收录,本诗应属于刘言史作。
(三)刘言史写过小说。
元代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引时天彝书《唐百家诗选》后诸评称:“刘言史有小说行於世,其诗铺张甚富,而咀嚼少味,正似其小说,独《竹间梅》二十八字,清洒可爱耳。”[14](P612-613)刘言史有七言绝句《竹里梅》,诗云:
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时。[12](P5324)
“间”与“里”词义相近,《竹间梅》即《竹里梅》。细读这首诗,诗风“清洒”则有之,“可爱”却未见。至于刘言史写过何种小说,今已不可考。从吴师道“咀嚼少味”的评语看,刘言史小说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唐人小说以传奇为主,刘言史小说可能是这一类。
三、关于《射鸭歌》的几点思考
刘言史曾作《射鸭歌》,全文已佚。皮日休在《刘枣强碑》中说:“武俊性雄健,颇好词艺,一见先生,遂加异敬,将署之宾位,先生辞免。武俊善骑射,载先生以贰乘,逞其艺於野。武俊先骑,惊双鸭起于蒲稗间,武俊控弦,弦不再发,双鸭联毙于地。武俊欢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词如是,可谓文武之会矣。何不出一言以赞邪?’先生由是马上草《射鸭歌》。以示武俊。议者以为祢正平《鹦鹉赋》之类也。武俊益重先生。”[1](P39)这篇作品写于刘言史造访王武俊期间,两人在野外举行“文武之会”时有感而发。
《射鸭歌》的具体内容,今天已见不到,文中记载《射鸭歌》与《鹦鹉赋》相类似,透过《鹦鹉赋》或可以窥测《射鸭歌》的相关情况,兹录《鹦鹉赋》全文如下: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绿衣翠矜。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网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金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剪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踰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悯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感平生之游处,若壎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躇。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抱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15](P942)
祢衡,字正平,汉末人,《鹦鹉赋》是其代表作。我们试从历史背景、依附对象、书写形态、艺术手法、作者心态等方面来比较这两篇作品。
其一,关于“历史背景”与“依附对象”。“议者以为祢正平《鹦鹉赋》之类也”的说法当有根据,笔者认为这个“古典”正是《后汉书·祢衡传》所说: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16](P2657)
此时,祢衡依附黄射;刘言史依附王武俊。黄射、王武俊作为“依附对象”,两个人身上有共同性。一方面,他们都是武将,从“颇好词艺”“射爱其词”的记载看,他们又都雅好文艺。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也类似,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黄祖、黄射父子名为刘表部下,实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唐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现象严重,王武俊名为臣,实有不臣之心,历史上其人也多次反叛。由此看来,这两篇作品都作于社会不稳定的动乱时期,作者所依附的对象都是附庸风雅的武人。
其二,关于“书写形态”与“作者心态”。从“何不出一言以赞邪”“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的记载看,祢衡、刘言史皆是受依附对象的请求被动地创作,祢衡因黄射赏识在宴会上以书写的形式作《鹦鹉赋》,刘言史因王武俊赏识在围猎场马上口述《射鸭歌》,此情此景何其相似。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两篇作品都是应“主”之请的被动之作,但其所抒发的都是愉悦状态下的真情实感。以《鹦鹉赋》为例,祢衡在赋中抒发了一种“得遇明主”的心态,他以鹦鹉“奇姿”“妙质“性慧”的“灵性”自比,“飞不妄集,翔必择林”,正喻贤臣择主。可以说祢衡在黄射这里找到了归宿感,以他“尚气刚傲,矫时慢物”[16](P2652)的性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比之下,刘言史一生漂泊四方,也在王武俊这里寻到归宿,遗憾的是,诗人如何用文字表达的已不可得知。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大相径庭,祢衡由于性格使然,终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其实在赋中他已经透露了这种危机感,“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身。故献金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由此看来,祢衡是懂得处世之道的,但他终究不能违背本性之真,后以言语非议黄祖导致杀身,落得悲惨结局。与此相比,刘言史心里则内怀城府,笔者曾就刘言史拒官“枣强令”一事作过辨析:刘言史造访王武俊在其为恒冀观察使时期……王武俊敬重刘言史,待其甚厚,两人的“文武之会”可证……王武俊谋反一事,刘言史或事先知晓,从“先生造之”一语看,刘言史是主动依附王武俊的,本希望求一寄身之所,未曾料想王武俊谋逆行径,总之,这可成为其不就枣强县令的又一原因。[3]刘言史最终并未杀身成仁,这是其值得庆幸的地方。
其三,关于作品的艺术手法。两篇作品都采用了动物的意象,《鹦鹉赋》以“鹦鹉”为意象,《射鸭歌》以“野鸭”为意象。《鹦鹉赋》《射鸭歌》皆是咏物赋,借物言情,抒发了作者“言志”的心态。《鹦鹉赋》“辞采甚丽”,已摆脱了汉大赋枯燥乏味的铺张叙写,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受,为了不喧宾夺主,这里仅作简要分析。至于《射鸭歌》,由于内容佚失,笔者妄测也是相同的风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