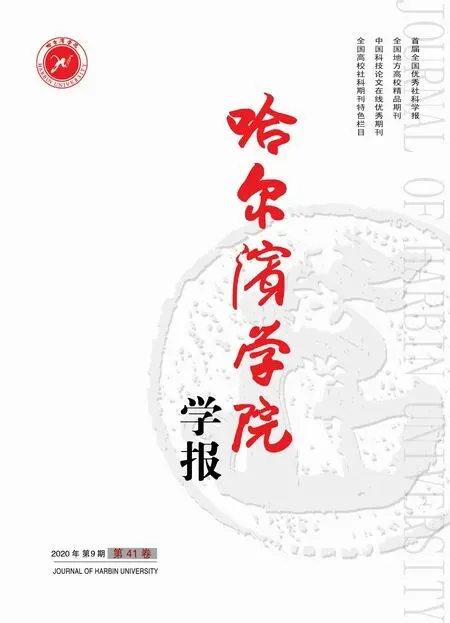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未遂犯的认定
任增亮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吉林 长春 130028)
一、案情简介
2018年3月晚间,付某驾驶摩托车途经某铁路道口时,因见道口栏杆闭锁,遂与道口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将所骑摩托车横置在铁轨上,扬言要让工作人员下岗。工作人员上前阻止,并表明即将有火车通过,但付某仍然不听劝阻,几番争执之下,工作人员终于在火车经过前将摩托车从铁轨上移走,未造成伤亡事故,但火车因此停车七分钟。事后,铁路安监部门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表示根据当时现场监控视频来看,由于付某的摩托车在铁轨上放置的位置特殊,所以即便这辆摩托车不被移走,火车头也会将摩托车撞开,并不会影响到火车的正常行驶,更不会有造成火车脱轨、倾覆的可能性。
本案中,关于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铁路安监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来看,尽管付某有较为明确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但其将摩托车横置在铁轨上的行为不存在实际危险性,即便工作人员未将摩托车移开,也不会对火车的正常行驶产生任何的影响。也就是说,付某的行为属于方法不能犯,不具有可罚性,故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付某的行为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由于未造成现实危险,所以未达到既遂的标准。根据我国《刑法》第114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存在既遂和不构成犯罪两种情况,不应存在未遂,故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付某的行为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本案中,付某已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客观原因导致法定的危险状态没有产生,故其行为应属未遂犯,而非不能犯。
上述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付某的行为属于方法不能犯还是具体危险犯;二是如果付某的行为属于具体危险犯,又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二、方法不能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分
不能犯从概念上理解,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犯罪结果,但其客观上的实行行为显然无法既遂的一种特殊未遂状态。理论界一般将不能犯分为方法不能犯(又称手段不能犯、工具不能犯)、对象不能犯(又称客体不能犯)、主体不能犯三种类型。[1]其中方法不能犯是指由于行为人采用的犯罪方法严重错误,致使犯罪结果无法实现的一种未遂。比如,甲误将白糖当砒霜,投放到乙的水杯里,其杀人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方法不能犯。
具体危险犯,是一个与抽象危险犯相对应的刑法概念,前者指某一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如确定具有危险性,则为具体危险犯;而后者是根据社会传统观念拟制出的法定危险,行为一经作出,即认定危险的存在,无需再经个案判断。如我国《刑法》第116条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就是一种具体危险犯,它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对行为人的行为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来判断是否存在现实危险性。而《刑法》第122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船只、汽车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一般社会经验,只要发生劫持船只、汽车的行为就会存在现实危险,因此该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就是一种抽象危险犯。
从概念可知,具体危险犯与方法不能犯的相同之处在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都未发生实害后果,而区别则在于是否存在法益遭受侵害的现实危险性,如果存在,则属于具体危险犯,反之则为方法不能犯。目前学界对于判断现实危险是否存在的标准存在很大争议,总结来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大学说:
1.纯粹主观说。这一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存在着明确的犯罪故意,即便结果没有发生,也一律不能认定为不能犯,但迷信犯(比如将尸体当成活人射击,因为行为人具有杀人的犯罪故意,因此应当以故意杀人未遂来定罪处罚)除外。这一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一是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等同于现实危险,有明显的主观归罪之嫌,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不能犯的存在;二是它将迷信犯排除在外,与自身的观点并不相符,难以自圆其说。
2.印象说。该学说以社会公众对行为的主观感觉作为判断危险是否存在的唯一依据,如果公众因为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产生了安全感的动摇,那么其行为就属于犯罪未遂。德国刑法就采用了这一观点。该学说以难以标准化的公众感受作为判断准则,将不能犯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并不适当地扩大了刑罚适用范围,因此不应适用。
3.抽象危险说(主观危险说)。该学说是指以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所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以社会普遍认知作为判断危险有无的标准。如果按照原计划,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具有危险性,即成立犯罪未遂,反之则为不能犯。[2]该学说目前被我国刑法学界普遍接受,它对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做了拆解分析,将一部分危险性不大的行为归纳为不能犯。如甲认为少量硫磺可以杀人,就打算将少量硫磺投放到乙的水杯里,结果一时失误投放了白糖。甲的行为按照社会普遍认知来看,并不具有现实危险性,即便按照原定计划投放硫磺,也不会威胁到乙的生命安全,因此甲的行为应属方法不能犯。抽象危险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判断标准清晰、具体,易于被司法机关掌握。但本质上这一观点仍是印象说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在印象说的观点中,社会公众是对行为人的全部行为进行感受,即除了行为人的计划行为外,还包括实际的作出行为;而抽象危险说要求公众仅对行为人的计划行为进行感受,从而判断是否存在危险性,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仍有较大的不足。比如按照抽象危险说,所有的对象不能犯都应按照未遂犯处罚,只有部分危险性小的方法不能犯才不具有可罚性。如甲闯入乙的房中,对着床上连开数枪,但误把床上的枕头当成了乙,而且乙很久以前就不在此居住了。甲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对象不能犯,但按照抽象危险说的观点,甲的计划行为是对乙开枪射击,这在公众看来具备危险性,所以不应属于不能犯。这一结论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4.客观危险说。该学说是站在事后判断的角度,结合所有情况来科学、客观地分析行为做出时产生现实危险的可能性。[3]如果事后判断当时的行为根本不会造成危险,那么该行为就属于不能犯。但某一客观行为没有发生实害后果,除行为人主动中止外,一定是出现了未能预料到的偶然因素。按照客观危险说的观点,这些偶然因素又都必然导致现实危险的不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未遂犯都不会产生现实危险性,这突破了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底线,因此并不可取。
5.具体危险说。该学说是站在事前判断的角度,以一般人的经验来对客观行为进行分析。当行为作出时,按照社会普遍认知存在危险的,应属于未遂犯,反之则为不能犯。这一观点中判断危险存在与否的对象是行为人的实际作出行为,这也是该观点与抽象危险说的最大不同。其不足之处与印象说一样,都没有说明社会普遍认知采用何种判断基准,因为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不同的人对于同一行为是否具有现实危险性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尽管上述学说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但它们对不能犯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步骤,即判断现实危险是否存在,只不过在判断对象是计划行为还是实际作出行为、判断角度是事前判断还是事后判断等方面上有所区别而已。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界定危险的本质,即危险是以行为作出时行为人或社会一般人的主观认识为依据,[4]还是以事后对行为的科学判断为依据。本文认为危险应当是在行为作出时的一种主观感受,如果站在事后角度去做客观判断,就会发现犯罪后果不能发生的“偶然性”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因此以事后客观判断为依据并不适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判断客观行为是否存在现实危险性时,应当在坚持事前判断的前提下对犯罪结果未达成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考虑原因不出现的可能性大小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对于可能性较大的行为,尽管因为偶然因素的出现不会产生危害结果,但出于对公众心理安全预期和社会稳定性的保护,也仍应认定为具有危险性。比如甲向乙开枪射击,但乙弯腰躲过了子弹,甲之所以没有开枪射中乙的原因是乙偶然性的弯腰,但乙没有弯腰的可能性很大,即甲射中乙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甲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未遂。但如果甲没有打中乙的原因是误把山上的稻草人当成乙,而乙本人并未在附近。由于此时乙出现在山上的可能性小,所以甲的行为应属于不能犯。再比如,甲在加油站与加油员发生争执,一气之下掏出打火机,想要点燃身旁的柴油加油枪,被工作人员及时阻止。柴油的燃点较高,且点燃需要达到一定的压强,因此甲想用打火机在正常的环境下点燃柴油是不可能的。但甲只是随机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加油枪去点,并未有意识的加以选择,也就是说他选中其他可燃物品的可能性很大,是具备现实危险的,所以甲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不能犯。
具体到前文的案件中,付某将摩托车横置于铁轨中央,由于其摩托车放置位置特殊,所以也不具备造成法定危险状态的可能性。但通过生活常识我们可以判断,摩托车“放错位置”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换言之,由于摩托车的横放造成火车脱轨、倾覆的可能性很大,这一行为是具备现实危险性的。所以付某的行为不属于不能犯,而是属于具体危险犯。
三、具体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
关于具体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这一特殊形态,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一部分学者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具备现实危险性是具体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只有存在危险,才有可能构成犯罪;如不存在风险,也就不构成犯罪,自然没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其他学者持肯定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当中规定的危险犯其实都是实害犯的未遂犯,因为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绝不仅仅只是为了造成危险状态,一定是为了寻求一个实害后果,如果将后果的产生看作既遂的话,那么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应该都是未遂,只是刑法按照既遂来定罪。[5]
否定说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将法律规定的“危险”与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相混淆。具体来说,前者是一种法定危险状态,如刑法中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应当产生类似于放火、爆炸、决水、投毒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这其中“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就是一种法定的危险状态,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应当是指能够阻却危害后果发生的偶然因素出现可能性较小所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需要根据个案来判断的风险,与法定的危险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一般而言前者的危险性要大于后者。
从我国《刑法》第114条、116条、117条、118条所规定的内容来看,法律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的发生作为上述犯罪既遂的标志,而实害后果的发生反而变成了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如果我们将危险状态的发生拟定为一种犯罪结果的话,就不难发现具体危险犯与其他实害犯相比在犯罪构成上并无实际差别,即具体危险犯与实害犯一样,都应存在未遂形态。行为人犯罪行为的着手与犯罪结果(危险状态)产生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当行为已经着手,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犯罪结果(危险状态)没有产生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可能在具体个案中无限接近,但绝不会重合。因此,具体危险犯应存在未遂形态。
前文案件中,付某已经将所骑摩托车横置在了铁轨上,即实行行为已经着手,只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从而使得法定危险状态没有发生,但其行为本身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危险性,因此付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具体危险犯的未遂形态。
综合上述分析,付某的行为在本质上应属于具体危险犯的未遂,而非方法不能犯。根据我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付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