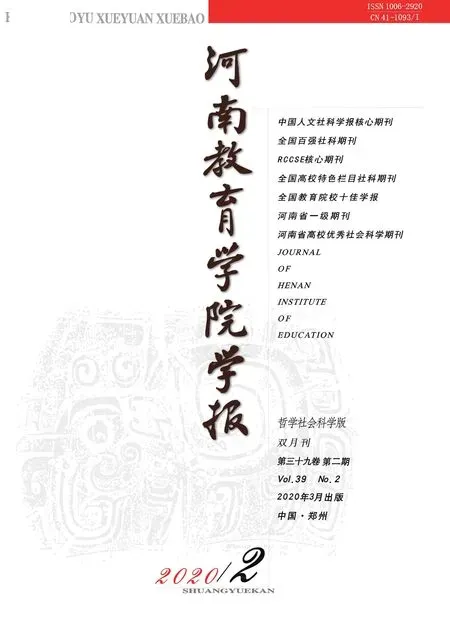跨文化视野下基于人类学范式的声景研究综述
王文慧
声景,即声音景观,由英文合成词“soundscape”翻译而来。随着时代的推进和语境的转变,声景的概念不断被重新建构。加拿大音乐家Robert Murray Schafer(罗伯特·穆雷·沙费尔)于1976年最早提出“声音景观”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环境中本身存在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价值。[1]科技史学家Emily Thompson(埃米莉·汤普森)在其著作 《现代性的声音景观》(TheSoundscapeofModernity)中将声音景观定义为:“有关听觉感知或耳朵的风景(an auditory or aural land-scape)。”[2]1孟子厚、安翔、丁雪合著的书作中则支持“世界声景计划”对声景的释义:“一种强调个体或社会所感知和理解的声音环境。”这很清楚地表明声景是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件来理解的,是通过声音来理解特定的时代中的人们与环境作用的方式。[3]3
从声景早期的研究来看,人类学的直接参与较少。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以声音为传播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声景资料的价值亦被研究者不断赋予新的含义。笔者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时发现,国内学者对声景的讨论通常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纳入其研究之中,研究对象及路径逐步转向民族志过程、日常生活等,关注存在于仪式信仰与城市文化中的声景,并呈现出学科融合的趋势。本文以“声景”来对应人类学视野下的声音问题研究,突出人类学概念中文化的整体性、多样性,强调以参与和观察为前提阐释声景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一、多学科交叉语境下的声景理论研究概述
国内基于人类学范式对声音景观的研究成果颇丰,探讨日常生活里的声音,深度呈现人与其所处的声音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就以下两个维度对人类学视阈下声景的理论性研究进行讨论:一是基于人类学范式的声音生态学对声景的研究;二是音乐人类学对声景的研究。
声景研究是声音生态学的主要任务。随着对声音研究的深入,声音生态学范畴的声音景观概念逐渐被其他有关声音研究的领域所沿用。由孟子厚、安翔、丁雪合著的《声音生态的史料方法与北京的声音》一书一改过去仅限于对声音生态理论层面的研究,在保持对理论论述的基础上,将研究内容聚焦到老北京声景文化所遗存下来的物质及非物质信息,通过对现存历史档案、田野录音等多种声景生态资料形式的整理与分析,具体展现对声景生态资料的应用取向。[3]范钦慧的《大自然声景——一个野地录音师的探索之旅》则是一本探讨声景的田野笔记。该书作者深入田野,通过长期的田野跟踪调查,记录生活中各种自然、人为的声景,形成声音民族志的文本书写。[4]作者立足博物学的学科视角,对声音的观察停留在搜集以及文化说明的层面,并没有对声音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声音表象的文化意涵做更深入的探讨。
音乐人类学研究者最早开始关注实践中的声景,研究范围涵盖了整个人类进行音乐活动的场景,并对如何以人类学视角研究声景进行了讨论。汤亚汀的《城市音乐景观》一书是国内首部以“声音景观”概念贯穿始终的著作。作为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具有时空流动性的音乐生活景观,城市声景与人类的日常生活以及声景所生成场域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该书结合实地考察,从音乐生活的时空流动景观、技术-传媒景观、经济景观、意识形态景观、人的景观以及多景观联动与互动等多个不同立面,对城市音乐景观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与论述。[5]曹本治的《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将仪式语境中的音乐景观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信仰、作为信仰仪式展现部分的音声、作为主体的人及其行为三者间的互动,同时,该书关于“信仰、仪式、音声”理论构想的建立与实践也为研究仪式音乐提供了理论框架以及方法论支撑。[6]
不同于以声音为本体的相关自然学科的研究范式,基于人类学范式对声音的整体性研究实际上是将声音及其所产生的场域作为一种文化事件来理解,以声音为切入点,重点突出声音的发生场景中人与时间、空间的互动,和声音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与意义。从上述两种声景研究维度来看,国内学者对声景的关注已经从仅研究声音转向通过声音来关注其所在地域社会的文化生活,采用口述资料搜集、参与观察等多种田野调查方法,形成了多学科相互交叉与融合的研究视角。可以说,声景研究聚合了视觉图像与声音信息,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生活场景中去考察,这也成为各相关学科选用人类学的范式对其进行讨论的主要原因。
二、声景研究的民族志尝试
关于声音景观的研究,国内学者用民族志的方法做过许多尝试。在民族志的写作中,研究者着重关注声景中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但也出现了不同面向的对声音问题研究的表述方式。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方法论研究和个案实践研究两方面。
张连海的《感官民族志:理论、实践与表征》认为研究者应关注民族志研究中的“身体感”,即把自己置于同被研究者类似的位置,获得自身与他者的感官体验,并提出将身体体验与文化观念连接起来,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深究被隐喻的地方文化。[7]萧梅的《从感觉开始——再谈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中提到的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也是类似的思想,即以个体经历式的实践本体论去建构双方行为。[8]前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感官及其手段的应用;后者则将这种通过感官所形成的“身体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引入音乐民族志的写作中。
杨民康的《“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研究中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的读解》和周凯模的《“仪式音声民族志”文本建构——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民族志书写》都是对音声民族志写作的方法论研究,集中体现了民族志研究者在理论与方法层面上的思考。杨民康主要通过对认知人类学和阐释学研究方法的梳理和理解来明确音乐人类学的考察对象与研究路径。他将某一声景文化定义为“文化活动文本”,“历史、社会、个体”等都被作为“文化活动文本”的研究范畴,通过微观的深描寻求存在于某种事物及群体之中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及文化结构模式。[9]周凯模以考察广东排瑶“歌堂仪式音声”时形成的数个民族志文本实验为基础,提出“音声民族志的文本建构”设想,认为解释学民族志文本的书写方法由“行为深描文本”(口述文本、书写文本和现场文本)与“意义阐释文本”(民族志行为阐释、音乐学音响阐释和符号学意义阐释)共同建构。[10]
徐欣的博士论文《内蒙古地区“潮尔”的声音民族志》是以内蒙古地区的潮尔音乐,即弓弦乐器“潮尔”与人声合唱“潮林道”为研究对象所写的声音民族志。论文将蒙古族及其自身对潮尔的听觉体验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潮尔的声音进行多维度考察,揭示了立足于蒙古族生活世界的潮尔的声音观念与审美意义,继而阐释由潮尔声音所透视出的地方历史文化。[11]林莉君的《浙江省磐安县仰头村〈炼火〉仪式的音声民族志》重点讨论了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深泽乡仰头村“炼火”仪式中的声音。该文作者把音声置于信仰体系中,分析存在于其中的“敬”“敬+娱”“娱”等多重音声,并指出声音作为“神圣”与“世俗”沟通的桥梁,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融合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12]
国内人类学者对声景研究的民族志书写实践,其关注的对象多为仪式中的声景,对存在于仪式之外的声景个案则较少采用民族志书写实践进行研究。尽管研究者尚未拓宽对音声民族志的研究视阈,但不可否认,现有的对仪式声景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仪式音声民族志”书写的逻辑框架,即通过对某一特定的文化事件中互为表征的“行为”与“意义”的深描,实现对从表征系统至意义系统的整个过程的阐释。
三、人类学范式的声景研究路径与面向
文化地理学认为声景是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是物理现象,更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心理情感体验现象。较早将声音景观概念纳入研究范畴的音乐学者主要关注音乐景观,他们以多重视角及研究范式,分析生活场域中的音乐,解读音乐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当下,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被各学科广泛采用,讨论的问题延伸到社会秩序、民间信仰、地方记忆等方面。就具体的研究路径而言,一方面,从声景的发展状态出发,探讨声景的仪式性、场域性和当下性这三种存在样态;另一方面,探讨声景的个体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以及声景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关系。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将基于人类学范式的声景研究分为仪式声景和城市声景。
(一)仪式声景
仪式在人类学研究领域里,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活动,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13]1仪式声景(ritual soundscape)指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或听不到的、对局内人具特定意义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14]笔者在梳理相关仪式音乐或仪式中的声音等研究时,发现多数研究者常选用“音声”一词来表述存在于仪式中的声景,特别是在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中。关于“音声”的概念,笔者参考前人文献研究成果,阐述如下:(1)“音声”最早由曹本治提出,与英文概念“soundscape”对应,特指仪式景观中的声音。[14](2)曹本治所提出的 “仪式中的音声”,即音声境域(ritual soundscape)概念同“仪式声景”相对应。曹本治主编的《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提道:“我们对‘仪式中音声’这一研究对象,就仪式展现中音声现象所给予研究者的情境感觉以及音声对仪式的覆盖与仪式场域的整体性关联,称之为‘音声境域’(ritual soundscape)。”[6]45(3)提出“音声”概念的意义在于强调仪式情境、仪式场域,认为“音声境域”(ritual soundscape)这一概念可以融会文化秩序、社会结构、生活场景、经济制度、政治环境、意识系统、信仰体系等多层面内容。[14]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仪式声景和仪式中的音声研究,两个概念可以互换。
萧梅的《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认为,生成于信仰仪式的仪式音声不仅是仪式展演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其作为仪式中具有支配性的象征符号,在建构仪式及表述信仰的过程中内化成文化模式,被其文化和社会群体所感知。[15]同时,仪式音声具有特殊的制度性。作者在文中通过对不同类型仪式和仪式场域的研究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反复论证在仪式的展演结构和音声属性上形成的音声的制度性虽普遍存在于生活的场域,但其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研究者在田野考察时只有注重仪式音声表述的细节、仪式种类和个案数量的积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仪式的内涵。
李萍的博士论文《无锡宣卷仪式音声研究——宣卷之仪式性重访》[16]基于人类学研究范式对无锡地区“念佛”仪式中的宣卷进行考察,通过对无锡地区保存的宣卷活动的民族志书写,阐述了宣卷作为仪式行为的历史本质和本意,反思了过往学界以说唱(或曲艺)界定宣卷,而忽略其原本仪式信仰语境的局限性。这与美国音乐学家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提出的“音乐人类学中的声音景观研究所关注的就是一种有特色的背景、声音与意义”[17]的理念不谋而合。
仪式不可缺少音声,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论证的问题。早期音声研究中,“由于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民族音乐对信仰体系中‘音声’的研究范围,暂时只能顾及听得到的‘器声’和‘人声’两大类‘音声’”[18]384-385。当然,由于“音声”一词的提出者是音乐学家,故而学界对仪式声景的研究主要以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中的仪式音乐为讨论对象。由此亦可以说明,“音声”这一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术语不能用来指代仪式中的所有声音。细究现有仪式音声的研究个案也不难发现,研究者不仅对乐器、歌声等声音形式进行研究,还从“非音乐性”的仪式音声入手来拓展声音研究的范围,如大量的“语言性”音声以及仪式所在的自然环境等各种形成声音的元素,力求更为立体地解读仪式文化与仪式音声之间的关系。
詹晶晶的硕士论文《国恩寺水陆法会“放焰口”仪式音声的考察研究》虽然是以国恩寺水陆法会中“放焰口”仪式音声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在研究“放焰口”音声过程中发现存有非音乐性且仅具有“语言性”的音声,并由此反思对于仪式音响研究单有音乐性层面的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贯穿整个仪式的所有音声进行研究以全面理解和表述音乐在地化的过程与意涵。[19]纪仁春的《南传佛教仪式音声初探——以景谷地区泼水节为例》聚焦具有较强地域性特色的泼水节期间各项仪式生产出的滴水、堆沙、朝仙等音声,并从声音的视角对南传佛教音声与南传佛教的传承、传播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0]文章虽然通过大量的观察资料集中展示了整个田野过程,但在表象与深层、结构与行为上的把握仍显不足,对仪式中存在的许多自然音声未能联系地方社会生活做更为深入的讨论。
(二)城市声景
近些年,人类学家对大都市进行调查研究的面向更为广阔,关心各种类型的社会——复合的、传统的、现代的,以及城市的和跨国的网络。[21]声音作为城市的听觉生命,是城市空间特性中鲜活生动的存在。尤其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声音景观也急速变迁且呈多元化,许多研究者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流动性更强的城市声景,通过观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声音,探究城市空间中人与声音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声音对历史的表征、对人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建构。
法国声音理论学家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译介到中国的《声音》一书,荟萃与整合了不同学科与声音领域交互所获的各种研究概念。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阈下集中呈现有关声音研究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从知觉经验的改变这一角度入手,提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结论,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论,拓宽了声音研究的可能性,同时也打开了研究现代社会声音景观的新视阈。[22]李志铭的《单声道:城市的声音与记忆》是一本以田野笔记的形式来记述城市声景的著作。作者通过自身的记忆,对现代城市所拥有的以及早已消散的、被遗忘的声景进行记录、描述、思考,并通过参与观察整理和阐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23]罗兰德·阿特金森的《音响生态学:都市空间的声音秩序》将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融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声音是如何参与建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以及影响和规训空间中人的行为等问题的讨论,来揭示声音的存在意义,阐述建构主体、民众参与之间的复杂力学关系。作者认为音响是可以被操作和建构的,无论是有规则性的乐音或者是无序的噪音,其在空间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24]这篇文章关注声景与生产力量的互动,强调学者较少关注的声音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波的博士论文《城市藏人声音景观的多元空间表达——基于成都的田野考察》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对声音景观的界定及阐述逻辑,研究视阈辐射到藏人音乐活动所在的文化空间,囊括与城市藏人音乐相关联的乐音、乐人、乐事及其文化意涵,从而追述藏人音乐在城市中的流变与发展情况。[25]论文虽然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但更多的是对音乐生活的记录,缺少深层次讨论,如多种外部力量对个体音乐生活的塑造,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接受与回应过程。
四、总结与思考
从声景最初的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基于人类学范式开展的声景研究成果较多,呈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跨学科视角,多数研究成果归属于音乐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虽然研究者在研究范式、价值取向层面具有较强的人类学导向,但限于研究对象所在的主体学科视域,各学科的研究还是以突出声音的本体内容为主,同与声音实际互动的人和生活的关联并不大。音乐学学者对声音的关注重点一直是音乐,无论是早期研究的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还是现在所关注的城市音乐,其本体论以及知识体系所支撑的都是对有旋律、有节奏的声音的研究。但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噪音、自然的声音都被引入到音乐创作中,形成表征审美以及传递一定特殊价值的可流传的音乐作品。这些曾被认为是非音乐的声音尚且能被作为具有社会意义的音乐创作素材,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开始关注和深入讨论它们与生活之间的互动吗?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对个体的身心塑造与群体的社会关系维护所发挥的功能不言而喻。反言之,植根于生活之中的音乐行为,亦是在社会行进的过程中生成与延续。因此,声音景观是日常社会中诸多文化景观的一个缩影,应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件来理解。从感官经验切入研究,可更为强烈地切身感受和理解声音的流动与特定空间之间的复杂性。
随着声景理论的不断推广,功能性声音以及生活中的声音逐渐被纳入研究的范畴,部分学者开始真正站在人类学视角关注一个社会事项所具有的各种声音,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中进行整体研究,讨论声音生态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但毕竟只有少数人关注。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声音早已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形成了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景观模式。任何的声音行为的产生必然渗透于社会文化的脉络之中,二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理应纳入对声音的研究框架中。基于人类学范式的“声音景观”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