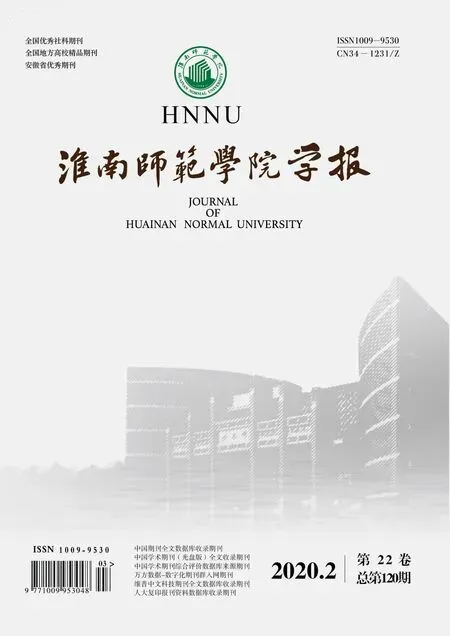归家之旅
——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行旅叙事研究
曹淑娅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3100)
纵观古今,归家主题一直是人类文学史上历久不衰的母题,并由此繁衍出诸多的子母题。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归家叙事开创了西方行旅叙事先河。英雄奥德修斯历经千难万险, 跨越地理空间和时空,实现宏大的归家历程。 《奥德修记》中归家主题对后期西方行旅小说叙事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返乡与身份困惑仍是中外文学热衷书写的题材。
与世界各地的后殖民文学一样,“出行”和“归家”是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的书写主题,作品描述远离保留地、对城市生活感到茫然无措的当代印第安人回归保留地,通过认同和回归本土传统文化实现自我文化和族裔身份的构建。本文选取当代著名美国本土作家N·斯科特·莫马迪、莱斯利·马蒙·西尔科、路易斯·厄德瑞克、杰拉尔德·维兹诺和谢尔曼·阿莱克西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通过分析当代印第安小说归家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探讨归家与文化身份构建之间的关联,为当下印第安人生存和发展拓展空间。 通过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大都市谋生存——回归保留地”归家范式的历史变迁、文学诉求和文化表征的展现, 丰富归家模式的内涵表现力, 使之兼具本土文化特征和现代的张力与韧性。
一、当代印第安文学与行旅叙事
“如果行旅被视为复杂、 普遍且不受约束的人类经历,那出行不仅是位置的移动和延伸,更多表达文化意涵”[1](P3)。 行旅不仅是地理空间和身体的位移, 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表征。 自1620 年载着102 人的五月花号船登录北美广袤土地伊始,美国便开启车轮上国家的历程。 美国借由 “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信念,披着“上帝选民”合法和正义的外衣,大行其道推行西进运动。 “天命论”赋予美国领土扩张崇高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是美国的持续性扩张原动力, 促使美国完成疆域主体性构建。美国行旅文学叙事与国家主体构建一脉相承,“行旅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紧密相连, 这种联系强化了美国被视为不安分的移民国家的描述”[2](P13)。 美国长篇小说之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1789~1851)开创了美国航海小说和边疆小说的先河, 其最富盛名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被视为美国西部拓荒小说的滥觞。 《皮袜子故事集》通过主人公猎人纳蒂·邦波在西部荒原的朝圣之旅展现了美国早期山林居民的生活, 再现了西进运动历史和开拓西部荒原的伟大历史进程。 行旅叙事是美国文学叙事的独特景观,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蕴含独特的文化表征。 从美国早期作家的行旅小说描写作家去欧洲探寻文化源头之旅到19 世纪美国作家书写本土行旅叙事, 从早期的行旅叙事与美国国家身份构建到二十世纪, 随着美国日益壮大迈入世界强国行列, 现代化和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观带给美国人的是尼采所言的“上帝不见了”的精神荒芜,行旅小说更多呈现“所遭遇的困顿、孤寂,以及在旅途的终点所达到的精神升华、堕落、乃至死亡的状态”[3]。
美国白人作家的行旅叙事是否适用当代印第安小说归家行旅叙事研究?学者田俊武在提及美国旅行叙事是否适用美国黑人行旅叙事时, 阐述为“答案是复杂的”[4]。 不同的历史境遇造就不同的行旅叙事特征。崇尚自由和敬畏自然的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祖祖辈辈生活在北美广袤的土地上。北美平原的印第安人以游猎采集为生活方式,他们居无定所,驰骋于草原、游猎于原野中。 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土地的需求急剧增加,欧洲移民和美国联邦政府打着“西进”和“山巅之城” 的旗号, 对印第安原住民“妖魔鬼怪化”,实施“印第安人驱逐法”(Indian Removal Act),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疯狂掠夺土地。 从早期遭遇驱逐、屠戮的灭绝政策、强制同化到保留地制度的实施,印第安原住民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被美国历史演变为“灭亡的民族”。 白人历史上伟大的“西进运动” 则是印第安人的 “血泪之路”(The Trial of Tears)。 大量的印第安人在联邦政府的武力镇压下远离祖先居住地,迁入西部荒凉不毛之地。 作为北美原住民,土地被掠夺,族人被屠杀,印第安人不得不开始了背井离乡之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保留地制度形成和推广时期正是美国国土和经济迅猛发展时期。贫瘠、荒凉、逼仄的保留地取代祖先世代栖息地,成为本土人新的家园、精神的寄托和化身,也成为他们抵制和反抗白人的场所和空间。
本土印第安人行旅与欧洲美国人行旅有着质的区别,本土人行旅历程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政策息息相关,他们在内部殖民中被迫开启了美国主流社会所言的“文明开化之旅”。
二、“归家”范式:回归部落、回归印第安文化、回归自我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以来,美国文坛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印第安本土作家,他们以本土裔在场的主动姿态书写部落历史和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抵制和反抗白人实施的内殖民统治和同化政策,积极探寻平等身份与话语权。N·司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在《日诞之地》(House Made of Dawn)中创作的归家之旅开启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行旅叙事之“归家”范式。 《日诞之地》(House Made of Dawn,1968)创作于文化觉醒和政治对抗的六十年代,当时美国国内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少数族裔为了各自的民族权力而举行社会运动。 在此背景下,美国印第安人为了争取自治权力和提高族裔意识,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活动应运而生,“红种人权力”运动首当其冲。《日诞之地》小说描述印第安青年阿韦尔回归保留地、回归传统文化、重获印第安文化身份之旅, “开启了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归家叙述之先河。印第安传统文化和仪式的认同和回归自始至终贯穿作品,主导着阿韦尔返乡之旅”[5]。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民族的政策深深影响着以主人公阿韦尔为代表的当代印第安人的命运。阿韦尔命运多舛,生父不详,年幼失母,由年迈而腿脚不灵便的外祖父抚养成人。孩童时代被政府送往保留地外的寄宿学校学习白人主流文化知识使其脱离本土语言。 艾勒克·博埃默指出,“切断一个人与母语的联系, 这就意味着与他的本源文化断绝了联系”[6](P263)。 在《日诞之地》中, 失语状态和“他者”形象是阿韦尔在保留地和城市生活的常态, 而这种常态使得阿韦尔在人生各个阶段的行旅都充满了荒芜感和无归属感。 在保留地及家园,他体会不到“吾心安处及故乡”;在洛杉矶,他更有种“背离故乡、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感。“失语”和“沉默的他者”将阿韦尔囿于部落和白人社会之外,这种疏离和压抑感割断他回归本土和融入主流社会。 “语言之所至乃神圣之所在”[7](P260)。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纽带,言语的缺失导致文化传统的断裂。 此时的阿韦尔唯有掌握本族语言方能获得话语权,建立部落和祖先的联系。在城市受挫后,他被迫回归保留地,祖父和比纳利通过部落传统仪式和吟唱让阿韦尔建立与祖先和部落的联系,治愈身体和心灵创伤。 故事的结尾,阿韦尔与族人一起在黎民到来之前参加部落赛跑仪式,“他能看见峡谷、群山和天空,能看见雨、小河和远处的土地,还能看见晨曦中深色的小山。 他一边跑一边低声吟唱颂歌。 随着歌词的节奏,他奔跑的劲头越来越足”[7](P258-259)。 在迎着晨曦的奔跑中,阿韦尔以自我而非萨伊德在《东方》中所言的沉默的“他者”和“异质者”姿态回归本土文化,构建本土文化身份。
三、印第安文艺复兴“归家”范式的承袭和发展:妥协与交融
美国著名的本土女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在代表作《典仪》(Ceremony,1977)中继承并发展“归家”范式,使归家主题更具时代感和历史感。该作品描述了主人公塔尤在二战结束后回到保留地的痛苦境遇。塔尤与阿韦尔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生父不祥,年幼被母亲抛弃。为了证明自己美国人的身份, 在政府的号召下参加战争。 战争遭遇使他患上创伤性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Disorder,PTSD),部落药师库吾士的传统疗法和西方先进的现代医药皆无法治愈其创伤。最终,在部落混血儿药师白托尼集传统与现代的典仪治疗下塔尤治愈了创伤,建立了与部落土地和文化的联系,重拾了缺失的传统和信仰,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本土文化主体身份。塔尤的这种归家正如他的混血身份,是传统与现代相交融之归。 在其后的作品《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th, 1991) 以及《沙丘花园》(Gardens in the Dunes, 1999)中,西尔科继续着归家范式的写作模式,讲述着因离开部落土地而迷失了自己身份的印第安人回归之旅。
路易斯·厄德里克( Louise Erdrich )被视为继莫马迪开创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大潮后的又一代表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作品蕴含印第安因素,家园感和地域感始终是其作品的中心主题。 在《爱药》(Love Medicine,1984)中,她描绘了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身份寻求, “展示当代印第安人如何在印第安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与妥协之中重塑自我,跨越印第安和白人社会, 以新的身份回归故乡”[8]。作品以家族中成员从各地归家参加死于冰天雪地归家途中阿姨琼的葬礼开始,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地域层面描述了纳纳普什家族三代人不同的“归家”之旅。 深受白人文化影响的祖父尼科为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离开保留地,最终谋取的工作是在好莱坞电影中饰演刻板的印第安骑士和人体模特,向白人展现白人心目中的印第安刻板形象。他被迫返回保留地,虽身为酋长却未能理解本土文化传统真正意义,徘徊于主流文化与本族文化的边缘,最终失忆而忘却往昔。 阿姨琼虽在保留地长大,却以白人身份要求自己。为融入白人社会,卑躬屈膝,招致白人的凌辱,使她成为一个踽踽独行、自怨自艾的边缘文化畸形人。 归家之旅终以死亡或病痛而告终,表明当代印第安人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回归之旅的艰辛和无奈。
第一代和第二代放弃本族文化身份迎合主流文化而被动和消极的回归之旅终以失败告终。以利普夏为代表的家族第三代子孙并未放弃归家之旅,他们秉承本土文化传统, 力求在多元文化之中生存和发展, 追寻自我文化身份之旅。 厄德里克作品中“归家范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霍米·巴巴(Bhabha,Homi K)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the Culture,1994)中所描述的杂糅性和第三空间”[8]。 厄德里克以此传达了对本土与白人文化杂糅的认可,发展和深化了印第安文学中的归家模式。
四、追寻和塑造当代印第安文化未来新的发展空间——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归家”范式的超越
杰拉尔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齐佩瓦族印第安男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多以魔幻、 讽刺和幽默书写当代印第安人历史在场,以主人翁立场书写被白人抹杀的历史。归家主题是印第安文学中历久弥新的常见主题,本土作家们以此表达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展现当代印第安保留地的真实面貌和处在历史感和地域感纵横相交的十字路口本土人的困惑和迷茫。维兹诺虽不否认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的归家范式是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抵制和抗衡,但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印第安传统的回溯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对白人臆造的印第安的回归,可能导致“当代印第安人陷入主流文学设定的他者情境”[9](P87)。因而,他在创作中有如《回魂者》中对逝去的印第安人重新回魂的回归式描写,更有倾向于舍弃印第安文艺复兴的既定归家范式,打破两种文化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而关注异质文化间的妥协与交融。
维兹诺(Gerald Vizenor)在作品中大胆地采用戏仿和改写,颠覆了固有的印第安人被殖民、被驱逐、被同化的历史命运,历史性地再现印第安人的话语权,使处于边缘的印第安文化恢复到与主流文化并驾齐驱的地位。他所描写的出行和归家让主人公走出保留地,主动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到大城市和别国生活与文化中,打破并超越了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中印第安作家热衷于沿袭的“归家”范式。 历史无法回首,回归保留地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印第安文化传统, 被同化政策“漂白” 过的保留地已不再是后现代的理想圣地。“消除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的二元对立,建立一个后现代的第三空间, 亦或如朝圣者一样去寻找‘想象的、转换的、生存抗争的’第四世界,后现代的后印第安人应该在后空间、 后世界传承部落文化,并创造新的历史”[10]。
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作为当代本土新生代作家代表,集作家、诗人和电影制片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 其作品虽多以保留地为故事背景,但更多地融入了现代和流行文化因素,冲破印第安文艺复兴中归家主题的藩篱,“阿莱克西致力于弘扬本土文化, 为本土文化与主流文化成功搭建交流平台”[11]。 谢尔曼·阿莱克西在《保留地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 1995) 小说中所描写的困惑、迷茫、贫穷、失业等是当代印第安人在保留地上生活的缩影和写照,也是促使作品中年轻一代走出保留地的外在动因。 作品以斯波坎保留地为背景,失业、酗酒、暴力和赌博充斥着整个保留地。在他看来,保留地是内殖民化的集中营,与主流社会所臆想的“田园牧歌式的保留地生活”大相径庭。 “他的作品更多表达了对保留地精神毁灭和幸福希望破灭的苍白无力感——尤其是离开保留地的深深内疚感”[11]。有别于同期印第安作家,谢尔曼认为印第安人有着本土和美国的双重身份。美国人往往为了追求梦想而离开出生地,因此,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本土人则有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觉悟。 贫瘠、资源匮乏、缺乏活力的保留地限制和妨碍了梦想的实现, 走出保留地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迈出的第一步。
当代印第安作家往往把情感寄托于保留地,因此保留地成为众多印第安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家园和故事的背景。 美国政府在20 世纪中期正式开始重新安置政策,鼓励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到城市生活, 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尽快适应城市的发展和生活,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选择离开贫穷的保留地而到都市谋生存。 随着印第安总人口的成倍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第安人去全美各城市生活的人数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三到四倍”[12]。而“在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中, 印第安城市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70%以上”[13](P21)。 在城市生活的印第安人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在保留地的人们相比均有所提高,但他们仍未能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城市印第安人的失业率远远高于美国平均失业率,“保留地的情况更是严重, 重新安置政策并没能解决保留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13](P72)。 因此,美国现实生活中的保留地与文学作品中对于本土人渴望回归保留地和传统文化的描述还是有所出入。
在《保留地布鲁斯》中,谢尔曼塑造了一群离开保留地去追寻梦想的当代印第安青年。 小说开篇,罗伯特·约翰逊( Robert Johnson),一位背着魔法吉他的黑人布鲁斯歌手,悄然而至于保留地的十字路口。 在这把吉他的魔力召唤下,保留地上的青年小伙子们托马斯·生火(Thomas Builds-the-Fire)、维克托·约瑟夫(Victor Joseph)、朱尼尔·波拉特金(Junior Polatkin)组成“郊狼泉“(Coyote Springs)摇滚乐队,并开始了他们的音乐之旅。来自其他部落的姐妹俩和部落传统代言人大妈妈(Big Mom)的参与成为乐队朝气勃勃、 融入现代和传统的因素。 在英语中“blues”表示忧郁、悲伤,布鲁斯或蓝调音乐蕴含这种悲伤的情感。 非洲裔美国人用这种自创、独有的音乐形式抒发他们无以纾解的悲惨命运之感叹和对白人的愤懑与反抗。 乐队不仅融入本部落的历史、传统和仪式,且是多部落和非裔多种元素的结合,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边缘与中心、少数族裔和白人主流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 乐队首次演出成功后,两个白人女粉丝贝蒂和维罗妮卡也加入了队伍。 在“骑兵唱片”公司的试唱中,郊狼泉乐队名落孙山,而“骑兵唱片”却与模仿印第安人而获欢迎的两位金发碧眼的白人女粉丝签约,这种戏剧性的结果讽刺了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复杂和虚伪的态度。带着部落记忆、传统文化走出保留地的乐队首次演出签约失败,表明当代印第安人走出保留地的种种障碍。 小说的结尾托马斯带着两位主唱毅然离开保留地去斯波坎市发展,预示他们走出保留地的决心。 阿莱克西通过郊狼泉乐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保留地现状,展现当代印第安人直面历史,带着本土文化传统,勇于探索,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境况。
五、结语
在《日诞之地》中,莫马迪首创“出行—回归”的当代印第安文学归家范式, 随之西尔科、厄德里克等本土作家发展并深化这一主题。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家们开始更多关注两种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弈、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等维度。 以厄德里克为代表的印第安作家,通过书写跨越中心与边缘界限的归家,传达出他们对印第安民族摆脱边缘化困境的思考。杰拉尔德·维兹诺和谢尔曼·阿莱克西刻画年轻一辈印第安人带着传统,怀揣梦想,走出保留地,跨进都市寻求自我发展的空间。通过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大都市谋生存——回归保留地” 这一归家范式的历史变迁与文学诉求的展现, 丰富归家模式的内涵表现力, 使之兼具本土文化特征和现代的张力与韧性, 使当代印第安人走出保留地的藩篱, 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迎接挑战, 为当下印第安人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走出保留地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传承本土文化传统, 回归是汲取本土文化和对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正如诗所言 “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