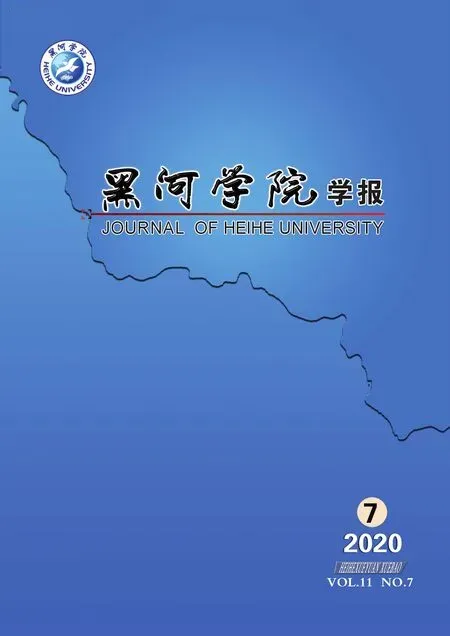王肇民与朱德群的艺术思想阐释
姚明睿
(淮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艺术思想建构中的地域性意义
地域性不仅是美术史书写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更开放的研究视野。“地域”就其与发生关系的对象,可以衍生出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的“人地关系”等一系列衍生概念,但始终体现以人为主体的核心关系。
王肇民与朱德群出生于现今安徽省萧县的农村家庭。赵庄村和白土村,作为两个稳定的社群在一定时间内都保持着相对纯粹和不受外扰的状态,即使物质水平发展超过现阶段,但其原有的文化体系仍会延续下去。地域性以这种共同的社会归属地概念为基础,对二人在艺术上的人文选择保持着连续和稳定的影响。这种连续性表现为王肇民和朱德群先后进入杭州艺专学习,即社群间的人通过这种“中心化”来寻求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对共同学府的选择不仅是导向也是个人对外部文化环境的回应,在家庭单位中,这种回应表达的更为有力。由于家庭成员间的文化吸收在途经上部分是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如父母的口传相授和自己观察所带来的耳濡目染的效果。朱德群回忆时曾谈到自己父亲每年夏季都要将字画在院中晾晒以防湿霉,并坦言这是一年中他最期待的时刻。这一过程虽然出于父亲对自己藏品的爱护,但也无意识地完成了对幼年朱德群艺术思考的启蒙,使其在日后经历中秉持着对传统书画艺术的坚持。
水彩画作为外来画种在刚传入中国时,是被保留在宫廷、贵族间欣赏的艺术作品,民间并不知晓其存在。随着19世纪通商口岸的开设,以风俗和景物为内容的水彩画才慢慢被民间认识并接受。中外交流频繁的城市地域成为民间学习和认识水彩画的先决条件。上海作为中外交流最密切的城市之一,也是当时最早开设水彩画学校教育的地区,面对平民大众的水彩画馆让人们得到了系统的学习,水彩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规模不断扩大。萧县的地理位置位于上海北部,受到现代化起步城市的辐射影响,当地不少从事艺术活动的人都求学于上海,例如,王子云、萧龙士等。作为萧县这一地域内的前辈画家,都对当地的艺术活动有影响。在当地这种艺术环境下,王肇民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到上海学习,但水彩画画中的概念更容易接触到。在学校的学习中王肇民就把美术课作为一门主课[1],说明他在学生时期就有较高的艺术认同。这种对艺术的自觉与对文化的敏锐感知力也是他日后发展的动力。
萧县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画艺术传统,在《清书画家名录》中就有龙城画派发展当地书画活动的记载。地域性不仅是他们艺术话语实践的文化背景,更体现出一种集体的文化自觉。
二、图像结构的对象化转向
王肇民与朱德群的艺术风格和材料语言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深层次的绘画理念中却有相同的部分,例如,绘画作品都传达出一种诗意的境况,再者二人的绘画图式结构都源自景物的现象式存在,在其艺术哲学中都有表征自身及存在的愿望。
1.水彩静物映像的重建
王肇民的水彩静物画结构折射出对趋小物像展现宏大结构的概括性。在创作过程中将知觉回溯至物象本身,强调对“他者”的确认来反正“本我”的过程,呈现出稳固而坚实的美感。在《画语拾零》中每个“内容都是不同的、随时变化的、甚至是昨是而今非的”[2]。
王肇民指出,具体的内容和抽象的形式之间没有相互决定的可能。通过强调内容的“实时变化”和“霎那的具体生活”,实际上正体现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原初物象的极度重视。作品中是趋小的花卉、水果,但在王肇民将这些结构转化时,花卉和水果作为概念的意义被缩小了,并没有从人文功能性视角来观看。有时人们惯于认定物象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可动摇的,王肇民的水彩景物画就对这些惯性的思考提出了质疑。作品以审美性去揭露出一个非人文的结构,形成没有任何波澜而凝固的对象,目的就是要穿过人文所编织的秩序已达到对事物原初的认识。在把握认识的过程中,重视写生和素描等两个方面。
写生的过程是人与物最直接接触的过程,好的作品是人对现实对象的自我表现,艺术家本人也在其教学实践中反复强调写生的重要性。以写生作为一种手段,王肇民的水彩静物画更主动的描绘了一切物的轮廓。色彩画定的轮廓随对象的起伏来变动,颜色、笔触等不断提示着触觉,借之以强化形体和深度。
物体的轮廓线被构想成一条包围着对象的实线,能够帮助观者对浮现的逻辑秩序产生印象,甚至协助能让被表现的对象在人们眼前进行表征自身和形构自身活动。同时,这条线也是理想中的边界线,使水果、花卉等在日常空间下的各个侧面都失去了深度。由于静物存在的每个向度并不是摊平摆在眼前的,而是充满穿插交错和无法穷尽的现实。因此,王肇民让颜色在边缘线之间流连,顺着物象的形体起伏来赋色,这个创作环节正如同人们在知觉过程中所经历的,展现了艺术家对知觉世界的图景。在写生的同时,侧重“人当物画,物当人画”的理解。并不是要剥夺人的思想性,因为王肇民坚持画中的“精神”要靠形来把握。作为一种途径,写生使他回到了现象中。
在《苹果》这幅作品中,几颗苹果在水平的桌面中分布,边缘明确和肯定强化了本身的形,颜色的丰富性被提高到了近饱和的程度又进一步扩充了形体的充实感。王肇民对静物的这种关照是他图像结构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少了这一过程只能暗示物的存在,而不能达到给形象以统一又不可凌越的审美价值。
在绘事中王肇民从不排斥科学性,认为画画强调基本功,必须学习素描。但对素描的手段认识是独特的,并指出“素描可以先画,也可以后画”[3]。后画的概念是从要点入手画过一遍后,再略加调整。在这个过程里不单是对几何透视、色彩规律特定知识的了解,还是对艺术家提出积极去描绘对象的要求、充实图像的完整性、完成作品中的主题。此时还没有达到作品的目的,需根据经验使笔下描绘的世界在他人的意识中萌发作者建构的意象。静物图像呈现出真实世界般的厚度,追随画作中水果和花卉素描形象,通过不断清晰的线索会发现艺术家所欲沟通的意味,使这些形象走入观者的意识中联结了彼此。
2.抽象结构中的观念
朱德群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所营造的是极富诗意的审美意境,作品已然走向了纯粹抽象的形式,没有精准的透视和三维空间概念,线和色彩是观看作品时给人们的直接感受,也是其抽象作品的主要结构。
在作品《动中静》中,周围充满着偏冷的蓝色和绿色,调色油稀释过颜色呈现出透明和半透明的色层,会烘托出一种气氛感,共同渲染着画面中偏左侧红色的一点。在这种色彩空间的营造中,红色就显示的极为纯粹。色彩的转化过程中,身体对色的感知便回到了所有既往文化思想的根源,艺术家以这种迈向根源的关注方式进一步形构出了艺术作品中色彩的独立存在意义。艺术家透过其艺术话语实现的色彩转化,所以,不在艺术家未经阐明的生活中,艺术家也不知晓自己对艺术的发展在自身存在上有没有功能性的意义,艺术家的创作如同人的自由选择,透过作品亦能看到画家的生活氛围,远离日常推理思维所自限的栅栏[4]。
线的元素是朱德群抽象作品诗意审美空间的重要基础。作为他抽象绘画的一条重要视觉语汇,对线的理解直接脱胎于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其间充满了对笔法、结体等书法技术的概念。在对线的关注中,整个还原过程是对语言文字结构的打破,将文字中识读的图像从文意中抽离,又由身体以绘画作品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塑造了艺术家与观者共同的视觉经验,达到某种精神层面的交流,并为其作品的诠释保留了最大的开放性[5]。
朱德群在绘制于1987年间的《白色森林》系列作品中线的作用特别明显,单纯雅致的白色色调突出支撑画面空间的各种线性结构,彼此交叠和偶发的意象形成一个自由诠释的关系,展现在作品的欣赏过程中。线的结构在朱德群后期的作品中逐渐成为主体,让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并内在地赋予可持续的生机,共同形成这个完整的审美系统。通过认知到表达的过程里,人与外在的景物逐步构筑起了纷繁复杂而又微妙的互动关系,促成对作品生发出多元性的阐释意义。
线和色彩的共同介入就是朱德群作品中的对象化转向。其实就生活环境中人们把握对象的方式来说,知觉是有适应性的,即外部环境有所改变,知觉系统也能做出调节,以维持自身身体并达到其存在的真实感。所谓的色彩、线条本就是知觉调节下不断构建的,就视知觉来说,有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三、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及视觉的社会性维度
通过对作品中图像意识的重建来反映主体性的过程中,王肇民与朱德群也从其对立面证实了艺术家存在的重要地位。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认为的“毕竟,艺术家是每个文明作为精神留给后世的,激发文明之精神的持久见证物的真正创造者”[6]。这种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艺术思想中现代性的重要方面,通过画家对客观物的凝视(gaze)展开。
艺术家在创作时所进行的观察不只是为了弄清细节,目的在于如何控制住所要表达的对象,参照这之间其所扮演的角色,凝视实际来自视觉中物与创作者的权力关系。王肇民艺术作品中凝视是一种对西方视觉中统一视觉经验的实践。在透视法的使用策略中,物的形象保持着几何的逻辑关系,作品的审美空间在一个脱离肉体的眼睛下形成,整合为一个理性的视点并以此再现作品所要传达的全部符号。空间被设想成这个理性化视点的发射物,形体在在这种设想下不可能脱离客观的观看方法。
景物在作品中的存在永不能超越被整合视域中的规则和方法,其汇聚了艺术品创作过程中所暗含的凝视的权力关系。而在朱德群的理解中,凝视更能把握绘事中的文化意义。水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作为媒介剂,单一并且常见,调和墨与颜料后又有不可完全控制的变化,其展开一种趋同文人“从心所欲”的文化意境。在作品中朱德群把文人画的笔墨趣味介入到画面的结构中,稀释的颜料通过宽刷急扫而下让油画颜料中的矿物质沉积在边缘,留下一种干涸后不可控的特殊肌理效果。这种对水性功能的强调,画家并没有含糊水墨与油画两种艺术形式的根本不同,反而利用了对媒介的积极手段,加强了作品独立存在的意义。
同时,艺术家身份也是凝视的产物,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什么往往受控于意识中打算看到的对象,视觉经验服从于这个社会文化描绘的世界,构成一种视像的话语。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应该强调视觉的社会性维度,因为个体在凝视中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一个主体间的感觉网络。
艺术家在创作时与作品是一个直接交流的过程,完全掌握过程中的视野。当其作品在展览和博物馆的特定文化空间下,不论是艺术家还是欣赏者都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观察者,艺术场域中的个体打破了画家本人最初所独享的视觉控制,被分享的视野融入了每个个体所凝视的景观中。画家之前对作品掌握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因观看者的出现而经受质疑,同时,人们的在场也为作品的艺术思想提供存在的证明。视觉的社会性维度更加体现作品中的图像都不再是消极观看和等待改造的客观对象,而是直接在身体和经验中出发,通过悬置成为有主体意识的知觉对象,打破了传统思想中的二元论,解释以人文的主题性,将空间与创作者的意义不断揭示出来、也印证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将对象的形式归结于如何被感知,意识难免要和血肉之躯纠缠在一起[7]。
四、结语
在当下的艺术环境里以艺术家身体为表达的案例很多,从传统的表现形式衍生到行为、影像、装置等,但这些并没有抹除绘画的生产过程。王肇民与朱德群的绘画艺术也没有离开对审美空间的关照,关于对审美的沉思,究竟由何构成、如何界定还都存在不确定性,但这也为其诠释埋下更多伏笔。如今信息高度发达,信息膨胀下知觉往往被物质生产所掩盖而显得无力。王肇民与朱德群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发展克服了这种价值虚无,也皆在不同意义上实现身体的延伸,以独特的绘画图式展现着对艺术本源意义的回应,以精神的层面跨越自身之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