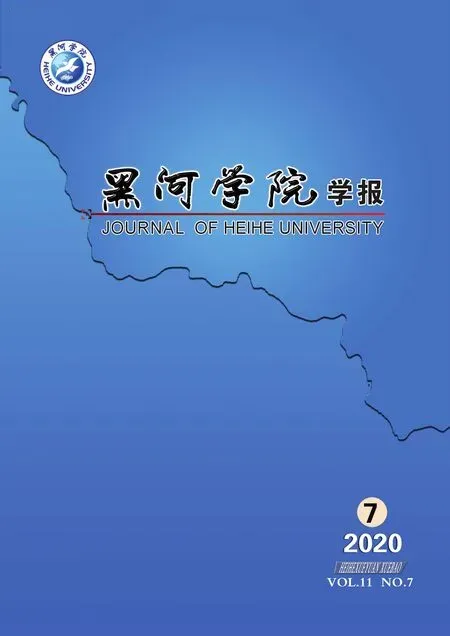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荒诞主题疏论
毛晓敏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影视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1200)
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现实主义主题持续引导着创作者们前行。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优秀电影铺垫着中国电影创作特色。虽历经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始终将镜头对准社会和人民,目击在大时代环境的瞬息变化中人的真实状态。在丰富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中亦有荒诞这一副主题紧密贴合,以高度理性的视角渗入作品的血肉中去,增添了现实主义主题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而其自身也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主题表达方式和创作表达风格。
一、荒诞主题
电影中的荒诞主题是建立在人类的文化共识、哲学(含美学)观点、文艺思潮、大量的艺术作品等之上的。“荒诞”释义的多元化衍生,需要在下文中进一步厘清。
1.“荒诞”之于辞典
在中国古汉语中,荒诞一词被解释为“不真实,不近情理;虚妄不可信。”[1],同样在现代汉语中,荒诞的词义被定义为极不真实或极不近情理,在解释的词意上,荒诞具有明显的贬损色彩,是与传统理性相反的行为状态。而在英语中,常用Absurd、Fantastic等词进行描述,其中absurd在牛津词典的中文翻译具有形容词和名词双重解释,作为形容词时为“荒谬的,荒唐的,怪诞不经的”,作为名词时则为“荒诞的事物,悖理的东西”[2],东西方在传统上都将荒诞界定为违反常理和既定规则的状态。中文语境倾向于一种批判色彩,英文语境倾向于嘲讽色彩。
2.“荒诞”之于哲思
在辞典层面,虽然中西方在诠释荒诞词义时稍有差异,但其情感色彩的倾向一致。然而,当欧洲启蒙运动重新将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奉若圭臬时,诸如笛卡尔、康德等一些西方哲人便打破既有规则,试图充分讨论人的主观精神与世界、宇宙的关系,这与中国古代先贤,如老子的“道”,庄子的“心斋”“坐忘”,以及明朝王阳明“知行合一”,近代王国维的“物我”观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社会又将理性思维重新作用在人类本身,应用理性和追求理性成了人类攀登主峰的捷径。人类攀登在向着理性终极的路途中,却不断遭遇着未知的阻挠,常常不能如意。实质上,这种不如意在中国春秋先贤出世前就存在,在古希腊哲学诞生前和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就存在,甚至普遍地贯穿在人类文明史的整个过程。
基于理性思维被广泛接受的视域下,荒诞的色彩倾向发生了变化,从负面向中性变化。之后,人类不断运用理性去关注自身生存状态,对抗宗教的、礼教的传统封建思想,荒诞才被认为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逐渐地被理解与接受。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点等一系列的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才最终把荒诞主题引导向关乎人类世界本质的学术层面。
二、“荒诞”形式
1.“荒诞”渗透文艺
西方哲学家试图用晦涩的推论和修辞去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文艺家们则用具象的丰富的文字、图像方式向广大人群传递荒诞主题的作品。20世纪,人类社会于工业化之后,出现了巨大的震荡。文艺家们目睹长久以来的社会和自然法则遭到剧烈破坏,感受到恐惧和焦虑。稳定安逸的生活秩序和攀登的理想被不断践踏,生存的信心周而复始地被破坏,内心逐渐产生了荒诞感。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艺家们创作热情高涨,特别是在文学和戏剧的创作上成果颇丰,在文学上,西方有卡夫卡的《变形记》《乡村医生》《城堡》,萨特的《恶心》《墙》,加缪的《局外人》《鼠疫》等;我国有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猫城记》,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高行建的《灵山》,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王朔的《顽主》等。在戏剧上,西方戏剧出现了法国“荒诞派”戏剧,其中包括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热内的《女仆》《阳台》、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些文艺作品都在各自表达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窥探理性秩序背后神秘的控制力量。例如,卡夫卡的《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先生,接受了工作却无论如何也走不进城堡,身份被别人和自己质疑,理性被神秘的力量压制,几乎接近崩溃。而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则用荒诞派戏剧的笔触描写了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到来的图景,然而“戈多”作为主体的缺失和含混,使得其生成一股神秘的力量,令两个流浪汉苦苦煎熬而又百无聊赖。
这些文艺家都将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当时社会发展动向,或许也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表达真实的目光纷纷对准了人类的荒诞状态。而身在其中的荒诞则是由于主体缺失、秩序混乱、未知的力量崇高、遭遇毁灭等造成的人的理性混乱倒错、虚妄迷惘的状态,对于旁观者来说能够观察到荒诞的状态便证明其具有理性而非荒诞的思维意识,而不见荒诞存在或身在囹圄,偏离理性思维。简单来说,荒诞是一种反理性的表现,创作和欣赏者会形成一种理性自觉,从此荒诞也逐渐成了各国文艺家创作表现真实、写实、现实等方法的重要手段。
2.“荒诞”糅合“现实”“喜剧”
若要在美学及艺术框架下厘清荒诞的本义,则需先辨析荒诞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现实主义追求真实客观再现社会现实,同时这种真实可以通过具有历史性准则的典型来构建。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构建的必须是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形态。荒诞是在人的个体理性力量遭到未知力量的攻击、毁灭后无可奈何、精神崩溃的状态。这其中,人的状态是真实的,未知力量也客观存在,多方面的存在以真实的面貌呈现。故此,荒诞实际上与现实主义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而现实主义在表达上的典型性又是荒诞主题为作品表达的方法之一。由此看来,“荒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而后,“荒诞”与“喜剧”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辨析。上文提及英文Absurd在释义上具有滑稽色彩。黑格尔认为,喜剧是“颠倒过来的造型艺术来充分补充悲剧艺术的欠缺,突出主体性在乖说荒谬中自由泛滥以致达到解决。”[3]也就是说,喜剧是悲剧的附着依存,喜剧制造了狂欢和滑稽后令观众进入一种怅然若失的虚无感。鲁迅认为,“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4]更是将一种无价值的虚无主体暴露在视野中,以达到滑稽后生成一种荒诞感。简单说来,喜剧的本身就是为悲剧服务的,或是一种技巧更丰富的悲剧样式。而恩格斯认为悲剧美学的哲学基础在于理性主义。喜剧恰恰是通过运用理性主义视角充分地暴露滑稽场面,制造短暂的欢娱体验,以此来丰富理性主义的表达层次,增强悲剧性的体验。然而,喜剧在技巧上致力于将观众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通过戏谑和嘲笑来达到滑稽感,而荒诞则亦可通过平视或仰视的视角去看待、体验人物。由此看来,荒诞与喜剧在表现目的上殊途同归,在技巧方法上既有重叠又有差异。
三、电影发展中的主题
作为20世纪之后文艺作品重要的表达手法,“荒诞”不断地变换着外表,作用在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类型中。电影艺术作为20世纪重要的综合艺术类型,在表现手法上采撷众艺术类型所长,又独具特色,使其能够表现多种题材作品,拥有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
中国的早期电影活动于20世纪20年代处在局势混乱、新旧文化强烈冲突的阶段,民众渴望复归平和良序的古典主义生活方式。电影的主题大多遵从于中华传统伦理,如《孤儿救祖记》《空谷兰》《儿孙福》等都在用大团圆的结局,表现感恩报恩、因果报应、宽以待人的古典伦理。
处于抗战时期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则把目光对准战争视域下百姓遭遇的灾难,生存状态的悲戚,在人的表现上更是一种悲壮精神。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风云儿女》《八千里路云和月》《渔光曲》《神女》《狂流》《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等一批电影。
建国之初的中国电影围绕挣脱旧社会迎接新中国的主题,“十七年”电影大多采用浪漫主义方式去痛斥黑暗的旧社会和塑造新一代英雄符号。大量的英雄人物在银幕上被歌颂,理想而豪迈的形象如“酒神”狄奥尼索斯般矗立在荧幕的中央。如《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柳堡的故事》《林家铺子》《林则徐》《英雄儿女》《董存瑞》《小兵张嘎》等。
经历了“文革”之后的中国电影进入转折和发展时期,电影创作者用敏感的思维去拨开云雾,用理性的力量呼唤真实的复归,创作中积极汲取新的影像表达手段,倡导纪实美学的浪潮。如《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于无声处》《小花》《芙蓉镇》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开始活跃在影坛上,他们在纪实美学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多样化的影像表达方法。将固有的影像方式思维打破,勇敢地突破电影影像表达的极限,探寻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影像表达新思维、新手段。诸如《一个和八个》《红高粱》《黄土地》《黑炮事件》《盗马贼》等。
而20世纪90年代直到当下,国内正经历着极速的改革发展阶段,电影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思维也冲击着艺术创作者的创作方向,电影呈现出以市场准则为标杆的形态,资本与票房指挥起电影艺术创作的节奏。然而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的力量注入,也让多样化的电影市场保留了电影发展的血脉。如《小武》《孔雀》《卡拉是条狗》《三峡好人》《世界》《疯狂的石头》《无人区》《Hello!树先生》《一个勺子》《无名之辈》《钢的琴》等。
四、发展着的荒诞主题表达
国产电影虽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现实主义主题一直是创作者主要表达的核心,而“荒诞”作为现实主义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也不断变化着姿态,贯穿在整个电影发展的脉络之中,特别是集中在早期电影“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和“新生代”。
1.荒诞之于早期电影
在早期电影时期,电影多以传统伦理道德为主要的理性规则。作品本身的理性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了荒诞意味,在三四十年代电影中体现得更加强烈。诸如文化影片公司费穆执导的《小城之春》,描绘的是一个战后坍塌的南方小城景象,在物质生存环境遭遇破坏后,一家人的生活依赖传统秩序维系着沉闷而绝望的状态,当丈夫的好友闯入,让这个家庭泛起了波澜,尽管人物情绪随着情节发生变化,但终究还是回归到沉闷而绝望的状态。剧情中的巧合和造化弄人,以及费穆在创作时应用的象征技巧,都在指向在当时时代背景之下,人们面对残破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性追求之间的错位,构建起早期电影中的荒诞。
2.荒诞之于“第四代”
到了20世纪80年代,第四代导演们将历史震荡后的伤痕用理性的思维娓娓道来,他们在作品中构建起真实的力量,而这与荒诞追求的真实不谋而合。诸如《城南旧事》中小英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空间的变化和时间的变化,而过去种种的人和事都在时空的变换中流逝,童年生成的印象,都要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和社会客观中被迫改写,一种对过去的怅然若失则饱含着荒诞感。除了《城南旧事》这样的客观写实审美,还有利用抽象的影像空间与画面构建去揭露真实,如《黑炮事件》在电影语言上对美术和戏剧的借鉴,其中会议场面的抽象化表达让象征和隐喻手段在电影语言中得到扩展。
3.荒诞之于“第五代”
创作力旺盛的第五代也在创作时尝试运用荒诞感去构建现实。尽管他们擅长在镜头的空间上和表达上扩展更多的界限,但所有的表达最终要归到关注现实。诸如电影《活着》,在创作时就将余华的原著中残酷现实场面有意识地向荒诞感转变。在影片中,区长春生的车撞到了砖墙,而主人公富贵的儿子有庆由于在砖墙后睡着了被倒下的墙砸死。在小说原著中县长的夫人同时也是校长大出血,有庆由于被抽血过量加上无人救助最终惨死。余华的小说原文中有庆的死是畸形的社会关系,人的恶被无限放大之后的惨状。而电影中,却把这种残酷改编成时代环境和个体宿命。这样的改变一方面在于电影审查政策,另一方面张艺谋也在通过思考电影如何逼近真实,如何通过制造荒诞,让人生发理性的思维,对人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作出思考。
4.荒诞之于“第六代”“新生代”
处在中国物质经济急速变化的第六代和新生代电影人,目睹了国内社会的极速变化,以及经验图景的崩塌、解构、重塑、分化、复兴,更擅长去思考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关注自身、关注社会,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大时代的变迁发展中,敏感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法国导演特吕弗的《四百击》是法国新浪潮的重要代表作,讲述了一个抗争教会学校封闭秩序的孩子,在逃离后的茫然感。意大利导演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讲述了主人公安东当掉家里所有的床单买的一辆自行车被偷,在寻找的过程中一波三折,最后自己还成了贼,面对贫穷和社会现实感到绝望和无奈。而第六代电影人在早期具有浓郁的法国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痕迹,似乎想用这种表达方式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如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作品讲述的是来自农村的小贵辛勤工作买的单车被偷,而后发现小坚从二手市场买走了,一番争论后两人决定共用单车,自己不幸还帮小坚背了锅,自行车也坏了。主人公的边缘身份使得其理性的追求得不到满足。共用单车和替人受过的情节设置都荒诞莫名,尽管如此结尾竟也是自行车被砸烂了,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第六代和新生代电影人并未止步于早期的模仿借鉴,他们积极汲取养分,包括周星驰电影中的“无厘头”等风格不断地扩大着国产现实主义电影中荒诞技巧的作用。诸如电影《钢的琴》,讲述了钢厂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与妻子小菊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在偷钢琴无果后和一群落魄的兄弟造出一台钢琴的故事。这部电影运用的影像语言丰富而别具特色,将制造钢琴的场景放置在一个废弃的工厂车间内,让钢琴制造这个事本身与后工业化环境之间产生错位,让主人公及其身边的女友和兄弟的小人物身份与工业的浪漫、西洋古典音乐的情怀产生错位,让主人公酒神般的行动热情和结尾时主人公的理性选择产生错位等等,这些错位都是创作者有意制造的荒诞感,令观众感受完百般滋味后一声叹息。再如电影《无名之辈》中,导演利用群像去构建一场乌龙劫案。然而两个劫匪偷的是手机模型,破案的是个落魄保安,小人物个体行动目的与其发生的事件之间产生错位。劫匪之一的胡广生,一直活在虚妄中,但却一次次被现实击破。而保安马先勇为了寻回当初做协警的尊严,一次次逼近各类案件的关键,却遭遇了一次次的宿命打击。特别是其中的马嘉祺,遭遇残疾求死而不得的心理将现实中的死亡观突出提及。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电影,都借鉴与尝试多样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在小人物塑造、错位关系、时空关系等方面竭力表现荒诞,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复归的还原现实思路上,不断汲取多样的思路和手法,与纯粹的市场化商业大片错位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艺术和市场的道路。
五、结论
19世纪末,西方现代技术不断闯入逐渐开放的国人视野。电影,也裹挟着商业目的,以放映西洋图景的缘起踏足国门。而经历过百年之后的中国电影,不断挣脱“他者”的语境,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收获颇丰,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范式和类型。与此同时,电影作为人类的一项艺术形式,也通过尝试不同类型的艺术表达形式,去追寻人类理性世界的真相。
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指导思想引领着一代代文学和艺术创作者攀登新的高峰。现实主义题材在不断吸取和扩展边界的进程中,或是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或是效法传统中华宝贵思想经验,终上演了一幕幕百花齐放的蓬勃繁荣景象。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电影,正在以更加自信的面貌面对世界,多样化的主题表达和艺术真实的客观追求也督促创作者们不断学习和实践创新。荒诞主题在艺术的变革中巧妙地变换着姿态,紧紧贴附在现实主义身后并为其发声,形成颇具特色的主题、表达形式、创作手法等,既是现实主义的衍生品,又使得现实主义主题的表达方式愈加丰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