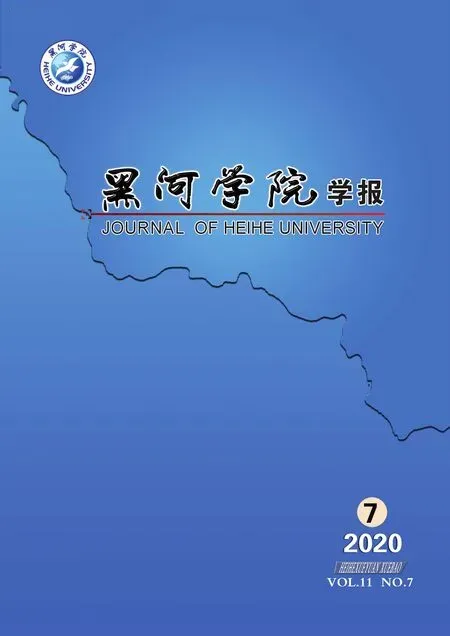《春月》中她者视野下的中国文化
陈桂峰
(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华裔美国女作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1938—)根据其访华经历,在参阅大量中国书籍、史料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春月》(Spring Moon,1981)。该小说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作为主线,描述了在中国历史变迁的广阔社会背景下从清末光绪年的1892年到文革的1972年80年间,苏州张姓家族和北京吴姓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小说有着特殊的历史叙事风格,中国元素味道浓厚,而这一叙述特征更是通过“她者视野”表现出来,意味深长,既展现了小说的民族性特点,也使得这些民族性得以在另一种文化屏幕下呈现“陌生化”效果。
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符号
包柏漪8岁时随母亲前往美国与父亲团聚,“中国”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一个遥远的符号。1973年,包柏漪与丈夫温斯顿·洛德陪同基辛格国务卿访华,27年之后重返回家路,“从那次旅行里活下来的是《春月》的精魂——它越过报纸的要闻,共产主义的理论,西方的原则,文化的鸿沟,政治的隔阂,和语言的障碍,深入到我家族的心灵和思想。”[1]464包柏漪潜心6年全力投入于《春月》的创作,小说明显表现出视角越界的叙事特色。双重的文化资源是其创作的优势,自由地行走于两个世界之间使其作品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在《春月》中,大量中国文化符号散落小说的各个角落,俯拾即是,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筑构造
青瓦屋檐、游廊、厢房、扇门、朱红廊柱、假山洞、大理石屏风、石凳、祠堂椽子、青铜狮子、雕花门楼、影壁……
(二)服饰装扮
绣鞋、旗袍、纨扇、紫红绸衫、绣花、刺绣、褐红色绸袍、宽辫莲花发式、簪子、玉念珠、长命锁、仙鹤补服、丝巾、寿衣、绣着鹭鸶的补服、紫红缎袍、绣金紫红斗篷、女儿髻、藕合色绸衫、翡翠耳坠、黑色瓜皮帽、皮里子缎袍、绸子皮袄、大红绣花裙、珠镶玉缀的遮耳黑绒帽兜、大红锦缎貂皮袍、坎肩、老虎鞋……
(三)家居饰品
粉红色的罗帐、红漆箱子、漆凳、花梨木衣橱、紫檀柜子、竹床、幢幡、青花瓷器、玉器、青铜器、水烟袋、文房四宝、花鼓凳、古玩柜、诗书画轴、镇纸、彩绘纱灯、唐三彩马……
(四)取名
春月,春者,“始也,东方之谓也”;月者,“阙也,太阴之谓也”。睿心院、静篁院、往返桥、懿德院、信义池、柏园、三花门、枫叶门、棋园、笛思园……
(五)民俗
1.关于胎教的训诫
“不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不然将来孩子会粗心大意……不要想伤心事,那也会传给孩子。”[1]6小脚大脚:小小金莲、鲤鱼脚。
2.婚葬仪式
寿衣是由针线好,父亲、丈夫、儿子都健在的全福人缝制的、奔丧守灵;做“七七”;穿着麻布孝袍、孝帽、白鞋;做佛事超度;送殡;居丧三年;扫墓;庚帖;姑娘出阁要哭;黄道吉日;龙凤饼;嫁妆;女儿宴;凤冠;闹洞房;请安;归宁。
3.节日
中秋供“兔儿爷”;除夕、新年祭灶、贴春联、守岁、祭拜祖先、放烟火;端午节赛龙舟。
4.过继子嗣
正严和爱莲过继了同宗的允坚当儿子。
(六)民歌、民间故事
“正月初一雪纷纷,户户门前挂红灯。家家庆贺团圆乐,独有他去筑长城。”[1]13“二十五孝”、卖身葬父的董永、以乳哺姑的唐氏、大脚歌、金莲歌、花木兰代父从军、炼金道士、报冤记、清官断案、矮将军、文灰村名字的由来、孩子出生时屁股上的蓝色印记是被冥世城隍一脚踹出来的、“拾鸡蛋”歌……
(七)民间信仰
观音菩萨托梦、风水、防灾病的护身符、庙里烧香许愿、关帝画像、香炉、大字符咒、灶王爷、算命、床底下放葫芦避邪……
(八)教育及思想
举人、中状元、翰林院、家塾、水师学堂、《三字经》《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同文会馆、顺从天意、“孝”“知恩图报”“忍”“君子有所欲求诸己,小人有所欲求诸人”[1]18、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九)饮食
烤鸭卷饼、虾、饺子、松花蛋、辣牛肉、酿香菇、古老肉、芝麻方酥、核桃饼、杏仁饼、芝麻饼、蜜饯……
(十)文学
沈祖濂的悼亡女文、《红楼梦》“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竹林七贤、李白《清平乐》、长生殿、桃花扇、狐仙、袁枚的诗、《诗经》、佛经、杨绛《干校六记》……
此外,小说还介绍了一些京剧、书法、中医等中国国粹文化。正是这些细微的中国元素营造了小说浓厚的中国韵味。对西方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作者所叙述的封建大家族故事则为这些文化的展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考究程度。短暂的中国之行并不能为包柏漪提供太多的文化信息,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符号更多的是作者通过阅读中国史料、典籍、文学作品等文字媒介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春月》是作者研究中国的产物。包柏漪认为,许多美国人实际上还不了解中国,之所以通过“写一个故事”描述中国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包柏漪传记的作者玛丽·维吉尼亚·福克斯(Mary Virginia Fox)称其是“为了改变的中国声音”(Chinese Voice for Change)。然而,尽管作者在使用中国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尽量秉持客观的立场,但其文化符号的选择与使用不自觉地带有西方视角的文化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借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这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不是中和客观性,继而产生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呈现出两者相互渗透的杂交状态[2]。也正因如此,《星期六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使西方理解东方的最卓越的小说之一”[1]3。
包柏漪跨越了两个世界的边缘,成为自由游走于双重世界的文化的越界者,将西方元素加诸于小说中的中国人物身上,使中西两种文化在小说中共存:秉毅美国留学归来,“开箱抽出一件浅驼色绸袍……随即脱下身上的洋式服装:上衣,背心,长裤,硬胸衬衫”[1]35,完成角色转换,重新变成了华夏人,而且试图将西方文明渗透到家族管理中;允愉教春月学英文;春月与秉毅一起阅读《奥立弗·特威斯特》、林纾翻译的《双城记》;明玉入读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文化教育,并深受影响;长风买来一台钢琴,和明玉合奏《坎普顿赛马曲》和《浅褐头发的珍妮》。这种越界通过“她者”的表述在另一种文化屏幕下呈现出“陌生化”效果。“陌生化”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该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将习惯、常识、意识等从表面上毫不相干的生活真实中分离出来,创造出内在相互关联的艺术真实,以表象的“陌生化”冲突呈现内在的震撼, 从而使对象陌生,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以此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3]。包柏漪认为,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其也一直声称中国是她永远的根,从小说中点点滴滴的中国元素可见包柏漪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但是小说中过多涉及中国革命、战争,也给西方读者造成了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并把中国定格在古老的达官贵人世家的深宅大院里,定格在动乱的战争年代。
二、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在异域的生活阅历及文化氛围的影响,包柏漪试图用异域文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其原本可能过的生活,而这也导致了她对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她者”视角的批判。面对中国父权话语中对女性的传统界定,作者聚焦封建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中国女性,让西方读者直面父权压迫下中国女性的异类、苦难及其反抗,发展出两代中国女性形象的抵抗叙事。
在小说《春月》中,作者多次提到中国传统观念中关于评判女性的标准:“女子以贞静为先” ,“女孩子应该呆在深宅内院,跟着娘学持家之道。”[1]65显然,作者对这些观念是相当不以为然的。包柏漪从父母那里听过许多家族故事,其中最让她感兴趣的是外婆。从外婆独立反抗的形象中,她似乎看到了自己血脉中流淌着祖先的个性。外婆是个缠足的小脚女人,无力改变社会对那个时代女性的要求,但她即使在缝隙中也要顽强生存,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骑马和在海中游泳是她的爱好。“三寸金莲”也成了包柏漪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之一。这种意象在西方现当代文学家中也曾出现过,如托马斯·胡迪的《茶杯之幻想》、赛珍珠的《大地》、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多罗西科的《一步一朵莲花:裹脚之鞋》、哈金的《等待》等作品中都涉及对中国“三寸金莲”女性形象的描述。但从中国人的视角对此进行描述,更能引起西方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兴趣,满足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认识体系[4]。
在男性审美中,裹足的女性特有的孱弱病态之美,赢得了男性的同情。大家族的女性只有通过裹足,才能在男性的家族权力结构中拥有身份和地位,而女性只有通过认同男性审美和道德伦理,并主动参与到这个审美、道德伦理和权力秩序中,才能在家族中获得身份、地位和权力。对于男性而言,裹足是对女性的征服;对于任何一个女性个体而言,裹足永远是一个残酷的刑罚。但在古典社会,裹足是女性进入男性世界的一个仪式。唯有通过裹足,受到男性的束缚,女性才能依附于男性,并在家族权力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裹足后的女性,即便有些许的挣扎反抗,最终仍选择屈服。
她的小小金莲酸疼,便学着梅花常帮她那样,按摩自己的小腿肚,但是她的手指力气不够。她疲惫地仰身倒下,擦掉一颗将要滴下的眼泪。她已经大了,不作兴再哭[1]8。
春月的裹脚充分说明古典时期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以及裹足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正是这种女性对男性依附和认同心理的内化与“三寸金莲”审美标准的形成,女性与男性共同延续着大家族女性几百年的裹足文化。对于张氏家族而言,只有裹足,家族的女性才能进入这个庞大的女性世界:
这一屋子的女子,有祖母辈的,母亲辈的,有守寡的,有大太太、有姨太太,有小姐,有丫头,还有仆妇,都聚居在这三十多进院子的祖宅里[1]5-6。
张氏大家族的女性世界有着分明的尊卑等级。除了女性辈分形成的身份差异之外,是否裹足也在主子与下人、尊贵和卑贱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女性文化心理鸿沟,不同的身份等级拥有着各异的文化认同。尽管女性世界自成一体,但对于男性世界而言,裹足将女性圈养在家族的庭院中,使她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封闭世界,是男性世界的一个影子。通过裹足,女性世界与外在世界隔阂,女性的欲望、独立人格与理想,甚至作为一个正常人行走的自由,都被男性所束缚和阉割。这是一种残忍的行径,揭示了古典时期中国男性的黑暗心理:一种独占的、淫欲的、专制的、甚至自卑的心理。只有将女性束缚在家族的世界中,成为男性的影子,男性才能完全独占女性的身体;只有通过控制女性的行走权和各自的情欲,男性才能显示出强大、威严。男女之间的家族伦理结构展示了一个封闭的古典家族世界。封闭性和权力结构同时隐喻着晚清帝国的封闭性和权力结构,一个充满了东方男性既妄自尊大又卑下,既残忍黑暗又貌似脉脉温情的世界。张氏家族男女的权力结构和道德伦理是晚清帝国权力结构和道德伦理的微缩标本。
在漫长的古典时期,女性个体的欲望和心灵史往往淹没在男性的话语叙述之中,她们的形象和心灵史或者幻影重重,或者早已烟消云灭。只有到了近现代社会,男性社会对女性的重新发现和女性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那个沉寂几百年的女性世界及其心灵史才有被重新书写的可能。在张氏家族,春月以前的家族女性,在男性专制的社会中喑哑失语。而到了春月这一辈,由于家族男性接触西方文化,国门在自愿与被迫中稍稍打开,个体意识的微风逐渐唤醒女性独立的意识。与被裹足的上一辈女性对男性的自觉依附相比,春月虽然也被裹足,但在其内心深处仍然葆有着走出这个封闭世界的自我想象。春月更期盼自己能够以一种开放的、独立的姿态行走,走出家族的封闭世界,走出女性对男性千百年的依附。
“大伯伯,蒸汽能开书里的那些船,还能让车子在铁路上跑,为什么不能做一双会飞的鞋?那我走起路来脚就不疼了。”[1] 62-63
春月渴望能够摆脱对男性世界的依附,自由自在地行走。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实际上这种期盼一直贯穿着春月的前半生。从出嫁被封在轿子里到守寡,春月的前半生都处在封闭的家族世界之中。只有当春月守寡回家,家族世界日渐坍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日渐式微时,她才真正看清外面的世界。
尽管春月渴望走出家族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家族的权势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甚至对金莲的审美想象,还紧紧地约束着家族的每一个人。
她独自含笑绕房间行走,轻移莲步,款摆柳腰,小心地整一整发髻,仿佛是戴着一顶珠冠。她在镜前优雅地屈身请安——头颈前倾,背脊挺直,右膝刚刚擦地,双手轻触左臀。她垂下眼睛说,“张家女儿承蒙过奖,愧不敢当。我算不上美人中的美人……”[1]81
长大成人的春月同样将金莲视为一种美,这种内化的审美心理让生活在传统和现代接壤之处的人欲罢不能。她们只能在古典的道德伦理和现代的独立意识之间徘徊,她们无力挣扎,更无力追求,她只能顺着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之势。这是这一代人的困境。春月出嫁时,其“三寸金莲”所受到的苛责,和她在新婚之夜扔掉小鞋与丈夫共同反抗包办婚姻,这两种行为共同存在表明了春月这代人要冲破传统道德伦理的艰难。
如果说在中国古典社会,女性裹足代表了一种拥有高贵、尊严和权力的话,那么在近现代中国,这种文化寓意必将改变。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裹足已经变成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裹足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一个界标,清晰地划出先进和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和东方的界限。
对于家族新一代春月的女儿明玉而言,在金莲和大脚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其价值抉择的自觉也分外明显。由于春月深切体会到裹脚对女性的摧残,充分认识到裹足把女性封闭在家族世界的局限性,还因为她自身对外在世界的憧憬,她假托丈夫的遗愿,说服婆婆让明玉摆脱了缠脚的折磨。虽然是明智之举,但在春月的内心深处,面对别人对明玉大脚的讥讽,她对这个大胆之举还是充满困惑:
“但现在春月有时也心里含糊,不知自己做得对不对。虽然她听说有些信了洋教的人家不给姑娘缠脚了,但左邻右舍的女孩儿还没有一个逃得过这关的。”[1]171-172
对于春月这一代的两难抉择,明玉是身无感触的。拥有大脚对于明玉而言,更具有一种本能的叛逆和文化象征意义,她经常炫耀她的大脚:
明玉公然炫耀自己的大脚和不寻常的念书识字,以此来抵制孩子们的侮虐和长辈们对这古怪的孤女的怜悯。
她此刻便在花园里反唇相讥地唱:
“金莲脚,
小又瘦,
冷了冻,
热了臭。”[1]172
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夹缝中的春月孕育出更为叛逆的一代。金莲在明玉这一代的文化价值观看来,已经摆脱了审美和道德伦理的束缚,变成了古典文化丑陋的遗物和象征。自从明玉从教会学校毕业以后,由于西方文化对个性的张扬,明玉彻底地从对男性的依附这个集体意识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更具有文化自觉性:
明玉一马当先,和秉毅并排矫健地走着,跨的步子和秉毅的一样大,不时停下来握手或鞠躬,向人祝贺或接收祝贺。在后面陪春月缓步而行的反而是长风……[1]308
明玉的大胆和独立的个性,她对现代文明精神的理解,使她勇于对抗家族的裹足陋习。为此,围绕着裹足,家族也爆发着守旧与趋新、传统与现代的争执:
“太婆婆,”她告诉她们,“全中国好人家的年轻男人都发誓再也不和裹小脚的女人结婚了。”
寡妇们咬定她是瞎说,她便毫不含糊地把一份剪报上的名单读给她们听。
女眷们仍旧不信,直到最后金娴开口说,“是真的。我听伟景的爸爸说过这些事。我还听他说过,他要劝我们的儿子娶大脚的媳妇。”
“如果他喜欢大脚,你为什么不放脚呢?”二婶婆甚为得意,仿佛“碰”了牌。
“你可以放,你可以放!”明玉力劝。
“那太疼了。”春月反对。“我们裹脚的头几个月流的那些眼泪呀,有谁能忘得了!”
女眷们沉默不语。
“就算放了脚走起路来一阵风,你忍心让人重受一遍这样的罪吗?”
“哎哟,不行!”女人们都喊起来,除了金娴。“哎哟!,不行!”
“只有像我女儿这样没吃过这份苦头的人,才想得出这种主意!生米已经成了熟饭,就算了。”
女眷们点头。明玉反驳的话如骨鲠在喉,但她咬住舌头强咽下去[1]326-327。
在是否从裹足到放足的问题上,明玉彻底的主张与春月更通人性的主张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两代人从不同文化立场上的冲突。显然,春月的主张更加尊重女性个体的自我独立意识和切身利益。而明玉则从文化冲突的抽象观念上主张彻底革新。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她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女性个体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幸的是,对于处在过渡时期的部分女性而言,如果说从天足到裹足,是屈从于男性专制;那么从裹足到放足,却也同样意味着对男性社会的屈从和依附。这种灵与肉的双重困境,深刻揭示了这一代女性的悲剧命运。为了自己深爱的丈夫秉毅,金娴自愿再次忍受非人的折磨,经历从裹足到放足的苦难,最后穿上了高跟鞋,但这依旧难以摆脱其对男性的依赖。
小说《春月》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种“她者”的建构,体现了作者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批判。来自异质文化的中国女性被凝固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三寸金莲如同刺在中国妇女脸上的“红字”,无法消退。这种西方话语中模式化的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她者”的典型表述,是符合西方品味的“她者”建构,形成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妇女的条件反射,同时也是西方霸权话语中被殖民的东方世界的隐喻——驯服、沉默。越南裔学者特瑞恩·T·明和(Trinh T. Minh-ha)在其著作《女性、本土与她者》(Woman,Native,Other)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专题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在西方流通的渠道,但是这种流通“只是在为将‘第三世界’女性视为更加不幸的姐妹的‘第一世界’女性的特殊性作广告而已。”[5]包柏漪在小说中试图解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建构起“自我”与“她者”的二元对立——一种西方女性中心主义思想。
包柏漪特殊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造就了其作品的独特性。华裔的血统,曾经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夫人的身份,让其“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在华裔美国文学的王国里,文化的多元是包柏漪文学创作的根基,在其文学叙事中体现了其文化越界的特质。包柏漪的文学世界里“寻根”的痕迹俯拾即是,寻找家族的根,寻找中国的根。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在她者视野下呈现独特的色彩,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意义与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