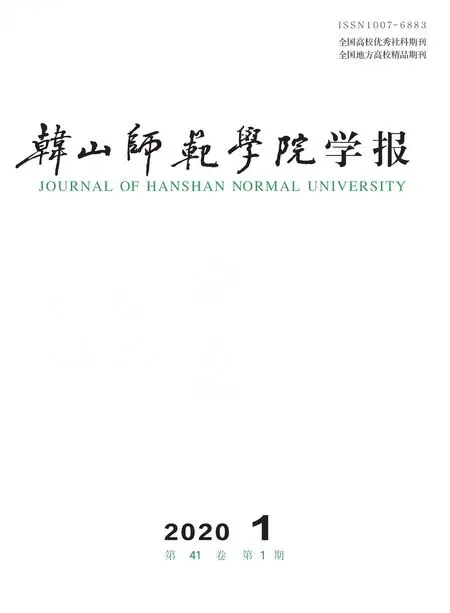车厢空间体验的文学书写
——解读施蛰存小说中的“车厢”
何颖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车厢——流动的现代公共空间
1908 年3 月的一个清晨,大地尚灰蒙蒙一片,一辆艳红色电车在上海街头穿过,电车的问世在上海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不单是上海近代公共交通诞生的标志,更是上海迈入现代社会的物质表征。电车、汽车或火车等现代工业流水线上制作出的交通工具在20 世纪20、30 年代的上海随处可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透整座城市,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一如马歇尔·伯曼所断言,现代人的原型即是“一个被抛入了现代城市车流中的人”[1]。
事实上,无论是在城市中穿梭的电车、汽车,抑或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火车、航行于水路之上的渡轮,他们都创造了一个具流动性的半封闭式的现代公共空间——车(船)厢。每日无数陌生人集聚在这一狭小的公共地带,以乘客的身份交织到底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谱写怎样的乐章?一方面,车厢将人们从日常生活轨道中强拉出来,尤其给女性的公共参与带来了新的速率,昔日授受不亲的男男女女被放置于互不相识却又紧密相近的关系之中,扮演着奇妙而浪漫邂逅的主人公;另一方面,玻璃窗外的一晃而过、交错相间的铁轨线,虽然是作为没有语言的物品而存在,却是某种外在的寂静力量的呈现,并成为触动“无意识记忆”的按钮,沉默、幻想,人们看似空洞而滞呆的眼神背后暗流着曾经沉睡在无意识深处而今不间断的迸发、涌现的人和事物。
敏感的海派作家们嗅到了车厢空间中那不寻常的气味,对于半封闭的路途时空,他们身陷其中的同时亦试图抽离做一名局外者,不动声色地去观察、描摹各色人物,记录行程故事,以及用文字来构建当时的车厢社会。如果说在京派作家眼中,人力车是北京市井文化、底层文化的文学表现,那么海派作家将形形色色的现代交通工具展示在读者面前,则是借助文学体验来传达上海百姓众生相。这也是施蛰存等人曾将创办的杂志以“无轨列车”为名的原因①1928年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3人合办文艺半月刊杂志《无轨列车》。在笔者看来,此名除了指明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定向以外,列车这一意象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它把新感觉派对机械化都市文明的沉溺、对瞬息变化的都市体验囊括其中。。与刘呐鸥等把笔墨重点放在对都市人生的直接描摹不同,施蛰存更注重心理的刻画与剖析,对车厢空间体验的书写容纳了更为复杂的内容。
二、施蛰存的“车厢”亲身体验
施蛰存的故乡在邻近上海的松江,出于求学与工作的需要,他经常乘坐火车往返于上海、松江以及周边城镇之间。后来定居上海,他每日亦是离不开公车的①根据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施蛰存在1923 年二月从之江大学肄业,三月赴宁波担任代课教员,他每周日必返回杭州以继续兰社的文学活动。自1923年八月上旬起,他赴上海继续学业并参与文学活动,自此时常奔波于上海及其周边乡镇之间。根据施蛰存在《我们经营过的三个书店》一文中的自述,他与刘呐鸥、戴望舒一天的生活,常是上午工作,午睡后坐车去虹口游泳,尔后再去四川路喝冰饮。用膳后则去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跳舞,玩到半夜才回家。,故而对车厢自是有一番独特的体验:上车时一番忸怩,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许多夹杂的目光的鹄”[2]24,尔后稍稍适应,便开始观察身旁的旅客,并“在幻象中凝演出他们的故事”[2]26。这种亲身体验无疑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一天,在从松江到上海的火车上,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连线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3]624
除《夜叉》这篇文章外,还有其他短篇小说的故事是发生在车厢上的,如《闵行秋日纪事》《雾》等,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因在车厢上相遇而相互交织;亦有独行者在车厢内沉浸自我,如《魔道》《狮子座流星雨》等,主人公乘着电车穿梭在繁华闹市之间,灯光普照的上海映照着他们那深陷苦闷与迷茫的脸庞。这些故事均基于施蛰存的亲身经历,他曾坦言自己曾在电车上偶遇一名神秘女子,为之神魂颠倒,甚至下车尾随;他亦时常是只身上路的人间孤独惆怅客,“两眼追逐着街车的速度……再回头,便又不能看到,更难免不有些无名的惆怅”[2]24。
施蛰存将车厢纳入笔下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是他熟悉的公共空间,更是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在其小说中,车厢不仅是男女邂逅的场景,也是乘客构建内心世界的触发点。同时,我们也应该去探究车厢空间书写背后所体现的城乡文化滞差,更全面的理解、分析施氏小说中的车厢空间体验。
三、车厢空间与被书写的车厢体验
文学评论家弗兰科·莫莱蒂(Moretti Franco)指出:“空间……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内部决定了叙事的发展”②参见弗兰科·莫莱蒂著《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转引自马特《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空间批评的新动向》,载于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美国文学研究》第85页。。在施氏小说中,当主人公登上车厢一瞬,车厢便延展成文本叙事的发生空间,以独特的空间特征影响着故事的发展,或冥想、或邂逅甚至是谋杀。我们不禁会发出一个这样的疑问:车厢于现代个体而言,在人际交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是普罗众生的情欲泄放
在悬疑小说家阿加萨·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笔下,车厢容下了一场毫无破绽的凶杀案,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中国作家笔下,车厢内的风花雪月无处不在,如刘呐鸥《风景》、张爱玲《封锁》等。陈建华教授在《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中说:“跟外国文学不一样,中国人不善写火车的罪恶谋杀,却不乏新婚蜜月或争风吃醋之类的旅行故事”[4]。然而在施氏的车厢文学中,浪漫艳遇有时却会掺和进欺诈或谋杀③《雾》《狮子座流星雨》等小说皆为车厢一段短暂的罗曼史;《闵行秋日记事》《魔道》两篇小说则涉及黑道、欺诈甚至是谋杀题材,前者是“我”在车上倾倒于一女子石榴裙下,下车尾随,与那神秘女子演绎了一段围绕“毒品”展开的故事;后者则是“我”在车中疑似被一妇人下蛊杀害的经历。,在陌生人当中展开的故事似乎在宣示一个“真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现代生活是时时刻刻在速度着”[5],这是刘呐鸥对时代的归纳。那究竟“速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行动?一波战栗还是一股冲动?施氏笔下的车厢诠释了这种”现代人精神”——车厢往往是邂逅得以展开的前提,旅程成就了一段短暂的罗曼蒂克。
卓佩珊太太盯着车上三位“春意盎然”的女乘客,偏偏自己是最不受瞩目的,然而一位衣着整洁的年青人却更关注她,有意与她亲近,“随着车身的簸动而推挤着,使他的腿屡次贴上了她的膝盖”并且“用文雅的眼睛注视着她的卷曲的美发”。卓佩珊太太在青年的凝视中看出了炽热,“不禁伸手去拂掠这新近电烫过的青丝”[3]206——卓佩珊太太心动了,对于这场邂逅,她心里生出了一朵花。
在这篇《狮子座流星雨》中,施蛰存在模糊隐晦间创设了一场年轻妇人的罗曼蒂克幻梦,这场梦是无声的,暗流涌动的——拥挤的车厢将两人距离迅速拉近,情欲的骚动弥漫在封闭的车厢中。卓佩珊太太与年青人并无言语交流,通过些许细节传递情绪远胜于让人物喋喋不休地讲故事,腿贴膝盖,撩发露耳,一个个小小的举措被无限放大直至其充满暗示性,忽然的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着充满了荷尔蒙,处处透露着暧昧。然而一切在卓佩珊太太到站下车的刹那戛然而止——这段邂逅似乎从未发生,却在太太的梦中留下了点点痕迹。
不同于卓佩珊太太若隐若现的想入非非,小说《雾》中的秦素贞的邂逅却是实打实的。秦小姐是一位古典浪漫主义小姐,她心目中的丈夫应是一位既会吟诗作画,又体贴人心,还能赏月饮酒的美男子。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她与一位文雅男子不期而遇,似天赐良缘。郎有情,“频频地看着她”[3]232,帮秦小姐拾起手巾时带着笑意直接将它放其膝上;妾有意,矜持的秦小姐盯着雾景发话给了他一个接近的机会,两人交谈甚欢,秦小姐甚至觉得:“就像现在的情形……假如青年绅士对她说明了他是在爱她,她想这一定是没有反对的理由的。”[3]232封闭的车厢酝酿着暗涌的情愫,使得秦小姐抛去了上车初的羞涩,临下车时将姓名住址留给了男子。这段佳缘并未善终,当表妹告知男子身份是“一个戏子,一个下贱的戏子!”[3]236后,她整个人都垮了,很是疲惫。
小说题为《雾》,封闭的车厢不正是这层雾吗?车厢的封闭性将世俗伦理道德、价值观全数拢去,使得秦小姐得以“避开了社会非难的限制和约束”[6],与男子交往。然而当离开车厢,迷雾散去,一切回归真实后,爱情又重新掺和进误解与蔑视。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是这样总结城市体验的:“以集中的、醒目的特点出现的诱惑,在都市短暂的人际关系中与个体的联系更为紧密。”[7]由于车厢的流动性,空间的狭挤性,男女主人公在车厢上的“邂逅”都具有这种”集中性”以及“紧密性”:作为日常公共空间,陌生各色人物穿梭往来的同时又会停留驻足——每一位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或多或少的神秘——空间的逼仄与身体的邻近,迷乱氛围使他们的欲望左冲右突,给人们的身心带来新的挑战。车厢的封闭性还使得男女觅得自己的空间,暂且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旋涡中脱身,个人内心的欲望之火得以点燃。然而,这种由肾上腺素瞬间增激造成的“恋爱”是暂时的,并且是脆弱的,难以禁受住外部环境的考验——下车后的分道扬镳意味着情感的搁浅,素贞小姐得知男子身份后竟自我鄙夷起来,卓佩珊太太在梦的潜意识中男子回归到妻子身旁,小职员“我”最终也与神秘女子脱离羁绊……
正如上文所言,都市文学往往将车厢作为饮食男女情欲宣泄的空间——这是新空间的演绎书写,但许多车厢小说依旧遵循着传统小说叙事的性别秩序,前文提及的《风景》讲述的就是男子燃青与一位有夫之妇在列车上相互引诱的故事。此外,“美人为祸”的传统价值观在车厢这一现代都市空间中难免有“借尸还魂”的倾向:女性在公共空间的露面形象经常被譬如为诱惑的现身,而这种诱惑常常又导致男性的危险处境,或惹祸上身,或人财两空,甚至命丧黄泉——就像穆时英的《某夫人》,山本忠贞在车厢内邂逅了一名妖冶而飘逸的女间谍,最终泄露机密,麾下中队被一网打尽。然而施蛰存在《雾》《狮子座流星雨》《春阳》等几篇车厢小说中却反转了性别关系,以女子为视角,变为“有男同车”,男子反而成为一个客体化配角,其言行始终被女子的观察视角所笼罩:男子的形象始终是模糊的,仅用如“整洁”“文雅”等并不能具化形象的寥寥几词概括;他们的小动作,如三篇小说中男子的“瞧”“盯”“凝视”,也是女子的直觉将其定义为是暗昧的举措。我们甚至可以如此理解,在这几篇车厢小说中,男性反而成为空想中的暧昧对象,成为一个仅仅被欣赏的客体,而我们的女主人公依旧是位“善女子”。
是的,车厢书写中的女子只是都市中的陈规女性,这有别于其他小说的女性“摩登”形象。姚玳玫教授在谈到此类“善女人”时指出:“(她们)是一个日常女性,在食色本性的支配下偶尔试图越轨而又越不了轨的凡人。”[8]她们不是他人的情妇,不是歌舞女郎,更不是神秘间谍,只是能够被理解的普通女人,穿着衣袖“长到手背”的旗袍,总是将大衣裹紧,从不会“把大衣领翻下来,让风吹进她的胸衣”[3]224,她们是社会不可或缺却又被认为是“可忽略”的普通女子。施蛰存把她们的车厢体验容纳进文学书写当中,是女性日常身份被确定的标志之一。
(二)是异化心理的温室
现象学中将空间分为现象空间与客观空间①据倪梁康《关于空间意识现象学的思考》一文,最早胡塞尔已经在空间问题上将人们导向对现象空间和客观空间的区分,尔后再进行直观空间和几何空间的区分。,其中现象空间又被称为心理空间(意识空间)。之所以作出区分,是因为人类对空间的感知不仅仅是由视觉和触觉所决定,还基于主体在精神上的构建。直白的说,人类对空间的体验是直接的、感性的,几何空间总是被填满了空间以外的许多意义,我们这里探究的车厢空间体验亦是如此。那作者是如何来表现这种空间体验的呢?——那就是剖析乘客的心理世界。正如陈良梅教授在研究空间叙事时指出的,要通过刻画人的内心来凸显人对空间的感知,“采用传统的模拟塑造现实中的人与事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9]。车窗内挤在人群之中相对静止的、沉默的个体,看着窗外流动的人和物,会发现在车厢上构造的视点是飞速的,稍纵即逝的,与漫步游街时所创的视野全然不同。此时,乘客们很容易就把思绪飘散,去构建独特的内心世界——这种创设有时甚至会放大异化的心理。
1.车厢内:一切被放大的观察
在《阿秀》中,施蛰存用了“湫狭”一词来形容车厢的潮湿仄挤。死水般的沉默,互不认识的陌生人,“满车的人啊!这样牲畜似的装载着”[3]46,整个空间充满压缩感,除了身体的不适,更容易使人联想起自己被生活的车轮和狭窄的生存空间压扁,此时焦虑感甚至成为病态心理,在思想漩涡中迷失自我。“害怕、厌恶和恐怖是大城市的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10]不管是“善女人”春阳阿姨、卓佩珊太太,抑或是时常游走于城市之间的男子,他们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观察车厢中的人——“数罗汉似的一个个地看过去”[3]46。他们常常因为一个小触点(观察点),敏感的神经在危险的思维中穿越——半封闭性空间放大主人公的感官功能,一举一动对于主人公而言都别有意味:“我正在车厢里怀疑着一个对座的老妇人。——说是怀疑,还不如说恐怖较为适当些。”在《魔道》的车厢内,主人公视眼前穿黑衣的老妇为“妖妇”:不仅模样古怪“伛偻着背,脸上打着许多邪气的皱纹”,还会透视术似的“当你的眼光暂时从她脸上移开去时,她却会偷偷地,或者不如说阴险地,对你凝看着。”当他发现老妇不喝茶只喝白开水时,更是确认她的身份“妖怪是不喝茶的,喝了茶,她的魔法就破了”[3]159。
整个旅程这个妇人都在不断折磨着主人公的神经——他太焦虑了,神经衰弱使得他各种感官错觉,妇人每一个动作在他看来都酝酿着恐怖:对着他嘴角牵动了一下、干枯而奇小的三个指头配合着喃喃然的嘴唇在做符咒、喝水是施行妖术前的准备等,虽然他几次三番竭力转移注意力,最终还是无法控制注意力,视线回归至妇人处处可疑的动作上,不得不颤栗起来。在读者看来,主人公这一切的内心独白无疑是荒诞可笑的,他甚至将最初在车厢中的焦虑蔓延到其他人事物上,这更是非理智的:他的焦虑是一种寄生的焦虑,依附于任何想法中,使人容易做出误判;同时,一旦被附上焦虑,确信“邪魔附身”,那么所有的言语行动就被定了性,一切行为都有了自圆其说的机会。
从车厢内人物心理流程的结构方式来看,《夜叉》与《魔道》颇为类似,不管是主人公“我”还是朋友卞士明,都是在心理上、精神上双重焦虑却又无法向他人言说的可怜人,他们虽然想竭力摆脱自己的内心狂想,可最终却被异化的本体拉扯着蜷回自己的幻魇。《夜叉》的主人公魔障似乎更甚,他在车厢内出现了更为怪诞的幻象:“后面一节的车窗中,忽然探出了那女人的头。她迎着风,头发往后乱舞着,嘴张开着,眼皮怒起着。”[3]197相较之下,前几篇车厢小说中的女性车厢心理体验并没有这么可怖,虽然她们同样会去观察周围的乘客并以此加上自己的焦虑与内心渴求:卓佩珊太太看着车内艳美的外国女人,想的是她们是否会有孩子——这是她焦虑自己生养困难的表露;素贞小姐盯着衣着暴露的车厢女子,卿卿我我的男女,想起的是道义廉耻——这是她对“性”的觉醒与胆怯的表现。
虽然主人公们担心自己会患上各类“即便吃药也不能预防的”[3]159神经病,可实际上他们已经难以从焦虑中脱身,长期的精神不宁使得他们在本就湫狭的车厢上如坐针毡——他们的车厢体验一直笼罩着“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②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施蛰存全集》第五卷《北山散文集》第四辑第2279页。施蛰存在《致杨迎平(一一通)》中解释“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的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
2.车厢外:飞驰而过的都市风景线
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强调了意识流作为表现手法在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11]。施蛰存本就是精神分析小说的大家,在车厢小说中他更是将这种意识流笔法运用至炉火纯青的地步。意识流是需要外物唤醒的记忆,正如伍尔芙《墙上的斑点》中作者的记忆阀门因墙上一块小斑点而打开,《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大街小巷和花园从作者的茶杯中脱颖而出,施蛰存笔下人物意识流的触发点往往是车厢外的风景。
窗外景物转瞬即逝,速度之快使得乘客们无法再像“车厢内观察”一样细致,只能走马观花,视觉感官呈现碎片化倾向,源源不断的视觉裂隙形成的空白,往往容易引起观察者意识流的产生以填补视觉深度的丧失:当《魔道》的主人公顾盼着窗外绕着圆圈的风景,一个隆起大土阜一晃而过——这个契机使得多年沉积的知识瞬间迸发,他开始觉得那会是某朝王妃的陵墓,无中生有的猜想进而成为带有意淫成分的遐想——墓中的木乃伊是沉睡的美人,释放了他心中被囚禁的性欲,他想亲吻木乃伊的嘴唇……甚至在某一瞬间发生了心理错失,车上的老妇人就是墓中美丽的王妃。
同样,在《狮子座流星雨》中车厢外霓虹大招牌一闪而过,卓佩珊太太看着它想象成是一双有劲的大手掌,替她挡阳——她与丈夫多年来隔阂越深,她期盼着能有这样的温暖,然而列车一直溜去,“黄金的光终究穿透了她坐着的车”[3]224;又听到车厢外小贩卖报的叫喊声,意识忽的飘去了自己家扶梯底下堆积已久的叠叠报纸,想着报纸又进而叨念起那些个头版廉价广告——这又拨动了、刺激了卓佩珊太太的敏感神经——妇产科医生广告、孩子。
上车-到站-下车-归家。卓佩珊太太完成的是一系列有秩序的动作,跟《魔道》的主人公相比,思维虽然同样是随意的,跳跃的,可毫无疑问,是更为清醒而理智,有着足够的自控力——倘若不是因为封闭的车厢暂时屏蔽了现实力量无时无刻的监视,高速运行景物稍纵即逝造成的思想空白,那囚禁的潜意识是不会冲决出来的。然而,压抑已久的情绪又要从何处宣泄?所以说车厢是异化心理的温室,可也是一个决堤口。
四、车厢空间书写的背后:城乡的交互与冲突
列车是乡村与城市沟通的桥梁、纽扣——时空距离的缩短使得城乡之间的交互更为密切。施氏车厢小说中的男女主角,都真真切切地参与在这场交互之中,不管是小说中的“我”、卞先生,还是素贞小姐,卓佩珊太太。车厢是城乡之间的中继站,他们在车厢的体验,有性涌流的扰动,有各种焦虑情绪的涌现,正如上文所总结的,车厢是异化心理的温室。然而,我们真的要把一切怪罪于封闭的车厢空间吗?环境仅是诱发,他们的压抑,敏感,早在登车前就已经积攒在内心,就像即将点燃的风暴仅差一只舞蝶。施蛰存处心积虑地去描摹男男女女在车厢的种种情态,难道仅是为了捕捉现代化都市下混乱迷失的灵魂?如果他有意如此,那应该把笔力放在摩登男女身上。施氏车厢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作为寻常百姓的缩影,他们不是已然和现代都市消融一体的摩登男女,有时候甚至和繁华都市格格不入,他们只是“拙陋和渺小”的普通人。笔者认为,施蛰存是希望通过平民男女的车厢体验来彰显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空间、新旧思想的交互与冲突。
(一)都市人对乡村的眷恋与失落
中国现代文学中,城市和乡村就像是红白两朵玫瑰。享受着都市繁华与便捷的海派作家们似乎觉得城市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12],而乡村就是一滩纯白月光。李欧梵认为这种对都市的“反叛”是一种“五四”式的意识形式形态:“就是乡下是好的,纯洁的……它把道德的意味摆进去了。”[13]施蛰存的车厢小说在这种基调当中,属于一种“变奏”——谱出都市人对乡土的眷恋与失落。
“乡野的风物和清洁的空气,再加上孤寂和平静,是神经衰弱症的唯一治疗剂。”[3]175在《魔道》与《夜叉》中,主人公“我”和卞先生都是“都市病”的重度患者——都市生活的各种压力致使心理极度压抑、扭曲,从身体到精神都几近被压垮。于是乎他们登上赴往乡野的列车,期待平静安宁的田园生活(景美人善)能抚慰疲惫的心灵,排解胸中压抑。施蛰存细腻地描摹主人公眼中的“乌托邦”:竹林峰峦烟雨天,乌桕芦花依水旁。在杨家牌楼里卞先生每日“领受这古风的乡村里的秋暮的恬逸”[3]193-194。同样,《魔道》的主人公“欣喜地呼吸着内地田野里的新鲜的香味”[3]162,领略在上海从未有过的安逸与舒泰。《闵行秋日纪事》中的主人公亦是受够了局促的寓楼,接受了隐居乡下的好友邀请,作了一次乡间短旅。朋友的邀请函点明了此次旅行的疗效:“遥想足下屈身尘市,当有吉士之悲……荷叶披披,青芦奕奕,可为足下低唱白石小诗,扑去俗尘五斗也。”[3]46施蛰存笔下为主人公创设的桃花源看上去是一个与都市空间截然相反的乡土空间,笔触间处处透露着都市人对乡土的眷恋——这不仅仅是优美景色使然,人情的朴素,宁静平淡的氛围,自然的亲切,也让他们无限追忆。
他们的憧憬只是一厢情愿,借乡村缓解抑郁的愿望落空了——他们的乡村经历并没有让心中的焦虑得到缓解,反而爆发了:《魔道》中的“我”在车厢中的惴惴不安屡次在乡野间被唤醒,被妖妇追踪、诅咒的怀疑愈发坚定;《夜叉》中的卞先生本想化解胸中抑郁才来到乡下,可不曾想在乡间反而被恐怖幻觉所困扰,才会在车厢上崩溃。乡村反而变成跟车厢一样,成为刺激、加重他们魔障的“温室”。
孙志文在归因现代人的痛苦感时,指出了现代人有三重疏离,其中第一种就是和自然的疏离。他指出:“大都市的居民……即使他们决定回到自然去享受自然的‘治疗’,都市人的概念仍然控制他们,使他们不能和自然做真实的相遇……人甩不掉都市的影响,即使是面对自然的美景……人仍然在疏离、无聊、挫折、恐惧之中。”[14]虽然施蛰存笔下的主人公自认是都市中的异乡人,但在耳濡目染间已经接受了都市文化的熏陶,成为了都市人,正如在说到与女子接触时,卞先生和《闵行秋日纪事》中的“我”都自然而然的回想起在都市调情时的手段。恐惧与焦虑镶嵌在这个“都市人”身份上,自然也渗透进他们身体每一部分,入骨入髓。另一方面,当我们随着主人公真正去凝视乡村时,会发现所谓的茂林修竹、清潭深渊不过是一种“假饰”:卞先生在林木繁密的高山上遇见妖媚的白衣夜叉其实是夜出幽会的农妇;《闵行秋日纪事》中的“我”在江边小镇发现车厢女子竟是位女毒枭;《魔道》中的“我”在竹林发现殉葬的男女——乡野间充斥着、萦绕着偷情、贩毒、陋俗等。现实中的乡村已然变了模样,甚至和城市一样令人无法忍受,都市人的“还乡梦”不再,平添许多失落。
“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15]。鲁迅的这句话现在看来也可是都市人对城乡感受的写照。他们对繁华充满现代化的城市并没有归属感,耗尽心思费劲力气在城市生存却换来了身体的空虚和精神的压抑;同样,现实的乡土也不是他们萦绕心头的那个旧乡,他们怀揣希望上车,往往只能怏怏而归。
(二)隐秘欲望的觉醒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
在前文我们论述了车厢体验中的情欲外泄,这里我们并不应该去谴责他们在车厢上的行为的放荡,或者是不检点,而是应该试着去理解他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因素——人物的思想是有困扰、有挣扎的,“性”不过是自主意识觉醒的一个显性方面,而与之相对的是传统价值观的禁锢。
我们且看看《雾》中素贞小姐的身世:神父的女儿,二十八岁的老处女,父亲是个守旧的人,生活在临海的小卫城,择偶标准为白面状元郎。虽然她好打扮自认为颇有情趣,懂得浪漫,可是从她的家世中我们得出的结论跟施蛰存是一样的——“她实际上和她父亲一样,是个守旧的人物”。虽然《狮子座流星雨》中没有交代卓佩珊太太的背景,可是单从她着急为丈夫生儿育女就知道她是个传统女子。在车厢上她们看见衣着略微暴露的女子会替他们感到羞赧——这无疑是传统保守思想在作祟。与此同时,内心的自我意识有了些许萌动,在潜意识中她们也渴望能展现自己的婀娜身姿、自己身上的奕奕光彩。落后、闭塞的小城镇弥漫着礼教道义,精神深处潜藏的欲望尚能被禁锢;然而车厢却是一个现代性的都市空间——昔日授受不亲的男子如今近在眼前,其他男女的亲密行为更是一种鼓动。在这些外因的催化下,自主意识渐渐复苏,直至无法压抑——她们开始幻想起甚至是实践起罗曼蒂克来。
从上帝全知全能的角度,我们明白所谓“车厢爱情”是稍纵即逝的,但陷入局中的她们太清醒了——长期传统文化的浸染,她们早已失去了勇气或者从没想过要去与现实抗争,等停车靠岸,一切似从未发生过一样,她们回归本无趣味的日常生活规律中继续运转。施蛰存塑造的这几位女子,她们并没有逾越“善女人”的底线——虽然她们在那里徘徊过、游荡过、试图涉足过。她们的情欲在道德的囚牢内作激烈的挣扎,最终还是压回心底,依旧在世俗社会中坚守着礼法。
结 语
人们停留在车厢的时间不过是以小时甚至以分钟来计算的,可是施蛰存依旧用大胆细腻的笔触将都市人的车厢体验从行动到心理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可谓是独具匠心。他所描摹的情欲体验,所推演的心路历程,表面上不过是几小时,或者是几分钟的状态,却是这些普通男女在“现代”与“传统”生活夹缝中挣扎的苦闷姿态的浓缩。我们在研究施蛰存的时候,往往会将他与刘呐鸥、穆时英归类,可是他却一再强调自己与他俩是不一样的。就拿车厢书写来说,他们确实是不同的,刘穆二人叙述城市人生的角度偏向新新都市人类,他们鲜活时髦的身影,熊熊燃烧的欲望;可是施蛰存的关注点放在了都市人的大多数,他们在城市新旧交替之际的徘徊与彷徨,他们对现实的挣扎与妥协。同时,施蛰存书写的女子车厢体验已经不再单凭男性视角来构造,而是极力去复原女性的复杂心理,这在新感觉派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更新”。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施蛰存是如何将国人在物质、精神的“过渡时代”中表现出来的漂泊无依感化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和冲动,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展开对现代化直观而又深入的思考。希望能够对重新解读施蛰存小说,更深入理解施蛰存的创作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能对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研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