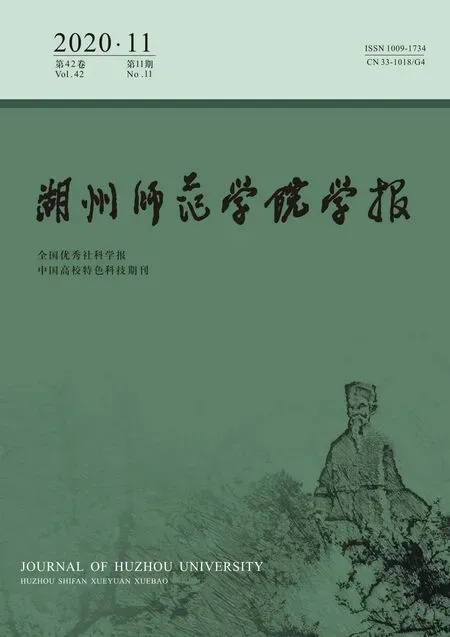“到处是商人气”*
——论鲁迅后期杂文对上海商业化的批判
温 武,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5)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鲁迅有感于广州杀人太过剧烈——“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1]465,便偕许广平远遁上海。寓居在共和旅馆的两人,起初并无久住上海之意,鲁迅做的是“我现住旅馆,两三日内,也许往西湖玩五六天,再定何往”[2]77的打算。初到上海的鲁迅也发现沪地“大有生气”:“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更有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3]81因此再三衡量下,鲁迅选择以“顶费五百”的方式赁居于拉摩斯公寓,自此鲁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海居住史。然而,揭掉了表面硬质的繁华与欣荣,摩登上海究竟还是以商业为骨骼支撑起的庞大身躯,并且像一面镜子冷冰冰地折射出各色人等的面孔。敏感于环境的鲁迅便有了“上海到处是商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的穿“湿布衫”的不适感。在后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便站在了普通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启蒙者等不同维度上对商业化的上海进行批判,而批判点落在了商业对民众精神的异化、商业对上海文人的诱惑、商业与殖民环境下产生崇洋媚外的西崽三点上。
一、商业环境对民众精神的异化
“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都商业化了。在中国内地还不明显,在上海这情形就十分明显了。”[4]168作为古老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试验场,商业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作为现代的一块“飞地”,20世纪的上海便获得了与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并列的殊荣——“东方巴黎”与“西方纽约”。其中“东方巴黎”的指喻所隐含的即是商业与消费意义上的。当代有学者也指出:“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至19世纪末,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商业、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商业大都市。”[5]168然而,一味地依托资本,依靠着金钱宣泄着自己的欲望,人们会最终在一层层的刺激中且痛且欢乐地沉沦下去。左翼作家便往往以批判者的眼光针砭近乎病态的商业气息,提倡书写“性灵”“闲适”的周作人对上海也流露出些许的不满:“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追求,结果自然又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6]
寓居上海的鲁迅,并没有同厦门与广州一样前往大学任教,反而是以“自聘”的方式,依靠着写作与翻译谋生。他在信中写道:“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并不想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7]67鲁迅通过阅读报纸和细心留意生活两种方式观察着十里洋场的方方面面并以此获得创作的灵感。但是在商业化的上海,鲁迅失望地发现:商业早已突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产生了新的异化机制。于是,鲁迅不无批评地写道:“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是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8]306“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9]397商业已渗透到了上海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以各种手段参与进了商业的巨网之中,成为了鲁迅冷眼旁观的对象。
在商业化的城市,各种沉渣争相泛起,在混浊的水面上打着旋地想成为资本链中的一部分,就连走街串巷的糖担也专以小孩为对手。在商业气息的沾染下,各种鬼蜮伎俩不断滋生。其中,最为鲁迅鄙夷的便是“吃白相饭”与“揩油”两种行为。在上海,游手好闲之徒将坑蒙拐骗的寄生生活当作了正经职业,骄傲地向人展示,而听者也不以为意。国民弱点中的懒惰,在十里洋场公开化、合理化,故而在鲁迅看来,“‘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10]218。这里仿佛又和鲁迅的另一篇文章《爬和撞》相照应着:“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11]278在鲁迅看来,“白相”便是这种带有以小搏大带投机性质的“撞”:本身已经趴在了地上,便无所谓更低的姿势。于是这又成了一种无形的投机资本,放心地做着于人有害而于己无损的事情。在另一篇《“揩油”》中,鲁迅便劈头盖脸地写道:“‘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12]269自我意识为金钱所蚕食,喷薄的欲望只能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实现,“揩油”便成为一条捷径,“恰如从油水汪汪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是有意的,并且也不失为损福济贫的正道”[13]270。在这里,仿佛又可以看见利己者从塞满的牙缝中挤出“替天行道”四个字。然而其还是怯懦的,因为到底还是“洋商的忠仆”。
市民的市侩与庸俗固然让鲁迅怒目以视,但更让鲁迅注意的是上海的女性在物欲的环境中自我物化、早熟地迎合着男性与商业社会。在常见的都市叙事中,女性往往成为现代都市物质化和情欲化的对象。新感觉派对女性身体的比喻,便往往借助现代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来表现女性充满现代性的肉体。如叶灵凤笔下的《流行性感冒》中“像一辆一九三三型的新车……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14],就将汽车与女性同喻。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女性往往是男性欲望的承担者,是在“男女聚散”的关系模式中处于被追逐者的地位。鲁迅笔下则不同,女性已经“时髦而通世故”了。“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15]531“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16]578城市给予女性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竟是取悦男性的生存哲学。而其结果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16]578鲁迅失望地发现娜拉出走后,躲过了名教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上海却依旧陷在了金丝铸造的鸟笼之中,然而套上枷锁的却是她们自己。
鲁迅以敏锐的眼光冷冷地审视着上海这繁华渊薮的黄金乡,上海便是长满着野草的地面。然而在憎恶这地面的同时,对被金钱化作的藤蔓缠绕而变得萎靡的野草也充满了厌恶感。
二、商业对上海文人的诱惑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以一纸《论文学家的态度》揭开了京、海派之争。沈从文还写了《论“海派”》进一步批判海派“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世风与文风,甚至还激烈地表明:“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17]110而苏汶则站在都市文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角度做出辩解。身处上海的鲁迅也加入到了这场论战之中,并从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利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这一角度,对京、海两派各打五十大板。鲁迅认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18]305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沈从文还是鲁迅对上海文学过度商业化都表示了批评。在鲁迅的后期杂文中,批评的焦点是因商业化而造成的“文人无文”与“文人无行”两种。
关于金钱观,鲁迅曾坦言:“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19]165在上海这个繁华的混沌之海,文人凭借着辛勤笔耕获得经济收入无可厚非。鲁迅后期选择杂文创作也有出于经济因素,而这对于居住“亭子间”的年轻作家更是安身立命的源泉。然而鲁迅担忧的却是文人过度迎合市场,心态趋于浮躁、功利,从而导致作品的粗制滥造。
鲁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代上海文学的勃兴便印证着鲁迅的观点。科举制度的取消、出版业的逐步成型、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催生了“才子佳人”和“黑幕小说”,而这些小说便因为过度迎合市场和时人低级趣味被周作人斥责为“非人的文学”。此外,咖啡馆、舞厅、影院、公园等消费娱乐场所也时刻刺激着作者。30年代的徐迟,即使是在上海的周围小城任教,在周末也习惯重返摩登之地便是佐证。[20]30后期的鲁迅想潜心创作,终以失败告终,原因便是:“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21]168各种名利、杂事引诱,潜心创作也成为一件难事。鲁迅也屡次在报刊或者信中表达了内心对上海文坛的失望,认为上海近年来的作品除了茅盾的《子夜》外便无佳作:“《子夜》诚然如来信所说,但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这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而已。能够更永久的东西,我也举不出。”[22]515颇有一副万顷花海,蜂来蝶往,热闹非凡,然而硕果独存的尴尬景象。另外,30年代上海各种主义风行,群雄割据。文人的笔尖是尖的,也懂得钻营新的商机。鲁迅为此讽刺道:“文豪是商定的,根子便是在卖钱。”[23]397
上海的商业化既已成为一注兴奋剂,刺激着文人的神经,但更让鲁迅警醒的是文人会在商业文化和政治高压的围堵下,精神和道德进一步地滑向无行的地步。而鲁迅认为的无行,并非是生活的不检点,更多指向的是文人成为当权者的奴隶,成为刽子手的帮凶。终其一生,鲁迅始终秉持“精神界斗士”的战斗姿态,其“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24]622。的知识分子使命担当感,让其始终有着“于天上看见深渊”的先觉意识并以此产生的责任感。早在1927年于劳动大学做的《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鲁迅便对青年学生提出“对于社会用不满意”“永远为平民说话且不顾利益”两点勉励。30年代,国民党对上海的独裁统治加强,一时间“文禁如毛,缇骑遍地”,鲁迅的文章无论新旧,也一并在查封之列,鲁迅也只能依靠着经常更换笔名来躲避检查。面对这个局面,鲁迅不无悲愤地写道:“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25]493然而此时,文坛上盛行的依旧是胡说八道的官样文字以及失去反抗意识与骨气的“奴隶文章”,他们也成了自命的“奴隶总管”:“政府帮闲们的大作,既然无人要看,他们便只好压迫别人,使别人也一样的奄奄无生气,这就是自己站不起,就拖倒别人的办法。”[26]48鲁迅的杂文怒斥“帮闲”与“二丑”文人为权贵帮凶与爪牙,并揭露其在血案中即使不直接带着血气,身上也必定冒着血腥味。
鲁迅还反对知识分子丢失反抗精神,以容忍换取苟安,以顺从换取金钱地位的行为。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的梁实秋,便主张做资产阶级的顺民,认为只要咬紧牙关往上爬,必定会有出头之日,并认定文艺是属于小部分人的精英文艺,大众无须染指。针对这种妥协且精英主义的论调,鲁迅则指出:“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27]199在这,鲁迅是站在了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梁实秋进行批驳,而鲁迅也讥笑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竭动力。鲁迅却发现商业繁荣的上海文人在名利的引诱下文思逐渐枯竭,甚至采取“剪贴,瞎炒,贩卖,假冒”等手段欺骗读者。更有甚者,却被政府招安,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了。
三、商业与殖民环境下产生的西崽
上海人对西方文化吸收、借鉴经历了一个初则惊、后则效的渐进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便衍生了“西崽”这独特的形象。“西崽本是上海人对于那些在中国居住的西方国家侨民家中的华人奴仆的称呼,后来被泛化而把买办也包括进来,指代一切为外国人效劳奔走以及以外国人为主人的中国人。”[28]他们是沟通东西的桥梁,是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同谋,也是商业与殖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并往往以媚洋、趋利、拜金、钻营等构成了近代上海的不道德形象。鲁迅曾以“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来概括“西崽相”,认为其在人格上兼具着主和奴、洋和土的特征。
在西崽的身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奴隶性。久居上海的鲁迅在杂文中描绘着十里洋场:“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29]52经过一系列的殖民尝试,洋人最终采取了“以华治华”的统治策略,人为地建立起了以洋人为顶端的统治金字塔,而“为洋前驱”的便是各种西崽。30年代的上海,这种社会结构已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小小的电影院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的缩影。在鲁迅的杂文中,洋人和上等华人联袂坐在电影院的楼上,楼下坐着中、下等华人,当电影演到黑色奴仆为拯救白色主人牺牲,主人缅怀忠仆的时候:“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30]309。这种感动大抵是物感其类,是华人将自己等同到了黑人的位置,也是对牺牲性命换取主人转危为安后,主人所给予肯定的感动罢了。灰色的幕布上调和了黑、白、黄三色,成了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画作。然而,在鲁迅看来,这群华人只是无可救药的“堕民”罢了:“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31]207
然而西崽终究是“无特操”:对待有利可图、仰仗着的洋人是卑躬屈膝;对待同胞,却又以主人的姿态自居着,甚至用死之铁骑,踏倒一切同胞,直至踏出一条供洋人观赏的洋洋大道。杂文《推》揭橥的便是西崽在对待国人时流露的“全民性的无爱”:卖报的儿童在收钱时,扯到了“高等人”的衣衫,被愤怒的一推之下殒命在车轮下,地上便多了一条淡淡的血痕。鲁迅得出结论:即使是所有的下等华人在索命的“推”下殒命,高等华人只会充当看客般发出喝彩的颂祝——“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32]205在这,鲁迅的笔虽然尖锐,然而却又是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黑暗现实:当高等华人掌控着中国,却无民族操守,一味媚外时,中国人民必将重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民族悲剧。如鲁迅笔下的阿金,鲁迅讨厌他们也并非出于仇怨,而是“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33]205,大抵还是因为公仇。
西崽毕竟游走在中西文化的裂缝之中,身上便杂糅着西方与东方的特征。“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34]171在鲁迅看来,西崽竟还是沿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处世原则,即使与洋人打交道、服事洋东家外在上沾染了“洋气”,但是其内核还是国粹的。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批判和揭露西崽是鲁迅后期杂文创作的重要成就之一。鲁迅用精简的笔调描绘出他们游走在华洋、主仆之间灰色特征,他们是近代上海商业和殖民的环境下孕育的特殊群体,是鲁迅对上海商业文化的有力针砭。
“我说鲁迅是个诗人,却丝毫没有把他当作是吟风弄月的雅士的诗人……他所有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35]89在李长之看来,鲁迅乃是一位诗人胜作小说家。当环境不相协时,鲁迅的思维之火便会迸发。鲁迅对上海商业化的批判是对其“立人”思想的又一贯彻。批判的目的固然是揭露,然而却也是在针扎般的阅读感受中催促读者一起寻找社会治理的良方,并以此达到“立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