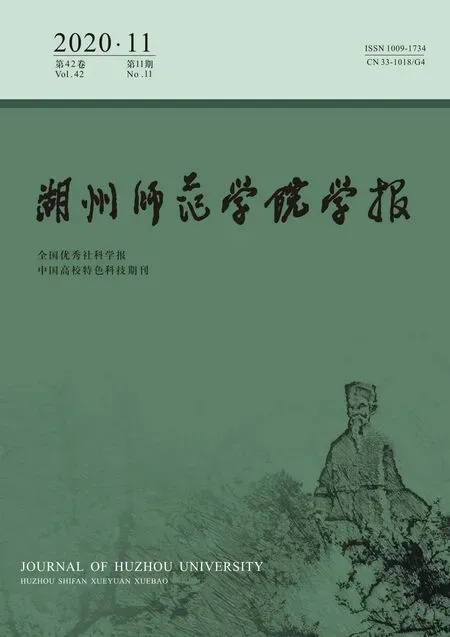近代中国法学教育中的“海派”与“京派”*
沈 伟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 200233)
比较教育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最好时代,“1911年至1927年,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1]66这一时期(本文所说的“近代”,仅限定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此说明)各地法律教育的发展,又以上海与北京最为突出,前者有声誉卓著的东吴大学法科,后者有闻名遐迩的朝阳大学法科,故时有“南东吴,北朝阳”的名谚。
20世纪20年代,上海和北京兴起了一波兴办法学院校(以下简称:法校)的热潮。上海一时间出现了多所院校,“上海之律师,固日见其多,而上海各大学之法科学生亦日见其发达,按上海之有法科大学,始自东吴法律学院,创办于西历1915年,继起者,则有持志大学法科、法政大学、法科大学三校,近者,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群治大学及东亚大学等等,咸有法科之附设焉。”[2]1924年,在全国26所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中,6所位于北京,分别是国立北京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民国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平民大学、朝阳大学;其中,前两所为国立,后四所为私立。上海在1919至1929年间,华资私立法校共有16所,1929年至1937年又有7所私立法校出现,其中,仅有一所存在时间短暂的国立暨南大学(1)1919至1929年出现的大学是: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科大学、文治大学、学艺大学、南方大学、远东大学、群治大学、持志大学、神州法政专门学校、大夏大学、中华法政大学、春申大学、东亚大学、大陆大学、上海文法学院。1929至1937年出现的7所大学是:复旦大学、文化学院上海第二分院、新民大学、华国大学、战时建设大学、新中国大学、三吴大学。。鉴于私立法校成为这一时期上海与北京两地法律教育之主流,因此本文将着重比较两地私立法律教育的异同。
一、教学阵容的差异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学院校师资呈现这样一种趋势,即教会学校多外籍教师,而华资法校则以本土教员为主,其中留学归来学生又成了华资法校的主力。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前者逐渐吸收华人教员的加入,后者通过招募留学归来学生来扩充师资。
早期东吴大学法科教员多由美国人担任,而且大部分来自美国远东律师公会,如罗炳吉(Charles Sumner Lobingier)、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阿乐满(N. F. Allman)等人。因与法国耶稣教会的密切关系,震旦大学法学院大部分教员来自法国,如该校教授民法的孔道明(R. P. Lapparent)、教授法律学的巴和玛守(M. Barraud)、教授中法法律的巴和述里(J. Barraud)等(2)《上海市教育局关于私立震旦大学立案问题(三)》,上海市档案馆藏Q235-1-651。,而且在早期24名教员中,有19人是传教士(3)《震旦大学关于学校概况的中、英文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Q244-1-5。。
华资法校在创办之初便颇为重视引进师资工作,其教员多由国人担任。私立上海法政大学刚开办时就聘请了前湖北司法司长张知本担任教务主任,前长沙地方审判厅庭长郭卫担任法律系主任[3]。远东大学的法科则有“何世枚、应成一、陆鼎揆诸博士,董修甲、郑觉民诸硕士,章世炎、康荣森、陈文伯诸学士”[4],并且由端木恺担任法科主任,“办理迄今,已经五稔,成绩甚为良好,自去冬开盛大之五周年纪念后,校长殷志恒更力求精进”[5]。持志大学成立时也聘定了各科教授,其中留学归来学生也占了很大比例,“国学系已聘定叶楚伧君为主任,教授为□三、汤济沧,查光佛诸君,其余各系教授已聘定者有南洋大学教授孙邦藻硕士,东南大学商科教授夏晋麟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刘芦隐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邹醒石君,美国纽约大学硕士童逊瑗,美国意里诺大学学士姚颂盘君,文学士邵桐轩君,并聘定复旦大学代理校长郭任远博士,及复旦大学教授何葆仁博士为讲师”[6]。
1920年后,随着早期留学生回国任教,教会学校与华资法校在教师层面的两极分化差距不断缩小。东吴大学法科校友吴经熊、盛振为、何世桢等悉数回母校任教(4)《1946年东吴大学校刊》,上海市档案馆藏Y8-1-204。。震旦大学的袁家潢、顾守熙等人也都一一留学归来。私立上海法政学院至1930年止,外国留学毕业教师人数为36人(5)《上海法政学院立案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Q248-1-2。,两年之后上升为39人(6)《上海法政学院廿一年度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Q248-1-623。。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留学生都学成于不同国家。据统计,1929年上海法政学院正式立案后,有教授38名,其中16人没有留学经历,22人是法学留学生。留学归来学生中,留学日本11人、留学法国5人、留学美国4人、留学比利时1人、留学德国1人。再如,在大夏大学6位法学留学教授中,留学美国的4位、留学日本和德国的各1位,他们在近代上海法学教育的构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92-93。
相比之下,北京私立法学院校的教员则几乎全是日本留学归来学生。如北京平民大学校长汪大燮曾任留日学生监督,专门部法科主任林卜琳是东京日本大学法学士,在该校13门法律类课程中,有11门任课教师为日本留学归来学生。北京民国大学也是如此,校长江天铎和总务长马鹤天都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8]1。虽然该校法律课程教员的留学生比例并不高,但教员大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的法学士(仅有的几个也是留日学生,如讲授商行为和票据的刘鸿渐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9]56,讲授战时国际公法的陈必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0]3)。北京中国大学为数不多的法律学系教员,也以留日法科学生为主,如戴修瓒、江元亮、王元增等。朝阳大学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聘请了一些英美留学归来学生,但他们大部分任英文刑法、英文民法、英文宪法的课程,主要法律类课程如宪法、行政法、商法各编、刑法等几乎清一色地由日本留学归来学生担任。以民法各编为例,在该课教员18人中,2人为本国法科毕业(叶在均和郁嶷),1人为英国法科留学生(梁敬錞,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硕士),其余均为日本法科留学生[11]49-68。
二、教学内容的差别
1913年,当时的教育部曾对法科课程作出系统的规定,认为“法政专门学校预科科目有:一、法学通论,二、经济原论,三、心理学,四、论理学,五、伦理学,六、国文,七、外国语(英、德、法、日本语择一种)。法律科的科目则规定有:一、宪法,二、行政法,三、罗马法,四、刑法,五、民法,六、商法,七、破产法,八、刑事诉讼法,九、民事诉讼法,十、国际公法,十一、国际私法,十二、外国语”[12]。但北洋时期教育部对上述规定的执行并不严格,尽管罗列了必修科目,但在条文后又提出“法政专门学校各科目授业时间,由校长酌量设置,呈报教育总长”,加上1924年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不啻将厘定课程之权交还给学校,故而并未形成统一课程之势,各校也算是各行其道自由发展[13]。
上海法校在教学层面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形成了多种法系荟萃一地的场景。如东吴大学法科素以教授英美法闻名,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教授“普通法”课程的法学院。震旦大学法科则偏重大陆法,尤其是法国法,其“概仿法国大学现行规程”[14],直至1932年仍保留了这一传统,如比较民法是“以法国民法为根据与各国民法作比较之研究,分四年授毕”,行政法也是“以法国行政法为根据与各国行政法作比较之研究”(7)《上海市教育局关于私立震旦大学立案问题(一)》,上海市档案馆藏Q235-1-649。。
此外,还有以教授中国现行法律为主的学校,如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科大学等,其开设的法律课程,几乎都是现行法的内容。还有教授各国法律的,如私立群治大学,最后两年英美法和大陆法的课程就占了很多的课时(8)《上海群治大学章程》,1924年。。相比之下,北京的法律教育则偏重教授中国现行法律。如北京平民大学法律系的课程,即是一例:
在负载电流方向为正时,逆变器输出电压u0在正的直流电源电压值+E和0之间进行切换;在负载电流方向为负时,逆变器输出电压u0在负的直流电源电压值-E和0之间进行切换;在负载电流方向变化的过渡过程中,逆变器输出电压u0在+E和-E之间进行切换.接下来将以u0在+E和0之间进行变化的过程为例,来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
法理学、宪法、行政法、民法总则、刑法总则、民法全部、刑法分则、商法全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政策、法院编制法、罗马法、法制执行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史、第一外国文(英文)、第二外国文。[15]7-8
不难看出,1922年,该校课程差不多全是中国法的内容,而且法律实习的相关课程也未开设。尽管1924年平民大学法律课程有所增加,但仍以现行法为主:
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民法总则、民法债权、民法物权、民法亲属、民法继承、商法、海商法、刑法总则、刑法各论、刑事政策、监狱学、强制执行、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破产法、法院编制法、中国法制史、罗马法、英文及日文、演习民事诉讼刑事诉讼。(9)《北京平民大学纪略》,1924年。
北京中国大学法律学系,除了罗马法之外,同样也没有开设任何外国法的课程[16]95。相比之下,北京民国大学的法律学系课程可能更丰富一些:
民法总则、债权总论、债权各论、物权、亲属继承、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总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英法、德法、法法)、商法总则、公司律、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法、宪法。
选修科目:证据法、罗马法、法理学、名著研究、法院编制法、社会立法论、中国法制史、欧洲法制史、财政学总论、经济学、社会学、强制执行法、诉讼实习、监狱法、外国语。
研究问题举例:中国各种法律案、风俗习惯与现行法律之冲突、各种法律原则、改良司法制度、律师事业、收回法权问题。(10)《北京民国大学学则概要》《北京民国大学一览》,1924年,第1页。
虽然北京民国大学开设了外国法的课程,但除此以外,与教授中国现行法的学校并无二致,而罗马法、中国法制史、外国语等课程均被划入选修科目中。朝阳大学法律系的开课情况也是如此,除增加了“英德日文法学原著、英文、德文或法文”一课外,其教学内容中其他外国法元素也较少出现(11)《朝阳大学学则》,1929年,第3页。。
三、法商结合的差别
此外,以教授法科为主的大学,其开设的商科和经济科的科目一半是法律课程。如从上海法政大学特别开设的商科和经济科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对商业经济学课程的渗透:
(商科课程)国文4、英文8、俄文法文或德文8、国际商约3、宪法4、民法概论8、商行为4、商法总则2、海商法2、票据法4、保险法2、公司法4、国际私法4、政治大纲4、统计学4、商业政策8、货币论3、银行学3、商业簿记3、商业史4、会计学4、商业经济4、国际贸易3、国际汇兑3、商品学4、商业组织3、运输学2、银行簿记4、商用统计3、商业实习6。
(经济科课程)国文4、英文8、法文俄文或德文8、宪法4、民法概论8、商法总则2、票据法4、保险法2、公司法4、破产法3、国际商约3、国际私法4、财政学8、经济学8、社会学6、统计学4、农业政策2、工业政策6、商业政策4、交通政策4、殖民政策4、社会政策4、经济史3、货币论3、银行学3、商业簿记3、会计学4、国际汇兑2、关税论3、海商法2、商行为3、经济学史6。(12)《上海法政大学章程》,1926年。
再如上海法科大学,其经济系的必修科目不仅设有财政学、会计学、银行学、保险学等专业课程,还设有宪法、民刑法、商法、公司律等法律课程,而且商科和经济科的教员也多是法科教授[19]121。
虽然同一时期北京的法校,如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也分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但关于经济学类课程,仅仅在选修课程中开设了几门法律课程。北京平民大学相对好一些,开设了宪法、民法总则、商法总则等课程,但相较于上海法校的开课数量,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经济学、经济学史、经济地理、财政学、财政史、货币论、银行论、经济政策、社会学、社会问题、税关论、统计学、会计学、簿记学、宪法、民法总则、商法总则、第一外国文(英文)、第二外国文。(13)《平民大学概览》,1929年,第7页。
当然,上海法校法科与商科、经济科的密切度远超于此,例如即便是院校法律系的必修课程也开设了商科和经济类的课程。如群治大学法科就开设了公司条例、货币论、银行学、簿记学等商业类科目。震旦大学法科也设有经济学说史、统计学、会计学、财政学等必修科目(14)《震旦大学1920-1934年法律系毕业生成绩册》,上海市档案馆藏Q244-1-909(1)。。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设的法学院校中仍可找到这些痕迹。如1930年的华国大学法学院仍开设会计和保险学的选修课程(15)《华国大学章程》,1930年。。然而,这一特征在北京法律院校中并未出现,以朝阳大学为例,1929年该校的课程表中并无会计、薄记学等类似课程出现:
宪法、行政法、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民法总则、债权总论、债权各论、民法亲属编、民法继承编、商人通例、公司条例、商行为、票据法、海船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强制执行法、平时国际法、战时国际法、国际私法、罗马法、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法理学、刑事政策、监狱学、财政学、政治学、法医学、英德文法学原书、英文、德文或法文。(16)《朝阳大学概览》,1929年,第34-35页。
北京平民大学和民国大学也是如此,前者并未开设任何有关商业经济类的科目,后者则将财政学总论和经济学两课列入了选修科目中。北京中国大学法律学系的课程,除了公司条例与商科略微相关外,并未设置任何商业经济类课程。
四、结论
近代上海与北京形成了“海派”和“京派”两种不同的法学教育风格,部分原因在于两地受到各自不同教育环境的影响。如上海的法学院校引进师资并没有特别倾向于某一国家的留学归来学生,这反而使上海法校师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在北京的法律院校中,留日归来学生就颇受青睐,这显然与北京初期法律教育环境中浓厚的日本色彩有关。不过,促成两地法学教育风格迥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得益于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北洋时期教育部实可谓“令不出部门”,其所颁布的条例形同具文,有相当一批学校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20]86。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公布,虽然缓解了国家办学能力的不足,但也让政府失去了对学校教育权的控制[21]89。该案确立的“壬戌学制”,不仅强化了1917年颁布的《修正大学令》中规定的设单科也能称为大学,而且废除了大学必须设有预科的规定,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办学门槛[22]。于此背景下,一夜之间私立学校充斥上海,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而法律院校的创立也掺杂其中。1924年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又一次肯定单科可设大学的规定[23],私立大学因此逐渐兴盛,如1926年建立的上海法科大学(17)《上海法学院一览》,1933年,第1页。,以及原仅是民间补习性质的法律讲习所[24],通过添增学科升格为大学的上海法政大学[25]。因此,办学标准的放宽和制度设计的不当,赋予了法学院校极大的办学自主权,这是造成京沪两地法学教育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26]137-138。
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上海法学院校科系设置的特征,受到该地区特殊法治环境因素的影响。1927年之前,上海租界内不仅有会审公廨,还有各签约国领事法庭的存在,由此出现了多种法律体系汇聚一地的局面。上海的外籍律师阿乐满就曾谈道:“既会中英双语,且掌握英美法和中国法的法律人,在现实中极其罕见,也是当时上海各大律所梦寐以求的人才。”所以,英美法、大陆法及比较法教育成为当时上海各所法学院校的授课重点。此外,上海繁荣的经济导致该地区法律纠纷多涉经济问题。例如对于会计学加入法律课程这一事宜,孙晓楼就曾提到上海司法实践中对会计知识的需求:“我们看法院里的民事案件,十分之六七是为着债务金钱的纠葛……我们读了法律,无论做法官做律师做实业机关的顾问,要使它有一个公平的解决,常常牵涉到帐目计算上的许多问题,所以读法律的不可不有会计的常识。”[27]34为保证法学院校学生毕业后能适应社会不同岗位的需要,校方有意增加经济类的课程。恰如震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彭廉石(Bonnichon)所说:“法律系养成律师人才,其毕业生可参与各种文官考试,并可进保险公司,实业界,新闻界等处服务。”[28]
法学教育界常称近代上海多产律师,北京多造法官,综上可见,这一传言的背后体现了两地近代法学教育的差异。以史为鉴,放眼当下,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应给予法学教育更多的自主权,在招生考试、课程设置等方面,不应千校一面,而要鼓励特色办学,“百花齐放”才能迎来中国法学教育的春天[29]128-131。回溯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国情……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30]因此,对当下法学教育的建设,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自信。同时,认真汲取既往的办学经验,不仅会对今天法学教育的建设提供有益镜鉴,而且能再次打造法学教育多样化形态,推动中国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