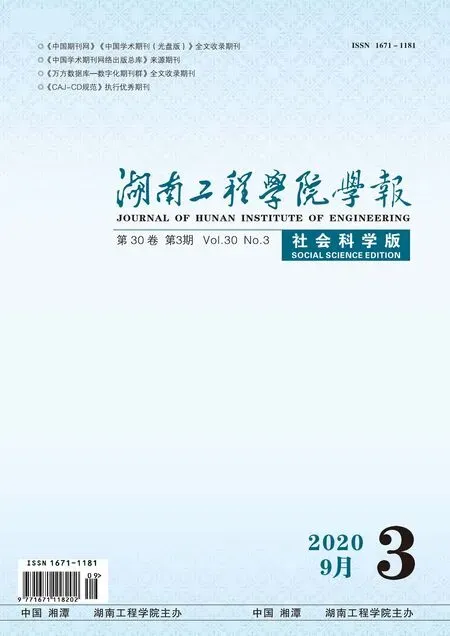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研究
余海涛
(闽南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泉州362332)
古代中国历代开国帝王早年的出生和成长都有不同的异象谶应,并随之被演绎成一整套的帝王受命神话,从而加强新王朝革故鼎新的合法性,隋文帝亦不例外。隋文帝出生不久便被女尼智仙带走抚养,直到十三岁时离开寺院,史书对其在这段时期的书写极具神话色彩。为方便研究,我们暂且称之为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目前学术界关于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日本学者塚本善隆的《隋仏教史序説——隋文帝誕生説话の仏教化と宣布》[1]137-143和藤善真澄的《北齊系官僚の一動向——隋文帝の誕生說話をてがかりに》[2]243-274是两篇对隋文帝诞生传说展开研究的文章。陈颖聪《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说与衍绎》则从文学角度探讨杨坚出生故事的演变。[3]156-161鉴于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故本文从早年政治神话的书写与流变、早年政治神话与政治天命的建构、早年政治神话中的政治预言考释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早年政治神话的书写与流变
隋文帝本为北周外戚,于大定元年废黜周静帝而受禅自立,建立隋朝,改元开皇。作为开国帝王,隋文帝早年出生成长事迹不可避免地被政治神话,所谓:“夫帝王之生,必有休应,岂非天命所属,历数斯在,警生灵之耳目,为天飞之兆朕者乎。”[4]16传统文献资料关于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记载不仅相当丰富,而且其书写与流变亦各有特点。
(一)官方文献资料的书写与流变
官方文献资料代表着官方认可的态度,其中暗含特定的政治考量,因此它的书写极为慎重,其流变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要求。对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书写肯定是在隋文帝登基之后,隋代内史令李德林、内史侍郎薛道衡和著作郎王劭等人均有相关著述留世,由于他们均为隋代官员,所以其著作可视为隋朝官方认可的文献资料。李德林《天命论》曰:“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5]1203-1204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颂》曰:“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图箓,彰乎仪表。”[5]1409不同于李德林、薛道衡以传统儒家帝王受命话语的书写,著作郎王劭则在《隋祖起居注》中加入大量佛教因素。这篇《隋祖起居注》被唐代高僧道宣收录于《集古今佛道论衡》而得以流传,史载:“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寺。于时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色充庭,状如楼阙,色然人衣,内外惊禁。帝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堕井,乃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佑,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以儿委尼,不敢召问。后皇妣来抱,忽化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6]379起居注是古代记载帝王的实录,《日知录》曰:“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7]1006故而,王劭的《隋祖起居注》影响深远,成为后世书写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基本史料来源。事实上,这些情况的出现都取决于隋文帝的态度,所谓:“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8]5589
唐初修撰前朝史书,其中记载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内容很多。《隋书·高祖帝纪上》曰:“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5]1这是记载在隋文帝“帝纪”上的内容,当属最权威的官方资料。《隋书》之中亦有其它零星记载,上述李德林《天命论》、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颂》均被收录。此外,正史《北史》亦有记载,但其内容与《隋书》所载基本雷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两书均是同一时期修撰,史料来源相同。《隋书》与《北史》所载隋文帝早年事迹的史料来源,我们认为其有依据。两书修撰者魏徵和李延寿都是史界公认的严谨学者,自不会无中生有,凭空杜撰。况且,史书的修撰者都经历过隋朝。再者,大量隋代原始文献的遗存以及隋朝遗老的访谈,均可补充史书之阙。据《旧唐书》记载:“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覩。”[9]5096《隋书》《北史》均为正史,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但所载隋文帝早年事迹内容则多半是虚构,目的就是神化隋文帝。这种官修史书的叙事方式由来已久,史载:“盖帝者之兴,未有不休徵先兆,以表眷命之符者也。”[4]205
唐代以后,对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书写具有官方性质的文献莫过于宋代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所载内容出自《隋书·高祖帝纪》。《文苑英华》则引自李德林《天命论》曰:“皇帝载诞之始,赤光蒲室,流于户外,上属苍旻。其后三日,紫气充庭,四邻望之,如郁楼观,人物在内,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怀,忽覩为龙,懼而失抱,帝惊动数旬,方始痊复。又尝寝于其室,家人开户正见一龙,太祖神异也。世塗不测,竅比丘尼智仙保养。智仙禅观灵雅,有玄谶云:‘此子方为普天慈父护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须忧也。’帝体貎多竒,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钟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锡。王生文加点乃为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间,雅望之如神。”[10]3931很显然,这里引用的内容与《隋书·李德林传》所载差异较大,带有明显的文学演绎特征。同时期的《册府元龟》对其记载则相当简略,曰:“隋高祖以西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4]18又曰:“隋高祖为人龙颔,额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4]473可见,这种书写实质上是对《隋书·高祖帝纪》的刻意分类节选。
由上可知,宋代官方文献资料关于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记载基本转引自唐代史书,它们之间不同的体例安排、内容节选、措辞增删等均带有特定时代的要求。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唐、宋两代官方文献主要以传统儒家政治神学的叙述方式,以受命帝王的标准来建构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
(二)佛教文献资料的书写与流变
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中的佛教因素表明佛教与之关系极其密切,因此,佛教文献资料对此进行了大量记载和宣传。隋文帝时期,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就公开宣扬佛教与隋文帝的关系,曰:“我皇帝受命四天,护持三宝,承符五运,宅此九州。故诞育之初,神光耀室,君临以后,灵应兢臻。”[11]101此后,唐代僧人对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进行了详细记载。僧法琳《辩正论》曰:“高祖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生于同州般若尼寺神尼之房。于时正气冥符,赤光满室,浮辉溢户,紫焰烛天。其内睹者,莫不惊异,互相禁约,不许外闻。比至三日,紫气冲突。其人物在内,皆成紫色。四邻望之,气如回盖,或似高楼。复有景风甘露,合颖连枝,池发异花,林生奇果,毒虫隐伏,吉鸟翔鸣。仍为神尼护持保养。”[6]508前述王劭《隋祖起居注》被高僧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收录。道宣在其另一部著作《续高僧传》中亦有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记载,但内容与《集古今佛道论衡》所载基本雷同,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指出了智仙尼的具体籍贯,即“河东蒲阪刘氏女也”。[12]667另据高僧道世《法苑珠林》记载:“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迁来。其后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13]1275如果说,法琳的记载是通过描绘一个美好的佛国图景来烘托隋文帝诞生的话,那么,道宣、道世的记载则明显具有护法护教的性质,即把隋文帝塑造成一个中兴佛教的护法帝王。由于《集古今佛道论衡》所载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引自隋文帝起居注,其权威性颇高,所以对唐代以后佛教文献资料的影响极大。宋代佛教文献资料主要有《石门文字禅》《隆兴编年通论》《佛祖统纪》,元代佛教文献资料有《佛祖历代通载》。这些著作所载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内容均在《集古今佛道论衡》范围之内。不过,《隆兴编年通论》《佛祖统纪》和《佛祖历代通载》三书都认为“及帝稍长,仙密告之曰:‘汝后大贵,当自东方来,佛法时灭赖汝而兴。’”[11]359而不是其它史料记载的“及年七岁”。此外,唐代佛教文献书写智仙尼的出现用“及帝诞日,无因而至”来表达,以强调其神秘性;而《隆兴编年通论》则曰:“居般若寺,会文帝生于寺”[14]510,这样书写应该更符合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隋贺德仁撰《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曰:“高祖炳灵略曜,载诞冯翊,渚浮虹气,室照神光。忽有天女飘然来降,现尼形象,自号智仙,容仪殊妙,音词清雅,擎跽沐浴,摩顶赞叹,谓元明太后曰:‘此子天挺睿哲,相貌端严,方当平一区寓,光隆佛教,宜简择保姆之才,鞠养于清净之室。’言毕不见,莫知所之。”[15]172可见,此佛教碑刻所载内容与佛教史书记载差距甚大,完全把女尼智仙神化,整个过程充满佛教“浴佛”的影子。
总而言之,佛教文献书写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中心人物不是隋文帝而是女尼智仙,它所论述的重点是佛的神力,其目的就是表明佛教必然灭而复兴,具有护教弘法的意图。
二 早年政治神话与政治天命的建构
《廿二史札记》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16]332不过,隋文帝虽然得天下容易,但是要想得到天下臣民的政治认同却并非易事,所谓“杨坚为人臣而篡取其君之位,其本不正”[17]115。可见政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是隋文帝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恰好可以从儒家和佛教两个方面完成政治天命的建构。
(一)早年政治神话的儒家式解读
前面我们提到对于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记载,官方文献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将其纳入传统开国帝王神话的叙事框架之中。传统儒家政治神学在论证开国帝王的政治天命时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描述其容貌异相。《册府元龟》曰:“域中四大,王居其一,《洪范》五事,貌为其首。是知清明在躬,而志气如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自古继天而王,出震应期,莫不体备纯元,器含异禀,实有圣德,焕乎英表。乘天地之正,故其仪可象;参日月之明,故其威可畏。”[4]472《隋书》对隋文帝容貌描写为“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5]1,这是一种典型的帝王型书写,即所谓“龙犀日角,帝王之表”[18]704。隋文帝入仕后,这种相貌被认为是帝王之相,史载“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8]5344,并因此而备受北周君臣猜忌。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帝(陈后主)闻隋主状貌异人,使彦画像而归。帝见,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屏之。”[8]5467从中可以判断,隋文帝相貌确实不同一般。或许正因为如此,北周武帝才发出感叹:“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5]2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出生有“王”字在手,这是明确指出他当有天下。但是,此后这个故事被演绎成“梁武帝有文在右手曰‘武’,隋文帝有文在左手曰‘王’”。这里坐实“王”字在左手,不知何据。然唐人小说《独异志》曾提到左手,曰:“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19]2193史载隋文帝出生时“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色充庭,状如楼阙”,这种自然异象的出现竟成为隋朝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依据。据《册府元龟》记载:“隋高祖受禅,召崔仲方与高颎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后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又圣躬载诞之初,有赤光之瑞,车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劝帝除六官,请依汉魏之旧。帝皆从之。”[4]43至于杨坚小字那罗延的“延”字亦被儒家谶纬神学收编,成为隋文帝受命的证据。史载隋开皇初,“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5]160王劭对此解释道:“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5]1602-1603从中可见,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儒家谶纬内容对塑造他的受命帝王形象极其重要。
(二)早年政治神话的佛教式解读
实际上,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叙事框架虽是儒家话语,但其内容更多的是佛教因素,这在历代帝王受命神话中绝无仅有。因此,对早年政治神话中的佛教因素进行解读,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与隋文帝政治天命建构之间的关系。
1.佛教佛化隋文帝。佛法东传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但征服了中国的上层思想界,也逐渐主宰了中国的民间文化”[20]402。不过,佛教也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现实,于是在南北朝时期积极攀附国家政权,形成“将天子视为地上权威与宗教权威兼有者”[21]290的政教结合的统治模式,在北朝形成“皇帝如来”理念,在南朝形成“皇帝菩萨”理念。虽然佛教认可世俗统治者帝王佛、帝王菩萨的称谓,但是“并未发展出一套神圣化的叙事、传说、传记来神圣化皇帝”[22]361,这表明佛教与帝王之间尚未完全契合。隋文帝是第一个被佛化的帝王,他的早年政治神话就是典型的佛化神话,前述官方文献与佛教文献记载相当详细,其中尤以“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一句最为典型。我们知道中古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以佛教神祗为名字,[9]316-317如唐太子李建成小字毗沙门。智仙尼给杨坚起小字那罗延亦是当时社会风气使然,后人往往认为这是为了保佑小杨坚健康有力量而采用的一个吉祥名字,如《一切经音义》曰:“那罗延。梵语,欲界中天名也,一名毗纽天。欲求多力者,承事供养,若精诚祈祷,多获神力也。”[23]340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实际上,那罗延是佛教的护法神,它与迦毗罗被明确为一对护法神,《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曰:“我遣摩醯那罗延,金刚罗陀迦毗罗,常当拥护受持者。”[24]108北魏洛阳平等寺“韩永义等造像碑”碑身下部就刻有“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另据李德林《天命论》记载:“有玄谶云:‘此子方为普天慈父护持正法。’”[10]3931这也说明隋文帝被预言为佛教护法神。因此,那罗延一词具有佛教政治神学意味。智仙尼以那罗延命杨坚小字,其实包含杨坚中兴佛法的深层意图,甚至把他塑造成转轮王。《法苑珠林》曰:“佛告舍利弗:菩萨有四法终不退转无上菩提。何等为四?一者,若见塔庙毁坏,当加修治,若块若泥,乃至一塼。二者,若于四衢道中多人观处,起塔造像,为作念佛善福之缘。塔中画作,若转法轮及出家相,乃至双树入涅槃相。三者,若见有比丘僧二部诤讼,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见佛法欲坏,能读诵说乃至一偈,令法不绝。为护法故,敬养法师,专心护法,不惜身命。菩萨若成是四法者,世世当作转轮圣王,得大身力如那罗延。”[13]1050更甚者,智仙尼极有可能以佛陀来喻隋文帝,所谓“第四观生处者。何等母人能怀那罗延力菩萨,亦能自护净戒。如是观竟,唯中国迦毗罗净饭王后能怀菩萨”[13]293。我们从隋文帝登基后大力中兴佛教的史实来看,佛教对他的佛化相当符合事实,史称:“兴复三宝,为法轮王。”[25]414不仅如此,佛化隋文帝早年事迹又被延伸演绎成月光童子转世故事。据《佛说德护长者经》记载:“又此童子。我涅槃后,于未来世,护持佛法,供养如来,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赞叹佛法。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时大行王,以大信心大威德力供养我钵。”[26]849此后,佛教在此基础上继续佛化隋文帝。据《历代三宝纪》记载:“缘此佛以正法付(咐)嘱国王,是知教兴寄在帝主。伏惟陛下应运秉图,受如来记,绍轮王业,统阎浮提。”[11]120总之,我们对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分析发现:隋文帝不同于其他开国帝王就在于,他既是儒家意义上的真龙天子,又是佛教意义上的佛祖圣子,具有世俗与宗教的双重合法性。美国学者芮沃寿曾指出,中古时期的帝王“非常依赖外来的宗教增加他们权力的可信度和威严”[27]53。佛教能够主动佛化隋文帝,并为之编造一套佛教的神圣性叙事故事,这对他政治天命的建构尤为关键。
2.隋文帝利用早年政治神话中的佛教因素。如果说佛化隋文帝是佛教对皇权主动献媚的话,那么隋文帝利用早年政治神话中的佛教内容,则是他主动利用佛教来增加其政治天命的合法性。隋文帝即位后要想利用佛教为政权合法性寻找依据就必须坐实自己的早年政治神话。智仙尼是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核心人物,隋文帝称帝后“尊曰神尼,为起金塔”,不断提及她以表明其预言的灵验。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及登位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以为口实。又云:‘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乃命史官为尼作传。”[6]379不仅为智仙尼作传,隋文帝还把她的图像与佛舍利广泛宣传于全国各地,以加强民众对她的认知。史载:“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13]1275另据《续高僧传》记载:“仁寿元年,帝及后宫同感舍利并放光明,砧磓试之,宛然无损。遂散于州郡,前后建塔百有余所,随有塔下皆图神尼,多有灵相。”[12]667可见,智仙尼不但生前对隋文帝准确预言,就是身后仍能大显神异。除此之外,隋文帝还通过把智仙尼图像与自己等身像放在一起,从而使佛教与政权紧密结合起来。据《金石续编》记载:“乃召匠人铸等身像,并图仙尼置于帝侧。是用绍隆三宝,颁诸四方,欲令率土之上,皆瞻日角,普天之下,咸识龙颜。”[28]3058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能够表明智仙尼的灵验和佛教的伟大,增强人们对佛教信仰的认同,但其根本目的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隋文帝的政治认同。隋文帝称帝后,立即把出生地(般若寺)和“龙潜”之地的寺院均改名为大兴国寺,据《续高僧传》记载:“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因改般若为其一焉。”[12]667“大兴国”一词明显暗含深层政治意图,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寺系统,与唐代武则天大云寺系统、唐玄宗开元寺系统的功能一样,都是利用佛教来维护政治统治。当然,作为早年政治神话中最著名的预言“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隋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践行。史书对隋文帝即位后复兴佛教多有记载。《隋书》曰:“开皇元年,高祖普昭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兢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5]1099《法苑珠林》曰:“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13]2893-2894对此,《长安志》一针见血地指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29]163隋文帝不仅在事实上中兴佛教,而且还不断重申自己对佛教的偏好以示官方宣传。据《广弘明集》记载:“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6]213《续高僧传》亦载:“朕祗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象法。”[12]611这种自我表现实际上有更深层的内涵,因为“一个表明自己佛教信仰的统治者,自然会获得宗教对其政权的支持并吸引有佛教信仰民众的拥护”[30]123。隋文帝大肆利用早年政治神话中的佛教因素,当然能够赢取民众支持,并借此为整合分治几百年的南北差异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文化纽带,从而达到维护王朝统治的目的。
三 早年政治神话中的政治预言考释
在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中,智仙尼“遂令晚得天下”和“儿大当贵从东国来”两个政治预言直接关系隋文帝受命称帝的问题。现对此进行考释。
(一)“遂令晚得天下”考释
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中有“遂令晚得天下”这个政治预言。此话颇为费解,按道理说,隋文帝受命既然是天命注定,又何来晚得天下之说。很显然,其背后可能深藏政治隐情。史书在记载这件事时说道:“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5]1故事的情节很简单。那么,智仙尼为何由此断定隋文帝会晚得天下呢?实际上,隋文帝由人臣到人主的过程就是由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的过程。因此,小杨坚变成龙形意味着它具有成“龙”的资质,而其母把他摔掉在地,也就是延缓了他成“龙”的过程。这当然是一种政治神学,可它却是对历史真实的比附。隋文帝能够成为帝王的关键一步就是他拥有得以辅政的权力,所谓:“坚承袭家荫,无赫赫勋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31]4也就是说,隋文帝在辅政时期已经具备成为帝王的条件,故可以“化而为龙”。但是,隋文帝由辅政丞相而迈向帝王宝座的过程中,由于曾被其母“惊惶堕地”,故而延迟了受禅称帝的时间。隋文帝欲要受禅称帝自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那么这又与其母“惊惶堕地”有何关联呢?很显然,隋文帝在神话中被自己母亲摔了一下,那就预示着现实中他受禅称帝必将来自亲人的“政治不支持”。隋文帝在称帝之前,其父母已经过世,那么“政治不支持”的人肯定是其妻儿或者兄弟姐妹。事实确实如此,杨坚在辅政之时所流露的觊觎大宝之心,立刻遭到自己亲人的反对。首先是母弟滕穆王杨瓒。据《隋书》记载:“未几,帝崩,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令废太子勇召之,欲有计议。瓒素与高祖不协,闻召不从,曰:‘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高祖作相,迁大将军。寻拜大宗伯,典修礼律。进位上柱国、邵国公。瓒见高祖执政,群情未一,恐为家祸,阴有图高祖之计,高祖每优容之。及受禅,立为滕王。”[5]1221-1222其次是长女北周静帝杨太后。《北史》曰:“初,宣帝不豫,诏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矫诏以隋文帝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招,心甚悦。后知隋文帝有异图,意颇不平。及行禅代,愤惋愈甚。隋文帝内甚愧之。开皇初,封后为乐平公主。后又议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32]529-530有意思的是,杨瓒妃宇文氏亦与隋文帝独孤皇后不合,史载:“瓒妃宇文氏,先时与独孤皇后不平,及郁郁不得志,阴有诅咒。上命瓒出之。”[5]1222考虑到宇文氏乃北周顺阳公主的政治身份,我们就很清楚两个女人斗争背后的原因。
按照常理,隋文帝受禅称帝,其亲属应该积极支持,而事实却是相反。所以,在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中增加堕地一幕,其实就是为了解释隋文帝亲人“政治不支持”的尴尬。
(二)“儿当大贵从东国来”考释
智仙尼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即指“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隋文帝受周禅而建隋,应该说是自关中而为天子,怎么说成是自山东入为天子?实际上,“儿当大贵从东国来”这个政治预言与杨隋氏族问题、周隋之际山东政治势力以及北朝佛教有关系。
1.“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与杨隋氏族问题。中古社会特别重视门第,新王朝统治者为加强统治的合法性无不自抬门第,攀附郡望。对于隋文帝的家世渊源,《隋书》曰:“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5]1不过,这个说法当是隋文帝伪造谍谱,冒充士族的官方认定。陈寅恪先生首先对此推测指出:“从文帝母系来看,疑杨家本系山东杨氏。”[33]289此后,王永兴先生《杨隋氏族问题述要》、袁刚《杨隋出自山东寒庶》等文章都对其进行详细考证,认定隋文帝家世出自山东无疑。由此,我们认定佛教徒智仙尼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实际上是隐晦地说出隋文帝乃山东杨氏。联想到唐初僧法琳的“琳闻,拓拔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12]210,以证明李唐之李非陇西之李一样,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智仙尼为什么能够透露出杨隋之杨为山东杨氏?这是因为当时的杨忠肯定不会知道自己儿子能够称帝建隋,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为自己以及后人攀附郡望,以回避自己山东杨氏的身份。智仙尼与隋文帝父亲杨忠为同时代人,抚养杨坚十余年,且“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那么她与杨忠的交情肯定非常深,因此多少都会了解到杨氏的家世信息。
2.“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与周隋之际山东政治势力。关中和山东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地理文化单元曾长期存在,特别是经过北朝的统治,直到唐初亦是如此,《旧唐书》曰:“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9]2703至于史学界用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两个概念来分析北朝、隋唐历史,更是人所共知。智仙尼“儿当大贵从东国来”的政治预言深刻地揭示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山东政治势力是周隋易代的关键。这从支持隋文帝“受禅”的重要人员名单中可见一斑。隋文帝得以受禅,关键在于依遗诏辅政,而推动这一事件的便是山东博陵望都人刘昉和山东荥阳人郑译。《隋书·高祖帝纪》曰:“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5]3以至于时人称之“刘昉牵前,郑译推后”[5]1132。后世亦认为:“高祖肇基王业,昉、译实启其谋,当轴执钧,物无异论。”[5]1144当然,隋文帝得以辅政只是他开始篡夺的第一步,紧接着就必须掌握北周实权,而山东博陵安平人李德林为其积极出谋划策。史载:“郑译、刘昉议,欲授高祖冢宰,郑译自摄大司马,刘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5]1198-1199由此,隋文帝掌握北周军政大权。面对杨坚的司马昭之心,尉迟迥等军事反对势力开始反扑,而帮助他出谋划策、镇压叛乱的重要人物则是山东渤海蓚人高熲。《隋书·高熲传》记载:“高祖得政,素知熲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国公杨惠谕意,熲承旨欣然曰:‘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辞灭族。’”[5]1179另据《隋书·李询传》记载:“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遣韦孝宽击之,以询为元帅长史,委以心膂。军至永桥,诸将不一,询密启高祖,请重臣监护。高祖遂令高熲监军。”[5]1122可见,高熲已是隋文帝股肱之臣,在平定外部军事叛乱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隋文帝亦开始清除内部北周宗室的反对力量,其中山东地区河南洛阳人元胄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5]1177隋文帝在清除内外反对力量之后,开始走上受禅之路,此时山东人士又发挥积极劝进作用。《隋书·崔仲方传》曰:“又见众望有归,阴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5]1448《隋书·卢贲传》曰:“周历已尽,天人之望实归明公,愿早应天顺民。”[5]1142上述山东地区人士均在隋文帝受禅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周隋易代的过程完全由山东人士所主导,无怪乎隋文帝称帝后感慨道:“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5]1143另据《隋书·高祖帝纪》记载:“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湝于冀州,除定州总管。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5]2亦可见山东政治势力对杨坚相当支持。岑仲勉先生指出:“自其受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无有如杨坚者。”[31]4-5其实,隋文帝得天下之易,关键在于得到山东政治势力的鼎立支持。
3.“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与北朝佛教。智仙尼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的政治预言与北朝佛教之间有密切关系。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北齐时期,《续高僧传》曰:“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12]501但是北周兼并北齐之后在其地推行灭佛政策,从而使佛教势力受到重创,佛教对来自关中政权的灭佛政策极为不满。所以,隋文帝自山东入为天子不仅是对史实的深刻揭示,更是对关中北周政权的一种反动,表明灭佛者必遭报应。《集古今佛道论衡》曰:“周祖窃忌黑衣当王,便摧灭佛法,莫识隋祖元养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识,事过方委知圣诈狂,自古皆尔。”[6]379很显然,“儿当大贵从东国来”这句政治预言具有护法护教性质。不仅仅如此,这句预言还与佛道之争有关:山东地区北齐政权重佛灭道,关中北周政权重道灭佛。北齐统治者一直对道教没有好感,史载:“(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5]1094后来更是进一步消灭道教,据《资治通鉴》记载:“齐主还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8]5131较之北齐,北周恰恰相反:“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5]1094《集古今佛道论衡》亦曰:“周武初信于佛,后以谶云黑衣当王,遂重于道法躬受符录。玄冠黄褐内常服御,心忌释门志欲诛殄。”[6]372因此,从佛教角度来看,把隋文帝书写为自重佛的山东地区入为天子,当然是论证他“天佛所佑”,也是表明佛教对道教的胜利。事实上,唐初诸位高僧大肆渲染这个预言并详细书写智仙尼与隋文帝的关系,其实也是对唐初帝王重道抑佛政策的一种反讽。
四 结 语
政治神话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世俗统治者建立神圣的合法性认同,以便加强其政治统治,而它要想使人们相信就必须存在于一个原型故事之中,同时运用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知识手段加以解释,并把这个所谓的原型故事变成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从而使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就是一个由历史、谶纬、佛教等众多内容组成的复合体。从对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内容的记载来看,官方文献资料与佛教文献资料差异很大。正史书写不言女尼姓名和佛教复兴的预言,而佛教文献却把两者记述的非常清晰,甚至称女尼智仙为神尼,这种处理方式可谓大有深意。所谓“有功于国,史录其勋;有政于民,碑传其德”[11]120,女尼智仙抚养隋文帝并预言他贵当天子,因此有大功于国家,不可不写。但正史不用“神尼智仙”而以“尼”泛称来论,则是消解佛教对政治的影响,主要突出隋文帝出生的异象,以此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与帝王的神圣性;而佛教书写则架空隋文帝,变成以神尼智仙为中心来论证佛教复兴。当然,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内容多为虚构,但这是传统惯例,“帝王创业,史臣记述,例有符瑞附会之语,杨隋之兴,何得独异”[34]158。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儒家内容表明隋文帝承天受命得到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支持;佛教内容则表明隋文帝承天受命同样得到新增的佛教合法性支持,特别是佛教佛化隋文帝更是明确承认他具有帝王和佛王的双重合法性。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当然是为新兴的隋王朝寻找合法性支持,但是它本身还隐藏很多历史问题,智仙尼的两个政治预言就透露出重要的政治史实。“遂令晚得天下”这个预言委婉地指出隋文帝受禅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其母弟和女儿均是“政治不支持”的态度。不过,虽然史书都提到“遂令晚得天下”这个预言,但各方目的未必一致:唐代官修史书很可能指责隋文帝得天下不正;而佛教文献则可能惋叹因隋文帝晚得天下而延迟佛教的复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这个预言更是包含几个重要史实。隋文帝本是山东杨氏,而山东地区又是佛教发展昌盛的地方,因此崇信佛教的他在受禅过程中得到了山东政治势力的鼎立支持,同时佛教史书也为他称帝大造受命政治预言。总而言之,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不仅关乎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涉及中古时期相关历史史实,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