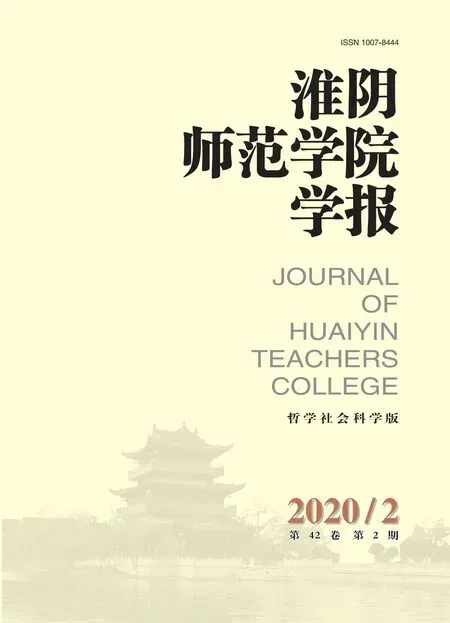学科体系创新与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
——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学术贡献
赵永春, 李西亚
(1.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2.吉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近些年来,学者们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2018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陈其泰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就是这些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1)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共五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第一卷《导论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奠基——先秦时期》、第二卷《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两汉时期》,为陈其泰撰著;第三卷《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为张峰撰著;第四卷《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兴盛——宋元明清时期》,为屈宁撰著;第五卷《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格局——近现代时期 中外比较背景下的考察》,为刘永祥撰著。
一、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属性
“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学术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1]要构建一个新的学科,首先要明确这一学科的学科属性。《中国历史编纂学史》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是以中国历史编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史学史的分支。
书中指出,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的《谈史学遗产》这篇论文中,最早提出研究、发掘“历史编纂学”遗产的任务,将“历史编纂学”视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期望它成为史学园地内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圃。1981年,白寿彝先生又撰写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文章,按照历史理论、史料学、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篇分别论述。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历史编纂学是史学史研究四大内容之一的学科构建的设想,但并没有最终完成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任务。陈其泰先生谨记白寿彝先生的嘱托和教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将研究和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开启了自己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旅。自2009年正式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史》课题组开始,又用了九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五卷本这一鸿篇巨帙,真正完成了白寿彝先生创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夙愿,树起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这面大旗,成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创立的标志,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其泰先生在白寿彝先生有关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论述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就是中国史学史的分支学科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可与历史理论发展史、历史文献学史相并列。而从这一分支学科角度看,除了全面研究、论述历史编纂学发展进程、主要成就及其理论问题之外,我们还要把跟它关系十分密切的历史叙事技巧(即白寿彝先生所讲四个部分中的‘历史文学’)也包括进来;同时,也要论述与历史编纂互有密切关系的历史理论和史料学的相关问题”[2]9。也就是说,历史编纂学科是史学史的分支学科。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认为,作为史学史分支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与史学史当然会有互相交叉、重叠之处,但既然是两个学科,按照不同的学科体系,所探讨和论述的内容则各有侧重,互有分工。如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以有珍贵内容、有编纂目的、有编纂技术的史书载体之出现”开始,即以《尚书》出现为“起点”,这与史学史或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事开始、或从“远古的传说”“英雄史诗”开始、或从古文“史”字释义开始有所不同。又如,史学史著作非常重视先秦诸子以及两汉、唐宋、明清时期史论的研究和论述,因为史论对于历史演进的特点和历史知识的运用,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历史编纂学科考察的重点则是具有一定体裁特点和编纂体例的史著,因此,对先秦诸子的史论以及两汉时期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代韩愈、柳宗元、赵匡、啖助的史论,宋代学者的义理与功利之辨,清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嘉道年间龚自珍、魏源的史论等等,则很少涉及和论述,因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是“以历史编纂思想、体裁体例成就及特点等为研究重点”,与史学史研究各有侧重而有所不同。再如,有关原书已佚之著作,以及宋代学者所著《困学纪闻》《容斋随笔》,清乾嘉考史之作《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虽是史学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但历史编纂学科则不作为研究重点,因为这些佚著今人难窥原貌,文献汇编以及考史著作,“因其内容性质较为特殊,难以从体裁特点、体例运用等项加以探究和评析”,所以略而不谈。至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为“其中论历代正史的编纂过程、体例特色等项内容,与历史编纂学直接相关,则是我们所要认真研讨的”[2]14-15。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作为史学史研究的分支学科,所研究内容虽然都属于史学史学科,但侧重历史编纂思想、史书编纂体裁体例、史书编纂技巧及其成就等方面的研究,对史学史研究通史无法深入探讨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体系、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研究范围以及资料的深入发掘等问题,均可以作专门的深入探讨。[2]8-15这就将史学史学科与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联系与区别说得明明白白了。
二、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研究内容与知识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要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对其构建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也作出了明确阐述。
书中指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研究内容,大体包括:“史家著史经历,史著主要内容、体裁体例的运用及其得失优绌;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不同史书体裁的产生和演变,不同体裁的关系;史官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官修史书和私人修撰二者的关系;历史编纂理论的成就;传统历史编纂学对东亚各国及世界的影响,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历史编纂学成就的吸收、借鉴等。”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任务,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1)对中国三千年历史编纂学的演进作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初步构建起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学科体系,深化和拓展中国史学史领域的研究;(2)创造性地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精华,发掘、阐释历代优秀史家的出色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揭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民族特色;(3)从历史编纂学这一独特视角,总结中华文明世代赓续、传承久远、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增添助力。”[2]3
书中不仅明确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学科的研究内容,还论证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研究重点,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研究重点应该包括“史著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史家著史精神;史著体裁选择和内容特色;史书体例运用;史学名著的史论成就;历史叙事技巧;史官制度的演变以及官修、私修的互动;史著成就的影响”,等等,并以古代史著和近代史著为例,探讨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重点。该书认为:“历史编纂学以时代条件和史家著史精神、体裁选择和史著内容特色、体例运用等项为基本构件,从这些方面作深入开掘、阐释,就能提出新课题,得到新创获。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时代条件的剧烈变动,史家的历史观点、著史的目的、史书记载的史实等都产生了极大变化,尽管如此,历史编纂学近现代部分却仍应以上述诸项为基本构件,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地关注进入鸦片战争以后史著的时代性,又要保持研究模式的前后贯通性。”[2]9-11这就明确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研究内容,构建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知识体系,明确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发展方向。
三、《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学科构建的学术贡献
陈其泰先生完成了白寿彝先生未竟事业,著成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五卷本)这部鸿篇巨帙,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历史编纂学虽然属于史学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但将其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在史学史研究框架下无法展开研究的有关中国历史编纂方面的各种问题,则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研究空间;在史学史研究框架下无法进行深入探讨的有关中国历史编纂各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一学科里充分地进行深入探讨。这就使中国历史编纂学科获得了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空间,成为史学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可以拓展对中国历史编纂学诸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式的探讨和论述。书中对以往有的人认为“史书的体裁、体例,似乎只关乎技术性问题”的模糊认识予以澄清,谓“史书的组织形式与其内容、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组织形式的运用,结构、体例的处理,不仅体现出作者的学识、才华,而且决定于其史识的高下”,并非简单的技术性问题。书中引用白寿彝先生对史书编纂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精辟论述:“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3]称“这是白先生根据几十年对中国史学演进的总结,和对当代史学发展的分析,以及本人长期治史的深刻体会而得出的认识,对于我们有十分宝贵的启发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对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和价值重新给予恰当的定位,谓:“历史编纂学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史识、史学、史才、史德达到何种水平的有效尺度。”认为:“史家再现历史的能力如何?其史著传播历史知识的效果如何?在这里都直接受到检验。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成为重要的新的学术增长点。”[2]4
光信号经光耦合器1分为两路光信号,其中一路在振动传感光纤中传输,另一路在参考光纤中传输,两路信号在耦合器2处合成一路光信号输出。当没有局部干扰时,耦合输出的光信号为稳定的干涉信号;存在局部干扰时,在振动臂传输的光信号受干扰发生相位延迟使得干涉光信号发生改变,进而得到干扰信息。
书中还指出: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深层意义还在于: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除了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制度的严密和文献价值的宝贵以外,还要大力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发掘出古代中国历史编纂学所蕴含的创造的力量、深刻的哲理和高度的智慧,由此进一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2]7。又说,对历史上的史学著作“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作深入的发掘、总结,就能更加充分地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所凝聚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从其体裁体例的选择、运用更加发现其和谐之美,从其历史叙事更加发现其生动之美,以此进一步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当今从事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研究应当树立的目标和应当具有的风采”[2]8。显而易见,中国历史编纂学科构建,确实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二)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著者不仅对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理论阐述,还亲自将其创建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付诸实践,对中国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末的历史编纂学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本。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依据史学名著所体现的历史视野和编纂思想、史书体裁的发展、体例的精当、史官设置和史官制度、历史编纂的理论成就五个方面的要素,将“三千年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划分为奠基期、确立期、发展期、兴盛期、嬗变期、近现代历史编纂的新进展六大演进阶段”[2]16-17。
该书在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划分为六大演进阶段的基础上,分别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编纂学史及其特点进行了创新性探讨和研究。该书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奠基时期,以《尚书》为起点,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优良传统。《春秋》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和私人修史的先河。《左传》《国语》两部名著,在七雄相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记叙历史范围更加扩大,叙事能力更加提高,体裁运用和编纂体例也臻于新境,为历史编纂巨著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加上西周以来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设置,以及出现了《战国策》《世本》等著作,便为中国历史编纂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2)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导论》,第18—20页,第187—294页。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确立时期。主要有四大特点:第一,司马迁《史记》所创造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互相配合、规模宏伟的纪传体通史的体裁成就,被后世史家视为著史的楷模;第二,班固《汉书》所创造的“断汉为史”的完整记载一个朝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历代“正史”纂修的“不祧之宗”;第三,东汉末年荀悦按编年体改编《汉书》以成《汉纪》一书,成功地创立了编年体断代史的新体制,开启了此后长期“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的新的发展趋势;第四,东汉一朝官修《东观汉纪》,开创了历代皇朝纂修当朝史的先河。纵观两汉时期的历史编纂,可以看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规模、格局、著史方法和成功标准均树立起来,纂修前代史和纂修当朝史的双重任务也从此明确,所有这些,都表现为传统历史编纂学已经确立,并影响到以后两千年的发展道路。”(3)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导论》,第21—25页;第二卷《两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时期。主要特点也有四个方面:一是修史成风,蔚为大观。二是史馆制度确立和大规模纂修前朝史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空前盛举。三是史学名著继出。不仅有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等名著,还有刘知几撰成对此前历史编纂成果进行理论总结的历史编纂理论名著《史通》、杜佑撰成典章制度通史《通典》,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四是史学体裁增加,史学范围扩大。在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之外,增加了不少史书体裁。除了上述史学理论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以外,还有史注、历史地理和地图、方志等史学体裁。(4)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导论》,第26—31页;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
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辽与北宋对峙、金与南宋对峙和元重新统一中国的不同阶段。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大量接受中原文化影响,原先处于后进状态的历史编纂事业得以迅速改观。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重视各朝实录与前朝史编纂,[4]主要特点表现在“史馆制度的发达和实录的大量纂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六部纪传体‘正史’编纂完成”、“《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编年体史书的兴盛”、“《通志·二十略》和《文献通考》等典制史的成就”、“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史书体裁增加和历史编纂范围的扩大”等六个方面。(5)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导论》,第32—40页;第四卷《宋元明清时期》,第3—310页。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总结与嬗变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四百余年历史编纂领域的总相,一方面是不少有识史家冀图摆脱明清鼎革文化嬗变的时代困境,寻找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又有其他史家希望保持传统格局并结合新的思考向前推进。两者结合起来,构成明清时期“嬗变”与“总结”相交织的独特内涵。其演进趋势和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明代的历史编纂呈现出从局部低落到多方探索的特点;二是清初历史编纂成果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价值;三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理论总结,提出史书编纂改革的方向;四是清朝中期以后,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史学家提出“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命题,中国历史编纂学开始由“考史”向“著史”方面转化。(6)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第40—52页;第四卷《宋元明清时期》,第317—675页。
近现代时期的历史编纂呈现出新的格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学术文化环境与中古时期已大不相同,“历史编纂的著述宗旨、史书内容和撰史范式都开始出现新的格局”。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魏源《海国图志》等书提出“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开创晚清典制体史书新局面;二是梁启超《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创辟“近代史学”新局面;三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与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相糅合,彰显历史编纂的中国气派;四是白寿彝提出“立体式”著史主张,并在具有新的综合体裁的《中国通史》中成功实践。(7)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第52—61页;第五卷《近现代时期 中外比较背景下的考察》,第3—390页。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运用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理论,对中国三千年历史编纂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内在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讨论,“彻底摆脱以往把历史编纂视为单纯技术性问题的看法,和孤立对待、只从表层着眼的路数”,“努力探索建立中国历史编纂学科的体系”。在其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科体系的基础之上,明确概括出,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编纂思想是史家恰当反映客观历史进程和成功运用体裁、体例的关键环节;前代史家对体裁的选择和应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智慧,并且生动地反映出中华文化重包容、重和谐、重革新的基因;史学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历史编纂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等等。(8)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一卷《导论·卷首识语》,第2—3页。将其创建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撰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科建设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本。
(三)对中国历史上的编纂学理论探讨具有前沿性
中国古代自历史编纂伊始,就有重视历史编纂理论探索的优良传统。《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在对中国历史上的编纂学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首次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系统阐释,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史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视著史事业为“名山事业”。第二,设置史官和史馆,将修前代史和国史作为朝政大事,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第三,史书体裁丰富多样,是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在历史编纂领域的体现。作者认为“史书体裁的选择,与史家的历史见识、学术视野、价值追求密切相关。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都是有识史家呕心沥血创造的结果,目的是拿出新的、容纳独特内涵的史书成果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第四,史家体例运用精当,独具匠心。第五,中国历史上史家著史的实录精神,体现了史家的信史追求。第六,中国历史编纂,不仅重视史书编纂的理论指导,还重视历史编纂发展演变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形成了历史编纂理论自觉的优良传统,创造了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历史编纂学理论。[2]63-141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将中国历史编纂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体现了中国历史编纂理论探讨的前沿性。
(四)论证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在世界历史编纂学史中的地位,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在《导论》和《中外比较背景下的考察》等部分,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在世界历史编纂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四库全书总目》将史书体裁区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梁启超《新史学》将史书体裁区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十种,其中正史再分为官书、别史两类,如此共细分为二十二类。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2]4
书中认为,中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不衰竭的创造力明证。该书还将中国与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进行对比,谓“古代希腊曾经有着著名的历史著述,但后来便没有了。古代埃及几经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所灭亡,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导致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连著名的《伊浦味陈辞》究竟是说明古王国末期还是中王国末期的情况,至今学者都弄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经典和传说,而几乎没有历史记载”。中国的记载则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且连续不断,日益丰富,得到外国学者的高度赞誉。“黑格尔将古代印度几乎没有记载与中国典籍的丰富相对比,感叹说:‘因为这个原因,最古老而又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反而要从亚历山大打开了印度门路之后希腊著作家笔下的文字里去找。’又说,‘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设施,都预备给历史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弗朗斯瓦·魁奈同样赞誉中国史书编纂的传统:‘关于历史学,这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德国著名教育家卡尔·伯克博士也对中国文明作了高度评价:‘中国人勤劳、聪明,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至今令人赞叹不已。我们德国人总说,当我们的祖先还穴居在树林里时,中国人民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专门设立一个子目‘中国历史编纂法简述’,称中国是‘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2]4-6这说明中国历史编纂学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该书主编陈其泰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总结说:“无论是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史学名著的大量产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史书体例的严密精当,史官制度的高度发达,有关史书编纂评论的多样见解”等诸多方面,“在世界各国中无疑都罕有其匹”,认为“与西方史学相比,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5]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对中国三千年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讨论,并与世界历史编纂学史进行了对比,认为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的学科,在世界编纂学史上罕有其匹。这就“构建起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话语体系”,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2]4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洱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