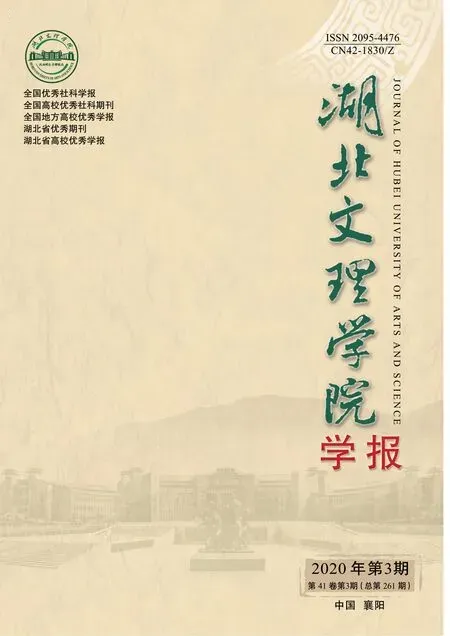汪曾祺当代小说中情爱书写的变迁
汪 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0)
作为个体的一种生理和精神体验,情爱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内容。也就是说,文学介入情爱的方式可能不只是关于爱情/性的简单叙述,还承载着作家对于特定时代人伦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的阐释,情爱由此被组织成一套“话语”,具备了特定的文化内涵。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人道主义的复归,爱情的位置重新得到确认,“归来”的汪曾祺以《受戒》这个“‘四十三年前的梦’的形式与现代文学中的性爱理想接上了榫”[1],情爱在他的小说中不单纯是书写对象,更是人性复归、文化复归的着力点。细究起来,汪曾祺创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情爱作为其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文学创作的始终,并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如果说80代初期他小说中诗情画意的爱情书写更多地继承了京派的遗风,表现出浓厚的抒情性,那么到8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以越轨的笔致大肆谈性言情,背离早期抒情的态度,更具有世俗意味和现实意义。
一、纯真恋情的赞美
(一)叙事策略:诗意书写
1944年,汪曾祺在《小学校的钟声》中写了19岁的“我”对一位女教师朦胧的好感,文本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不断渲染环境和细节,刻画“我”飘忽不定的心思,最后以“老詹的钟又敲起来”留下“情”的余韵,散发出浓厚的诗意。到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际的汪曾祺迥异于主流文坛将爱情作为“控诉”的写法,选择在抒情写意的氛围中表现男女情爱。一方面,他采用“回忆”视角,把目光投向“远景”,在一定的“心理距离”中完成对爱情的诗意言说,《受戒》源于儿时在小庵里见到的生活,“四十三前的一个梦”[2],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懵懂的恋情经过几十年反复沉淀,除净火气后只剩下纯粹的美感,《大淖记事》是童年的一点朦胧向往,“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3],巧云和十一子历经磨难的感情反而表现出内在情绪的欢乐,《晚饭花》和童年记忆有关,李小龙每天隔着晚饭花看王玉英隐约表露出少年单纯的情愫,可以说,“小说是回忆”的叙事立场不仅意味着将“记忆”作为素材,更重要的是,“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4],对于旧生活的“记忆”被老年汪曾祺经过自身经验进行了审美处理,展现在文本中的爱情多浸透着作者对生活的诗意感受,四十几年前的事用80年代的感情写出来,他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来静观既往的人事,惆怅寂寞的情绪反而被回忆的温暖所取代,而“爱情”在回忆的视角中始终停留在“过去”的美好之中,灰暗一面也被巧妙掩盖。其实细读文本,《大淖记事》《晚饭后的故事》多少已经透露出痛苦和遗憾的影子,巧云不幸被刘号长玷污,十一子被打残,郭庆春和许招弟被捉弄的命运,比之于《受戒》的温暖,这些都呈现出清冷的色调,但由于此时汪曾祺要给读者一点心灵滋润,突出“过去”之于“当前”的意义,故人往事则显示出较多和谐的意味,“彰显了诗化的审美自觉”[5]。
“当汪曾祺以‘记忆’的书写展开叙述时,个人的感情、情绪以及人格特质更有助于‘气氛’的营造”[6],故事情节相对而言淡化,“氛围”“意境”的营造显得尤为重要,他往往会用大量笔墨来铺排周边风景及风俗,而对于爱情/性过程本身却并不直言,在关键处点到为止、刻意留下空白,一定意义上,“氛围”不仅即“人物”,“氛围”也是“情爱”的情境化表达。《受戒》之荸荠庵、芦苇丛,《大淖记事》之大淖,《晚饭花》中“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2]528,“空间的自然性表征着‘食色,性也’的自然属性”[7],文本内男女的生理欲望与“自然”相契无间,当写到明海性意识的觉醒时,作者不多做铺叙,而是通过自然风景暗示出来,“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2]337少年的“紧张”源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小英子答应给明海做老婆以后,故事戛然而止,又转而去写生机勃发的芦苇丛,“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2]343颇为节制的笔法让“性”本身回归了自然,同样以“景语”代替“情语”的还有巧云和十一子最后鸳情成真的描写,“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2]429在相对封闭的时空,作者闪避了性的真相,“男女共效鱼水之欢的情欲放纵也显得含蓄、隽永”[8],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时间上的童年性与空间上的自然性共同完成了乡土诗境的建造。
(二)情感模式:理想之爱
在早期的情爱书写中,汪曾祺所写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多是普通人的正常情感,即便如小和尚明海名为“受戒”实为“破戒”的性萌动,三师父唱着“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的情歌,方丈有一个19岁的小老婆,“这儿的媳妇”都是自己跑过来的这般与常理相悖的行为举止,也由于发生在“荸荠庵”“大淖”的乡土风俗中,“策略性避开了病态意识形态的批驳和发难”[7]22,只不过是合乎人性的自然表达,如果再深入文本就会发现,在表层的反叛性叙事背后,隐藏着汪曾祺独特的情感模式,正是这种情感模式支配着他对小英子“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4]3的赞美和含蓄朦胧的表现方式。统观《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王四海的黄昏》《晚饭后的故事》等作品,虽然不是每一部都有着统一的情感模式,像《珠子灯》孙小姐终生守寡、《徙》高雪郁郁而终这样凄凉的爱情实际已经发生了叙事的转变,但固定的情感模式在其代表作中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构筑了田园牧歌般的“理想之爱”,在这个模式中人物一般都是从青山绿水中走出来的少男少女,充满了生命力,其中女性在这个结构中尤为突出,她们能够无视“礼”的羁绊而自由地伸张“情”的诉求,并能在最后终成眷属,这一情感模式在具体的文本中又体现为“初恋情怀”“根植乡土”以及“终成眷属”等形式。
汪曾祺关注青年男女的爱情,尤其爱写初恋,“青春期恋爱的特征首先是它的浪漫色彩”[9],《小学校的钟声》里十九岁的“我”,《受戒》“一十三省属第一的”明海、灵秀的小英子,无不洋溢着青春美好的气息。初恋之美好正在于其与实际考虑无关,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儿女们尚未入世且葆有“赤子之心”,《晚饭后的故事》郭庆春、许招弟两小无猜,“郭庆春看见招弟耳垂后面有一颗红痣(他头二年就看到了),就在那个地方使劲地亲了一下。招弟格格地笑个不停:‘痒痒’”[2]400,他们对于异性的好感朦朦胧胧,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亲密举止的含义。反之,在成人眼里这个举动就有了不同的含义,“有一次许大娘看见郭庆春亲招弟,说:‘哪有这祥玩的!’许大娘心里一沉;孩子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一天一天大了哇!”[2]400少男少女的单纯无邪与成年人的忧心忡忡两相对照,凸出了青春恋爱的纯净与美好。但是“少年的感情是纯情感的、精神的,但又不是柏拉图式的。因为首先,它也是在延续世代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次,它终究也要导致性的接近”[10],未成年男女的“性”意识往往还处于蒙昧之中,初次对异性充满了好奇与倾慕,但止于往前一步,这种爱情“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11]。对于这种稚嫩恋情的描摹,汪曾祺将其放置在“乡土世界”中,重构了“桃花源”般恬淡自由的“高邮故乡”,根植于“高邮故乡”百无禁忌的文化氛围中,“她们感情的发育是很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她们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12],“大淖”“芦苇荡”赋予了他们无拘无束的性情,爱情嵌于野性的自然空间中,远隔“外面”“穿长衣,念子曰”的世界,表现出未受世俗沾染的清澈动人。基于“和谐”的审美追求,汪曾祺所构建的“理想之爱”通常都会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形式结尾,王四海放弃了卖艺的生活,和五湖居的老板娘貂蝉“生了个白胖小子”;明海“受戒”后在小英子大胆的追问下“破戒”,巧云和十一子终成眷属等,温馨的结局实际上意味着作家对于爱情理想境界的驻守。
二、本真欲望的释放
(一)叙事策略:拒绝诗意
1985年以后,爱情/性越来越多地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情爱也始终伴随着“性爱”存在,“性的自由本质不断被承认”[1]280,与过去追求美、诗意不同,此时汪曾祺“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13],昔日如梦如幻般温情的回忆终究被残酷的现实所戳破,让他不得不开始正视。在《毋忘我》中,徐立和吕曼曾经是旁人眼中的“天仙配”,吕曼逝世后,徐立将骨灰盒放在干净的写字台上,时常在花瓶中放入毋忘我,一年以后,吕立和新妻搬家时却遗忘了阳台一角的骨灰盒,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的荒诞、悲凉感直指诗情的溃退,从这以后,汪曾祺逐渐剥离“诗意”的外衣,回归人性的逼仄真相,他不再着意于回望童年的温暖,而是注视着眼前的人生,不再铺排风景风俗来渲染爱情美好的氛围,而是“删繁就简,直击真相的枯、瘦、冷”[14],他的文字越来越简洁,悲凉之气汇聚笔端。
这一时期汪曾祺痴迷于“性”的直白描写,尤其是性器官的大量展现,如对女性脚和乳房的描写,“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15]434,“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腿修长。脚很美。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15]443,“杨素花人高马大,长腿,宽肩,浑身充满弹性,像一个打足了气的轮胎内带,紧绷绷的。两个奶子翘得老高,很硬”[15]336,脚和乳房都与“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过去他写一串小脚印把小和尚的心弄乱了仅仅暗示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现在“脚”“乳房”的大量裸露则喻指无拘无束的“性”。其次,他写男女情事时不满足于点到为止,出现了“性场面”“性过程”的赤裸描绘,“走近窗户,听到里面还没有完事。美人娇声浪气,声音含含糊糊。丈夫气喘嘘嘘,还不时咳嗽,跟往常和自己在一起时一样。”[15]275“从此以后,章叔芳三天两头就去宗毓琳住的方厅。少男少女,情色相当,哼哼卿卿,美妙非常。”[15]360“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了王厚堃,把舌头吐进他的嘴里,解开上衣,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他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15]404,更有甚者如《鹿井丹泉》写人兽之间的性爱“一日,归来将母鹿揽取,置之怀中,抱归塔院。鹿毛柔细温暖,归来不觉男根勃起,伸入母鹿腹中。归来未曾经此况味,觉得非常美妙。母鹿亦声唤嘤嘤,若不胜情。”[15]412在汪曾祺眼中,这些“故事本极美丽”,然而“理解者不多”,与同一时期《废都》《白鹿原》中带有“表演性质”的性描写不同,汪曾祺的笔法保持着一贯的洗练、简约,他对“性爱”的直接展示具有祛魅性质,“阳光化处理了乱伦描写的主题,略去了噱头式、猎奇式、偷窥式的惊艳、压抑、苦闷、焦灼的心理描写,亦未涉及形而上学的‘性’的玄思与辩解”[7]22,“性”作为人的一部分是生命的表现,性力乃是生命力的表征。
(二)情感模式:世俗之爱
在文学史上,汪曾祺以多写民间小人物以及富有日常气息的家长里短等特质而游离于主流之外,他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是民间审美意识,这一点在情爱故事中也不例外,但是早期的“民间”由于理想化的处理更接近于“桃花源”,世俗气息也为诗意所笼罩,带有“梦”的色彩,90年代,汪曾祺声辩道:“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13]245,彻骨的寒凉与幻灭惊醒了他,浪漫的“理想之爱”已不是他所着力构建的对象,相反,过去在《珠子灯》《王四海的黄昏》中闪现出相当异质性的悲凉感成为主导情感模式的重要因素,他此时的兴趣已不在于情侣之间行如礼仪的爱,而是浸透了世俗的悲欢、浮沉的小人物率性的爱,晚期汪曾祺所关注的情爱带有更多的“烟火”气,从《毋忘我》、聊斋新义系列以及《小孃孃》等情爱题材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由“理想之爱”向“世俗之爱”的过渡,世俗生活展现出本来的面目,原来情爱不只是青梅竹马的懵懂,乡土世界的清新,还有男欢女爱的欲望,市井小镇的喧嚣,其中他尤爱写那些畸形的性爱,文本集合了各种不伦之性,这里有乱伦:岑明和虞芳的师生恋、谢普天与谢淑媛的姑侄恋;这里有露水姻缘:薛大娘靠上了保全堂的吕三、小轮船上卖唱的男女;有婚外恋:张三的老婆和油头光棍私通、邱韵农喜欢上女售票员;有忘年恋:《名士与狐仙》里小莲子和杨渔隐结婚,更有比丘归来和母鹿的人兽恋。
社会背景的虚化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不伦之性”的道德重负,然而,这批成年男女生存的世界毕竟不是理想化的乡土世界,他们身处“居民楼”“剧团”“后街”“上海”,家规很严,听不到有人大声说笑,免不了旁人的闲言碎语,指指点点,总体呈现出压抑、沉闷的特征,在空间结构诗学上,内中的伦理道德、是非标准等,显然与远隔“市声”、野性自由的乡土不同,指向了“城镇世界”的情境营造。生存于这样的文化世界中,谢淑媛与谢普天的爱情终究不被认可,只能落荒而逃,岑明因为“窥浴”被乐团的演员殴打,薛大娘拉皮条被谴责,“城镇”的文化规范与“情爱”的自然性发生了冲突,人欲“难脱俗世伦理的监视与规训”[7]23,必得先“合理”然后才“合情”,“理”与“情”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以伦理本位的文化空间中,非常态的情爱叙事背后潜隐着悲凉之气,也许正如他曾引用其师沈从文的一段话“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6]现世之痛苦、尴尬、无常代替了和谐、温暖与单纯,温馨和谐的结局让位于颓败寒凉,《忧郁症》里裴云锦婚后不堪重负,郁郁而终;《小孃孃》里谢普天的家族风雨飘摇,只能与姑姑谢淑媛相依为命,即便出逃之后,谢淑媛最终还是死于难产,他再次逃离,命运的灭亡感压顶而来,如此强烈的败落感与绝望感让人感到狰狞可怖;而《鹿井丹泉》鹿女跳井,归来圆寂;《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里邱韵农退休后执着地追求爱情,放弃美满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毅然决定与情人结婚,生命的猝然而止结束了他的“作”,儿女和单位的否定显示了他的溃败;《露水》里偶遇的男女决定相依为命,男子却突然去世,一句“露水好大”道尽了世事无常的苍凉,最终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即便如《兽医》表层在姚有多与顺子妈喜结连理时结束,似乎有重返早期谐和温情之意,然而“顺子妈把发髻边的小白花换成一朵大红剪绒喜字,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了一双绣了秋海棠的新鞋除了孝”[15]422,她面临的仍然是未知的命运,在深层次上表现出作者的犹疑与哀悯,感受到世俗之爱的复杂与辛酸。
三、变迁的成因
(一)文化语境的发展
从创作的历时性角度看,汪曾祺对于情爱问题的思考一直在不断成熟和完善,创作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追究其根源,情爱书写的变迁首先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氛围的确为汪曾祺的归来提供了契机,他自觉地要给80年代的人们一些蕴藉,要给读者带来欢乐,要以“人性美”驱散几十年笼罩在文坛和心理的阴霾,调子自然是轻快的,即便如《大淖记事》中隐现“不和谐”的疼痛,也被结局的温情巧妙掩盖。另一方面,乍暖还寒的80年代初,新旧思潮正处于交替之际,过去的痕迹不可能被抹得一干二净,这也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自由是有限的,1981年人民日报刊载评论员文章《认真讨论一下文艺创作中表现爱情的问题》,批判了爱情描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表现男女之间那点庸俗的低级趣味,有的甚至是猥亵的色情描写”“存在着一些糊涂的、相当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强调“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17],《爱情的位置》《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主流作品都无一例外出现“性的缺席”,将爱情作为“控诉”“反思”的介质,这不过是十七年文学模式的再现。而1980年汪曾祺的《受戒》写成之后并未直接发表,而是先在编辑部内小范围传看,他直言“原本也是有顾虑的”“发表这样的稿子是需要一些胆量的”[4]5,创作的“劫后余惊”心理表征为“爱情的理想化”“乌托邦气质”及“性的淡化”,他策略性地以“边缘”的叙事姿态避开意识形态的打击,在处理情爱题材时小心翼翼,几乎没有越轨之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性”一时之间摆脱了文学体制的束缚,大批性文化心理小说纷纷浮出地表,汪曾祺的心理障碍也越来越少,逐渐向人性更深处挖掘,开始涉猎“性爱”领域,他有了“拷问现实”的勇气和自信,“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说的内容渐趋沉着。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18]曾经虚无缥缈的气息渐渐散去,闪现在《珠子灯》《八千岁》里的哀痛终于稳定下来,抒情的态度已经不合适来表现现实题材,或许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现实生活有时是梦,有时是残酷的、粗粝的,对粗粝的生活只能用粗粝的笔触写之”[19]。
(二)主体性的回归
激烈变幻的政治文化环境导致汪曾祺“主体性”的长期遮蔽,一旦有机会重新开始文学创作,汪曾祺便充分地发挥创作的自由。当他回忆起多年来经历的苦难,返身看到人性被摧残的真相时,“他精疲力尽地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他就迫不及待地直奔故乡,直奔童年。”[20]固然文坛需要“伤痕”“反思”的批判,同时也需要“美”和“人性”的抚慰与净化,这也成为汪曾祺早期创作的心理动因——“要有益于世道人心”[21]。其一,以童年的视角写青年男女的初恋,“自然人性”的呼唤肯定了人的尊严及价值,田园牧歌般的世界暗合了民众内心的乌托邦向往;其二,考虑到效果问题,意识到作家要对社会、对读者负责,“我写旧社会少男少女健康、优美的爱情生活,这也是有感而发的。有什么感呢?我感到现在有些青年在爱情婚姻上有物质化、庸俗化的倾向,有的青年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纯洁的爱情。”[22]当然,汪曾祺说到底是一个有着清醒的艺术追求的作家,对于旧题材的选择也是为了使自身获得较大的创作自由,对他而言,“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23]对于旧生活,他能充分地发挥主体的力量,以个人的名义对故人往事进行想象和虚构,按照人性进行重组,而对现实生活,他则感到“相当浮躁”,无法达到完全认同的地步。
1983年,汪曾祺意识到“如果继续写下去,应该写出一点更深刻,更有分量的东西”[18]21,到1986年创作《毋忘我》,他质疑了现代人忠贞的情爱观念,现实人生的荒诞使得他彻底地清醒过来,“忘”才是这世界的真相,那些温馨的爱不过是编织的“梦”,1986到1996年他表现出开放的创作姿态,把眼光转向了“丑陋”“凄凉”的民间世界,尽管小英子、明海、十一子、巧云的爱情堪称绝唱,然而此种“理想之爱”总有回避苦难、责任的嫌疑,隐隐约约显出作家的精神软弱与自欺,当情爱虚幻的纱幕被揭开后,他终于摆脱了“为时代立言”的藩篱,以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洞观世相,在文本内毫无顾忌地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原来除了明子、十一子的天真无邪,还有王厚堃伪君子般的举止,关老爷无耻放荡的嘴脸,除了两情相悦的欢喜,还有辜家女儿被迫卖身的辛酸,谢普天、谢淑媛在性爱与伦理之间的苦苦挣扎,岑春明、顾艳芬出于生理欲求而发生的尴尬情事。如果说,早期的汪曾祺还未脱离“既定意识形态”,对于题材的选择及主题的表达存在顾虑,那么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汪曾祺才真正面对了“自己”,以个人独特的体验开拓新文风,点出了历史真相,表露出对现实的怀疑与批驳,正是这样的使命感与个人化完成了主体性的最终回归。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汪曾祺一生历经坎坷,复杂的政治环境、乱世中的人生体验,“我行我素”的创作追求等都促使他对情爱不同的理解与表达,根本上,爱情将人的种种体验熔于一炉,“情爱”本身并不重要,它的另一端连接的其实是“人”,汪曾祺将两性置于情爱关系中,以此考察人性的丰富与局限,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情怀,对于那些引起争议的畸形两性关系,汪曾祺也只是客观展示没有被扭曲的人性,不表明自身倾向,这种“不介入”的叙事态度意味着他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评判。诚然,汪曾祺那些恬静温馨的爱情多为人熟知,而后期沾染了“鬼气”“毒气”的性爱看似与前一面陌生甚至矛盾,实为互补,只有将80、90年代的小说中的情爱书写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汪曾祺,既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