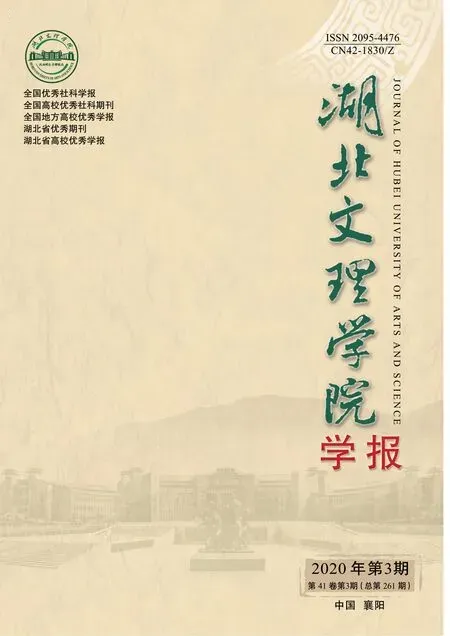论清代红楼戏中的“单元剧”
袁 睿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作为古典文学的高峰,《红楼梦》小说自问世以来得到普遍关注并成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宝库。其续写、改编之作层出不穷,据时人的记述,“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1]在各种改编形式中,以红楼戏较为突出,自成一派,有“唱遍棋亭”[2]之誉。
自孔昭虔《葬花》伊始,文人群体、民间艺人纷纷染指红楼戏创作。仅清代作品至少出现23种之多:传者14种,曰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孔昭虔《葬花》、万荣恩《潇湘怨》、吴镐《红楼梦散套》、吴兰徵《绛蘅秋》、石韫玉《红楼梦传奇》、朱凤森《十二钗》、刘熙堂《游仙梦》、许鸿磐《三钗梦》、陈钟麟《红楼梦》、周宜《红楼佳话》、杨恩寿《姽婳封》、褚龙祥《红楼梦填辞》、徐子冀(梦道人)《鸳鸯剑》。佚者9种,曰谭光祜《红楼新曲》(据石韫玉《红楼梦传奇》之《幻圆》谱曲)、封吉士《红楼梦南曲》、严保庸《红楼新曲》、张琦《鸳鸯剑传奇》、无名氏《十全福》、林亦构《画蔷》、无名氏《扫红》、无名氏《乞梅》。
这些作品虽出自同一题材,但风格多样,对原著情节、人物乃至思想的改编程度差异较大。清代红楼戏的复杂样态,体现出小说戏曲两种不同叙事文体转换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也展现了戏曲家在叙事技巧方面的探索性尝试。
一、以角色领纲——“单元剧”对传统戏曲改编模式的超越
由古代小说向戏曲的改编,大多遵循着两种传统模式:整体改编与片段改编。前者通过统括全文的方式,对小说内容进行全面覆盖式的改写。就篇幅而言,整体改编之作多为长篇大套的“超级传奇”,比如其中陈钟麟的《红楼梦》传奇长达8卷80出,为现存最长的红楼戏。这类作品共计8种,约占现存清代红楼戏的57%,比重较大。后者则抽取小说某个经典场面或某段独立故事,以折子戏、短剧等形式展现。孔昭虔的《葬花》、刘熙堂的《游仙梦》、杨恩寿的《姽婳封》、徐子冀的《鸳鸯剑》皆属于此。
整体式改编的优势在于较好地还原小说情节,以便于没有阅读过原著的观众轻松理解剧情。但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中短篇小说,像《红楼梦》这样的巨著则很难驾驭把握,过度牵拉的篇幅造成了情节松散、主题模糊等问题。吴克岐在评价陈钟麟的《红楼梦》时指出:
“夫传奇与演义,体制迥不相同。传奇者传其奇,藉片语单词已足歌成雅奏;演义演其义,非连篇累牍不能评其始终。陈氏传奇未明此理,至蹈演义之习,不免为识者所讥。”[3]“连篇累牍”、大而无当便是这类作品的通病。整体改编的红楼戏混淆了小说与戏曲的文体特征,造成刻板冗余的审美缺陷。
片段改编与整体改编的优缺点正好相反,它情节紧凑集中、便于搬演,但是对于不了解原著的观众却显得突兀片面。部分作品由于改动幅度较大,与原文脱节严重,容易造成对小说的误解,可谓创新有余而“忠诚”不足。
“单元剧”恰好介乎二者之间,它既保留了转述原著的完整性,又兼顾到戏曲文体和观众审美的需要。通过以角色领纲的方式,在叙事的“全”与“精”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
所谓“单元剧”“以角色领纲”,即在小说中选取若干人物作为戏曲主角,将这些主角作为剧本纲领,引领几个独立的叙事小中心。每个叙事小中心便是一个单元,单元内部是封闭完整的集中性叙事;单元之间以暗线串联,展现红楼众人的生活面貌。就各单元来看,叙事风格与片段式作品无异,都是关于个体人物的叙事段落;就整体来看,叙事效果与整体式作品相近,能够忠实、完整地展现原著小说的主体情节。
这种写法相当于小说珠链式结构在戏曲文体中的全新变体。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珠链式结构非常适合群像描写类型的作品,《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名著都以这种叙事结构闻名。小说以前一人引起后一人,以上一事逗出下一事,整体连贯顺畅;每个部分又能实现个别人物的专门性描写,成为一颗颗精华凝聚的“珍珠”。无论是通篇阅读还是片段欣赏,都能令读者获得完满的审美体验。《红楼梦》小说以封建家庭为叙事场地,人物的关系、事件的勾连更为错综复杂,显然不适合珠链式处理,只能采取网状覆盖。但当小说叙事的娓娓道来与戏曲演绎的精巧奇紧相碰撞之际,网状叙事显得冗长、纷乱。机械性地照搬原著叙事结构无法满足文体转换的需要,叙事转换出现了断裂,改编者必须通过采取全新的叙事策略才能更好地弥合这个裂痕。
戏曲文体的珠链式结构——“单元剧”因此应运而生:它实现了整体连贯又局部独立的审美效果,不仅适合舞台演出的实际需要,而且在塑造人物、厘清主线等方面较网状叙事更具优势。许鸿磐的《三钗梦》和褚龙祥的《红楼梦填辞》二剧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单元剧”叙事法。
《三钗梦》为四折杂剧,由题名可知,该剧选择了十二钗中的“三钗”为主角敷演故事。剧中第一折为总述,渺渺道人出场讲述大观园众人的前世今生;后面三折分别以晴雯、黛玉、宝钗为主角,讲述她们的事迹,每位主人公一折篇幅。而宝玉等人作为配角,随机出现在各折中,用以烘托主角。
《红楼梦填辞》与《三钗梦》的结构相同,只不过篇幅稍长。全剧分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又分八出。第一单元以王熙凤故事为主线;第二单元以林黛玉故事为主线;第三单元以晴雯故事为主线:即以八出的篇幅演绎一位女主人公的命运悲欢。各单元情节联系并不紧密,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叙事集团,但通过她们命运的发展,侧面反映出贾府的兴衰变化。
其实,有的红楼戏非常适合“单元剧”改编,但作者受到小说叙事顺序的束缚,造成了结构缺憾。比如朱凤森的《十二钗》传奇,立意、叙事构想与《三钗梦》非常相似,其中《断梦》《出梦》两出,更是借用《三钗梦》的内容。朱、许二人为好友,两人同为“红迷”,相约改编红楼戏堪称一段佳话。许作率先完成,其“单元剧”形式令人耳目一新。朱凤森受到启发,将其敷演为二十出传奇,主要人物也由三钗增加至十二钗。可惜他没有借用许作最成功的叙事模式,而是延续了整体改编的传统路子,完全依照原著的叙事顺序,使得十二钗事迹碎片化严重。如晴雯故事相关的《撕扇》《殒雯》《诔花》三出,分在上卷第七出和下卷十二、十三出两处,情节接续很乱。而且由于剔除了贾府其他人物关系,完整性也远远不及其他“全本”红楼戏,成了整体改编和单元改编之间的“鸡肋”之作。朱、许两剧的对比,更加彰显出红楼戏“单元剧”叙事的优越性。
二、“单元剧”的叙事得失
作为整体改编与片段改编的调和体,在叙事效果和演出实践上具有优势。叙事方面,其文脉线索更为清晰、主要人物得到强调;演出方面,它与折子戏的特质相似,适应了舞台,却对观众群体的鉴赏门槛有一定要求。
(一)文脉线索清晰
长篇章回体小说以广阔的叙事视角和细腻复杂的情节著称,能否厘清和再现复杂的文脉线索决定着戏曲改编是否成功。传统改编方式下的红楼戏,都无法做到完美。“单元剧”另辟蹊径,以确立线索主角、划分叙事责任的方式奠定了明晰的结构框架,与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所提倡的“立主脑”“减头绪”的制曲方法不谋而合。“单元剧”的出现,打破了长篇章回小说向戏曲转化的叙事壁垒,为文体互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现存的红楼梦“单元剧”叙事结构精巧,文脉线索清晰,坚固了重点与全篇之间的平衡。《红楼梦填辞》择取的王熙凤、林黛玉、晴雯三人,分别牵引出贾府的家庭关系、宝黛钗爱情、阶级压迫与歌颂独立人格几个重要线索,基本涵盖了《红楼梦》的小说主题,做到了“全”。贵妇、小姐、丫鬟的不同身份,展现了多种封建女性形象,契合原著刻画女性群像的创作意图,做到了“忠”。在各单元中,作者将主角相关的情节进行浓缩荟萃,既保证了人物形象的完整立体,又突显了原著中的经典情节,做到了“精”。综之,单元与单元间切割清爽,不拖泥带水;整体上文清专一,一气呵成。“单元剧”独特的叙事结构对厘清原著文脉助益匪浅。
(二)突出主要人物
“单元剧”的最大特点是以角色领纲。角色先行的做法使观众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于主角身上,几组单元转换下来,便可对原著中的主要人物拥有大致印象和了解。以角色领纲的做法一方面暗示了改编者对原著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促进了主角形象在更广泛群体中的接受与传播。
《红楼梦》小说登场人物众多,形象鲜明者亦不罕见。仅就女性形象而言,十二钗各领风骚,其他大小配角不计其数。在有限的叙事篇幅里如何取舍?这显然与改编者的主观好恶有直接关系。
《三钗梦》与《红楼梦填辞》都是各选三钗,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黛玉和晴雯。所不同者,前者选取了宝钗,后者选取了王熙凤。钗黛之争自清代绵延至今,出现过“尊黛抑钗派”“尊钗抑黛派”“共尊派”“共抑派”以及“各有取舍”等多种派别和观点。晴雯和袭人作为戴钗的“影子人物”也天然地被划归为两个不同阵营。在两部“单元剧”中,黛玉、晴雯都成为作者心目中的主要角色,她们的形象也如书中一样,代表了美丽、聪慧、高洁等美好的品质,作品“尊黛”的思想显而易见。
此外,《三钗梦》的另一主角宝钗在作者笔下受到微讽。《三钗梦》以梦贯穿全剧,开篇《勘梦》交代宝黛钗雯四人的仙界身份。除了沿用原书中宝玉神瑛侍者、黛玉绛珠仙草的身份外,还给宝钗配了神芝仙子、晴雯配了芙蓉仙子的身份。在他们下界前,渺渺真人曾分别示警,希望宝玉改掉“石心”“石性”,黛玉、晴雯各自珍重,言语间颇具怜爱之意。对神芝仙子宝钗则是严厉的告诫:
【寄生草】堪叹人间宝,谁怜坠井钗。你冷香莫犯痴淫戒,肉香慢恋肌肤爱,喜天香剩有灵芽在。可知道镜中薛媛空断肠,休教艳朝霞、五花神光坏。[4]
四人下凡,皆因“偶动你怜我爱之心”,真人却唯独对宝钗教训勿动“痴淫戒”,甚至吓以“神光坏”之险,可见在作者心中,黛玉等人的爱恋是清澈无暇的,宝钗的爱具有世俗成分。
后面二折,晴雯、黛玉先后魂归天界,得证真身都非常顺利。宝钗在宝玉出家后,也得到了警幻仙姑的接引,却难以悟明真身。警幻仙姑以转轮镜照之,她看到自己“颤巍巍珠冠点翠”的样子,竟自叹曰:“呸!原来是个俗物!我好恨也!”其雍容富贵的装束和自厌之情都暗示了作者对宝钗形象的不满。
两部作品体现了许鸿磐、褚龙祥作为《红楼梦》读者的阅读感受和浓厚的“尊黛”思想。通过戏曲改编的再度创作,其作为读者产生的阅读体验升华为作者意图,进而向更多的读者推广。由于“单元剧”主角明确、删繁就简,人物刻画与小说相比,虽不细腻却更为鲜明突出,因而更宜为读者感知和接受。在传播过程中,作者的爱憎情绪也附着其中,形成了原著→改编→观众的二度传导,在《红楼梦》接受史中具有特殊意义。
(三)适宜演出需要、欣赏门槛提高
这种选取原作中重要人物独立成剧而非面面俱到的改编方法,避免了情节的冗长拖沓,更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从这一点上看,“单元剧”具有与折子戏相等的演出优势,可以灵活适应大型戏院、乡间演出、家庭堂会等不同舞台场所需要。另外,由于情节的精选,出场人物也不冗杂,对于戏班演员调配、行头道具、舞美布置等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小。
从另一方面讲,篇幅过短影响了故事细节的展开。“单元剧”只择取重点事件,无法细腻详尽地复刻原著。因此对于不熟悉《红楼梦》小说的观众来说,即便看懂了剧情,也只能形成对人物的大体印象,了解其生平遭际梗概而已,与阅读小说时的品咂式体验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个门槛问题在其他两类红楼戏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是由于小说戏曲两类文体的叙事属性造成的。即便是相对细腻冗长的整体改编作品,也无法完全等同于原著;至于毫无上下文衔接的折子戏,就更考验观众的欣赏水平了。
戏曲毕竟是源自民间的俗文学样式,它的受众群体以普通观众为主,只有受到民间欢迎和肯定的作品才能具有繁荣性和生命力。《红楼梦》“单元剧”、折子戏预设的欣赏门槛增加了观众的观赏难度,失却了舞台亲和力,在大众传播和接受过程中难免出现劣势。因此,尽管红楼戏存目丰富,但留下文本且具有演出活力的作品不多,至今上演之作也多集中于几个常见桥段。与原著在小说界的独领风骚相比,红楼戏的泯然沉寂值得深思。
三、“单元剧”为何独现红楼戏?
元明清时期小说戏曲间的改编互动并不鲜见,《三国》《水浒》《西游》一类时代累积型题材,小说曲艺齐头并进自不必说;就连《金瓶梅》《红楼梦》这样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也渐染了曲艺改编的风气。在《红楼梦》“单元剧”出现以前,小说的戏曲改编从未冲破整体和片段改编两种常见叙事模式的束缚。以现存《金瓶梅》戏曲为例,边汝元的《傲妻儿》、郑小白的《金瓶梅》属于片段改编;李斗的《奇酸记》以及傅惜华、马廉收藏的四种传奇残本都属于整体改编。这些作品与本文提到的两类传统叙事模式的红楼戏具有相同的叙事缺陷,反映出长篇网状叙事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时的共同困局。
可以说“单元剧”的出现为戏曲改编者提供了一条新路,这种叙事为何单独出现于《红楼梦》的改编作品中?这与戏曲文体的自身发展规律及《红楼梦》小说的接受历程具有密切关系。
(一)清代“某主题”短剧集的变体
红楼戏“单元剧”作品整体叙事步调连贯一致,内部却可以拆分,这与清代盛行的“某主题”短剧集的形制极其相似。“某主题”短剧集,即作者围绕某一话题或某一情绪选取多个典故敷衍为一组戏曲作品,创作时间相对集中,各篇作品格式整饬、风格雷同。
张仲平下海多年,早已不把自己当作什么知识分子,他宁愿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合格的生意人。什么叫合格的生意人?就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利益的商人。张仲平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那就是外面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家里夫妻和睦、夫唱妇随,有那么一种中产阶级的从容自信。
这种戏曲集早在明末已经出现,汪道昆的《大雅堂乐府》和徐渭的《四声猿》是早期代表。《大雅堂乐府》创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四种一折短剧组成,分别名为《远山戏》《高唐梦》《洛水悲》《五湖游》。顾名知义,四种作品依次写张敞画眉、襄王神女、曹植洛神、西施范蠡之典故,表达文人的风流闲适之意。这套戏曲集从语言格式到内容思想、主题情调都和谐统一,是“某主题”短剧集的开山之作。《四声猿》稍出其后,也由四种短剧组成。尽管各剧折数由一至五出不等,但题目工整押韵;何况剧中典故皆选奇人奇事,旨在振聋发聩、传达进步心声,亦是前后呼应。
清代以后,杂剧开始了案头化发展,写心抒情功能更加发达。“某主题”短剧集成为文人炫才自娱、抒情遣兴的常见写作方式,剧本的篇幅形态也日趋固定。桂馥的《后四声猿》、舒位的《瓶笙馆修箫谱》、石韫玉的《花间九奏》、周乐清的《补天石传奇八种》等不断涌现。他们以名人典故为题材,构建了一组组雅致精炼的戏曲集。集中各剧呼应统一:《后四声猿》抒发文士苦闷、《瓶笙馆修箫谱》旨在风雅玄谈、《花间九奏》表达闲情逸致、《补天石传奇八种》为前人补恨。
与传统的杂剧传奇体式相比,以短剧为元素的戏曲集在形式上更为新颖、更好驾驭。短小的篇幅不易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却适宜展现经典场面、突出作者的情绪意图。而更多时候,其借用的典故已经退化为主题背后的象征标志,作者引用典故并非为了讲述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特定情绪。
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不能忘情吟序》中记述了自己晚年罢官后,将年轻歌姬樊素放还自由的故事。桂馥(《后四声猿·放杨枝》)和石韫玉(《花间九奏·乐天开阁》)都在集子中选择了这个故事,但前者情绪苦闷,因此白居易被塑造成凄凉的老翁,离别之景心酸悲伤;后者心情愉悦,因此白居易被描绘成豁达的长者,分手之时快乐和谐。
上文提到的“单元剧”在形式和抒情表达上都与这类戏曲集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如果将“单元剧”拆分作几个独立的短剧,在叙事上并不突兀。且每个小单元的折数固定,出场人物、语言表现也前后呼应,将之视为一套《红楼梦》短剧集亦未尝不可。其次,作者对各单元主角的选取正如“某主题”戏曲集一般,带有既定的主观情绪和表达诉求。通过角色的选择和场景色调的渲染将自己的爱憎感受先行传递给观众。这种欣赏暗示使改编之后的作品承载了曲家个人的风格,是凌驾于简单文体转换之上的真正的“改写”。当然,同“某主题”戏曲集一样,这种改写并没有改变叙事走向,并不妨碍观众了解原著故事。可以说,“单元剧”就是“某主题”短剧集的变体。
红楼戏取材于小说,但本质是戏曲,与其他戏曲作品一样遵守戏曲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创作必然受到当时戏曲文化的影响。表达上借鉴了当时流行的短剧集样式,但由于作品内容连贯性的要求,作者们采用了折中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呈现出“单元剧”的全新样态。
(二)嘉道以后的深入式阅读
《红楼梦》自乾隆间问世以来,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追捧。数百年来,长情不灭,围绕《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曹学”等专门性学问,由原著延伸的续书、曲艺、诗词、图谱、批评不计其数。由于《红楼梦》在当时的高度流行,尤其是文人圈子的热捧,形成了“无人不知红楼梦”的共同认知。文人曲的二度创作直接以此为基础进行更概括、更抽象的文艺改造,反映出文人作者较高的创作预设和思维壁垒。
以文人圈子对它的熟稔程度来说,“单元剧”不存在任何阅读理解障碍。作者对于情节详略取舍的叙事功底反而在文本情节外增加了另一层鉴赏乐趣。品读红楼戏不仅是在重温《红楼梦》经典,而且成为一场读者反馈的再创造盛宴。面对同样的材料,如何加工、继承、创新,是体现作者功力和增加同人交流的绝好话题。因此,清代红楼戏的改编经常伴随着文人曲会、清谈等活动产生。从现存的文人信札和笔记中,也可以看到关于红楼戏改编在文人圈子中被津津乐道的记载。比如已经散佚的谭光祜《红楼新曲》,曾有过文人间的清唱表演:
往在京师,谭七子受偶成数曲,弦索登场,经一冬烘先生呵禁而罢。[5]
谭七子就是谭光祜,从这句记述中可知他曾在京师一次聚会中即兴演出。在《红楼梦》最为盛行的京城,红楼戏的即兴演出、随性改编作为新兴话题之一,在文人圈内并不罕见。
嘉道时期,读者们对《红楼梦》的接受不止停留在单纯的阅读、品评层面,而是上升到阐释、溯源的学术高度。这种情况一方面基于广大受众对原著的狂热喜爱之情,另一方面受到乾嘉汉学考据之风的直接影响。当时的文人多兼具学者身份,他们在史地、训诂、音韵等专门性学术训练中积累了坚实的学术素养和系统的治学方法,同时也养成了考据成痴的思维惯性。面对充满谜团的旷世奇书,他们展开了精深博洽的系统化研读。其成果不仅表现为相对严肃的人物考、系年考、索引等谱录集成,而且拓展到颇具趣味性的酒令谱、骨牌谱、戏谱等领域。红楼梦研究一时间门类纷杂、蔚为大观。
作为红楼文化的衍生品,红楼戏也受到了这种研读风气的影响,“单元剧”的出现就是文人圈子对《红楼梦》深入式阅读的直接体现。
首先,文人读者对《红楼梦》的熟稔使其在改编过程中更加游刃有余地拿捏剪裁,以及准确展现原著的精髓主干。从清代红楼戏的整体改编作品和“单元剧”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单元剧”更宜突出线索、展示人物的结论。尽管其篇幅与长篇传奇相比似乎处于劣势,但最终的表达效果却令我们惊讶。“单元剧”清晰的叙事层次,精巧的结构布局完美地解决了长篇网状小说向舞台艺术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难题,而驾驭这种新颖叙事法的前提必须是对原著烂熟于心,理解透彻。这一点在现存的《红楼梦》“单元剧”作品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三钗梦》只有短短四折,除了第一折总括全书,交待主角身世背景、预告人物命运外,后面分配到每个单元的篇幅仅一折而已。在一折篇幅中完整地叙述人物生平经历,并准确反映其性格乃至作者对他/她的态度绝非易事。而许鸿磐在甫一开篇便抓住了“梦”的核心,将人生的荒诞与悲凉与“梦”对接,先声夺人。其后黛玉、晴雯、宝钗的命运也完全围绕一个“梦”字,这一基调与原著“人生幻梦”“惝恍迷离”的悲观情绪何其契合!
黛、晴、钗三人性格不同、遭际各异,作者对她们的爱憎情绪也不尽相同,但她们逃不脱梦幻般的宿命,她们悲剧性的结局如出一辙,这便是大观园众姊妹的共同之悲。戏曲开篇三人下凡历劫、命运预判的“仙梦”书写与原著第五回预设判词的叙事顺序相映衬,而三次梦碎带给观众的震撼也向小说结尾家族倒掉、各自飘零的大悲剧式表达竭力靠拢,忠实地传达出曹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创作心理。
其次,学术研究的惯性和素养使红楼戏书写开始追求精准性,并赋予其辅助观众快速了解原著的工具功能。作者借鉴了其他红楼文化研究形式,通过附录、凡例等手段弥补了戏曲文本无法向读者展示小说全貌的缺失。褚龙祥的《红楼梦填辞》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甚至称得上“红楼人物索引录”与红楼戏的结合之作。在戏曲文本之后,作者增加了几组附录,包括:《红楼梦稗说谚语》《谐音目》《曹雪芹先生删订红楼梦稗说缘起》《红楼梦男女姓名考》(并贾氏世系图)等。其中《姓名考》按照身份将小说出场人物细分为“贾府眷属”“贾府戚属”“贾氏族属”“梨香院女戏子”“栊翠庵道姑”“贾府婆儿”“荣府家人”“荣府门下清客”等数十个品类,并于人名后标注人物关系、表字、参与事件之类的人物简介。全书可指出姓名的四百零二人,在这篇《红楼梦男女姓名考》中收录俱全。
目前存世的《红楼梦》人物谱以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以及寿芝的《红楼梦谱》较为知名。《红楼梦填辞》附录部分虽然在篇幅和细节上不足以与这些专门性著作比肩,但其准确性、全面性毫不逊色。且对于《红楼梦》的初级读者来说,《姓名考》及所附《世系图》简明扼要,清晰精准,是快速厘清人物关系的得力工具。
总之,在嘉道以后的学术氛围和《红楼梦》研究热潮中,红楼戏作为红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单元剧”的全新改编模式。
四、余论
小说戏曲是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均为叙事文学,在题材、风格、结构、人物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共性与互动,但各自的文体属性又使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红楼梦》作为网状叙事的长篇小说,在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存在天然的叙事壁垒,以传统戏曲叙事模式套用的一批红楼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原著的光辉。“单元剧”模式的开启顺应了清代短剧戏曲集的发展潮流,解决了红楼戏改编的叙事难题,也反映出汉学发展带来的学术与文学之融合。《红楼梦》“单元剧”既是红楼文化的有趣现象,更是清代文化的特殊景观,对古代叙事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