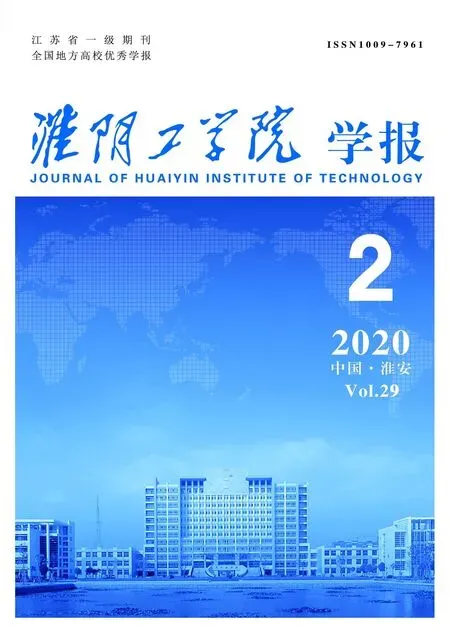金庸小说“有”“无”哲学观念的文化演绎
樊红玉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金庸小说文化内涵丰富,道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中得到精彩演绎。金庸小说体现道家“有”“无”哲学观念,“有”“无”观念及其衍生的朴素辩证思想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另外,对金庸小说的评论方法众多,角度多样,有针对其武功进行分门别类探讨的,有在道家视野下对小说进行宏观评论分析的。文学评论“将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结合,既可以将作品的诗意和魅力尽可能动人地揭示出来,又能帮助人们形成敏锐开阔的审美能力[1]8。”现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文化领域分析评论金庸小说,以“有”“无”哲学观念为落脚点,更全面地展示金庸小说的魅力。
1 《老子》中“有”“无”的哲学观念
《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2]1。无,是天地万物的开始、开端。有是天下万物的起源、始祖。徐小跃认为这是从宇宙论、本体论意义上对“无”的解释。与“有 ”相对的“无 ”,表示没有、不存在,而空间意义上的“无”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没有”,而是强调“没有”后面的状态,即“没有”装、据、填、充东西的地方。徐小跃指出,“此两种意义上的‘无’都不是老子《道德经》‘无’的主要内涵 。”[3]10也就是说,老子论“无”主要是从宇宙论、本质论、本体论层次,即从哲学层次阐释“无”。《老子》讲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110。对“有”“无”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王弼、何晏坚持“贵无说”;冯友兰支持“有无相生”,不认为“有生于无”。在此,更倾向于“有”“无”辩证存在,赞同“有无相生”之观点。《老子》中“无”含义较多,结合金庸小说中的武功,这里采用和“有”相对的“无”的意义,基于此意,“有”等同于存在,“无”作不存在理解,即世间的一切事物,其产生都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老子》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117。”姑且不论明哲先贤对此深奥入里的解释,这句话浅显来看,正印证万物从无到有的过程。万物产生经历从无到有的道理虽平凡之极,却是世间至理。从生物学角度考察人类的起源,按照目前公认的说法,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例证。再者,从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迭,新旧朝代兴衰,同样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相生发展。结合金庸小说,对“有”“无”观念的探讨不能局限于生物学、历史学领域,更要深入到文学、哲学层面。
2 金庸小说中“有”“无”观念的文学表现
金庸小说中,对“有”“无”观念的文学演绎最充分的当属武功。武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有无相生,小说通过这三个方面,对道家的“有”“无”观念进行文学演绎。
2.1 武功的创造和拥有体现道家从“无”到“有”之思想
2.1.1武功创造从“无”到“有”的厚积薄发模式
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远远高于生活”。武功在金庸小说中不能仅被当作武术,而要被看作是近于道的艺术。艺术的产生需要生活的土壤,新武功的创造同样需要一定的土壤。新武功的产生过程类似地底原油,经过漫长的演化、沉积,在合适的际遇下喷薄而出。
张三丰痛惜俞岱岩,身受重伤,生死难料,心情怫郁悲愤。他根据王羲之《丧乱贴》笔意,加上此时心境,凌空书写“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4]11024个字,创出倚天屠龙功。被争相抢夺的《九阴真经》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一名官吏在遍览道家典籍后有悟所创。杨过一人集古墓派武功、打狗棒法、全真教内功心法、弹指神通等于一身,加之对小龙女的思念,促使他创出黯然销魂掌。这些武功的被创造,需经过厚重地积累,才能使其从“无”到“有”,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不胜枚举。不仅武功的创造体现从“无”到“有”,武功的拥有也注解了道家从“无”到“有”的哲学思想。
2.1.2武功从“无”到“有”的途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小说人物武功从“无”到“有”,主要依靠自我刻苦用功,以师父的指点为补充。郭靖、萧峰之所以最令读者敬佩,在其英雄壮举之外,踏实练武才拥有高强武功也是原因之一。郭靖坚守勤能补拙的原则,练功比别人多付出十倍百倍的辛苦,在文末终成高手。即使如此,《神雕侠侣》中,郭靖仍每日勤奋练武,他比黄蓉武功进境更大。萧峰继承其父武学天才的基因,这点比郭靖幸运,但萧峰练武同样刻苦。他自小师从玄悲,练武从无一天间断。虽有天赋,后天的努力更是他拥有高强武功的原因。
2.1.3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胜于“有”
《老子》讲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遵从道,顺应自然,不强加干涉,这样就可更好达到目的。金庸小说中,无招胜有招是武功的最高境界,它的哲学基础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无招’并非什么招也没有,而是不被既有招式所囿,可以包含任何招式。‘无招胜有招’,将各种招式忘得干干净净,其实并非全忘。忘掉的只是形式,精髓没忘,这得之于道家重精神实质的传统,体现了‘有’与‘无’的辩证关系[5]10。”
“无”胜于“有”的例子,在金庸小说多有体现。比如,独孤求败使用的剑,从利剑、软剑、重剑到木剑,体现无胜于有。风清扬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时强调,招式要灵活多变,做到无招胜有招,使敌人无法破解。风清扬强调的是将各种武功招式融于一体,不拘泥守旧,使敌人无法预测,这样以别人无法察觉的“无招”,可轻易胜过一眼判断出来的“有招”。这上升到艺术层面,达到“道”的境界。还有,张三丰当着众人的面演示太极剑法,不担心剑法被别人学会,因“众人只看了数招,心下大奇,原来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相同”[4]855。张三丰听张无忌说将剑招全忘光了,才让张无忌上场对敌。最终,张无忌打败八臂神剑方东白。他之所以取胜,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张三丰创造的太极剑法来源于道家思想,道家讲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64。所以,太极剑法在起点上就高于其他。其二,张无忌将所学剑招忘得干干净净,方东白无法根据平素的经验和刚才的观摩推测其招式,失去料敌先机的机会。
2.2 从“有”到“无”,阴阳消长
“无论是抽象上‘有’与‘无’,还是具体事物‘有’与‘无’,都是并列相生的循环关系,‘有’不能凌驾于‘无’之上,‘无’也不能凌驾于‘有’之上。”[6]234《老子》中“有”与“无”循环往复,不仅有从“无”到“有”的思想,还有从“有”到“无”的思想。
通常,武侠小说多写书中人物武功的由弱到强、终成一代武林高手的发展过程,对武林高手内功、外功的从有到无鲜少提及。在金庸小说中,有几个人物,他们起初武功高强,但由于某种原因,或武功全失,或所创武功无法发挥威力,亲身体会到武功从有到无、由强变弱的感受。
杨过心系小龙女,创造出——黯然销魂掌。由于杨过与小龙女相隔十六年终于重逢,心中的思念、悲伤、孤独、无望等心情已被喜悦取代,在营救郭襄使用黯然销魂掌时却发现,“虽在危急之中,仍无昔日那一份相思之苦,因之一招一式,使出去总是差之厘毫,威力有限”[7]1360。
与杨过相比,鸠摩智是真正意义的武功全失。他曾以火焰刀独战大理五大高手,武功之高可见一斑。可惜,鸠摩智对武功充满贪念,为求武功不择手段,有愧高僧之名。尽管扫地僧对其劝诫,可是鸠摩智不听劝阻,强行练武以致走火入魔。枯井底,幸得段誉将其内力吸收殆尽,鸠摩智得以保全性命。武功全失之后,他深刻反省,终于大彻大悟,巡游各地,只参禅悟道,不问俗事,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得道高僧。在金庸小说中,推崇道德甚于武功。远离道德只用武功持强凌弱,那武功仅为武术,只是技;若是使用武功的同时注重道徳,则武功近乎道。鸠摩智从无徳追求武功高超,到因无德导致武功丧失,最后大彻大悟,从无徳之人发展为没有武功的有德、大德高僧,道德品质、人生格局得到极大提升。鸠摩智人生境界与认识经历从无到有的历程,构成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循环。事物发展总是矛盾双方的此起彼伏,阴阳消长,而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发展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2.3 “有”“无”相生 ,循环互动
虽然王弼本中部分段落将“无”看作“有”的更高层面,但实际有和无互为根基,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缺一不可。“这里的‘有’和‘无’并非由‘无’生‘有’的单线关系,而是并列关系。‘道’正是通过反复将‘有’毁灭为‘无’,又从‘无’中生发出‘有’,才完成了自身的循环运动。”[6]234从无到有的前提是无中必然包含产生有的因子。如张三丰创造倚天屠龙功,他武功高强,内心对徒儿担忧的心境和体会到王羲之《丧乱贴》笔意的这些基础,是这门武功从不存在到存在的必备因子。杨过的黯然销魂掌,基础是他融会贯通前辈武功和对小龙女不变的情意。正有此为基,黯然销魂掌才应运而生。如哲学中量变引发质变。量的积累是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变,即一个事物的“有”,必然经过一定基础的积累,才能从不存在状态变为存在状态。
“有”“无”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无”中生“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两者一体两面。“有”“无”相生符合质量互变规律,即量变引起质变,引起事物的“有”和“无”。从个人武功来看,“有”“无”相生的关系并不明显。但站在历史宏观角度考察武功可发现,武功的产生和消失,还是体现“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首先,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功的创造,在内部矛盾的作用下,经过大量积累发生量变,到一定界限时,产生质变,从“无”到“有”。一门新的武功被创造,从不存在到成为事实上的存在,一定发生在能够促成它产生的因素存在的基础上。另外,一门武功的消失,从存在变为不存在,同样存在推动其消失的因素。“无”中包含着推动“有”产生的因素,有中包含着推动无发生的因素。老子讲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2]165就印证“有”“无”相生、质量互变规律。从这个角度讲,道家的“有”“无”相生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得到完美演绎。
3 金庸小说中“有”“无”观念的文化意蕴
3.1 厚积薄发,天人合一
武学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依“道”而为,使武功不仅是强身健体、对敌救人的工具,同时是自身到达臻境的外化显现。遵“道”而行,达到“无我”的境界,这是天人合一的必然要求。张三丰依据《九阴真经》创立武当派,该派内力绵长,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即取法自然。他面对庄稳龟山、蜿蜒蛇山苦思冥想三昼夜,忘却世间一切,本我消失,以天地为师,与自然融为一体。其时五感不敏,忘乐忘忧,忘饥忘渴,忘记一切,唯思想奔腾如海,保留本我,沉浸两山之上。当悟道之后,他豁然开朗,进入超我之境,达到天人合一的高度,创造出真武七截阵。杨过断臂后,以自然为师,在悬崖山洪冲击下,领悟剑理。张三丰和杨过都是通过感悟自然之道,进入忘我境界,领悟高深武功,包含深奥哲学沉思。
3.2 道家辩证思想的折射
道家思想充满辩证思维,以“有”“无”为基础,衍生出“智愚”“虚实”“刚柔”“正邪”等辩证概念。智和愚,指人的智识高低。在道家学说中,庄子将“智”分为“小知”和“大知”。《逍遥游》提到“小知不及大知”[8]13,“小知”只是小聪明,“大知”才是大智慧。郭靖初见江南七怪即被嫌弃愚笨,石破天被人叫“狗杂种”不觉受辱,他们没有小聪明却拥有大智慧。众人费尽心力,反而是郭靖和石破天脱颖而出,分别练成高深武功。至于虚与实,军事中讲究“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草船借箭、空城计,将兵法中虚实发挥得淋漓尽致。虚实的结合,亦活跃在其它领域。我国书法中有虚笔实笔之分。清朱和羹《临池心解》云“作行草最贵虚实并见。笔不虚,则欠圆脱;笔不实,则欠沉着。专用虚笔,似近油滑;仅用实笔,又形滞笨[9]222。”在创作中,有虚写和实写的论述,精品的诗、词、小说以及散文等虚写和实写具备。生活器物更是有虚有实,如《老子》对车轮、器具和屋室的论述,有虚有实,器物才能使用。至于刚柔,《老子》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2]187。”此不仅为治国之道,其实结合人身讲,对应人坚持不懈亦贴切。水滴石穿,柔能克刚,自古以来天下之事,坚持不懈,一切皆有可能。学会太极拳和太极剑的张无忌,领悟到道家以柔克刚的意蕴,竟挫败金刚门硬功高手。最后,分析在“有”“无”基础上派生的正邪观念。究竟何为正,何为邪,正邪的划分标准是什么?金庸通过正邪观念,展示出人性的复杂。正派之人,未必不干坏事,邪魔外道中人,并非全都作恶多端。道家的辩证思想,使炎黄子孙运用哲思辩证看待问题,这是往圣先贤留下的人生智慧。
3.3 独特的艺术世界
3.3.1将武功进行艺术化、人格化、道德化处理,创造独特的艺术空间
王国维谈到治学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10]29。”三境界说亦适用人生境界,金庸将此说进行武侠式改写,在小说中对武功的描写达到艺术境界,武功被艺术化、人格化、道德化,不同武功进境对应人生不同境界。独孤求败在不同年龄段使用不同的剑,以剑代指武功强弱,象征不同的人生境界。金庸将武功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武功具有艺术色彩。朱子柳将一阳指和书法完美结合,以笔代指,武功中包含书法;范百龄痴爱下棋,以棋盘为兵器;太极拳、两仪剑法、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等含《周易》文化。金庸小说中武功还有人格化特色。周伯通了无心机,自创左右互搏术,从武功名称可见其顽童性格;丁春秋阴毒,擅用毒和化功大法,轻则化人内功,重则下毒致人死命;姑苏慕容机谋,家传武功是斗转星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善借力打力,是其处心积虑复国的武功外显。除以上特征,小说中的武功还具有道德化色彩。郭靖、萧峰、洪七公三人一心为国为民,降龙十八掌刚猛正气凌然;同样练习《九阴真经》,梅超风练就九阴白骨爪,一身邪气。小说对人生境界解读以剑为指引,将武功进行艺术化、人格化、道德化处理,以主人公武功的提高,作为其人生提升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他的人格思想得到磨练。由此,金庸创造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
3.3.2淡然看待生死,构建放达豪迈的艺术境界
小说中对生死的思考很是深刻。张翠山淡然看待生死,将人生看作虚无,超脱名缰利锁。他看到都大锦身死,黄金仍在,联想自身虽独战少林三僧取胜,百年后仍尽归尘土。张三丰危急时刻宁愿受屈辱也要保存刚悟出的太极拳,随即想到“我却盼这套太极拳剑得能流传后世,又何尝不是和文丞相一般,顾全身后之名”[4]834。张三丰对死亡的轻视与文天祥一般无二,对声名的勘透更高一筹。令狐冲命不久矣,依然放达饮酒,不惧死亡。在《庄子》、佛家教义中“生亦何欢,死亦何哀”都可找到意义相近的说法,这被金庸化用,演变为小说中人物的生死观。“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4]697,这被明教众人在无力抵抗时吟唱出来,显示出悲天悯人的生死观。萧峰大战聚贤庄明知不敌,一句“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11]695不畏生死之气概尽显。在儒家思想中,为了大义,不怕牺牲。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儒释道三家都不惧死亡。道家修身养性,随性自然,冲和平淡,追求自由。但小说对道家文化的表现存在偏颇,如体现道家思想的主人公们对社会责任担当不足,避世归隐,是其弊端,要慎思之。司马迁言道: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追寻国家大义,承担社会责任,为此看淡生死,是份属当为之事。
4 结语
“有”“无”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结合《老子》对“有”和“无”进行解读,更觉玄妙无比。借助金庸小说中的武功阐发“有”“无”的辩证关系,能够变难为易,化繁为简。武功,这一被武侠小说家构想出的事物,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表现小说家甚至是国人对于身体的信心,体现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从“有”“无”的哲学观念对金庸小说进行研究,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蕴,为深入探索古人哲学智慧、学习先贤人生哲思、树立当代文化自信做贡献,同时也拓展了金庸小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后来者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