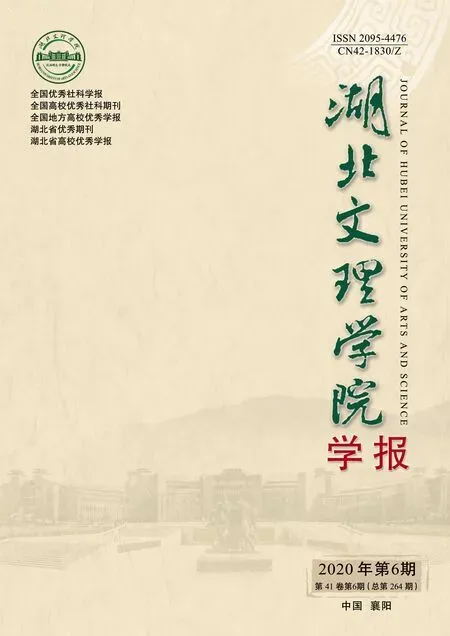时线性断裂与人物呻吟里的历史真实
——探析《来生再见》叙事策略
李嘉欣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何顿,湖南人。早期作品主要致力于表现城市市民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的环境里对金钱与欲望的追逐,展示了一个充斥金钱与欲望生命形态的都市王国。后何顿创作题材由都市题材转变为历史叙事题材,在叙事策略方面开始进行探索。
《来生再见》是一部表现战争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该书从黄抗日被迫参加抗战的视角开始展开,还原了湖南三大历史战役的原貌,作者把对抗战的记忆往深处挖掘,一点一点渗进去,一步步还原历史的真相。在作品中作者扒开历史的外衣,深入国民党的抗日作战,去呈现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揭示了战争中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诉说战争的残酷无情。《来生再见》独特的叙事安排,为其赋予了探讨价值。本文旨在从小说的叙事结构、视角转换以及时序方面入手,深入文本,感受作品在叙事策略方面的独特性。
一、复调叙事——历史真实的客观呈现
复调小说理论最初是由巴赫金提出,他指出复调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1]这些声音在文本中都是独立的个体,各自独立发声,且不受限于作者,且文本中的人物意识也不受限于作者的控制,文本中的人物与作者是一样对等的客体,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力。对于复调叙事,童庆炳又进一步对其进行阐释:“在这里,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通过叙述者声音与主人公声音的对立而表现出来。这种在同一个叙事中并行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的叙述方式可以借用音乐术语称之为‘复调’式叙述。”[2]253
《来生再见》的复调性叙事结构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叙述中穿插史料依据、儿辈的探寻与父辈的记忆并行、将历史的浪潮与个人命运间悲剧性的冲突并行演绎。
(一)在叙述中穿插史料依据
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有时是通过父亲的回忆引出展开对战争的叙事,并在回忆里穿插着史料依据,深入对战争的叙事,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进一步描述战争泯灭人性的残酷。在描写衡阳保卫战争中,“我”陪父亲来到他最不愿意回忆的衡阳。父亲再一次踏上衡阳的土地,悲痛地回忆起经历过的那场衡阳保卫战:蒋介石命令第十军的将士一定要死守衡阳7天以等待增援,然而在衡阳死守了47天后,却什么都没有等来。“在那些天里,日军的飞机、大炮在这儿整天整天轰炸”“遍地都是尸体”“有的没了手臂,有的没了头颅,……在那种残酷得不能再残酷的环境中,人觉得自己是在与魔鬼打交道,或者是生活在地狱里一般”这不仅是父亲对战争亲历的叙述,更是父亲对战争发出的呻吟,是悲痛的呻吟,也是无奈的呻吟。
在叙述完父亲对衡阳保卫战的回忆后,作者紧接着穿插了史料依据,通过插入《湖南文史材料》中老兵朱懋禄的《衡阳保卫战追忆》,进一步深入揭示还原历史的真相,一方面是对衡阳保卫战进一步的补充与解释,还原了衡阳保卫战中国军和日本军为争夺据点展开激烈厮战的真实过程,揭露了日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描写了国军勇敢地与拥有先进战斗力和充足兵力的日本军从6月23日一直坚持到8月8日,却终究还是没有等来所谓的增援,控诉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而另一方面通过向读者展示真实的历史材料依据,也旨在告诉读者父亲对战争的回忆是真实的,作者在小说里对战争的描写也是真实的。
作者在父亲的回忆里穿插着史料证据的复调叙事,增加了对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同时也突破回忆里的意识形态对小说的限制,使得历史与小说文本形成一种互文性的表达。但其实不管是回忆里的发声,还是史料依据的发声都是在表达同一个主题。而这样的安排建构也扩充了叙事空间,增加了叙事张力。两条叙事线索彼此互补,最终完成复调叙事,增加了文本的亲历感。
(二)儿辈的探寻与父辈的记忆并行
小说《来生再见》的文本中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字体,两种字体展示了儿辈的探寻与父辈的回忆两条不同的叙事线,两条不同的叙事线互相穿插,两种不同的字体互相穿插,给人一种作者似乎是在讲述着两种不同故事的感觉。但其实这才是作者在叙事构思安排上的匠心独运。在小说的开始,作者以文中主人公黄抗日的儿辈小毛的身份出场,回忆父亲与母亲生活的时日岁月,回忆父亲一生参加过的大小战役,回忆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抓走关押被迫写下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然后开始讲述父亲的故事,切换成另一种字体,在父亲的记忆里把故事继续写下去。
父亲记忆里的那些战役中,几秒钟前还好好的传令兵,被炮弹炸上了天,落下来的是肉块和血雨。安乡留在他记忆里的是隆隆的炮声和机枪扫射声,是战火连天的硝烟和炸毁的一幢幢房屋,是一片废墟,是一具具国军官兵的尸体,是血淋淋的鲜血,是全团1667名官兵只剩3人的恶战之地。
这两条叙事线同时进行,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独立自主、互不干涉,但实际上却是互相交融。这两条叙事线平行发展,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便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复调叙事结构。复调性叙事小说在结构上克服了传统小说在叙事模式较为单调的缺陷。复调性的叙事模式也给文本带来了更大的叙事空间。
复调性叙事小说在结构上摒弃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用开放兼包容性的特点为读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阅读环境,使读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杂糅的多声部中去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并且对事物进行新一步的判断。
(三)将历史的浪潮与个人命运间悲剧性的冲突并行演绎
在历史大浪潮下,每一个的命运都有可能受其影响甚至被重新改写。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抗日也难以幸免历史浪潮的捉弄。主人公黄抗日原名黄山猫,他身材瘦小,长相怪异。在抗战打响征兵的时代里,本应应征入伍的是中签的哥哥黄阿狗,父母认为哥哥黄阿狗身强力壮,颇能干活,并且可以保护家庭。于是父母就偷梁换柱,让胆小羸弱对家庭做不出什么贡献的黄山猫顶替哥哥应征入伍,而年仅二十岁的他也是无奈的。黄抗日一生共参加三次战役,在常德会战中被日军俘获,后被国军官兵解救。然而半年后,于衡阳保卫战结束时,又与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投降,编入伪军。几个月后黄抗日又被湘南的游击队所捉捕,于是又成了游击队员。成了游击队员的黄抗日在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所逮捕,被关押了五天后被游击队解放才获得自由。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的浪潮里不断被搅动,起起落落,沉沉浮浮。让读者不禁从历史的浪潮下开始思索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关联。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后,黄抗日也终于可以告别战争安生过日子。然而命运并没有就此饶恕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黄抗日被认为是国民党高级特务而被关押审讯,精神一度濒临崩溃失常。他被红卫兵关押在红楼三楼西头的一间房里,窗户不仅钉死,而且加上了结实的木护窗。黄抗日就是被关在这样的一间房里,被迫写下多达十几万字交代材料,也被逼无奈装疯卖傻,只能用吃排泄物的方式来保命,妻子也因此绝望而自尽。这样一个经历过近百次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战役还能有幸存活下来的英雄老兵,却被曾经是国民党黄家镇治安队副队长的黄花菜告发,而组织却也相信一个小人的揭发而不信赖自己的同志。在历史无情的浪潮推动下,个人命运就这样无情地遭到历史悲剧性的改写。小说在表现黄抗日这个卑微的抗日老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和左派政治的含泪控诉。
而作者将历史的浪潮与个人命运间悲剧性的冲突并行演绎,又再次形成了复调性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客观描述。拥有复调结构的小说,其文本中常常会出现多种声音,这些声音各自独立且不相融合,每个声音也并不依赖于作者的意识,是与作者一样对等的客体,也不需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才得以展开,各自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力。每个声音都是一个主体,不囿于自身,也不沦为作者表达意识的工具。
二、视角的迭合与转换——历史事件的全面展现
所谓叙述视角,其实就是指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所处的着眼点,是作者表现人物、描写事件、揭示背景时的叙述角度。叙事视角其实是文本的关键,每一个文本都必须建立起一定的叙事角度,这样然后才能把文本中的人物、行为、事件、背景一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对于叙述视角,童庆炳认为:“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2]250小说《来生再见》中共采用了两种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而小说在视角方面的特色不仅仅在于运用了两种叙述视角,在小说叙述文本中还不时切换人称叙述视角。
“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强。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靠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3]306小说通过“我”的回忆带给读者一种真实的感觉。
然而,因第一人称内聚焦型的叙述视角受到时间、空间和叙述角度的限制,令作家难以为读者展示更全面的故事情节。为了给读者展示更全面的故事情节,作者在叙事视角方面还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第三人称的全知型叙述视角虽具有零聚焦叙述的无限性,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有时会限制读者的思维,使读者过多关注故事的本身,忽略了小说叙述者与小说受述者之间的交流功能。因而,作者在叙事时将两种人称叙述视角迭合并不时转换。叙述人称的转换缩小着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不仅便于展现文本中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克服了第一人称聚焦性人称叙述出现的视野死角。
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在不断追寻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探求历史的真相。小说中的“我”——小毛,开篇就开始交代关系,而“我”是按照“我爹”黄抗日的历史经历来叙述的。这部小说中,“我”作为第一人称,是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我”在带领“我爹”重走战争所留下来的遗址路线的同时,穿插着讲述关于“我爹”在抗战结束后的生活。
小说中,“我爹”黄抗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押审讯时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成为小说中“我”创作的直接激发点。作者还在小说中插入了《湖南文史材料》《中央日报》等真实史料,来加以补充叙述,从而达到使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显得有理有据的目的,同时赋予文本一定意义上的真实性。
然后作者开始转换视角,以小说中的“我”,以黄抗日的小儿子角色出场,也在创作一部同样名为《来生再见》的小说,从这样一个的独特视角出发,开始换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来进一步表现主人公黄抗日的经历。这种带有个体直接实践经验的材料的加入,成为小说突破意识形态的重要切口。
“同第一人称相比,第三人称在叙述上有两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非人格性’,即第一人称‘我’总是某个具体人物,‘直接’地出现于作品之中。而在第三人称叙述里,叙述者看不见摸不着,如同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这种非人格性使得叙述者能够灵活自如地周游于被叙述对象之间,拥有比第一人称更大的叙述空间。具体讲,既可以逗留于人物的外部做外部视察,也能够潜入人物的内部做心理透视。”[3]315
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述,从“我爹”黄抗日的视角,以“我爹”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关押所写下来的交代材料和历史资料为开始展开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作者站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从回忆出发,对黄抗日等人的打仗经历进行描写,俯视着故事文本所发生的一切。作者从一个老兵的独特视角出发,以一个老兵的口吻,用老兵的言语探索、重现并揭示那段沉重的战争历史。
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下,每一个人物和事件都在自然有序地发生着,同时何顿也充分赋予了人物权力,让文本中的人物能够自由地进行对话,不受作者的约束限制。这样一来,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就使作者在展示人物性格上更为方便。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视野开阔的全知型叙述视角,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来叙述故事,使小说文本在不同情节里会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者,从而实现全知型的叙事目的。
不同的叙述人称在叙述中具有不同的艺术功能。小说同时运用双重叙事视角,使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紧密结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转换,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得以全方位地讲述,使得人物性格命运的脉络更加分明、故事的发展更清晰完整,为文本增加了叙事张力。文本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带领下进入黄抗日的回忆中,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中转换,使得读者能从不同角度来阅读文本,全面观照。作者通过两种不同的叙述视角,为读者还原历史的真相,得以重新审视历史。
三、时序的去顺序化——历史空间容量的拓展
在小说的《序》中,作者说:“本小说时间是打乱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又放到了中间或者前面。……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但那样的话,也许要写一百万字,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便于长话短说。”[4]3作品是在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下展开的,“人并非总是理性地、顺序地、连贯地、完整地回忆往事。当叙述进入人物意识深处时,故事时序已不再适应。”[8]《来生再见》在时间上打破了故事时序,使其在记忆的支配下展开。作者之所以在时序安排上采用去顺序化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时间把故事说清,另一方面也扩展了文本中人物的叙事空间:黄抗日自20岁开始,共参与了近百次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战役,前后共4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所俘,整整打了11年仗。而数十年的打仗经历却仅仅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以至于让人无法在短时间讲述清楚,因此作者精心安排布局,在时序上采用去顺序化方式,不断对小说的情节进行颠倒、转换、跳跃,模糊传统小说时序化的叙事观念,从而来讲述黄抗日复杂的一生。
在《来生再见》一书中作者运用去顺序化的叙事方式,打破传统小说时序化的叙事模式,叙述了小人物黄抗日一生所经历的多个历史时期,循序渐进,一步步托出主人公身上所背负的沉重历史事件。作者摒弃传统的小说时间叙事的结构,将主人公黄抗日的一生切割成了一段段若即若离、断断续续的故事情节,打破时间顺序再重新拼凑起来,这样看似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但同时也增加了主人公黄抗日故事的神秘感,这样一个不足为奇的小人物身上却有一种传奇性的神奇经历体验,同时也暗示了战争的残酷性,以至于经历过战争并且能够存活下来反而成为了一种传奇般的不可思议,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小说神秘感。
小说中,作者把主人公黄抗日的回忆经历,打碎成一段又一段的零碎情节。比如小说在故事的一开始讲述父亲黄抗日犯迷糊把女儿错认成了自己的亡妻,由此引出亡母李香桃和父亲的故事,紧接着轻描淡写了父亲和母亲在文革时期受到的种种迫害,并没有深入描述父亲和母亲在文革时期受到的迫害,反而陡然一转,转向父亲1943年在湘北作战的经历,回忆那场全团1667名官兵只剩3人的恶战。过后才把父亲在文革受过的种种迫害进一步补充描写。“在‘左’的年代里,偌大的一个中国,几亿人口被划分为简单的两种人,好人或者坏人;革命或者反革命。”这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情节,不按时序化描写,虽然看起来似乎支离破碎,断断续续,但其实综合串起来依然可以拼出黄抗日的一生。
中国传统小说大都力求故事的完整,在时序上的安排,一般都采用顺序化为主。作者一反常态,打破传统小说的按时间顺序叙事的传统模式结构,运用去顺序化的时序安排进行叙事,使得小说中的过去和现在都被交叠在一起,不断地进行跳跃转换,也不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来叙事。作者似乎也有意将黄抗日的一生打碎,分成若干碎片,又将这些碎片看似随意地拼凑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就像作者在书中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敬请诸位读者注意一下年月日,只要你心里对年月日有数,你就不难理清头绪。”[4]3
应该来说,这样去顺序化的时序安排是作者苦心经营安排之后的结果。而按照小说中主要所想要描述的内容是主人公黄抗日一生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如果采用传统小说顺序化的叙事描写,虽然会使故事情节有先有后,秩序井然,脉络清晰,但会使文本简单易懂反而没有特色之处,也会使小说的篇幅巨大,更加无法充分体现黄抗日一生的波澜起伏。而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采用去顺序化的叙事之后,一段段碎片化的经历故事,反而使得主人公黄抗日的一生显得扑朔迷离,带着一种无尽的神秘感。
《来生再见》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大量的关注与研究,这与其独特的叙事安排是密不可分的。叙事策略上的独特安排,选取了并非虚构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作为表现对象,真实地还原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力图对历史做尽可能真实的还原。作者在叙事策略上的安排建构,着力让历史的真相在具体的情形中得以再现。作者在极力还原历史的同时,也旨在让我们正视历史,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