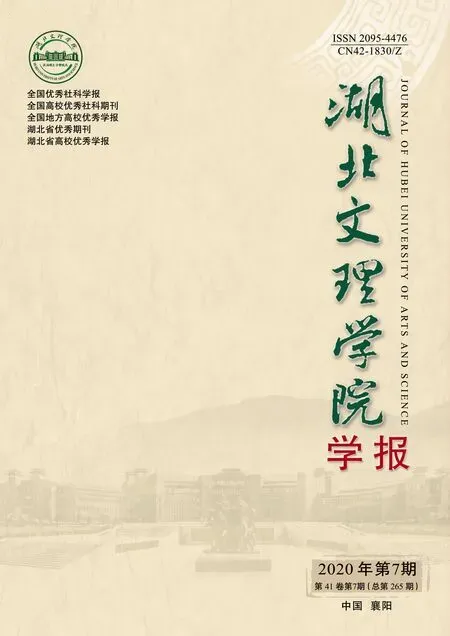六朝诸葛亮的贤相形象(上)
瞿安全
(湖北文理学院 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北 襄阳 441053)
开篇之前,有必要介绍古人按角色评价同类杰出人物的一种方式。经过正面分析和长期积累之后,往往会形成一种简便的类型化评价,其核心要件是才能和功业,尤其是才能。大致又可分四种方式。一是类似评价,包括罗列和对举。二是近似评价,是指以才能为核心的总体近似,大致可分为两人并称和直接评比两种方式。三是象征评价。已有定评的人物或单指,或并称,开始虚化成为本类型的某种象征,如“吾之子房”和“当世伊吕”。四是最高评价。同类型中一位或数位人物堪称最高典范或最高层次,成为本类型的绝对象征或代名词。这几种方式,或者偏重内部比较,或者偏重外部定论,总体上人数由多到少,人物由实到虚,标准由宽到严。前世人物成为一种标杆,当世人物会归类评比,再经后世考察认定,或者加以调整,如此反复不断。因此整个系列因后来者加入而生长延伸,调整变化,又总有一些人地位不变而保持相对稳定,作为系列生长的根基。当然,历史人物之间的评比,充满了困难和风险。没有完全相近的时代,也没有完全相近的个人,至多也只是一种最大意义上的近似,但由此可以反映评论者的眼光及对象的历史地位。
本文所谓相,是指实质意义上的宰辅,为照顾不同历史情境,含义稍微放宽,包括中枢文臣。为相者辅佐君主,论道经邦,其角色又可细分为开国创业、治国理政、受遗顾命等。顾命大臣一般系权宜设置,主要保障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和顺利过渡,考验顾命者是否品格忠诚,是否具有驾驭大局的政治智慧,而不直接涉及治国之才。本文所指贤相,主要指前两种角色,从上古到两汉,贤相辈出,经过品评,似乎可分为多个层次。至迟自西汉以来,稷契咎繇等-伊吕周召等-管晏等三个层次之分清晰可辨。
一
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1]930,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与徐庶等友人切磋,向庞德公等师长请益,读书观其大略,思想综贯诸子,文武兼资,堪称通才,胸怀宽广,志在天下,这是其成就功业的主观条件。
论客观条件,历经秦汉数百年专制统治与思想改造,汉末三国的政治体制与思想观念迥异于先秦时期。唯东汉末年又逢乱世,君臣际遇在某些方面有类先秦。
诸葛亮在隆中,藏器于身,正如东晋袁宏所说“孔明盘桓,俟时而动”[2]2125。他一面冀遇明主,有所作为;一面抱膝长啸,居然隐士风范,如不遇其时其主,宁愿隐居终老。从曹操拥献帝都许开始,中经建安三-五年(198-200年)关中初定,再到建安七-八年(202-203年)曹袁之争告终,北方大局初定,寓居荆州等地的北方人士陆续回归,诸葛亮从年方少年到年过弱冠,始终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见用于吴,诸葛亮并未南下团聚。从叔父到自身均与刘表有着亲旧关系,却不出仕荆州。建安六年(201年)刘备颠沛来荆,数年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1]876,直至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诸葛亮方才出山辅佐。足见其冷静沉稳。除了东汉政治混乱尤其是党锢之祸促成的隐逸之风影响以外,或许另有深层独到的考虑。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1]
裴松之评语:
臣松之以为袁孝尼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殊远。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以分,谁能间之?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设使权尽其量,便当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岂其然哉!关羽为曹公所获,遇之甚厚,可谓能尽其用矣,犹义不背本,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1]
裴松之怀疑《袁子》所记非实,理由一则是诸葛亮一向忠诚,不致中途生变,二则是刘葛相遇,希世一时。此论确实有理。不过,能贤而不能尽,则不足相辅,正好反映诸葛亮心声[3]。曹操、孙权虽能用人,而政自己出,气量仍嫌褊狭,丞相大多难以有为。诸葛亮选择刘备而非孙权等人,实在情理之中。《袁子》所记即便不是细节的真实,也可说是大节的真实。
刘备喜称如鱼得水,刘禅基本举国相从。刘备“弘毅宽厚”[1]892,刘禅亦“可次齐桓”[4]2275。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920;后主时期,诸葛亮不仅陈力就列,而且鞠躬尽瘁。诸葛亮慎于出处,独善兼济,择君而事,公忠体国,诸多方面颇具先秦古风。
陈寿、常璩均就刘备托孤一事对刘葛际遇大加赞赏。西晋袁淮《袁子》,东晋袁宏《三国名臣颂》称颂诸葛亮治国,均强调其君臣际遇之难得。《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袁子曰:或问诸葛亮何如人也,
袁子曰: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1]
《文选》卷四十七《赞·三国名臣序赞(袁宏)》: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2]2125
李兴之文亦称“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
诸葛亮去世,蜀臣李邈上疏,诬蔑其“身杖强兵,狼顾虎视”[1]1086,蜀国内外此等质疑中伤正复不少,又足见秦汉专制之后先秦风尚终究难以完全复制。而且,刘备父子于诸葛亮,亦似有未尽之处,后主于其未必全无嫌隙,古今学人均有发微。建安时期,诸葛亮的职务从军师中郎将升至军师将军,长期镇守后方,足食足兵,实际角色类似萧何,权力地位均似有限。刘备称汉中王,法正、刘巴相继为尚书令,直至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李严虽继任尚书令,远离成都,职权受限,诸葛亮才得以全面主政。后主即位后,十余年间他大权在握,总理军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918,相业才全面展开,内政外交用兵,政治经济文教等面面俱到,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与成就。
自西晋开始,刘葛际遇已经成为君臣际遇的最新典范。或因时人出于崇敬诸葛亮而有所美化,而据前文所述逻辑,美化诸葛亮必先美化其君臣际遇。另外,放眼三国以至六朝,刘葛际遇已属难得。媲美诸葛亮才德者可能不乏其人,有此际遇者确实寥寥无几,大多因君主忌刻昏暴,有其职而无其权,有其任而无其用,相业于是乏善可陈,本人甚至不得善终。只有先秦苻坚之于王猛,差相仿佛。王猛治秦之所以能比为诸葛亮,这大概也是关键因素。
二
诸葛亮的贤相角色可以细分为开国创业、治国理政、受遗顾命。六朝时期诸葛亮顾命亦为典范,本文略而不论。
魏晋之世,一些北方史籍及言论出于敌意,对诸葛亮多有诬罔歪曲。即便如此,所指罪名多是所谓不识时务,专权擅势,而不是为政有失。某些具体举措的记载不实,裴松之等学人均有驳正。如后主即位之初益州郡大姓雍闿、牂牁太守朱褒抗命,《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记载益州从事常房察觉,杀朱褒主簿。朱褒攻杀常房,诬其谋反。诸葛亮于是诛常房诸子,徙其四弟,欲安朱褒。裴松之认为执政必会调查此事,岂有妄杀无辜以悦奸慝,“斯殆妄矣!”笔者以为此说有理。至于北魏崔浩认为诸葛亮偏据一隅,不识时务,抗衡上国,不能比为管萧之亚匹[5]960-961,或因北魏占据中原自居正统,崔氏有意贬抑蜀汉及南朝政权,其论诸葛亮,重心也不在治国而在军事成就和政治形势,而且不计历史情境,言语刻薄,立论武断,亦不足为训。
六朝时期人们具体分析诸葛亮治国,有赞扬和溢美,也有批评和质疑,本文略举数例。
习凿齿对诸葛亮南抚夷越似有溢美,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同书卷三十九《马良传附弟马谡》注引《襄阳记》等。根据有关史实,此后南中出兵出赋,而且叛反不常,只不过旋即平定,可见南人不复反之说不实,钱振锽早就指出这一点[6]2461。当然,民族问题向来复杂,又因形势所限,南中事件未足贬其功,其实无需虚饰。
用人方面,诸葛亮慧眼识才,破格用人,提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包括中枢大臣。蜀臣吕凯称其“与众无忌,录功忘瑕”[1]1047,所言非虚。诸葛亮提拔杨洪和何祗,“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不过,其用人也有失误,比如误用马谡,习凿齿就批评说:“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1]984
诸葛亮恭敬谨慎,躬亲细务。曾为丞相主簿的杨颙对于这种工作作风不以为然,劝谏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诸葛亮谢之”[1]1083。
诸葛亮治国成就,总体上来说,新旧融合,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上既注意开源,亦注意节流。他去世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1]929,泰始十年(274年)二月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指出“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1]931从侧面证明政治和社会秩序良好。西晋傅玄说诸葛亮“治国有分”[7]132,似本于荀子。《荀子》第五篇《非相》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又《荀子》第十一篇《王霸》: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上文已经提及,荀子思想以礼为核心,治国主张礼法并重。所谓分,强调上下尊卑清楚,官员百姓各安其分。傅玄此评,或许就是肯定诸葛亮用法治国,秩序井然。
不过,陈寿总评诸葛亮治国成效,并未强调物阜民丰。袁准所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也是一种笼统评价。蜀汉以一州之地支撑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或攻或守战争连年,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不小,其政策体制或不免紧张。
文治方面,诸葛亮正己修身,选拔人才注意德才兼备,开立学校,设置学官,可以看出他重视德教文治,但三分危急,或有未遑。比如史官未置就受后人批评,陈寿说诸葛亮虽达于为政,犹有未周,至北魏李彪犹称其未曾留意,久而受讥[1,5][8]347。陈寿、袁准等人均未肯定其文教之美。陈寿说百姓“畏而爱之”,蜀国“风化肃然”,而非风俗淳美或淳厚。隋人王通感叹:“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9]46虽然肯定了诸葛亮的理想,也说明这一理想未曾实现。宋代学人不少感叹诸葛亮王道不纯,理论出发点有失迂阔,针对性却不无道理,即诸葛亮文治有限。故此,杨戏赞其“敷陈德教,理物移风”[1]1080,李兴赞其“教美于鲁”,似嫌过誉。
诸葛亮治国的主要手段和突出表现,无疑是法治严明,对此三国及后来人士一致称许。《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陈寿上诸葛亮集表及史评: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1]
无论是上表还是传论,主要篇幅都在叙述法治。又吴人张俨称其“刑法整齐”,西晋袁准称其“行法严而国人悦服”[1]934。两晋之际李兴称其“刑中于郑”。嗣后人们比其为子产和管仲,似乎都有此原因。
诸葛亮通晓法家学说,无庸赘言。他与法正等人创建《蜀科》,其著作亦包含类似内容,此为有法可依。其次是执法必严,已见上引。又《益部耆旧传杂记》亦载“时诸葛亮用法峻密”[1]1015。其三是赏罚分明,公平无私。张裔当面称扬诸葛亮:“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1]1012蜀汉亡国,樊建等人随迁洛阳。《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1]
可见包括张裔和樊建在内的蜀人对此感受颇深,非常敬服。李严、廖立事件是最明显的例证,习凿齿引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之例为比,强调诸葛亮用法无私,“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1001其四是严而不酷,平和允当,并无法家刻薄寡恩的流弊,“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就是一证。所以袁宏也说“人无怨声”,“刑罚不滥”。
魏晋之际,诸葛亮名满天下,传闻故事亦复不少。陈寿著史之前,西晋武帝时扶风王司马骏与部属讨论诸葛亮,郭冲条列其中五事,其一就涉及治国用法。《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蜀记》曰: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踰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为亮之异美,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谨随事难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难曰:案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寻冲所述亮答,专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1]
郭冲五事具体细节确有失实,章学诚表示五事实皆可疑[6]2453,裴松之所难不无道理,不过仍需具体分析。针对裴松之指出诸葛亮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李安溪认为“先主外出,既常镇守成都,则不嫌于专制矣。此难未确。”[6]2454是说有理。“刑法峻急”一语亦无可议,陈寿评语略同。后人评“刻剥百姓”似嫌语气太重[6]2453,裴难当是。相比陈寿所说百姓“无怨”,“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亦嫌太过。所以,此条精神基本符合陈寿《三国志》及相关记载,具体细节及语气可能夸张失实。《资治通鉴》基本采用,只是删去“刻剥百姓”一语,“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改作“人多怨叹”。胡三省注曰:“孔子曰:‘政宽则济之以猛’,孔明其知之。”[10]1784-1785
郭冲条列五事,意在为诸葛亮辩护。此条涉及治国而突出法治,足见魏晋时人认同诸葛亮治蜀用法,上纠汉末之失,近除二牧弊政。据田余庆先生分析,诸葛亮治蜀用法,核心在于不论亲疏远近,应用共同的刑赏准则,一统于法,消除差别,从而巩固蜀国统治。廖立、李严等被废,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为解决新旧矛盾的政治问题[11]190-207,[12]213-243。则诸葛亮用法,亦出于政治上的长远考虑。总之,正如胡三省所言,诸葛亮用法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郭冲此条不惜夸张其法治严峻,更加证明这一点。
东汉后期以来,纲纪废弛,政治混乱。用法救世,振衰起弊,几乎成为时代共识,是故三国皆行法治,士大夫亦多学法家。而魏吴用法,一则严酷,二则任性,三则不平,似乎多师申韩,用法御下。比如两国均设校事制度,深文罗织。诸多大臣或身受其害,或畏惧不已,史实甚多,此不赘述。而诸葛亮用法不仅切中时弊,似又贯穿儒家精神,公平无私,有理有节,严而不酷,峻而无怨,有其利而无其害。两相比较,优劣自明,魏晋时人或亲身经历,或辗转相传,因此诸葛亮法治才会获得如此称赞。
又上引袁宏《三国名臣序赞》称诸葛亮“治国以礼”,《文选》注云:“为国以礼”[2]2125,似出自《论语·先进》。子路率尔而对,孔子哂之,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13]938,此礼似偏指礼让。《论语》有时礼让并称,但多有针对性,礼当然不限于让。袁宏此语更有可能本自《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3]79袁宏评诸葛亮治国以礼,并无具体论证。我们只能从其《后汉纪》政论入手,略作分析。袁宏会通儒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14]132,认为仁义名教无不本于天理自然,即人心天性。落实于治道,则主张德刑并用,重在内化。如:
古之哲王,知治化本于天理,陶和在于物类。故道之德礼,威以刑戮,使赏必当功,罚必有罪,然后天地群生穆然交泰。”[15]206
所以圣人顺应人心,济乱制法,立法成治,后世忘治之本,不通分理,如商韩用法,不能为治[14]114-115。论德刑关系,则认为刑法禁之于后,礼教明其善恶,示以耻辱,如不能化民之心,而专任刑罚,则求世休和而不可得[14]577-578。依此理解,诸葛亮用法,一则宗旨在于致治,二则并非纯粹用刑,还能齐之以礼。那么,袁宏对诸葛亮法治以及治国气象的理解可能更为深入,评价也似乎更高。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评诸葛亮当政,“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注引《华阳国志》曰:
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1]
裴松之亦以为“赦不妄下”,诚为可称。又《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西晋袁准著作《袁子》:
袁子曰:亮治实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远,非求近速者也。
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
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1]
按魏晋时期本末论盛行,含义多样。袁准《正书》指出:“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16]1773此处是否同解,尚未可知。诸葛亮论蒋琬为社稷之器,而非百里之才,“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1]1057。与“治实而不治名”似乎意义相近。结合治实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远,有余力而及小事等语,所谓诸葛亮治国知本,本立而后末治,似乎是指其把握全局,着眼长远,既注意保障底线,又注意长治久安,保障全面整治,全民受益,避免苟且、急迫、片面和琐碎,更不会为求虚名而施以小恩小惠。赦不妄下,应是为政知本的具体例证,其法治似亦贯彻此种理念。
综而言之,诸葛亮治国成就,或许政治层面高于经济层面和文教层面。论其为政,可能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间。举凡经济,民族,文教上的未能尽善,概因时势多艰,治国非易。严格来说,蜀汉政权虽然建立,诸葛亮终其一生仍在创业,并非和平状态下的治国丞相。尽管他苦心孤诣,矛盾处理得宜,百姓生活安宁,究竟不能如统一王朝气象雍容,长远规划,全面落实。或许时人及后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除了一些具体细节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外,并没有指出其治国有何重大失误。不仅如此,结合二袁所论,诸葛亮虽治小国,规模气象确实不凡。在六朝人眼中,诸葛亮能够超越同侪,比肩先贤,或许这才是关键所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