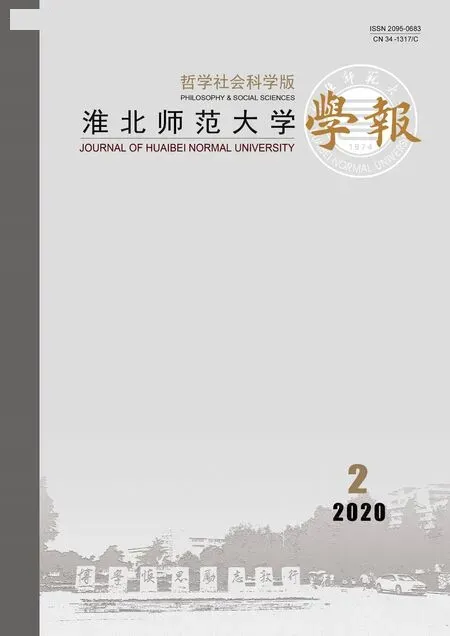从陈映真小说看其思想的超越性──以小说集《忠孝公园》为中心
赵修广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台湾眷村长大的赵刚近十年来《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2011 年)和《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返台湾1960年代》(2013年)等著作把陈映真研究推到新高度。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他在文本细读上下了很大功夫,对陈映真小说的分析与解读有很大贡献,特别是对其中“左翼男性主体”成长历程中的理想主义反思、两性关系问题和外省人在台湾的处境问题每每有令人豁然开朗的论断,当然也有对某些细节寓意的过度诠释等可商榷之处。他认为,“陈映真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恰恰正因为他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不以‘思想’为名、出名。但,除了他,还有谁,以思想之孤军,强韧且悠长地直面这百年来真实历史所提出的真实问题?”[1]吕正惠也说:“陈映真是台湾三十年来的作家之中最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的人”[2]219。陈映真2016 年去世后,赵刚在祭文中表达对先生超越性思想与实践的崇仰:“陈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动了冷战年代知识青年如我的荒废之心。先生是一个战士。他的小说是战斗的文章,更别说他的论文、他的文论、他的《人间》杂志,与他的人间出版社了。先生哪里只是对抗台独的斗士,他是中国人民的斗士,是第三世界的斗士,而他更是孤身对抗一种‘文明观’的斗士。这是先生的永恒业绩。”[3]陈映真留下的文学与思想遗产宝库有待进一步挖掘梳理与阐发以便更好继承,这是一个巨大工程。我们从陈映真长达40年的小说创作里,能够清晰地看到近现代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史,体认他历久弥坚的正义信念、底层立场、国族认同,以及在台湾当下语境里“不合时宜”的他仿若堂吉诃德一般对美日经济与文化霸权的反抗中体现的现实战斗精神与深沉厚重的历史感、思想的前瞻与超越性。
一、“向外批判与往内反省”的左翼思想者
陈映真少年时读到鲁迅的《阿Q 正传》,大学时用“做家教挣来的钱在牯岭街的旧书摊上买书”[4]36,涉猎了鲁迅、巴金、茅盾的作品以及《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还有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的经典著作。1959 年读大学期间发表小说处女作《面摊》,写身携病弱年幼孩子从外地到台北做饮食小买卖的一对夫妻艰难谋生中从一年轻警官那里感受到的善意体恤与温情,这一短小稚拙的少作标示出他的底层立场和以鲁迅为楷模的旨趣。那孩子令人揪心、不时“爆发”的“长长的呛咳”、咯血如同鲁迅小说《药》中的华小栓一样,是社会底层人民深重疾苦与不幸的隐喻。而孩子执著寻找、凝望、不停念叨“橙红橙红的早星”的情景在小说不长的篇幅里出现4次之多,寄寓着对红色中国大陆的深切向往。
《面摊》之后陈映真小说的人物大多以感伤、凄然的自戕而告终。《我的弟弟康雄》以一名嫁为富人妇的姐姐的口吻,倾诉了对18 岁即自戕辞世的理想主义者弟弟的伤悼和无尽的哀痛。“激进的弟弟”康雄仰慕雪莱,曾“在他的乌托邦里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但这一切不过是耽于空想罢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他幻灭和自尽。康雄这个“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5]赵刚2010 年解读此篇小说时认为,康雄“不是一个虚无者,因为他还有一种很深的宗教或道德情操,一种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非比寻常无可救药的深度许诺,深到不为我等现代凡夫俗子的善美真诸价值所可以论测;它一旦崩坏,他的生命也将无以立。”“沛沛然有著这种洁身自好不欺暗室的道德情操,以及饥溺如己的社会意识的康雄,怎会是一个虚无者?”[6]
在陈映真去世三年后的2019 年,赵刚再次将他与鲁迅做比较,有了新的发现:“康雄也死于自己所累积的慢性的毒:他的孤独、的冷漠、的傲慢、的拒绝,的‘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语出鲁迅《一件小事》,引者按),即先前所说的‘局外人之毒’。”“一种孤独的、傲慢自是的‘左’,带来了一种深刻的虚无不诚。”[7]《呐喊》是陈映真读初中时的第一本启蒙读物,鲁迅从自剖出发反思人性的阴暗面,启发导引着早慧的他走向时刻省察自己的爱国、左翼的人生道路。“《一件小事》让‘我’(希望以及我们吧)理解到,固然我们要看到这体制的、‘局内人’的毒,但也更要看到与彼紧张乃至对立的自身之毒。自己要先识毒解毒,然后才能解他人之毒;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此而言,鲁迅与孔子并无二致。”“我相信,不只是《呐喊》时期,鲁迅终其一生恐怕都在与这个虚无的、冷漠的、恶意的、否定的‘毒’搏斗着吧。对抗这个毒,与学习、成长、热爱生命是一体两面。”[7]
青年陈映真在岛内白色恐怖中深感压抑,无时无处不身受社会体制与环境之毒──“局内人之毒”,同时,也像鲁迅那样勇于解剖自己,直面自身之毒──“局外人之毒”,改过自新,实现生命的不断超越。他对传统左翼理念的超克,是从自反、内省开始的。康雄与姐姐的身上都有陈映真的影子。陈映真在1960年代和七等生与王文兴等人同属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阵营,但陈映真与后者的不同在于他总是将性或青春期苦闷和左翼的、禁忌的理想主义,以及一种非体制化的基督教信仰,绾在一起作为人物的人格背景与小说叙述、论辩的基础。“从宗教与传统中汲取抵抗现代与当代的思想力量,是‘陈映真左翼’或‘陈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却又长期被忽略的特质。这个意义,超越了一般将宗教等同于个人信仰与解救的那个层次。”[1]
取材于圣经故事、为叛徒犹大翻案的短篇《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 年)是讽世并自剖的进一步深化。小说里的犹大眼界高远,襟怀阔大,反对代表以色列上层社会的“奋锐党”人自诩为上帝特选子民的褊狭,反对外族奴役,更反对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主张超越犹太民族失国为奴的“被虐”情结,联合被压迫的“外邦人”包括“那些无数的为奴的罗马人”一起反抗、颠覆罗马贵族阶级的暴政。犹大对“神之子”耶稣先是心折,后来发现他虽有“高贵的仁慈的风采”,有毋庸置疑的“对待罪人、贫贱者和受侮辱者的诚挚的爱情”[8]26,并且能大义凛然地谴责“法利赛人”等“支配者”,挑战“图谋暴利的制度”,但是却止步于自我神化的作秀,“漠视群众的激情”,只会耽于“梦想”,无心发起实质性的人民解放运动。犹大失望之余,欲借罗马人屠杀耶稣之手,“激怒那些深爱着耶稣的群众,叫奋锐党人起来领导推翻罗马人的运动”[8]31。然而目睹“这些疯狂地喊着处死耶稣的人众,不正就是七日前以王称颂着他的那些人吗?”,犹大见识了人性的诡谲、险恶,凝望绞刑架上的耶稣,“他忽然明白:没有那爱的王国,任何人所企划的正义,都会迅速腐败。他了解到他自己的正义的无何有之国在这更广大更和乐的王国之前是何等的愚蠢而渺小”。[8]32-33
此作肯定犹大唤起“人民的崛起和革命的胜利”的奋勇精神之外还蕴含对苗头初现的台独潮流的警觉。早于岛内台独思潮兴起近20 年,青年陈映真已经对之产生警觉与论辩,足可见他眼光与思想的超前。赵刚认为奋锐党代表了一种右翼的“民族主义基本教义派政党”[9],“陈映真对‘奋锐党’的批评几乎完全可以是作为之后对台独民粹主义的批评”[10]。犹大可看作时年24 岁的陈映真审世与自审的重要凭借。陈映真在1960年代的台湾“看到了自我的苦闷与人间的疾苦在台湾社会中如何生成,而这背后的历史脉络,无不指向了中国的贫弱与分断。”“陈映真尖锐地批判了犹大无能于爱与信仰的状态,失去了现实土壤与人间情感的理想,必然会轻易地走向背叛。”[11]同时,这也是陈映真的自我批判。“纪录、理解、解释并批判这个世界时,陈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着自己。这个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与往内反省’的双重性,使得陈映真的文学从来就不具一种说教味、训斥味,一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大势的支撑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极为夺目地显现出这样一种真理使徒的姿态样貌。历史上,左翼,作为另一个启蒙之子,当然也有过那样的一种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陈映真从很早很早,就已经展现了他对这样的一种‘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状态的忧虑。于是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一篇中,塑造出‘犹大左翼’这样的一种原型,指出他在‘理想’与‘自省’、‘恨’与‘爱’之间的失衡。我们当然也要读出,那是陈映真对自身状态的反省。”[1]
拿《将军族》(1964)与歌剧《白毛女》(1945)、电影《红色娘子军》(1960)做一比较,有助于深入体认陈映真的社会批判与心之所向。这三部作品都是古典“英雄救美”叙事模式的现代变形演绎。不同于《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中女主人公的被拯救成功,《将军族》里拯救者──大陆退役老兵“三角脸”与被拯救者“小瘦丫头”在台湾的黑暗环境里都难以逃脱恶势力的侮辱与戕害,自惭形秽,怀着对来世身心纯洁、两情相悦的梦想殉情自尽。“在《将军族》中,两个饱经挫败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托在一个神秘的渺不可知的未来世界——来生”[12]。因为处于“新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一九五〇──九六三)”和“一九六三年以降的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阶段”[13]26的台湾,处在“外来(美国)干预”“封建主义”笼罩下,人生自然要呈现“被牢不可破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13]22。
《将军族》里凌虐、逼迫“小瘦丫头”卖淫的“大胖子”与寄予她无限同情与无私援助的“三角脸”都来自大陆东北,却分别代表了人性善恶的两极。一是前者对女孩灭绝人性的肆意侮弄与残害;一是后者与台湾女孩间相濡以沫的阶级情感。“陈映真,找到了一种把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情感、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从基督那里得到的,和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在他善良而敏感的天性中烙印下来,那就是一种‘底层’的立场,也是一种超越国族、种族、宗教藩篱的立场: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理解和关怀的。”[14]
陈映真直言不讳自己“是个主题先行的作家”[4]49,对“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大不以为然。他的可贵在于,“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弱势关怀的层面取得了奇妙的结合,而宗教信仰下养成的自省、谦卑,以及对‘爱’的期求和宽容,也使得陈映真的思想不曾倒向偏激,使他的写作即便‘主题先行’也不会僵硬得令人生厌。在理念上或许激进,在面对复杂的台湾现实的时候,他的文学,可能更多了‘温情’。”[14]“主题先行”并不意味着与艺术自律水火不容。洞悉人性百态与真谛的作家或许并不刻意追求艺术的精致圆熟,但却因胸怀、立意、眼界的高远,会在不经意间成就浑然大气的艺术气象。这样雄才大略的高手,在现代左翼作家中,如茅盾、丁玲等人,并不罕见。陈映真的《将军族》《夜行货车》《山路》等也是这样的杰作。
二、不变的正义情怀与第三世界归属意识
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而度过七年囚牢生涯的陈映真1975年出狱后曾供职于跨国公司,在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成为严斥买办文学、捍卫民族立场的中坚力量。同时或稍后,更以《夜行货车》《山路》等小说宣示第三世界归属意识,提醒左翼人士勿忘解放人类历史使命,彰显了台湾当代乡土文学呼应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生命力与审美价值。
《山路》的女主人公蔡千惠为了替在白色恐怖中自首叛变的哥哥赎罪,与富裕家庭决裂,来到一贫如洗的烈士李国坤家,代行儿媳、长嫂职责,而当小叔子成功跻身上层社会白领阶层后,那随岁月流逝而日渐淡忘的普罗大众理想情怀,却在暌隔几十年的昔日恋人黄贞柏出狱之时蓦然袭上心头。千惠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与家人良心的救赎,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惊醒、意识到“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15],在不知不觉间告别了青年时的信念。对丢弃信念的追悔、罪感令她无法面对“还阳复活”的贞柏,遽然病逝。
赵刚称道陈映真的36 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篇篇传世的‘列传’,比历史还真实的历史。”“陈映真文学,其实竟是历史的救赎,它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并遗忘的‘后街’人们以眉目声音,再现他们的虚矫与真实、脆弱与力量、绝望与希望,让读者我们庶几免于被历史终结年代的当下感、菁英感与孤独感所完全绥靖,从而还得以有气有力面对今日指向未来。”[1]除了以“死亡”情节模式的设置表达悼念烈士、理想受挫之外,早前陈映真还密切关注经济起飞之后“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即“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炫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13]27。在台湾经济起飞的1970—1980 年代,跨国资本控制下的芸芸众生无计逃脱美国经济、文化霸权的笼罩,跻身中产阶层的所谓精英之士不乏对洋大人奴颜媚骨、曲意顺从的。《夜行货车》马拉穆国际公司里,台湾职员林荣平为升迁而讨好美国上司摩根索,不惜以情妇刘小玲作诱饵;刘小玲的现任情人、公司新锐詹奕宏无法忍受摩根索酒酣之际对刘小玲脱口而出的糟践中国人的脏话,起身要求他为失言道歉,并愤而辞职。本来因刘小玲的前情而嫉恨不已、屡屡诉诸暴力的詹奕宏最终接纳了她,赢得她的倾心相许。刘小玲取消移民美国的计划,随詹奕宏一起返回南方乡下。
詹奕宏向摩根索发难,起因于却不止于刘小玲被冒犯。其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勇敢捍卫个人与民族尊严的傲岸身躯显得格外动人。陈映真赋予詹奕宏一种素朴的人道主义甚至左翼思想感情,詹奕宏本就同情被压迫者、被害者,他不忘民族本源,不会陷入“族群民族主义”的感情黑洞。小说结束在“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这一句。某些独派文人据此津津乐道“本省愤青詹奕宏把一个‘外省婆子’带回南部故乡本土了——这还不让人提气吗?”,因而激赏此作。殊不知陈映真在此处刻意以“南方”取代台湾社会惯称的“南部”,“‘南部’是地理名词,而‘南方’则可以且经常是政治概念。‘南方’就是第三世界”,“陈映真鼓励詹奕宏站上一种反抗的第三世界的位置”[10]。
“回顾陈映真的小说创作史,我们看到了《万商帝君》是陈映真头一次以小说的形式直面迎击了台独运动,但不是第一篇直接(而非以寓言的方式)介入台独运动。第一篇是《夜行货车》。以陈映真的敏锐,他是在预见此一汹涌大潮即将来袭之前,写下这篇小说,并营造了‘詹奕宏’这样的一个人物典型,企图‘打预防针’,引导青年感觉,导引它走向一个超越狭隘本土意识,具有某种左翼第三世界观与素朴人道主义的政治方向。”[10]
詹奕宏回归乡土,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反抗、摆脱美国政经与文化霸权的情志与夙愿。而作为对照,《万商帝君》里可怜的乡下仔林德旺为跨国公司优渥的物质环境所“俘获”,怀抱着“经理梦”,背弃乡土与亲人,却始终无法跨越阶级鸿沟获得晋升,成了疯子。好似鲁迅笔下的“狂人”,穷困潦倒的林恍惚间竟从饮食店的菜肴里发现“掺杂着人的耳朵和指头”[16]的“吃人”证据,这当然是由于他神经错乱的缘故,但需要注意的是,陈映真师承鲁迅,透过癫狂者林德旺的幻觉视角,把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实质作了具象揭示。林德旺是台湾的象征,他对跨国公司美式生活方式的痴迷与追随、对升迁的渴望,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及、一厢情愿的幻梦而已,其悲哀不幸是盲目崇仰美国、离弃乡土、曲意顺从新殖民主义文化逻辑,鄙视第三世界却最终伤害自身的台湾命运的缩影。詹奕宏与林德旺,一正一反,陈映真藉此阐明、倡导明确的第三世界归属意识与弥足珍贵的主体意识。
三、近现代史视野中关于殖民主义恶灵的思辨
2000 年国民党败选后,秉持台独理念的民进党首次执掌政权。《忠孝公园》叙写此时台湾岛内日本殖民历史沉滓泛起,国家认同歧见纷纭、族群撕裂下大陆来台苟安一隅的政治投机者侥幸心理破灭的混乱情状。小说对美日新老殖民幽灵徘徊肆虐,盘根错节、纠结缠绕的历史罪恶难以清算,正义不得实现的种种政治怪象有不动声色、深入肌理的刻画。它选取前台籍日本兵林标和来自前伪满洲国日本宪兵队的宪警马正涛这海峡两岸两位80岁左右老人的视角,以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展示殖民后遗症作祟岛内等灾难。
《忠孝公园》的篇名大有深意存焉。陈映真以饱经沧桑的阅历洞彻人性的复杂、善恶纠缠。马正涛与林标两人年相若,且都曾进入日本在殖民地战时的军、警体系,先后经历日本人、国民党的统治,一路从血雨腥风、颠沛流离中走来,不同的是出身剥削阶级的马正涛甘作日本人的鹰犬、国民党的爪牙,出卖良知,丢弃民族气节、人格,“有奶便是娘”地取媚主子换取个人仕途通达。他是为虎作伥、血债无数的投机分子,后半生苟活于台湾,国民党败选后失去依恃,畏罪自尽。而台湾农民林标在二战中被历史潮流裹挟着编入日军出征菲律宾,被宫崎小队长打掉两颗血牙还被骂作“清国奴”。天良未泯的他,曾冒险救助日军铁蹄下的菲律宾华人侨胞一家。一生处于社会下层,是被欺压盘剥的“穷人”,但因为身中皇民化运动之毒,在1990 年代中期李登辉亲日路线误导下,他迷失了自我,那些几乎湮没的历史碎片──“天皇赤子”身份,竟然又凝聚成形,如鬼魂附体,时而作祟。老林标怀着争取日本政府“恩给”“补偿”的心愿加入台籍日军“战友”集体怀旧运动。他荒谬混乱的国族认同和对自己身遭日军官欺凌屈辱史的不追究,颇有阿Q 之风。令他绝望并“咆哮”的是他们这一群体作为“天皇赤子”的忠孝心迹遭到始料不及的嘲弄与鄙弃。
战后台湾经济受制于美—日经济圈,民族工业不能独立自主和壮大,工人权益无保障,资本积累是以牺牲底层人民的权利、福祉为代价而完成。林标一家三代人不幸离散的境況正是在美日台反共—安全体制中资本积累下的结果。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和战争责任因冷战格局的形成一直没有得到清算,因而,在日台间出现了历史依然作为“现实”而非“历史”而发生作用、殖民主义改头换面存在的诡异现象。“人性在历史的变动中经受磨折与考验;而当下社会里,族群的异议与纷争、身份的焦虑、文化的失据,莫不根源于艰难而扭曲的近代史。”[14]
“陈映真几乎是竭其苍劲之力,以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直面当代台湾的殖民主义恶灵。他以前伪满洲国特务与前台籍日本兵这两条虽说没有交集但共处一个东亚时空的生命并行线,刻画出当代台湾忠孝家国社会基底的毁败崩颓。否定被殖民者的家国认同,让他们对所从来的过往世世代代的集体劳动与精神天地失去敬与畏,让他们失去一种历史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且沾沾自喜于当一个志愿亡国者,是新旧殖民的共同目标。”[17]从《面摊》到《忠孝公园》,陈映真鲜明坚定的底层立场、左翼第三世界观、中国情怀始终未变。他坚拒狭隘偏激的“台湾意识”。对识不破美日台社会政经、文化结构的欺骗性与其阶级壁垒、种族歧视的反动实质,怀抱中产阶级“经理梦”的林德旺,效忠日本天皇的林标,陈映真采取“哀其不幸,怒其不悟”的复杂观照态度。既然个人的价值取向、国族认同在迷狂中背离了自己所属的阶级、民族,而向兜售政治谎言的当局、殖民经济与文化霸权靠拢,充当炮灰、牺牲品的不幸命运也就成了必然。林德旺只能身绘“血红、斗大的英文字:MANAGER”在癫狂中发泄积郁;林标则悔之晚矣。
当年鲁迅感念藤野先生“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18]其间“小”与“大”的甄别与区分正见出鲁迅的伟大。他完全摆脱了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桎梏,永远站在受欺凌荼毒、反抗不义的人民一方,如左拉为蒙冤的犹太军官倾力辩护那样履行现代知识者的正义使命。“《阿Q正传》(1921)的伟大,首在它对阿Q 的暴露分析是包括了作者自己。”[7]陈映真与鲁迅的心灵相通,他不光是伟大的爱国者,还有着更博大的国际主义情怀。历经台湾白色恐怖、经济起飞,以及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扩张,他的第三世界立场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愈加坚定。作为孤独的时代先行者,他的思想与实践无疑具有超越性。
陈映真作为知行合一的学者型作家、公众知识分子,对传统左翼思想、理想主义既坚守又有超越。他始终站在社会底层以及遭受新老殖民主义迫压的第三世界一方,反抗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与阶级压迫,为讨还历史公正、社会正义而奔走不辍。他以小说、戏剧审美艺术形式,亦诉诸思辨、论议,回溯历史,介入现实,揭发美日政经、文化霸权渗透操控台湾的伪善、欺骗性,剖露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美学政治霸权对第三世界全方位的宰制,从而证明反帝反殖民主义不仅要从知识、道德、实践层次着手,也要着眼于日常无意识的美感经验与判断层面。他从台湾近现代被日本殖民统治、冷战中充当美国反共桥头堡的纵深历史中发掘社会诸种病象的症结所在,对台湾存在的数典忘祖、仰美鼻息、媚日的政经与文化结构痛加针砭。台湾与大陆休戚与共、永难分离,陈映真是主张“在中国历史的现代中”[19]筹划台湾未来、心系天下苍生福祉的守夜人,他的价值追求、思想的超越性,给予我们宝贵启示与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