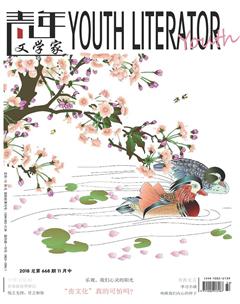论陈映真早期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
摘 要:台湾作家陈映真对现代主义历经“接受——反思——批判”的过程,其早期创作的《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劇》两部小说集便带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以悖德的描写为前卫,大量死亡叙事的充盈,皆指向他早期的创作并未脱离现代主义的范畴。
关键词:陈映真;早期小说;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柳飔(1994-),女,汉族,重庆巫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2
台湾作家陈映真被大陆学界定义为台湾左翼作家,甚至有人称其为“台湾的良心”,将他定义为两岸文学交集的连接点。陈映真将自己的小说完全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在现有的关于陈映真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大都追随陈映真的思路。笔者以为,陈映真早期创作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他是从现代主义阵营出走的小说家。
一、陈映真之现代主义观点
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陈映真曾提及“是不是现代主义,不能仅仅看技巧的问题。比方说,我刚刚所讲的,中国的第一篇了不起的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实际上就有很多所谓的现代主义的质素在里面,比方说潜意识,或者不正常的心理学,特别是他的很多散文诗是如此,可我们绝对不能说鲁迅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他认为自己只是单纯地采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却在作品“意义”的追求上与现代主义产生本质的矛盾。
首先,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而是由许多具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派别汇成的一股文艺思潮。“光复以后,三十年来台湾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可见一个特点,就是——西化,受西方的影响或东方日本的影响很大。”台湾社会出现“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权威的反抗”思潮,文学同人杂志纷纷创刊,《文学杂志》、《笔汇》、《现代文学》指导台湾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向,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台湾传播开去。
现代主义几乎形成一股合力席卷台湾文坛,陈映真也身陷其中。他于1966年之前创作的小说悉数刊登于《笔汇》、《现代文学》。“《笔汇》笼罩于现代主义的潮流之下”,故陈映真初登文坛所倚靠的正是现代主义发声的重要阵地,并积极参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论及《现代文学》,“可以说是当时台大外文系的习作杂志,他们学自西洋文学,以中文实践。在西洋文学中找传统,去模仿西方文学的内容”;《文学季刊》,最开始的时候,“西方的东西在这本杂志中仍占有很大支配力,我们也曾花过很多力气,把还看不太懂的西方文学评论很吃力的翻译出来,同时又介绍作家和流派等等。”陈映真最初所采用的文学形式依然是借助西方输入的形式和情感,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来源一致。故在此之前,陈映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则是暧昧不清的。
其次,陈映真认为现代主义是一个创作方法的概念,现代主义忠于反映这个时代,“反映现代人的堕落、悖德、惧怖、淫乱、倒错、虚无、苍白、荒谬、败北、凶杀、孤绝、无望、愤怒和烦闷”。陈映真早期作品中,运用了比较多的象征手法,很多死亡意象,有很多绝望、虚无、苍白的东西,以表达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的心绪情感。从这个维度观之,其早期创作未能脱离现代主义的范畴。
《我的弟弟康雄》一辑便交织着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由贫穷造成愁苦心绪的形成,以及改变现状的苍白无力感;《家》记叙父亲离世后,在众人议论中的“我”如何不堪沉重的家庭最终走向个人的毁灭;《故乡》仍以父亲的死亡为叙事背景,着力描写大学毕业的小知识分子的恐惧,尤其是对农村生活、家乡的陌生与不适应。
综上所述,陈映真对现代主义特点的把握阐述正好接合起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他沉湎于小知识分子极端心理世界的描摹。陈映真将自己早期小说的色彩归纳为“契诃夫式的忧悒”。因此,他早期的创作并未脱离现代主义的范畴,只是陈映真自己和一般的闷局中的小知识分子的无气力的本质在艺术上的表现而已。
二、陈映真早期小说的现代主义分析
六十年代之交的台湾文坛沉浸在西方现代主义模仿的潮流之中,陈映真不仅没能摆脱现代主义的影响,反而进行着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他会同朋友一起创办《剧场》杂志,宣传现代主义的方法,介绍西方文学流派。其早期文本也充满着“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弥漫忧悒、感伤、苦闷的情绪。
首先,夸大官能、肉欲的存在,以悖德的描写为前卫。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夸大了官能、肉欲的重要性,以官能和肉欲证明个人的存在,以悖德的描写、反社会的描写为前卫”的特征都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我的弟弟康雄》一辑中每篇小说都出现情欲的萌生、个人心性的自由表达。其小说多以自传体形式,以第一人称来展开故事情节,擅于采用大胆的直白和细腻的心理分析,其中关于“情欲”的露骨描写充盈在他的文字之间。《猫它们的祖母》中娟子同外来军官陷入翻云覆雨的情欲中无法自拔,甚至在娟子祖母病危之际依然深陷其中:
“这样欢愉的片刻中袭击着他,这很激怒了他,便吻着伊吻着伊,高连长的声音这才逐渐地荒废过去。他兴奋起来……他感到征服和残杀的快乐了。夜似乎极深,但欲望却一直在上升着。”
《那么衰老的眼泪》讲述康先生与其保姆阿金结合引起家庭极大震荡的故事,并多次在叙述中毫无遮拦地对性爱进行描写;除去直接的刻画,《死者》一类便隐约表露个人情欲的萌芽,但主人公所迷恋的对象却是悖德的,《死者》中林钟雄因外公去世回到家乡,在尴尬无法融入的氛围里对自己的二舅妈产生出朦胧的情愫。陈映真早期小说中存有“夸大官能、肉欲的存在,以悖德的描写为前卫”的特征,无疑证明他曾在现代主义风潮的侵袭之下以实践伴随着无尽的反思。
其次,死亡叙事的充盈。陈映真笔下的人物已经构成一组独特的死亡系列现象,各式的死亡构成死亡的价值和审美意义,在《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剧》两辑中,其中每篇小说都伴随着主人公的病态与离世,或以父亲死亡为叙事背景。
《我的弟弟康雄》中,康雄正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怀抱着献身于建造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世界的热情,但是处于力欲维持既有秩序的上层与希望有所改进的下层之间,这种理想主义便带有不彻底和空想的性格了。同康雄一般的人,还有《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面对战争的创伤、民众的麻木、后代的无望,他同样选择成为一个活在想象里的改革者,但他们对自己无力改变现世耿耿于怀,在内心百般折磨中消亡。
如果说康雄、吴锦翔是在外界与个人内心世界的碰撞中败北,在旧体系的包裹中挣扎至死。陈映真笔下还有如同《家》的主人公一类的人物,父亲的死亡标志着旧体系的倾颓,面对如何建立新的秩序他们无能为力,他们选择逃避,终而离开他不愿再接触的故乡。
上述作品中充满着对生活和理想狂热追求和在丑恶现实面前碰壁后无穷忧郁的情调,是陈映真自己思想状态的反映,他在意识到小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的性格本质之后,意欲从那种无力感中挣脱出来。
“他不曾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的运动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他不曾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
故对于初登文坛的陈映真而言,浓厚的社会意识并未融入进他的创作,他更多的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脆弱而又小心地自伤自怜,他开始描写一系列知识分子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下,在走向末路的过程中所伴随的人性探讨,对倾颓、虚无的刻画,正成为陈映真小说中现代主义色彩的注脚。
“陈君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是一些贫困的、虚无的、充满浪漫气质的青年们,一方面被思春期的苦恼所困扰,一方面则怀抱着美丽的梦想,而康雄一群人便是最好的代表。”
陈映真欲用小说人物的死亡来撕碎潜藏于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改变苍白与荒谬的挫败感,康雄群体以几乎同样的原因、方式走向末路;同时他以乌托邦的破灭,来预示终极关怀的丧失,个人绝对的自由与解放或许是不存在的,但知识的功能就在于寻求某种乌托邦,这样才不会丧失改良的动力。
综上所述,陈映真早期小说中对个人情欲的直白刻画,大量采用死亡叙事,表明他仍然无法逃脱现代主义的审美标准,他倔强地用无数死亡来抵抗不自觉流动的忧悒、孤独与苦闷。这种抵抗自然成为陈映真在《唐倩的喜剧》一辑之后的出发点,从现代主义出发,导向另一种创作风格的形成。
三、总结
陈映真对现代主义创作经历“接受——反思——批判”的过程,同时也经历批判程度上的变化。陈映真文艺思想的转变是社会、经济、文艺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战之后,台湾的精神生活陷入“西化”的迷阵,“对自由的向往或对西方倾倒的心态,是三十年来台湾新思潮的主流”。陈映真也在这一思潮中苏醒,他首次意识到“民族性”的重要性,不再支借西方输入的形式和情感,着手去描写当时台湾的现实社会,力欲证明现实主义的无限辽阔性。
综上所述,陈映真的创作理念是呈现明显变化的,其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色彩是无法隐蔽的事实。从早期(1959-1965)的现代主义绝对影响之下的青苍、忧郁的创作,到《文学季刊》创刊之后的现实主义、民族文学的倡导。陈映真多次在不同场合中试图主观割裂自己与现代主义阵营的关联。其文学立场的根本性转变发生在“乡土文学论战”的爆发之后,他在随后的创作生涯中极力倡导台湾的现实主义写作,希望挖掘台湾社会的真实素材,寻找能真正反映一个时代的文艺。
参考文献:
[1]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J].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
[2]陈映真.陈映真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2009.
[3]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M].台北:台北洪范书店,2001.
[4]陳映真.唐倩的喜剧[M].台北: 台北洪范书店,2001.
[4]陈映真.将军族[M].台北:远景出版社,1975.
[5]尉天聪.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A].陈映真作品集[C].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6]黎湘萍.台湾的忧郁[M].北京:三联书店,1994.
[7]古远清.一个陈映真,两种不同诠释[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8期.
[8]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J].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