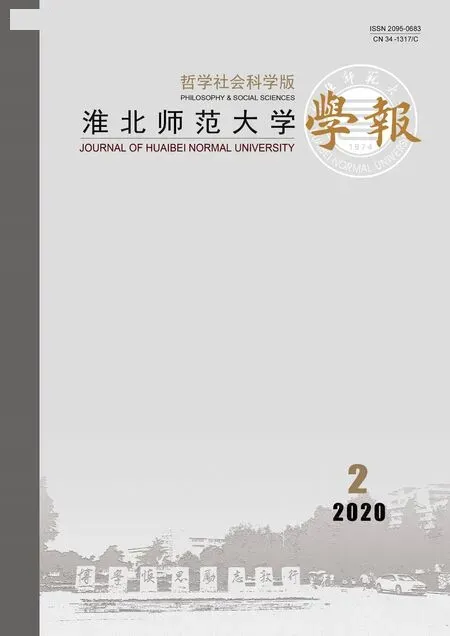清代士绅家族闺秀女德闺范内的追求与自由——以清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女性文学活动为例
吕 菲,吕 迅
(1.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230061;2.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100006)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最为繁盛的时期,所谓“超轶前代,数逾三千”[1]。不仅涌现出诸多个性鲜明、成就斐然的女诗人、女作家,更有色彩趋同、风格一致的才媛群体以地域与阶层方式显现。本世纪以来随着对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升温,对文化重镇桐城的才媛关注度也日益增强。桐城历史悠久,文理昌炽,清代更以桐城派名震天下,且世家望族林立,其中又以桂林方氏与麻溪姚氏文化成就最高,享誉全国。明清女性文学呈现家族化特点已为学界公认,尤其是地方士绅家族,其女性文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家族特色。所谓士绅,指的是地方上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官僚与文化地主的统称,是拥有一定特权的地方精英与名流①本文中士绅的概念综合了费孝通《中国绅士》(1953)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955)以及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中的观点。。清代士绅家族在国家阶层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桐城方、姚、张三大士绅家族的发展及特点看,麻溪姚氏家族在文化上可与桂林方氏比肩,比宰相张家略强,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比桂林方氏符合地方士绅望族的连续性与影响力②桂林方氏以中一房(方以智)和中六房(方苞)人才出众。中一房入清后不仕,后代多以薄田教馆度日。中六房自明末迁往金陵,且遭受丁酉科考案和《南山集》案两次重大打击,直到第十七世方观承才重振。,其女性文学活动也更为丰富,也就更具有样本意义。本文拟对清代麻溪姚氏闺秀群体的文学活动进行考证与分析,并以此为观察窗口,解读地方士绅家族闺秀共同的文化境遇。
一、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文化背景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因自元时世居桐城大宥乡之麻溪,因而得名。麻溪姚氏是清代著名的文化望族、文学世家。清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引乔损庵言:“国朝自康雍以来,父子祖孙踵为大儒,著书之多……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历三百年而未有矣,则未之前闻,求之史籍,亦罕其匹。”[2]据统计,姚氏家族成员留有著述者91 人,著作百余部[3]3。像清初姚孙棐、姚孙森以诗名重一时,姚文烈、姚文勋、姚文然兄弟皆能文章,有“江北三姚”之称,又有姚士陛与兄弟士在、士封、士陆、士对声响文苑艺林,更有桐城文派开山祖姚鼐,桐城诗派的先导者姚范,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姚莹,清末文史名家姚濬昌、姚永朴、姚永概等,可以说对整个清代文学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姚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同样突出。桐城知名文人潘江言道:“蕊榜珠联,瑶篇玉缀。(姚氏)一门科第之盛,盖吾桐所未有也。”(《龙眠风雅》卷二)[4]姚氏家族在清代取得进士、举人、五贡功名者71人,出仕为官者446人。[3]3乾隆时大学士刘统勋曾上疏弹劾:“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5]从中足见姚家的仕宦实力。其中著名的如姚文然,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姚棻,官至福建巡抚。姚元之,官至左都御史。姚莹,官至广西按察使,因保台抗英而彪炳史册。
姚氏家族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颇有造诣。《皇清书史》中收录了姚氏族人8 人,分别为姚士陛、姚孔嵚、姚文然、姚柬之、姚訏、姚孙森、姚孙棐和姚鼐。[3]40姚氏文人中还诞生了两位清代著名画家:姚文燮与姚元之。
自五世开始,姚家就陆续迁往桐城县城,由耕读传家渐至仕宦望族。族中有西堧、亦园、南园、兹园等园林别业。作为邑中大族,姚氏子弟多能扶危救困,以德为先。每遇灾荒年间,姚家均施粥平粜,赈济乡里,是地方士绅阶层的代表①详见吴婷《清代桐城科举家族姚氏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可以说,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政治、文化背景显赫,硕宦名儒辈出,家学深厚,人文蔚然,利于家族闺秀才媛的生成。
二、清代麻溪姚氏闺秀群体分段特色
据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②傅瑛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黄山书社2010年版。按:以下简称《辑考》,本文所引闺秀诗文如无另外说明均出自本书。,全清一代桐城麻溪姚氏闺秀(含嫁入)有诗文著录,文献可查的共计35人,著有诗文作品40余部。其中不乏博学多艺的历史知名女性。例如:方维仪(姚孙棨妻),明末清初著名女诗人、画家,有《清芬阁集》《宫闺诗史》《楚江吟》等。姚含章(张英妻、张廷玉母),“生平《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卜之书,而尤好禅学”[6]441,著有《含章阁偶然草》。张令仪(姚含章女,姚士封妻),有《蠹窗诗集》十四卷、《蠹窗二集》六卷、《锦囊冰鉴》等,剧本有《乾坤圈》《梦觉关》,是清代少有的女性剧作家之一。姚陆舟,有《玉台新咏》《闺鉴》《陆舟日记》《凝晖斋诗存》等。姚倚云,晚清著名女教育家,有《蕴素轩诗》《沧海归来集》《蕴素轩词》等。
八世葵轩公姚希廉家族一直被学界作为桐城麻溪姚氏的主要世系。姚莹在《姚氏先德传叙》云:“自明季以来,读书仕宦,人物称盛者,皆葵轩公后也。”[7]结合《辑考》并《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有文献记载可考的姚氏闺秀也集中在葵轩公这一支的长房(南车公姚承虞)和三房(似葵公姚自虞)中。总体来看,麻溪姚氏闺秀的文化生活与清代其他士绅望族人家相比并无二致,主要包括:诗文的教学、阅读与创作,文学聚会唱和,日常书信、题赠等文学往来,琴棋书画等人文艺术,还旁及医药、数学、星象、周易等学问研究。不过,在清代绵延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姚氏才媛的文学活动也具有一些特色:
(一)清初③本文清初取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至康熙亲政,即1636—1670。文学聚会及社团活动丰富
姚氏家族第十世到第十一世时取得功名和为官者开始增多。到了第十二世姚文烈、姚文然这一辈(顺治-康熙初年),更是人才卓越,可称为姚氏家族的一次高峰。[3]6此时期,姚家女性文学活动同样达到峰值,尤其是聚会唱和与往来互动。例如姚凤翙(姚孙棐女,姚文然妹)《同叶妹夜话因忆同盟诸姐妹存亡聚散感赋一律,索诸姊妹和之》:“忆昔西园会,相期松柏心。雁行何日聚,搔首一长吟。”《满江红·春日偕诸姐妹雅集西园并践五妹张夫人北上》词中道“把当年,兰亭曲水,新翻佳话。”[8]226将诸姐妹的西园聚会比作东晋王羲之兰亭曲水流觞的文学雅会。另如《集江嫂虚阁赏盆梅限梅字》《月夜过访八嫂江夫人》《十九嫂索书近诗》。张姒谊(姚孙棐媳)亦有《和十九娣左夫人拟征妇怨》《冬日偶招长姊吴夫人表姊钱夫人及同盟诸姊妹饮保艾阁,即席偶成,时雪》,在《哭纕芷阁左盟姐》诗中描述了她和盟姐左如芬(姚文熊妻,有《纕芷阁遗稿》)“看花濡墨朝吟句,对月传觞夜度萧”[8]270的闺中生活。左如芬亦有《寄怀五娰张夫人(张姒谊)》及《秋日病中喜诸姊夫人过访留饮》等。
上述姚凤翙与张姒谊的盟姐妹以及姚凤翙诗中的“西园会”①姚凤翙为方孝标子方云旅妻。方孝标侨居金陵,后因丁酉科考案,一家被流放。然据潘江《龙眠风雅》卷二十:“(姚凤翙)初入门,即迎君姑刘太夫人于毗陵返里就养。姑妇相依者二十四年。”故可知姚凤翙的“西园会”等文学活动场所依然是在桐城。出现不止一次,带有明显的社团色彩。
在《龙眠风雅》正集和续集中,除了方维仪外,姚凤翙与张姒谊是收录诗歌最多的姚氏才媛,分别是79首与91首。姚凤翙是姚孙棐幼女,张姒谊是姚孙棐五儿媳,二人是姑嫂关系,同属姚家第十二代。虽然她俩诗中的盟姐妹与西园会的具体成员已难以考证,但这种家居式的女性文学社团从留存的诗词看是切实存在的。姚孙棐家中有八子三女,女儿和儿媳就构成一个才媛群体。他的三个女儿姚凤仪、姚凤喈和姚凤翙全著有诗集。其长媳方氏(姚文烈妻),是桐城著名文人方拱乾之女。张姒谊有一首诗为《伯娰方夫人以水仙见赠赋谢》。三儿媳夏氏(诗人夏承春女,姚文然妻)、八儿媳江氏(名宦江之湘女,姚文炱妻)均在姚凤翙诗中提及。包括张姒谊在内,姚孙棐家先后娶了张英家族的三个女儿,左光斗的两个孙女也前后嫁入姚家。姚孙棐的侄女姚宛(姚孙榘女)也颇有诗名。如算上葵轩公一脉其他房头的女眷,才媛群体人数还会更多。
多位姻亲才媛也参与到姚氏闺秀聚会唱和中,例如张姒谊堂姐张氏(张秉彝女,吴德音妻),即张姒谊多首诗中提到的履雪阁吴姊夫人或长姊吴夫人。张姒谊表姐吴氏,钱勖仍妻,著有《随鸣阁诗集》。左如芬有首诗《寄怀随鸿阁钱夫人山居》写相聚“承欢同彩服,伴读共青毡。”(《龙眠风雅》卷五十)[4]
(二)清代中后期女性文学活动范围进一步拓宽
进入清中叶,姚门出现了一位重量级的才女张令仪(1668—1752)。这位著作等身的女诗人在中年后经历了两次长途游历旅居:第一次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张令仪与家人南下至浙江,历经十月之久;第二次是她在雍正六年(1728),年已六旬时北上去京师,一年后返回桐城。她以大家闺秀的足履步入公众领域,并全部以诗文记录下来。在江南游历时她就作诗百余首,在上京途中更是作了《北征草》《舒城道中》《过临淮》《晓渡黄河》《徐州道中》《抵都门》等十七首诗记录了旅途的整个过程②详见吕菲《清代桐城女作家张令仪的生平与思想》(《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女诗人畅游杭州、北京诸地美景,与亲友聚会唱和,书写人情风貌,此举无异于男性文人的文学游历。
若干年后,张令仪孙女姚德耀(约乾隆间在世),因随宦之故,在与家中堂嫂马遵贞“虽间隔数千里,赠答往还无异几席间”[8]217的同时,又与长白完颜董兰芬结盟唱和,“粔籹花胜而外,日以诗筒赠答。”[8]217于姚氏闺秀的文学活动中又添写跨省及跨民族交流的一笔。
及至清末,女诗人与教育家姚倚云(1863—1944)的文学活动见证了姚氏闺秀交游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其诗作《通夫子和顾延卿见贻原韵》《用韵赠刘秋水兼示阮绩青》《和易仲厚见赠原韵》中可见她与顾延卿、易仲厚等男性文人的文学交往。19O6 年,姚倚云还应张骞之邀,担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大家闺秀开始担任社会公职,成为近代女性教育的先驱者。
三、姚氏闺秀文学活动的文化解析
(一)家族为才媛的生成与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化环境与条件
关于家庭对才媛的作用前人已有论及,在此可关注两点:一是平等,二是自由。
首先,家族男性的支持,给予女性平等宽松的文化环境。
明代以降,德才兼备的女性观日益为社会主流文化所接受,士绅望族姚氏也不会例外。姚鼐曾言:“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矣,于女子亦宜矣。”(《郑太孺人六十寿序》)[9]121他的女才观可作为姚家整体代言。从明末清初姚孙棐对女性诗才的佩服,姚文然延师授女诗文,到姚文熊教妻学诗,为妻结集,姚文燕、姚士封等人与妻唱和,再到姚棻、姚莹及至晚清姚永楷兄弟对家中女性为文的支持①参见温世亮《清代桐城麻溪姚氏闺阁诗歌繁兴的文化因素》(《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姚家男性的支持和肯定,促进了家族内闺秀的文学活动,给女性提供一个相对宽松与平等的文化环境,使得闺秀们在家中可以同男性成员一起分席赋诗,吟咏酬唱。像姚凤翙有《春夜偶集诸兄小饮分得诗字》《甥侄辈赋香奁诗依韵三十首偶戏和之》,姚宛《小年夜同子艺侍饮北堂限韵》,姚凤仪《予做梦夫子诗蒙大人及诸兄弟赠句再赋》等。姚濬昌曾在《三釜斋唱酬小录》序中详细记录了三釜斋唱酬参与者,“闺中则予次女蕴素(姚倚云),长女之女马君挺。”②参见汪孔丰《清代桐城文化家族的姻娅网络及其文化特征——以麻溪姚氏为中心》(《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闺秀可以平等参与家内的文学活动,在当时的中华帝国并非特例。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以及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文献中多有记载。这也说明地方士绅家族的家庭内环境契合了社会外环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其次,家族联姻增加了闺秀文化交往的自由度和延展面。
桐城方、姚、张、左等大姓家族累世通婚,互为姻娅。正如张英在《潘母吴夫人七十寿序》中所言:“吾族则外家也,吾里则皆姻戚也。”[6]347家族联姻将各大家族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宽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增加了交流渠道和机会,不仅可将各姻亲闺秀网联,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整个桐城的“局域网”,而且因姻亲之故可以与家族之外的男性文人交流。如姚若蘅“与上元张雪鸿先生有戚谊,从张氏受六法。”[8]241姚素与表弟张缃蕖及舅父张曾虔有诗歌唱和。张凝(姚检吾妻)与姻亲马庆旋有文学交流,存《和马庆旋先生咏柳原韵》四首。马庆旋又为张凝之女姚鉴含的诗集题词。作为亲戚往来,文学交流更为自由。
联姻带来的家族间文化交融及闺秀间交相师友的文化功能不言而喻。除了前文提及的外,还有像方维仪教导两个外侄女姚凤翙和姚凤仪学诗。姚含章师承其长嫂方氏(方体乾女)。与张姚两家均有戚谊的吴坤元(清代桐城三才女之一)与张姒谊、姚凤翙等都有诗歌往来。
家族联姻延展了士绅家族闺秀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他如合肥李鸿章家族联姻安庆太湖赵氏(赵朴初家族)、合肥张树声家族以及曾国藩、张之洞家族,使这几大家族的才媛也因此有了联系③详见吕菲《清代安徽才媛家庭化现象的文化分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二)反映出闺秀具有自我意识的雅好与追求
士绅家族闺秀积极地从事文学活动,带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其中包含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性别意识、阶层身份意识与价值追求等。
明末清初,桐城文人大兴结社之风。像方以智主盟复社,姚孙棐与吴道新等结西山诗社,又与方体乾、龚鼎孳等举秦淮社。姚文然、姚文燮等结潜园社。姚孙棐还多次在家中亦园举行文会。这一时期姚氏才媛的社团群聚活动同样频繁。她们西园雅集、结盟唱和,发展出专属女性的社交网与相对独立的社交领地。这既是一种对男性世界的效仿、看齐,更是潜意识里的一种平等追求。恰如完颜董兰芬在姚德耀《清香阁诗钞》序中所言:“庶几见文字之交,知心之雅,不独男子然也。”[8]216
至于闺秀们日常生活中的雅好书史、性耽吟咏、涉猎文艺,除了兴趣及平等尝试外,还有一种世家闺秀对自身精英身份的标榜与确立。这种身份是有别于社会底层及劳动者阶层女性的。文学既是一种娱闲的爱好,抒情遣怀与交际需要,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当时能吟诗作赋的才媛几乎全部为大小士绅家庭中的女性。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六曾载她和吴藻、席怡珊等才媛于初夏泛舟皋亭,吟诗联句。村中妇女咸来观看,不能理解她们的风雅。沈善宝在记叙时,作为才媛的自得跃然纸上。
与丈夫闺中唱和的雅趣以及父兄亲朋赞赏的现实功能促进了这种雅好的发展,在发展中逐渐带有闺秀对自身价值与自我实现的追求。正如张令仪的远足游历,就体现出一种自我追求。她还在诗中道:“总误平生缘傲骨,但高人处只诗魔。”[10]473女诗人为自己的诗才而自豪。张令仪曾先后两次刊印了自己的诗集,诗歌对她来说已为毕生事业。再如姚倚云初将诗作附在丈夫范当世诗后,“迩年又裒前后所做,钞存之,为若干卷。”[8]250独自刊印为《蕴素轩诗》。
此外,在闺秀们所作的诗歌中,明显可见一种性别关注,即自发地将女性人物、事件作为创作题材,表达自己的心情感悟。姚宛有一首《读小青诗》,便是对晚明才女冯小青的赞叹。另如姚素《和雄县旅店壁间武林十五龄难女韵》,姚凤翙《次梁溪女子原韵》《吊蟂矶夫人》,姚凤仪《题定远徐贞女卷》等等。女性关注女性,是一种性别共鸣与性别自觉。
(三)闺秀所有的文化追求与自由都合乎女德闺范
美国学者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提出,女性是同一的(社会性别)和女性是差异的(阶层)二元原则。一方面赋予部分女性权力,另一方面又将她人规范在分离领域里。[11]此言切中肯綮。从姚氏闺秀的文学活动可以看出,作为大家闺秀,地方女性中的精英阶层,她们在文化上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自由。例如可以受教育,进行诗文创作交流,可以平等地参与家中文化活动,还可以做一些学问研究,甚至出版诗集、结社与游历,但至始至终,所有的活动都遵循着女德闺范,没有任何逾越行为。就好比是她们的诗文写得再好,也只限于闺阁之内,而不会去打开科考的大门。即便姚倚云在清末担任女校校长,照样是授经义,推“原《二南》之化”[8]250。她要求学生“为人师表,尤注重妇德。一切偏宕激烈之学说概屏弗谈。”要“抑骄忌、守贞洁、勤女工、躬节俭。”①参见陈晓峰《姚倚云女子师范教育思想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依然没有跳出女德闺范的圈囿。
姚氏闺秀所作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诗,其次是词与短小散文,创作剧本的仅张令仪一人,而清代比较流行的弹词和通俗小说无一人涉及。之所以闺秀多选择诗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由于诗歌有上自儒家《诗经》的传统。“诗之为教,温柔敦厚,可以陶淑性情,可以正人心,维世教。”[12]闺秀们可以在诗歌的创作上谋求妇德和文采统一。对文学体裁及内容笔法的选择是大家闺秀遵从女德下的自律,绝不等同于一般才媛。像桐城栖梧阁主人吴氏,好读历代群史,而艳词小说,屏绝弗观。[8]201姚凤翙“不欲以女子炫才华,间有吟咏,亦写其至性,弗矜藻缋。”[8]218清末世家闺秀单士釐编写钜制《清闺秀艺文略》时,同样一篇女性弹词和小说也未收录,甚至对当时著名女诗人秋瑾只字未提,其中的女德观显而易见。
闺秀们自觉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对女性道德规范的要求。女德闺范已深入灵魂,指导着她们的言行与生命轨迹,稍有违规怀疑,高度的道德自律就会袭来。张令仪就自责过自己的游历行为:“自念我何人斯,放浪湖山,得睹名胜,诚为过分!”[10]382在《辑考》所录对姚氏闺秀的各类记载中,处处可见对女德积极自觉地实践。例如以贤德谦退称名的姚含章,“平生之德行无憾于两姓者”[8]250的姚倚云,“贤明识大体,治酒浆腆洗黾勉,以求承堂上之欢”[8]268的张姒谊,刲股救夫不效后,誓死殉夫,“众责以抚孤为大,乃不复言死,缟衣蔬食,教督二子”[8]238的姚陆舟,姚节妇方维仪更以六十余年苦节获姚氏举族修祠祭祀。《姚氏先德传·贞节》上记载更为详细,共记载烈妇53 人,贞烈3 人,贞女9人,节孝150人。[3]10诸如此类并非只发生在桐城,只独姚门。他如贵州名宦黄彭年妻刘季瑜,出身名门,耽文史,娴绘事,在丈夫和婆母病中两次刲臂和药以进。江苏著名学者阮元之女阮安,产遗腹子为女后,旋即殉夫。甚至满州女诗人希光都割股为夫疗伤,夫死殉之②详见石晓玲《清代士绅家族对女性的道德形塑——以女性忆传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5期)。。翻开《清代闺秀诗话丛刊》,里面记载的贞洁烈女比比皆是。
时代与社会风尚使然,将女德几乎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从这一点讲,雅好与追求、平等与自由无疑都要退居道德妇职之后,德主而才辅。正如方维仪为姚凤仪诗集作序道“其节愈坚,其诗亦愈工。”“传其诗,正所以传其节耳。”[8]228翻开同时代人给这些闺秀所写的序或小传,无一例外地全在彰显其德,附带才是其才。张廷玉和姚永楷作为同胞兄弟为张令仪与姚倚云诗集写序,虽时隔百年,均是先写其德,写女诗人在学针黹、工织纫之余学学诗。在德主的思想下,有的闺秀甚至会因德而抑才。如姚乔龄母马氏(乾、嘉间在世)平生颇喜吟咏,以非妇人所重,不自收拾,仅存百余篇。[8]178左如芬的诗作“每不以示人,辄云此非女子事也。”[8]306
综上,在女性文学盛极一时的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闺秀文学活动同样十分出彩。她们雅集结盟、组织社团、闺中唱和、分席吟咏。其中我们看到闺秀们对文学的追求,对成为女性精英的自我塑造,看到家庭给予闺秀在文化上的平等与自由度,看到才媛的活动空间还随着时代发展有所拓宽,但一切可自由的选择都在女德闺范之内。所谓“德才兼备”在她们身上不是简单的二元、平分秋色,而是明显的德主才辅,所有的文学追求、才华雅好都要由道德统帅。
明清士绅阶层在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承担较多民间管理和教化职能,体现礼教权威与儒家传统。桐城麻溪姚氏,清华望族,诗礼传家,属于地方士绅家族的典型代表。这类家族尤重对女儿的教育,以正伦理纲常,不令家族蒙羞。是以士绅家族闺秀的道德感、对家族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家族荣耀感比一般女性更为强烈。闺秀们浸濡着家族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家学家教,努力履行着孝女与贤妻良母的角色功能。姚德耀于归后,克尽妇职。以令“当时咸啧啧称其贤,不愧名门闺范。”[8]216姚鼐亦言:“(人言吾族)宜出贵女……然余以为吾族女实多贤。”[9]122
姚门闺秀多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大家闺秀出嫁后全部为正妻嫡母。彼时正妻和妾室分属两个阶层,道德要求与身份责任有明显区别。就像姚文鳌在《寄送五弟入都》诗中所写:“大妇温恭小妇柔。”(《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十)[4]对大妇张姒谊所用的“温恭”二字明显带有道德色彩。《名媛诗话》曾载浙江阳湖名门闺秀恽岫云(恽珠侄女)的丈夫和公婆相继去世,留下侧生小叔和庶出女,在“两姬他适”的情况下,“岫云孑然一身,抚养幼稚,经理丧葬,为外立嗣。”[13]妾室可以改嫁,正妻嫡母则必须担起家庭的责任,遵守她的“职业道德”。再如《辑考》记载桐城名士孙临在抗清兵败后,诀别正妻方子耀(方以智妹):“养亲教子以累汝,汝其勿死!”接着就跟妾室葛嫩一同赴死。“于是,恭人(方子耀)抚育二子,垂涕以教,作《寒香阁训二子说》。”[8]166
诚如麻溪姚氏,士绅家族的闺秀们,在被刻上时代印记的同时,又戴上家族的光环。身份、家风和女德观决定了大家闺秀不可能像那些风尘才媛一样出入酒席歌场,与男性文人饮酒唱和,题扇索诗,也不会开放到去干谒名流,成为随园或陈文述女弟子。她们的文学活动、文化追求亦或人生就如同绽放在高门深院内的花朵,优雅、灿烂,但永远被圈囿在那一片土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