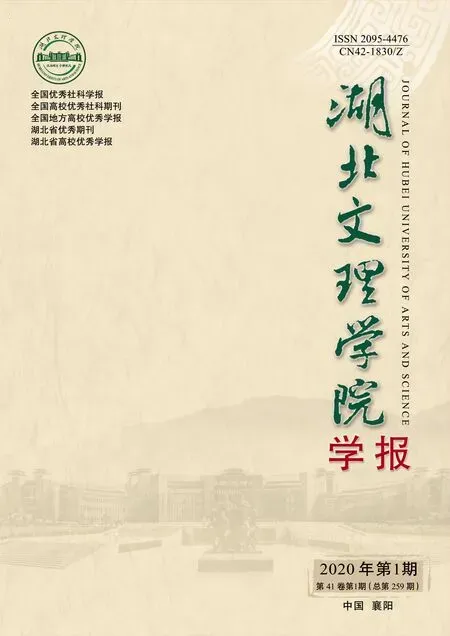明代戏曲理论从“画工”到“化工”的演变
王玲玲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明代戏曲批评史上《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地位之争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探究论争中诸位戏曲理论家提出的“本色”“当行”论(1)如一峰《当行论──戏曲编剧艺术漫笔》(《民族艺术》,1995年第2期),从臧懋循的“当行”引出,展开明代诸位戏曲理论家对《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及其他名剧的评价,探究“当行”的戏曲意义;王汉民《“本色论”在明代的两次论争》(《戏剧》,1997年第4期)其第一次论争则是对这场戏曲作品地位论争中何良俊、王世贞等人就“本色”展开的问题进行探究;刘于锋《曲学史上一次戏曲本体特征的论争》(《戏剧文学》,2009年第10期)认为“在论争中,明代曲家在本色观上,认为本色与填塞学问无关,而在雅俗、深浅、浓淡之间”;敬晓庆《明代戏曲本色说考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通过明代的名剧之争与意法之争来论述明代戏曲“本色”论的发展。赵春宁《明代<西厢记>与<琵琶记><拜月亭>的高下之争》(《中华戏曲》,2006年第2期)除了“以本色、当行为标准”之外,还提出“以音律为标准”“以戏为标准”对这场论争进行分析。;二是依托于论争重点研究其中单部剧作的戏曲意义(2)如刘小梅《南戏<拜月亭记>及其历史影响》(《戏曲艺术》,2004年第3期),着重探讨《拜月亭》在这场戏曲作品地位的论争的独特地位和戏曲风格;冯俊杰《明代士子眼中的<琵琶记>》(《中华戏曲》,2008年第1期)依托于论争中诸位戏曲理论家的观点来重点研究《琵琶记》的戏曲地位。;三是将戏曲作品地位论争与元曲四大家的成员及其对他们评价的论争、汤沈之争等放在一起考量,研究“论争”这一独特的理论批评形态(3)如敬晓庆在其硕论基础上写就博论《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对明代名家之争、行戾之辨、名剧之争、意法之争等做全面地分析;祁志祥《明代的戏曲美学论争》(《艺术百家》,2017年第4期)从戏曲美学视角,从明代诸多论争中总结出“本色论、情趣论、折中论”等三方面。。本文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借用晚明戏曲理论家李卓吾在论争中所提出的“化工”与“画工”说来探究明代戏曲理论的演变。李卓吾《焚书·杂说》谓:“《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1]96这几句话以“化工”与“画工”之高下确立了《西厢记》《拜月亭》高于《琵琶记》的戏曲地位。“化工”之作以《西厢记》《拜月亭》为代表,剧作者以自然为美,推崇真情。“画工”之作以《琵琶记》为代表,剧作者以宣扬伦理道德为创作宗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穷巧极工”,导致剧作品感人不深。
一、明正德以前戏曲理论之重教化:“画工”阶段
明正德以前统治者内部矛盾冲突严重,为巩固统治而过度强调封建伦理道德,如朱元璋称:“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2]这一阶段社会思潮为“程朱理学”,它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指导思想,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程朱理学”从客观条件出发,依据外在的条条框框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强制百姓遵守社会准则,故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十分严重。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戏曲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了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工具。明初法律规定,民间演剧不准妆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但“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3],故戏曲创作内容受到限制。同时,参与戏曲创作的文人也在渐少。明初科举恢复,与元代长期废止科举致使大批文人转而从事杂剧创作的局面相反,明人得以参加科举考试,故不再热衷于戏曲。何良俊《曲论》谓:“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4]6。基于以上原因,明初戏曲理论的发展由元代的活跃局面转向沉寂。相较于元代一大批的戏曲理论专著如《录鬼簿》《青楼集》《唱论》《中原音韵》等,明初戏曲理论著作甚少,只有一部《太和正音谱》,其他皆散见于序、跋之中,不成体系。
朱权《太和正音谱》,其名“太和”即是天下太平、政通人和之意,是将戏曲定性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他言:
猗欤盛哉,天下之治也久矣。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咸被仁风于帝泽也,于今三十有余载矣。近而侯甸郡邑,远而山林荒服,老幼瞆盲,讴歌鼓舞,皆乐我皇明之治。夫礼乐虽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无以显礼乐之和;礼乐之和,非自太和之盛,无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5]29
(《太和正音谱·序》)
盖杂剧者,天下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5]57
(《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朱权作为一位皇族戏曲家,其身份决定了他对戏曲艺术的认识具有“太和”之局限性,他把戏曲当作体现“太和之盛”同时又能促进“太和之盛”的工具。“太和之盛”方有“礼乐之和”,礼乐又可以教化人心,促使盛世的安稳。而能有这“太和之盛”皆因“皇明之治”。戏曲的政教功用自汉代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有之,其言“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6]3197“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6]3202。元代夏庭芝《青楼集志》也认为戏曲在君臣、母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上“皆可以厚人论(伦)、美风化”[7]7,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也认为戏曲“曰忠,曰孝,有补于世”[8]。明初戏曲的政教功用发展至高峰,这有其积极意义,可为戏曲正名,将戏曲置于诗、文同等位置,但其负面效应远大于此。戏曲作为一门艺术,过于强调其教化百姓的功用,戏曲就会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而失去戏曲的艺术审美性。这一点体现在明初的戏曲创作中。
戏曲理论是戏曲创作的反映同时也指导着戏曲创作。这一时期的戏曲作品教化思想浓厚,甚至充斥着假道学的风气,偏离了戏曲创作的正确轨道。高明所作《琵琶记》是明初戏曲创作重教化的典型代表,其第一出《副末开场》云:“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9],他以有“关风化体”为创作宗旨,讲述了一个“子孝共妻贤”[9]的故事,故塑造了“全忠全孝蔡伯喈”[9]的形象。故该剧得到了朱元璋的褒奖,“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5]483由于统治者对《琵琶记》的称赞,一大批宣扬伦理道德的戏曲作品产生。
成华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邱濬所作传奇《五伦全备记》,继《琵琶记》之忠孝,提出忠、孝、节、义、信等“五伦全备”。他在该剧凡例中指出:
此记非他戏文可比,凡有搬演者,务要循礼法,不得分外有所增减,作为淫邪不道之语及作淫荡不正之态。[5]210
并在卷首开场白中曰:
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风日好,物华鲜,万方人乐太平年。今宵搬演新编记,要使人心总惕然。[5]210
每见世人搬杂剧,无端诬赖前贤。伯喈负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气定冲天。这本《五伦全备记》,分明假托名传。一场戏里五伦全,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5]211
邱濬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作“圣贤言”,而非“吾心之言”。李卓吾《藏书·儒臣传》中就“圣人之言”与“吾心之言”谓:“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10]戏曲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充斥着假道学的气息,则缺乏戏曲的艺术性。诸多戏曲理论家对此作出批判,如吕天成《曲品》谓:“大老钜笔,稍近腐”[11]228。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亦言“一记中尽述伍伦,非酸则腐矣”[11]46。邱濬作《五伦全备记》后不久,邵灿创作了《香囊记》。其第一出《家门》谓“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观省名行。有缺纲常。那势利谋谟。屠沽事业。薄俗偷风更可伤。怎如那岁寒松柏。耐历冰霜。闲披汗简芸牕。谩把前修发否臧。有伯奇孝行。左儒死友。爱兄王览。骂贼睢阳。孟母贤慈。共姜节义。万古名垂有耿光。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12]。从《琵琶记》到《五伦全备记》再到《香囊记》,戏曲创作均代“圣人言”,而缺乏“吾心”之作。明初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作品,如成化年间姚茂良作有传奇《金丸记》《岳武穆精忠记》《双忠记》,弘治年间周礼作传奇《东窗记》,正德年间沈龄应杨一清之邀,撰写《四喜传奇》献给武宗并受到赏识,等等。可以说,这些剧作以《琵琶记》为首皆为“画工”之作,宣扬教化思想,感人不深。
二、明嘉、隆间戏曲作品地位论争开启:从“画工”向“化工”过渡阶段
明嘉靖、隆庆时期人们意识到“程朱理学”对百姓身心的束缚,下层老百姓意欲摆脱这些条条框框,社会兴起了“王阳明心学”。它强调人性本善,不需要依据外在力量去强制百姓,只需要稍微提醒以唤起百姓内心的良知,百姓就会自觉遵守规则从而达到统治者的意愿。此时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也趋于和缓,明代戏曲理论得以向前发展。戏曲理论重教化的风气从明初持续至明中叶,走过了百余年漫长的低潮期,戏曲理论家开始对戏曲理论作精细化探索。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开启了一场聚焦于戏曲作品《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地位高低的论争。
论争自何良俊始,他认为《拜月亭》居于《琵琶记》《西厢记》之上。而在此前,《琵琶记》作为“南戏之祖”得到统治者的称赞,《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经典有“天下夺魁”[7]173之美誉,以此二剧为南北曲之首为诸多戏曲理论家所认可。何良俊高呼《拜月亭》居于二者之上,引起了诸多戏曲理论家的注意。王世贞首先发出反对之声,何王二人的观点逐渐形成论争的热点。何良俊《曲论》曰: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余谓其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盖其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其《拜新月》二折,乃檃括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拜月亭·赏春·惜奴娇》如“香闺掩珠簾镇垂,不肯放燕双飞”,《走雨》内“绣鞋儿分不得帮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根”,正词家所谓“本色语”。[4]12
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祖宗开国,独尊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即不喜,则习者亦渐少,而《西厢》《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独此二家。余所藏杂剧本几三百种,旧戏本虽无刻本,然每见于词家之书,乃知今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4]6
何良俊言《拜月亭》“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正词家所谓‘本色语’”,故比之《西厢记》《琵琶记》更高一筹。他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当行”“本色语”。对于“当行”,他举出《拜新月》二折、《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等例子,具体讲了“彼此问答”“叙说情事”两方面。“当行”,也就是彼此问答不需宾白;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如此“可谓妙绝”。他对“叙说情事”的内涵,并举了《王粲登楼》与《西厢记》正反两例加以阐释:
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至如《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作调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岂堂庑哉![4]7
从中可看出,何良俊作为文人士大夫,其审美标准明显有别于普通百姓。他认为,对于情词,剧作者容易描摹,普通百姓也喜欢听。而作为文人,他以诗歌的意境来审视戏曲,推崇“羁怀壮志”“托物寓意”,故言《西厢记》为“调脂弄粉语”。对于其“本色语”,诚如俞为民先生言“理论家们在运用这一术语来评论作家和作品时,却都根据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批评标准”,何良俊“在运用‘本色’这一术语时,也有着自己特定的内容与标准”[13]。从他所举《拜月亭·赏春·惜奴娇》和《走雨》中的两句话来看,他之所谓“本色语”似指戏曲语言的俚俗,曲白杂以乡语、口语。从其反例“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来看,“全带脂粉”指的是儿女之情兼语言不够质朴,“专弄学问”也就是言语富丽,用典频繁。何良俊对“本色”的理解似有所偏颇,“偏”在“全”和“专”上,依照当时的审美,《西厢》是略带些“脂粉”,《琵琶》也有些“弄学问”,但何元朗如此用词,显然是不合适的。[14]从何良俊的戏曲理论来看,他对“当行”的阐释,以及看到《琵琶记》“弄学问”的特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他以士大夫的审美,对“情词”加以否定,对《西厢记》之真情视而不见,可谓是其局限性。故可以说,何良俊的戏曲理论具有从“画工”向“化工”过渡的倾向。
何良俊推崇《拜月亭》,引起了王世贞的批驳。王世贞认为《西厢记》高于《琵琶记》高于《拜月亭》。其《艺苑卮言》认为《拜月亭》有“三短”:
《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谓胜《琵琶》,则大谬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禆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5]519
北曲以《西厢》压卷: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是骈丽中情语。……“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是骈丽中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梦里成双觉后单。”是单语中佳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5]513-514
而高明《琵琶记》“冠绝诸剧”:
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5]518
王世贞的《拜月》“三短”是参照《琵琶记》来讲的,其有“词家大学问”、有“风情”且有“裨风教”“使人堕泪”正是《琵琶记》的特点。相较于何元朗批判《琵琶记》“专尚学问”,王世贞对“词家大学问”予以称赞。他充分意识到《琵琶记》作者“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却以此为戏曲之美,对《琵琶记》“作者之工”赞曰:
偶见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鱼,期逼春闱,诏赴春闱。郡中空有辟贤书,心恋亲闱,难舍亲闱。”颇疑两句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诏”,曰“书”,都无轻重。后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鱼,期逼春闱,难舍春闱。郡中空有辟贤书,心恋亲闱,难赴亲闱。”意既不重,而“期逼”与上“欲化鱼”字应,“难赴”与“空有”字应,益见作者之工。[5]518
这充分体现出王世贞“工美”的戏曲思想,即以“画工”为戏曲审美标准。有“风情”且有“裨风教”更是承袭明初戏曲为封建专制而服务的特点。可以说,王世贞对何良俊观点的反驳透露出他仍以明初“画工”为美。相校而言,何良俊的戏曲理论则稍有进步意义,有向“化工”过渡的趋势。至此,戏曲理论家就何王二位的观点进行再探讨,形成两派。明中叶后期,何良俊的观点居上风,支持他的戏曲理论家有沈德符、徐复祚等人。这些戏曲理论家对何良俊的观点加以发展并对王世贞言《拜月》有“三短”加以辩驳。
沈德符对何良俊的戏曲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他在《顾曲杂言·拜月亭》中谓:
何元朗谓《拜月亭》胜《琵琶记》,而王弇州力争,以为不然,此是王识见未到处。《琵琶》无论袭旧太多,与《西厢》同病,且其曲无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则字字稳帖,与弹搊胶漆,盖南词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至于《走雨》《错认》《拜月》诸折,俱问答往来,不用宾白,固为高手;即旦儿“髻云堆”小曲,模拟闺秀憨情态,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终不及也。向曾与王房仲谈此曲,渠亦谓乃翁持论未确,且云:“不持特别词之佳,即如聂古、陀满争迁都,俱是两人胸臆见解,绝无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厢》,才华富瞻,北词大本未有能继之者,终是肉胜于骨,所以,让《拜月》一头也。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而不及王实甫,有以也。《拜月亭》后小半,已为俗工删改,非复旧本矣,今细阅“拜新月”以后,无一词可入选者,便知此语非谬。[4]210-211
沈德符对何良俊观点的继承表现在他认同何良俊所言《拜月亭》问答往来不用宾白之妙,《琵琶记》虽有可取之处,但不及《拜月亭》。将《拜月亭》与《琵琶记》相比,认可《琵琶·咽糠》《描真》“亦佳”,但较之《拜月亭》即旦儿“髻云堆”小曲,则不及也,并对《拜月亭》模拟情态之形象逼真大加称赞;将《拜月亭》与《西厢记》相比,认可《西厢记》“才华富瞻”,但较之《拜月亭》,稍逊一筹。他将“才华”比作“肉”,从其沿袭何良俊的观点来看,似将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视为“骨”。并且,他认为《琵琶记》与《西厢记》有共同的不足“袭旧太多”。沈德符较之何元朗的观点,其发展表现在从语言扩展到曲律方面,认为《拜月亭》为南词全本中唯一可上弦索者。因此,沈德符不单是从案头之曲来看待这三本戏曲著作,同时注重戏曲的演唱功能。
徐复祚对何良俊、沈德符的观点是批判性地继承。其《曲论》曰:
何元朗谓施君美《拜月亭》胜于《琵琶》,未为无见。《拜月亭》宫调极明,平仄极叶,自始至终,无一板一折非当行本色语,此非深于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无大学问”为一短,不知声律家正不取于弘词博学也;又以“无风情、无裨风教”为二短,不知《拜月》风情本自不乏,而风教当就道学先生讲求,不当责之骚人墨士也。用修之锦心绣肠,果不如白沙鸢飞鱼跃乎?又以“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为三短,不知酒以合欢,歌演以佐酒,必堕泪以为佳,将《薤歌》《蒿里》尽侑觞具乎?[4]235-236
王弇州取《西厢》“雪浪排长空”诸语,亦直取其华艳耳,神髓不在是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4]242
由上看来,徐复祚对三本著作的戏曲地位排序是《西厢记》高于《拜月亭》高于《琵琶记》。一方面,他从“宫调”“平仄”方面称赞《拜月亭》,认为何元朗“未为无见”;另一方面,他肯定了王弇州对《西厢记》的褒奖,注意到《西厢记》之“神”,赞其为“当行”“本色”之作,是“南北之冠”。同时,对王弇州之《拜月亭》有“三短”予以批驳。他指出“弘词博学”不为声律家之事,也就是不以文章的标准来论戏曲。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风教”乃是“道学家”所为,而非声律家之事,一改明初戏曲理论道学化现象。总体来讲,徐复祚从明初戏曲重教化的理论中脱离出来,意识到戏曲的审美特质。故其戏曲理论符合从“画工”向“化工”的过渡。
三、明万历以后戏曲作品地位论争的进一步发展:“化工”阶段
明代社会思潮从“程朱理学”到“王阳明心学”,其特点都是企图让百姓被动或主动遵守社会规则,以维护君主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到了晚明时期,市民阶级兴起,资产阶级的萌芽产生,出现了“王学左派”。相较于“王阳明心学”,有其进步之处,它更注重百姓的需求,强调顺从民性。其中,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他不再以圣人或者君主的准则为“道”,而是以百姓的合理需求为“道”。李卓吾也是“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关注百姓穿衣吃饭这一类的实际生活需求。其《焚书·答邓石阳》谓: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1]4
李卓吾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百姓最关注的无非是吃饱穿暖,其他的事情都与穿衣吃饭相类似。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顺从民性,以民为本。从“程朱理学”到“王学左派”,明代的思想完成了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变。这一时期统治阶层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开始瓦解,戏曲作品地位高低的论争在心学思潮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吕天成、王骥德等戏曲理论家对何元朗阵营的观点进行针对性地批驳,认为《琵琶记》《西厢记》高于《拜月亭》。但其评判标准则不同于王世贞,这一阶段的戏曲理论家更加注重戏曲所传达的“真情”以及戏曲的传神境界。除此之外,李卓吾对以上两派的观点进行辩证地吸收,提出“化工”与“画工”说,认为《西厢记》《拜月亭》的戏曲地位高于《琵琶记》,在这场论争中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吕天成《曲品》上下两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上卷将高则诚列为“右神品”:
永嘉高则诚,能作为圣,莫知乃神。特创调名,功同仓颉之造字;细编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笔先,片言宛然代舌;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关风教特其粗耳,讽友人夫岂信然?勿亚于北剧之《西厢》,且压乎南声之《拜月》。[11]210
与之对应,下卷将《琵琶记》列为“神品一”:
《琵琶》蔡邕之托名无论矣,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真有运斤成风之妙。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词隐先生尝谓予曰:“东嘉妙处全在调中平、上、去声字用得变化,唱来和协。至于调之不伦,韵之太杂,则彼已自言,不必寻数矣。”万物共褒,允宜首列。[11]224
吕天成对高则诚及《琵琶记》给予很高评价,称其“勿亚于北剧之《西厢》”。所谓“勿亚于”,也就是“大于等于”,他认为《琵琶记》的戏曲地位要高于《西厢记》,至少二者也应双峰并峙。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注重戏曲所蕴含的“情”,但戏曲理论家们对戏曲作品的评论标准往往不统一,其间蕴含着他个人独特的阅读感受。他认为《琵琶记》乃是“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其词之高绝处,布景写情”。同时,吕天成认为《琵琶记》“且压乎南声之《拜月》”,将《拜月亭》列为“神品二”:
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质,遂开临川玉茗之派。何元朗绝赏之,以为胜《琵琶》,而谈词定论则谓次之而已。[11]224
(《曲品》下)
吕天成看到了《拜月亭》之“天然本色”,开“玉茗派”创作风气。但与《琵琶记》相比,则“次之”。总体来讲,吕天成认为《琵琶记》高于《西厢记》高于《拜月亭》的戏曲地位。
王骥德认为《西厢记》高于《琵琶记》高于《拜月亭》。他针对何元朗所谓的“本色语”“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等问题进行有力批驳,认为《西厢记》《琵琶记》正是“本色”之作:
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递为桓文。然《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琵琶》遣意呕心,造语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顾多芜语、累字,何耶?《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故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以望《琵琶》,尚隔两尘。元朗以为胜之,亦非公论。[15]109
王骥德认为《西厢记》“全带脂粉”也就是“组艳”,《琵琶记》“专弄学问”即“修质”,由其“体”所决定,二者皆为本色之作。其《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对“本色”作出阐释:
当行本色之说,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盖本宋严沧浪之说诗。沧浪以禅喻诗,其言:“禅道在妙悟,诗道亦然。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又云:“须以大乘正法眼为宗,不可令堕入声闻辟支之果。”知此说者,可与语词道矣。[15]112
这里的“词道”即是指戏曲创作的规律性。王骥德以他所理解的“本色”,评判这三本著作,认为《西厢记》《琵琶记》是“本色”之作。上述诸多戏曲理论家认为《拜月亭》为本色之作,无可争议。而对《西厢记》《琵琶记》之本色,则争议较大。事实上,《拜月亭》作为早期南戏,起于民间,可谓民间化的本色,而《西厢记》等是被雅化了之后,堪称典雅化的本色。戏曲产生之初,杂有乡间俚语口语,发展至后来有了文人的参与,经过提炼、修饰,这时的“本色”则体现出人文精神与自然律则的统一性。王骥德认为“本色”一词源自严羽: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16]
严羽之“本色”被引入戏曲则见于徐渭《南词叙录》:
填词如作唐诗,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种妙处,要在人领解妙悟,未可言传。[5]487
并且,徐渭就“本色”作进一步阐释: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我呴呴也。[17]
徐渭以婢女扮作夫人为喻,辨析“本色”与“相色”。婢女的特点是“素”,涂脂抹粉、插带装扮成夫人,只觉羞涩,而无夫人的气质,反而遮掩其“素”。换言之,“本色”就是要与剧中人物特定身份相符。这番话道出了徐渭“贱相色,贵本色”的原因。据此,徐渭认为南戏有一高处,即“句句是本色语”:
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则《玩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5]486
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徐渭之“本色语”,指没有时人文气。“以时文为南曲”自《香囊记》始有。但同时也体现出,“本色语”并不等同于“俚俗语”。可见,王骥德作为徐渭的弟子,就“本色”与“妙悟”的关系充分地借鉴了徐渭的观点。并且,王骥德认为《琵琶记》“本色”之作,但也看到其“遣意呕心,造语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这正是李卓吾所谓“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对《琵琶记》之“工”,王骥德作进一步地阐述:
《琵琶》工处甚多,然时有语病,如第二折引“风云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无有”,三十一折引“也只为我门楣”,皆不成语。又蔡别后,赵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减祥鸾罗幌,香消宝鸭金炉,楚馆云闲,秦楼月冷”,后又曰“宝瑟尘埋,锦被羞铺,寂寞琼牕,萧条朱户”等语,皆过富贵,非赵所宜。[15]110
王骥德从语言和剧中人物形象上指出《琵琶记》工处之不妥。故综合来讲,王骥德认为“《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对《拜月亭》,王骥德予以一定的肯定,称其“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但与《琵琶记》相比则远不如。他对王世贞、何元朗的观点综合评定:
弇州谓“《琵琶》‘长空万里’完丽而多蹈袭”,似诚有之。元朗谓其“无蒜酪气,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遂欠风味”。余谓:使尽废驼峰、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说也。[15]110
从王骥德所设例子来看,他肯定了王世贞的观点,而认为何良俊的观点是“一偏之说”。晚明另一位戏曲理论家李卓吾与吕天成、王骥德的戏曲观点稍有不同。
李卓吾认为《西厢记》《拜月亭》高于《琵琶记》。李卓吾的“化工”与“画工”说对这场戏曲作品地位之争具有总结性,他对何、王两派观点中较为中肯的部分有所吸收和融合,而非一味地肯定或否定。以上两派戏曲理论家具体所论争的点有:《琵琶记》“词家大学问”,《西厢记》“才华富瞻”,有无裨风教、是否感人,“本色”与否。对这些论争点进行分析,实则是以“自然”为美还是以“工”为美,尚“风情”还是尚“风教”。李卓吾推崇“化工”是以“自然”为美、尚“风情”的表现。
从论争过程中诸位戏曲理论家的观点来看,以“自然”为美的戏曲理论家除了李卓吾,还有何良俊、沈德符、徐复祚、王骥德等,以“工”为美的戏曲理论家以王世贞为典型代表。李卓吾在《琵琶记卷末评》曰:“《琵琶》短处有二:一是卖弄学问,强生枝节;二是正中带谑,光景不真。此文章大家之病也,《琵琶》两有之。”[5]548李卓吾认为“二短”是“文章大家之病”,也是“画工”之病。尚“风情”的戏曲理论家有李卓吾、何良俊、沈德符、徐复祚,尚“风教”的戏曲理论家有王世贞、吕天成。而王骥德虽盛赞《西厢记》之“风情”,同时也对“风教”之作《琵琶记》予以很高评价。无论是“风情”还是“风教”,能否动人,始终是戏曲艺术的至高标准。王世贞认为《琵琶记》“歌演终场”能“使人堕泪”,吕天成认为其“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李卓吾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见解:“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1]97李卓吾初读《琵琶记》也如王世贞、吕天成一样,“一字一哭”“一字千哭”“一字万哭”[9],认为《琵琶记》是感人之作。但其反复阅读之后,发现《琵琶记》之感人是浮于表面的,入人心者不深。李卓吾对“真情”的关注和阐述要高于诸位戏曲理论家。综合以上两方面,李卓吾将《西厢记》《拜月亭》归为“化工”之作,较之“画工”之作《琵琶记》,更胜一筹。
综上来讲,明代戏曲理论经过了从“画工”向“化工”的演变。明初戏曲理论以朱权《太和正音谱》为指导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为封建专制服务的“画工”之作,假道学风气盛行。明中叶何、王二人对戏曲作品《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地位高低的讨论形成热点。何良俊、沈德符、徐复祚等人对天然本色的《拜月亭》的推崇体现出戏曲理论从“画工”向“化工”的过渡。晚明吕天成、王骥德对何良俊阵营的观点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批驳,李卓吾对以上诸位戏曲理论家的观点进行总结和进一步发展。戏曲创作的艺术性得到关注,“真情”突显出来,戏曲理论发展为“化工”阶段。
——《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基于国际理论家的视角》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