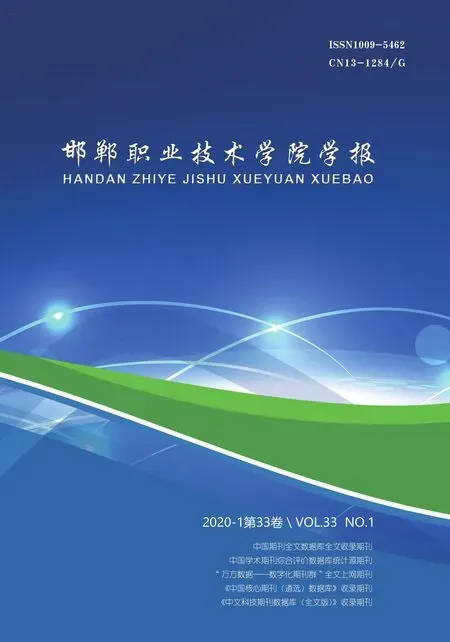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的多维度阐释
王悦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
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在革命家身份之外,李大钊同样在史学、哲学等方面有所建树,依靠扎实的理论沉淀与学术基础,提出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题。正如他所言:“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252页。李大钊认为,历史集“观”之大成,其中学问包裹在人类的自我意识里,是人类认知自我、他人、社会的重要理念依靠,具有社会性、实践性与指导意义。因此,如何寻找到更好的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在探索真理、寻求本源之路上指导未来中国的发展,这一问题,成为了李大钊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动因。而在这样的研究思辨之外,为宣传“理想的主义”,李大钊毅然决定要开始在中国的思想理论层面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旗帜。1919年9月与11月,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其中,他着重总结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其理论的首要之处便是关于“过去”的阐说(即历史论)。②“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杜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8页。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与他所求初心契合,能够成为率先影响中国发展进程与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因而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里,李大钊以多维度的视角,完成对这一重要史观理论的详尽阐发。
一、探索群众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体
事实上,李大钊并非从一开始就明确持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理念。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向世界传递出“十月革命”胜利消息,推动着李大钊早期民主观的形成,因此,在政治革命的现实实践之下,李大钊认识到,“庶民”是社会中最为庞大的群体单位,其力量与感召作用自有其强大所在。1916年,李大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强调“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46页。认为民众意识、民心指向才是真正能创造社会未来的指导力量。由此,李大钊的早期历史观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了“民彝”理念之上,将“民彝”作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方向。②“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39页。所谓“民彝”,即人民群众的心之所向,从人类自然存在来看,它是每个人想要去追求自由、平等的本性意志,是人类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是一种集体性、固有化的理性状态,不能随意变化;而从政治发展来看,“民彝”决定了政治的未来,成为政治发展的指向。虽然此时的李大钊还未对客观物质层面多加关注,但这种“民彝”史观却也凸显出李大钊强烈的“群众”意识,进一步成为他靠拢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基础。
李大钊抱有深切的爱国爱民情怀,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念将人民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因此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特别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群众理念作为自己的共鸣体。但与李大钊不同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生产者,因此所谓历史本质上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属于劳动群众的历史。这种理念,有力地纠正了李大钊先前“民彝”史观当中的幻想色彩。因此,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通过汲取马克思主义对群众力量的坚定信念,在全新建构的群众观基础上,阐述了更符合现实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
作为历史的主体,群众力量是历史发展的核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强大作用,认可“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69页。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发现自有文字以来人类的历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更坚定地认为这种“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层面之上,是通过劳动、分工所形成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局面。李大钊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人类的全部,但它却呈现出了人类历史的痕迹,与人类历史始终相伴,④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89页。而群众便是在当时需要觉醒、需要夺回权力的中心,只有当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李大钊正是在唯物史观的理念当中,寻找到“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⑤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67页。的革命真理。
由此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中,从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维度来看,李大钊肯定了马克思群众观念的现实意义,这种群众理念有力地将传统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向历史、向人类去树立一种新的“人生观”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67页。,有力地呈现出人民的决定力量。正如他所赞誉的那样,马克思将其特有思想理论予以创见的说明,向从前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拓展,最终产生出了伟大的理论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1页。[7]。
二、发掘经济作为历史发展动因
李大钊的思考充满了一种时间意识,在面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流转之间,他不仅能够将生命与自然以时间为轴,一线相贯、一脉而来,注入充盈之力,与此同时,也充满了在宇宙与无限中,对寻找古今生生不息之奥义的渴望。⑧“其得永享青春之幸福与否,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82页。因此李大钊在很多作品当中,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都充满了哲学色彩,希望在哲学层面探索历史精神,发掘历史的理论指导力量。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是如此,作为李大钊发掘的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中“第一块基石”⑨王怀超,秦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8页。,李大钊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作标准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存在,同时,他也特别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指导社会经济实践的重要意义。正如李大钊称,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形成对社会组织的来源认知,由此才可秉现实之状态来观察经济状况,凭经济状况才能良好地对社会未来的阶级走向有所把握。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176页。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将“唯物史观”与客观物质可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建立人生观念这些过程联系起来,②“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参见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页。这是来自时代的立场。从李大钊对马恩观念的接受与学习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他对以经济学为首的客观物质层面所产生的关注。1919年5月,李大钊在《晨报》刊载了《劳动与资本》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过程中,也同样认为经济作为客观物质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除所谓的“经济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即马克思特有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一般称为唯物史观,因为种种理由,我想称为经济史观也可以。”③[日]河上肇,《河上肇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246页。河上肇以经济为视角的分析成为了李大钊的重要参考,因此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中,李大钊也坚定地认为,通览历史物质之要件,也唯有经济现象变化最多,影响最大。④“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0页。将社会进程的发展维度放置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又站在经济角度再度细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其分为“经验式说明”或“社会组织进化论式展现”两大要点。⑤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7页。
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李大钊站在唯物主义的视角,认为马克思将“物质生产力”作为社会内部构造的最高动因。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1页。而基于河上肇的阐述,李大钊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中也特别阐述了生产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具体来看,即正是在生产力不断变动的情况之下,社会也会逐步发生变革,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才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推进。李大钊分析道,正是随着这样的历史推进,资本主义最终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化。正如手臼形成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而蒸汽制粉机则推动了资本家社会的来临一般,特别是对于社会革命现象来说,正是随着生产力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当逐渐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时,其生产力愈是力量壮大,就愈会与无法适应的社会组织之间产生冲突,在此矛盾之下,社会组织便走向“崩坏”状态,“新的继起”随之产生,社会革命也由此到来。
由此看来,李大钊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以经济作为物质原则的前提下,将历史与阶级斗争产生了内在的联动作用,其形成的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化的指导原则,可以在社会建设的不同板块之间有序建立,以此形成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潮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的李大钊,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放置在以“经济”为核心维度的社会理论当中,形成了一种纵向化发展式的阐论。而在经济史论的色彩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发展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动因方面回答了历史的进程问题。在此角度下,唯物史观更是成为了一种“变革的社会学”⑦[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页。。
三、反思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局限性”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量篇幅向国人来重点介绍、阐论“唯物史观”,构成严谨的研究系统:纵向来看,李大钊建构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即孔多塞、圣西门等人对唯物史观的理念,以及马克思在其间所获的启发,⑧“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西斯蒙第、圣西门、蒲鲁东、罗德贝尔图斯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196页。横向来看,他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材料为重要参考,在其基础上总结唯物史观的部分论点。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是马克思进入中国大门的重要开山之作,同时,也是李大钊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概括包含了个人许多主观认识,尤其是作为注重实践的革命家,也不乏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考量,以革命实践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批判,在此期间,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仍然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对马克思的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置于自己的辩证法维度中进行解读。
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界定为一种“经济史观”的形态,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史观是一种“决定论”,本质上来说,李大钊对于这种“决定论”持有一种矛盾性的态度。首先,李大钊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当中所强调的经济因素之外,人种等其他相对较弱的变化性因素同样也可对社会现象形成一定范围的影响。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54页。更为重要的是,早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便已经从革命性的实践现实当中发觉到人类身上巨大的能动力量,特别是在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他相信作为世界革命的重要浪潮同样也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也相信人民能够从这样的革命实践中将中国从压抑中拯救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实践更是燃起了李大钊想要看到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希望。由此可见,李大钊的历史哲学观念,本身就带着对人民群众力量的积极意志,带有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式思维。
但当时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他将唯物史观单纯放置在经济决定论当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仅仅将生产力作为动力,因而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其并不具备革命实践的土壤——而这恰恰就是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境况。在此解读下,李大钊并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仅仅将“经济”作为依托的做法,认为这种观念会将经济因素推至一种绝对化、膨胀式的状态,甚至为经济物质本身加上一种“命定式的色彩”。而当李大钊关注到马克思派的社会党活动时,他发现正是由于这种命定之说,会导致这些派别难以提出建设性意见,难以组织革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李大钊担忧这种唯物史观是否会为多个国家社会党造成负面影响。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64页。而对于中国革命实践来说,李大钊同样认为这种单方面的决定论观念也会成为阻碍,“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的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66页。
站在理论的批判维度,李大钊的史观理论在自身的积极的革命热情和明确的辩证思维下,他的批评是具有意义的:李大钊并不盲从马克思主义观念,而是能够积极地将中国社会的革命进程融入其间,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既有严谨的学者品格,同时又具备革命家情怀,渴望能够在唯物史观当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正是由于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较为局限,因此,李大钊自视中国革命的实践会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走向一种消极性的停滞,这种观念,与中国当时对革命的迫切需求形成了一种矛盾关系。但是,正是在他的误读当中,我们却能感受到李大钊与马克思之间关于辩证化思考与能动性支持的某种契合。李大钊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的认知,改进并完善了自身的理解与阐述,将历史哲学思考更好地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四、《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指导性意义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中,走进唯物史观,介绍唯物史观,阐论唯物史观,本质上是将唯物史观带入近代中国、寻找救亡之路的过程。在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读意义重大,不仅扭转了中国近代史语境下的历史哲学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源头,同时,李大钊在其中体现出对学术和革命工作的伟大热情,依然对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一)中国近代史历史观念的重要转折
以历史的实践寻找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以历史观的探索来指导、思考祖国的发展。对于历史观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通过对于唯物史观的解读与思考,批判、扬弃了自身与中国传统的历史理念,做到了“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①韩一德,王树棣,《李大钊研究论文》(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259页。
从李大钊自身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从“民彝”走向唯物史观的重要桥梁。在此之前,李大钊格外重视“民彝”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民彝”力量的推动下所完成的,因此,人民群众才是历史不断推进、向前发展的主人。而与“民彝”史观相对,李大钊否定从传统而来的英雄史观,认为英雄代表的是“众意总积”,因此,当远离庶民,英雄便也不复存在,离开民心所向,英雄则不再具备英雄之力……如果人民过于崇拜英雄之性,则在某种程度上,民心一旦有所遮蔽,民众则再次“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48页。。“民彝”史观为李大钊打下良好的群众理念基础。但本质上,李大钊对民心本性的过分重视却也削弱了其中的现实性意义,使“民彝”史观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观唯心色彩。而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民彝史观转而变为唯物史观的催化剂。
从近代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念来看,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成为将人民从传统愚昧引导至科学旗帜下的重要动力。在李大钊看来,中国传统历史论几乎都与“神道”相通,归于天命之下,带有浓厚的宗教气味。因此,对于当时探索存在意义的哲人来说,都不约而同将人类的命运走向归于一种宿命之论,受控在神的法则之中,而国家治乱兴衰之变,亦是如此,正是“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因此,崇拜能够感知天命甚至抗衡天命的伟人、圣贤、王者、英雄等巨人式的历史观应运而生,而这种崇拜的目的也不过“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27,228页。总体上,这些传统的历史哲学理念都是一种极强的唯心论调。而李大钊个人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较大,因此结合唯物史观的客观基调,他将实证的、经验的方法结合进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既站在群众历史的角度,批判将历史个人化的思想理念,同时以经济作为原则,改变一直以来的以神为本的命定观,将历史哲学问题从封建的色彩中清除,从而转向科学化论证。
与此同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李大钊将唯物史观阐论作为革命指导的重要参考纲要,在马克思原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下,注入了更多来自近代中国的实践意义。在此,历史哲学命题不再唯哲人而考量,转而成为了一股面向大众的觉醒力量。这种信仰引导了李大钊怀揣着更多的热忱,想要号召更多的知识分子走进工农当中,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农群众。因此,之后的李大钊积极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进行讲演,组织领导青年、工人、农民等群众性运动,启发群众的革命性,引领中国革命和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他所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此也成为了他践行唯物史观的重要印证。
由此可见,李大钊真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下历史哲学命题的形态变化,即一改愚昧无知的思想态势,注入科学力量,并将目光聚焦于人民的思想动态当中——这无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奠定作用。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意义与启示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他的社会主义理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一旦离开他特有的历史观而去考察其社会主义简直是无稽之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的详尽阐论,才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界的传播。
当然,早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主义理念便已经受到想要改良中国现状的有识之士关注,例如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但从本质上来看,他们或是将马克思主义观放置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语境下进行阐述,或是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而宣传。在此,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高高在上的理论观点,本质上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割裂开来。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诞生,恰恰是对前人传播局限的弥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相结合之基础。其中的唯物史观理念,不仅在李大钊的解读下,成为深入、全面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更是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到中国革命,指导中国未来走向的思想源泉。可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入到近代中国的社会当中。而后,李大钊又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新审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念,接连地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多篇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章,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在阅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触动,逐渐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他特别将李大钊视为自己在北平遇到的“大好人”,视为“真正的老师”,可见,李大钊对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青年来说,其引领作用是巨大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开启意义,同时,在百年之后的今天,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探索精神对于当下的中国思想理论进程依然有着重大启发——身为革命家与研究者,李大钊做到了不盲从、重实践,冷静客观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环境、现实基础相结合,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启发国人。我们要从李大钊同志得到启发,在新时代继续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以开放式心态,促进理论改革,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