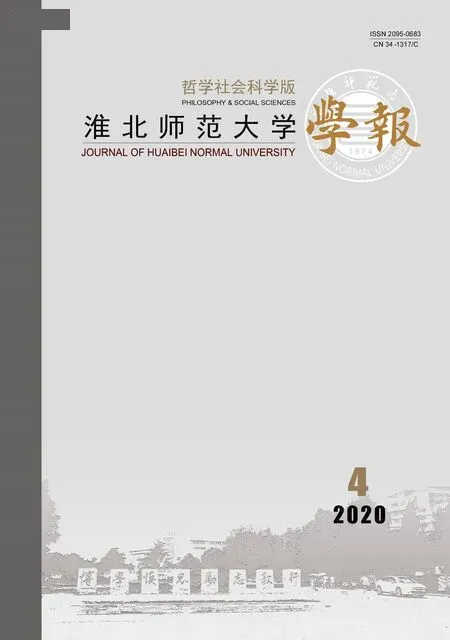《东方杂志》(1920—1932)戏剧翻译与创作
杨 梅,侯 杰
(1.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2.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翻译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北235000)
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持续办刊近半个世纪,有“杂志之杂志”“近现代史研究的资料库”之美称,学界重视该杂志思想文化价值的挖掘,而对其新文学实践的实绩却关注不够。发表文学作品1000 多篇,创作作品500 多篇,“就作品的数量和规模而言,《东方杂志》不亚于一般的文艺期刊”[1]137。为摆脱1910年代与《新青年》论战造成的“落后”“保守”的形象,提高市场销售量,《东方杂志》于1920 年实行“大改良”。改良的宗旨之一就是“大力输入新文艺”[2],1920到1932年的《东方杂志》从封面设计到栏目的设置带有浓厚的文艺色彩,先后设置“世界新潮”“世界论坛”“新思想与新文艺”“文艺情报”“东方与西方”等栏目译介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并在“文苑”等栏目中将翻译与创作作品并置刊载十几年,文学气象蔚为大观。1932年以后,由于战争和更换主编,杂志的文学内容减少,政治色彩变浓。近年来,《东方杂志》的翻译研究逐步增多,如陈发明、赵黎明论述了1920 年以后《东方杂志》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3],侯杰分别论述了《东方杂志》1904—1911年的科 学 翻 译[4]、1911—1919 年 的 政 治 翻 译[5]以 及1920—1932 年的文学译介与创作的关系[6],而对《东方杂志》戏剧文学的译介和创作关注不够。本文旨在以《东方杂志》1920—1932年的戏剧理论译介、作品翻译及其与创作关系为例,探讨杂志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与贡献。
一、戏剧理论译介
1920年1月,主编钱智修在“改革宣言”《本志之希望》把文学置于很高的地位,“能描写自然之美趣,感通社会之情志者,莫如文学”,然少数文言译籍“于西洋文学,将弥失其真”,故他提出杂志“拟以能传达真恉之白话文,多译名家之代表著作,且叙述文学之派别,纂辑各家之批评,使国人知文学为何物”[7]。五四后,新文学创作不济,白话翻译西洋文学仍是各大期刊的首要选择。从数量上看,《东方杂志》1920—1932年“文学介绍”共298篇,其中戏剧及戏剧家介绍42 篇。杂志翻译戏剧作品54篇,仅次于小说翻译的数量,可见戏剧译介是《东方杂志》文学翻译之大宗。
(一)“综合地研究”
“文学介绍”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为普及国人文学常识,《东方杂志》倡导“把西洋文学做综合地研究”[8],国别文学史概况译介包含了欧美各国戏剧介绍。雁冰(沈雁冰)的《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17卷6-7期,1920年2-4月)就译介了爱尔兰的讽刺剧、历史剧和农民剧;愈之(胡愈之)的《近代英国文学概观》(18卷2期,1921年1月)介绍了英国近代悲剧家比内罗、喜剧家琼斯以及擅于心理描写的戏剧家高尔斯华绥等,又介绍了夏脱(后译“夏芝”“叶芝”等)、沈琪、葛雷古夫人及萧伯纳等戏剧家;愈之的《近代法国文学概观》(18 卷3 期,1921 年2 月)译介了“自然派”剧作家小仲马、讽刺剧作家沙尔道、浪漫派剧作家弗朗西等;愈之的《近代德国文学概观》(18卷7 期,1921 年4 月)介绍了莱森的剧评和薇兰的莎士比亚剧翻译。宋春舫译介的《法兰西战时之戏曲及今后之趋势》(18 卷21 期,1921 年11 月)介绍了戏剧家白尔斯登、浦而显等人的作品;宋春舫译介的《现代意大利戏剧之特点》(18 卷20 期,1921年9月)介绍了意大利的新兴剧种。张毓桂译介的《文学与戏剧》(17 卷17 期,1920 年9 月)则以欧洲历史著名戏剧家为梗概,论证了“戏剧并不只是文学的一部分”。
(二)“纵深的”研究
同时,《东方杂志》认为西洋文化之所以能够开创近代文化的新局面,全赖“各种专门学术,有精深之研究,不绝之发明”,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重“横向发展”,而轻“纵深发展”[9]。戏剧的“纵深研究”一方面体现在对戏剧流派专业性介绍,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相关流派作品的翻译。
《东方杂志》的译者群体大多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也是《小说月报》的译者,这两个杂志都推崇现实主义文学。《东方杂志》重要译者胡愈之认为新文学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练才能放出灿烂的光辉,“这写实主义的摆渡船,却不能不坐”[10]。宋春舫译介了《戏曲上的德模克拉西之倾向》(17卷3期,1920 年2 月)描述了西方戏剧发展的宏观规律,梳理了现实主义“平民戏曲”的由来,把“平民戏曲”分为四种不同主题的类型:“研究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问题”“改良法律问题”“描写人类堕落状况”“解放妇女问题”,而这些戏剧共同的主旨“皆具不平则鸣之趣旨,而为平民一吐气扬眉也”。显然,宋春舫定义的19世纪的“平民戏曲”没有脱离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范围,这些“问题剧”属于五四文学推介的“为人生”文学。宋春舫不仅关注“平民戏曲”的欧洲历史,而且还把欧洲的戏剧运动和中国的戏剧改良结合起来,他在《小戏院的意义由来及现状》中这样写道:
在近代戏院的历史里面,最有趣味,最有意义,而且同时对于我们讲改良中国戏剧的时候,最有研究的价值的,就是这个小戏院运动。[11]
《东方杂志》仍持1910年代“包容”“多元”的文化立场,还译介了对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持“反对态度”的浪漫主义、未来主义、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流派。宋春舫译介的《近世浪漫派戏剧之沿革》(17 卷4 期,1920 年2 月)梳理了欧洲浪漫主义戏剧的沿革。除了宋春舫的《现代意大利戏剧之特点》介绍了“未来剧”,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就刊载了《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11 卷2 期,1914 年8 月),改良后又翻译了《未来派跳舞》(18卷9期,1921年5月)、《未来派建筑之奇观》(22卷16期,1925年8月)、《意大利未来派的食物》(28卷14期,1931年7月)等。对于表现主义戏剧的译介有编者译介的《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18 卷3期,1921 年2 月)、俞寄凡译介的《表现主义小史》(20卷3期,1923年2月)、章克标译介的《德国的表现主义剧》(22卷18期,1925年9月)、华林一的《表现主义的文学批评论》(23 卷8 期,1926 年4 月)等。幼雄(胡愈之)翻译的《叇叇主义是什么》(19卷7 期,1922 年4 月)是中国最早介绍“达达主义”的文章。胡愈之高度评价了唯美主义先驱克次(John Keats)(后译“济慈”):
像五六十年以前史文朋(Swinburne)莫理士(Morris)等人所唱导的艺术的生活观,和后来王尔德(Wilde)“为艺术的艺术”的极端的主张,都可以说,多少是渊源于克次的。[12]
对一些作家的综合性译介,也会提及作家本人在戏剧方面的建树,如愈之译介的《介绍爱尔兰诗人夏芝》一文就介绍了夏芝为了建立爱尔兰的国民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重点介绍了夏芝的《加丝伦尼霍立亨》。介绍戏剧理论或流派以后,《东方杂志》往往紧接着翻译相关作品,进一步加深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理解。
二、戏剧作品翻译
欧洲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经典小说受到《东方杂志》的青睐,如俄国白银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等,但《东方杂志》戏剧翻译却呈现多姿多彩的“多元特色”。除了翻译少量的现实主义戏剧,还翻译大量未来派、表现主义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作品。总体来说,戏剧选材以胡适提倡的“名家名译”为主,既重视俄、日、英、法等文学强国的经典或流行作品,也重视比利时、爱尔兰、瑞典及犹太民族及世界语等“小国”或“小语种”戏剧。
(一)现实主义戏剧翻译
《东方杂志》翻译的俄国戏剧都是短小的喜剧,如济之(耿济之)翻译了乞呵甫(后译“契诃夫”)的独幕短剧《熊》(20卷3期,1923年2月)(又名“《蠢货》”),还翻译了卢那却尔斯基的喜剧《爱艺术的国王》(21 卷13-14 期,1924 年7 月),曹靖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21卷19、21 期,1924 年10-11 月)。英美现实主义戏剧翻译有子贻翻译美国M.C.Davies 的寓言剧《两副面孔的奴隶》(19 卷11 期,1922 年6 月),邓演存翻译高尔斯华绥的《小梦》(19卷13-14期,1922年7 月),赵惜迟翻译英国Alfred Sutro 的独幕剧《街头人》(19卷19期,1922年10月),钦榆与芳信合译Sarah Jefferis Curry 的《恶魔的黄金》(23 卷19 期,1926年10月)等。
《东方杂志》比较关注日本“白桦派”、法国的古典主义与自然主义戏剧。仲持(胡仲持)翻译了日本古典主义戏剧——古狂言《莫须有》(19 卷5期,1922年3月);张定璜翻译了有岛武郎的《死及前后》(20 卷19 期、24 期,1923 年10、12 月);仲云(樊仲云)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没有能力者》(21卷11期,1924年6月);葛绥成翻译了菊池宽的《时间之神》(23卷8期,1926年4月);章克标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爱欲》(23卷14-17期,1926年7-9 月);宜娴(胡仲持)翻译了菊池宽的《复杂以上》(26卷17-18期,1929年9月)等。王了一翻译了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无可奈何的医生》(27卷15-16期,1930年8月),他还翻译了法国哥克多的独幕剧《人类的呼声》(27卷20期,1930年10月)及勒纳尔的《绝交的乐趣》(27 卷23 期,1930 年12月)等。
(二)现代主义与“小国”戏剧翻译
《东方杂志》对新潮的现代主义戏剧独有情钟。宋春舫是“未来派”戏剧的主要译者,他先后翻译了法国San Seondo 的“未来派”独幕剧《眼睛闭了》(18 卷14 期,1921 年7 月),意大利独幕剧四种:《换个丈夫吧》《月色》《朝秦暮楚》《只有一条狗》(18卷13期,1921年7月)。《东方杂志》也翻译了几部德国的表现主义戏剧,如仲持翻译Karl Ettlinger的《利他主义》(18卷16期,1921年8月),余芷湘翻译Roderick Benedix 的《好的预兆》(20 卷6-7 期,1923 年3-4 月)等。杂志也捕捉到当时欧洲“流行”现代主义戏剧,如旅魂翻译了法国喜剧《盲人与驴》(20卷12期,1923年6月),王靖翻译意大利Giuseppe Giacosa 的《灵魂的权利》(19 卷2期,1922年1月),芳信翻译了夏芝的《加丝伦尼霍立亨》(21卷7期,1924年4月)等。
比利时、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小国或者小语种民族的戏剧,也是《东方杂志》关注的重点。追逐文化热点的市场效应是《东方杂志》选材标准之一,欧洲小国或小语种民族文学,曾有多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可以解释杂志翻译这些小国或小语种戏剧的动因。
《东方杂志》一向倡导“世界语运动”,据“《东方杂志》全文数据库”,①参见“《东方杂志》全文数据库”:http://cpem.cp.com.cn仅胡愈之在1920年代宣传世界语的文章就达15 篇,天月从法国世界语杂志Revuo 选译了H.J.Bulthuis 的戏剧《美洲来的姨母》。雁冰翻译了意大利James M. Beck 的《和平会议》(19 卷14 期,1920 年7 月),爱尔兰作家唐珊南的《遗帽》(19卷16期,1920年8月),爱尔兰葛雷古夫人的《市虎》(19卷17期,1920年9月);愈之翻译了犹太剧作家宾斯奇的《外交》(18 卷12 期,1921 年6 月),瑞典剧作家淮特的自然主义戏剧《秋之火》(18 卷20 期,1921 年10 月);王靖翻译了西班牙龚少尔兄弟(Quintero)的独幕剧《光明的早晨》(19 卷10 期,1922 年5 月),愈之翻译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西班牙戏剧家倍那文德(Jacinto Benavente)的《怀中册里的秘密》,钟显谟翻译了西班牙戏剧家Olave Bilac 的独幕喜剧《黑蝴蝶》(23卷24期,1926年12月);杨袁昌翻译了奥地利显尼志劳的《生存的时间》(22 卷14 期,1925 年7 月)、《最后的假面孔》(22 卷24 期,1925 年12 月),赵伯颜翻译了奥地利Arthur Schnitzler 的《绿鹦鹉》(25卷15-16期,1928年8月);徐蔚南翻译了比利时著名剧作家梅特林克的《茂娜凡娜》(23 卷3-6 期,1926年2-3月)等。
三、戏剧创作
(一)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文学栏目中,《东方杂志》经常把翻译与创作作品并置,暗示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除戏剧理论译介从宏观层面涉及到戏剧思想及语言特色介绍,许多作品翻译的“译者识”充当“阅读引导”,常常分析作品思想价值及对国内戏剧改良的启发意义。
从予在《茂娜凡娜附言》中讽刺了该剧改编电影的中文译名《为国牺牲》不切原作中心思想,并借用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的评论加深国人对这部戏剧的理解:
我则以为梅氏此剧完全在暗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精神与新气运。脱离中世以来的因袭道德的羁绊,而趋向清新美妙的生活,创造自由的天地;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梅氏藉着恋爱把这精神表现出来,这便是本篇中心思想之所在。[13]
同样,从予在《第二梦的著者倍雷》中分析了《第二梦》作者倍雷的写作技法和语言特征:“把人物的情性,用对话体明白的说出;至于布景叙事则但用记述的文笔”[14]。
洪深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不少戏剧作品,虽没有直接论述戏剧的理论文章,但在其改写的《少奶奶的扇子》正文前附有长篇“序言”,以“剧本与说部”“何谓像真”“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剧本之三件事”“改译”等9 个部分向读者普及了戏剧理论。特别是在“改译”部分,洪深认为:“改译云者,乃取不宜强译之事实,更改之为观众习知易解之事实也。”[15]宋春舫在“未来剧”《换个丈夫吧》(18卷13期,1921年7月)篇首认为中国戏剧改良向欧洲借鉴,不能只翻译理论,还应注意翻译剧本,加深对西方戏剧理论的理解:“要研究未来派的戏曲,先得译出几种未来派的剧本来。……我们脑筋里,向来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一定先要看了剧本,然后可以下几个评语。不然,就是‘盲人骑瞎马’了”[16]。《光明的早晨》篇尾“记者附志”介绍了龚少尔兄弟的滑稽风格,并提醒读者《小说月报》有关此兄弟二人的译作。《绿鹦鹉》篇尾的“记者附志”介绍了这部戏剧“对句”的语言特征
除了译介,《东方杂志》还刊登国人原创的戏剧理论。周作人认为“新剧当兴而旧剧也决不会亡的”,他提出了中国戏剧的三条道路:“一、纯粹新剧:为少数有艺术趣味的人而设。二、纯粹旧剧,为少数研究家而设。三、改良旧剧,为大多数观众而设”[17]。由此观之,改良旧剧是戏剧创作较为可行的一条道路。但是,吸收了西洋戏剧的“写实”和“模仿”技巧的“北剧”,演化成所谓的“文明戏”,在五四前后已经出现颓势。欧阳予倩认为这类戏剧是“旧戏与欧洲戏剧的杂交产物”,“不中不西,不伦不类”。[18]洪深力图引进西方戏剧的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进行戏剧改良,来完成传统戏剧向现代戏剧的过渡,以《赵阎王》进行的“突围”,这种意在革除“文明戏”商业习性的实验却失败了。
(二)改写、改译和创作
此期间,《东方杂志》共刊载白话新剧46篇,其中包括不少名家改写或改译的西方戏剧。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赵阎王》(20 卷1-2 期,1923 年1月)实际上是洪深对奥尼尔现代主义戏剧《琼斯皇》的改写,意在影射中国当时的军阀混战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作品发表后,读者市场反响平平,而该剧在上海的公演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了。洪深把“怪异”的表现主义手法搬上舞台,来表达类似说教的启蒙主题,远远超过了当时观众的审美情趣。这些“文明戏”的看客习惯了“消遣”的主题,对怪异舞台表演和严肃现实主义戏剧主题不感兴趣,而更看中注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文明戏”。事后竟有人骂主演“赵大”的洪深是“精神病人”:“前夜实演时,观众颇不明了,甚至有谓此人系有精神病者。”[19]61接受了《赵阎王》的教训,洪深的改译唯美主义代表王尔德的Lady Windermere′s Fan(后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定名为《少奶奶的扇子》,剧本的发表和公演却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原剧是反映英国上层社会的风俗喜剧,被洪深改编为一部充满道德劝诱的“道德剧”。洪深在“序录”中提及了“布景之佳”和“扇子”在剧中发挥的八大妙用,而没有提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扇子”的文化隐喻含义——“与人为善”。扇子作为核心道具,是打通中西戏剧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码,中国观众对“少奶奶”“扇子”这种本地化改译策略会欣然接受而无文化冲突之感。配角人物,原剧中只有男仆“帕克”,而洪深在《少奶奶的扇子》中凭空附加了贴身丫头“菊花”,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礼仪的考虑,使改译更为真切。洪深发挥了原剧中“善”的因素:良家妇女对于婚姻的不忠诚、不检点,最终差点导致女儿走上和她自己相似的堕落之路。这种道德情结,十分吻合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价值观及佛教中宣扬的“果报”或“现世报”的道德逻辑原理。在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中,“报应”思维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模式,这个原则符合了儒教文化核心的伦理价值观,起着对大众“教化”的作用。因此,《少奶奶的扇子》用中国的传统伦理“归化”了异域文化价值,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认同。
《东方杂志》刊载的改译作品还有,洪深改译英国剧作家倍雷的Dear Brutus而成《第二梦》(22卷9-11 期,1925 年5-6 月),汪梧封改译英国H.A.Jones 的《谎》(28 卷13-14 期,1931 年7 月)。顾仲彝也是善于将外国剧“中国化”的剧作家,他改译法国Arnold Bennett 的作品而成《结婚的一天》(25卷14 期,1928 年7 月),改译Hamilton 的Jack and Jill and a Friend而成的《两小说家一画师》。顾仲彝改译美国剧作家Eugene Walker 的The Easiest Way定名为《梅萝香》(23 卷20-23 期,1926 年10-12月),洪深在该剧“序言”中评价道:“改译本有几处小事实,不很像上海。大概顾君是个学者,终年埋首在书本子里,所以对于这种恶劣的生活,不能十分熟悉;虽然,这就是顾君的幸福了。”
受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东方杂志》刊载的其他新剧作品大多关注社会问题。20 世纪20 年代初倡导妇女运动的语境下,洪深由宋朝民间故事改编的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申屠氏》(22 卷1-4期,1925年1-2月),颂扬了敢想敢做的中国妇女形象。熊佛西是另一位在《东方杂志》发表剧作较多的剧作家,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8部戏剧作品和2篇戏剧理论的文章。他的《一片爱国心》(23卷10期,1926年5月)反映了异国恋青年的爱国与爱情的冲突;四幕剧《蟋蟀》以三兄弟为追求女主人公而自相残杀的故事,暗讽了中国的军阀混战,熊佛西因此遭到张作霖的逮捕;三幕剧《爱情的结晶》(27卷17-18期,1930年9月)仍然反映了妇女问题。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回家以后》(21 卷20期,1924 年10 月)描写了一个不忠贞的留学生发现结发妻子具有新式女子不具有的优点,戏剧令人反思不同文化影响导致的道德伦理问题。洪深在顾仲彝改译的《梅萝香》“序言”中评价道:“这剧本是描写繁华场中堕落女子种种生活的社会剧”,顾仲彝创作的《张将军》(28卷24期,1931年12月)同样是有关妇女问题的社会剧,该剧塑造了一位不畏军阀、机智勇敢的女主人公“二姑娘”形象。一些短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东方杂志》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重要平台,科学剧《爱之光》(19 卷24 期,1922年12月)正是普及哲学和科学知识的一个短剧。
结语
《东方杂志》为达“使国人知文学为何物”之目的,戏剧翻译和创作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横向研究”——“综合地”译介戏剧理论常识,又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纵深发展——深入地介绍戏剧专业理论、翻译经典及流行戏剧作品,进而促进国内戏剧改良和创新。作品的翻译以“名家名译”为主,精准把握读者市场的文化热点,除了翻译欧洲及日本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还十分热衷翻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国”及“小语种”戏剧作品。在译介理论与翻译作品的基础上,《东方杂志》以中外比较文学的视野,将翻译作品与创作作品并置,暗示创作与借鉴之间的关系,名家改译、改写和创作的戏剧,充分吸收西洋戏剧的技法与思想内容,并把作品的主题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关联起来,显示了现实主义思潮对中国戏剧改良与创作的深入影响。整体上,《东方杂志》为一大批译者和戏剧家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戏剧翻译和创作实绩体现了该刊践行五四新文学“稳健”“包容”的文化立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建构必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