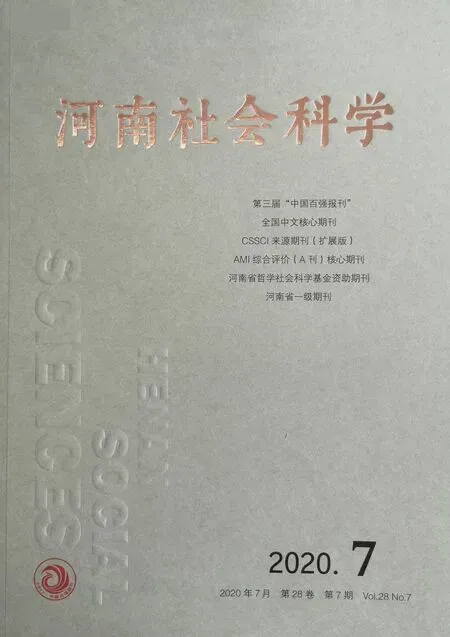论罗伯特·库弗小说的创新思想
杜 钦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2.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罗伯特·库弗是美国后现代流派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文学理论的积极建构者。作为学者,库弗对小说的革新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作家,库弗善于把自己的创新思想用各种独特的手法表现在自己的小说中。无论是学者库弗还是作家库弗,其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都受到当代哲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解构主义与接受理论。
一、传统与革新的关系
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解构主义与接受理论相继诞生。哲学界与文论界的新声必然会引起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革新。
《书签》(The Marker)是库弗的短篇小说集《符号与旋律》(Pricksongs & Descants)中的一篇,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库弗正面表达了他对于传统与革新的看法。熟悉经典文学的读者不难分辨出,故事的开头是对现实主义描写手法的仿讽:房间里,杰森正在读书,同时看见妻子正在铺床并用肢体动作邀请杰森与她做爱;杰森做好阅读标记,熄灭了灯。至此,现实主义风格的有序性、和谐性、完整性都在文本中得以充分体现。可见,库弗对于传统文学的形式与特征有着极其精准的把握。同时,在传统的“期待视野”模式的作用下,读者会默认杰森夫妇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下意识期待接下来的线性叙事。
然而,故事却骤然坠入后现代的荒诞情节中:灯熄灭的瞬间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改变了位置,杰森找不到妻子和床;而当他终于在妻子笑声的引导下找到了床,正在和妻子做爱时,灯又忽然被打开了,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杰森发现与他做爱的实际上是一具僵尸。最后,作为惩罚,警察击碎了杰森的睾丸。习惯了传统叙事方式的读者也许会对这种“去中心”了的情节感到莫名其妙、晦涩难懂,而实际上作者正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情节撞击”来提醒读者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存在及日渐凸显。
库弗用“断崖”式的“拼接”(collage)手法,将两种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文学风格粘连在一起,可以说将后现代作品中的荒诞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库弗并没有像贝克特一样,把荒诞的解释权留给读者,相反,他借用警察这个角色清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你知道,严格来说我不是个保守主义者。我并非没有认识到传统的神圣性……我也并不想与那些认为传统有着内在劣根,因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它的人联手。我自认为……是有一条中间道路的,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认识到传统其实是创新最理想的土壤……”[1]91
可见,库弗并不是一位因思想过分激进而一味追求革新、否定一切传统的后现代学者。一方面,他明白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与革新实践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传统的宝贵价值,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最好的创新多萌发于传统,传统本身就是培育创新最合适的温床。现代及后现代作品中不断存在的对经典作品的仿讽之作便是最好的例证,如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玻璃山》是对经典童话的仿讽,再如香港作家李碧华的《青蛇》是对民间文学《白蛇传》的仿讽。实际上,对传统不屑一顾的创新多会成为无本之木,如昙花一现,难以给文学带来有价值的影响。所谓的“中间道路”也在警察的最后一句话中得到明确阐释:“回顾(review)与改进(revise)是一个人永无休止的任务。”[1]91传统的价值需要在回顾中得以确认,而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只能在改进中得以保持。
故事中杰森与妻子的隐喻可以理解为艺术家与其创作活动的关系:当传统的艺术形式已变得陈旧腐朽、难以满足艺术受众的需求时,继续因循守旧、不加改进的创作模式,就好像与僵尸做爱一样,乏味、恐怖、令人作呕。事实上,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文艺界,而且也适用于我们的工作乃至日常生活中;这也是此短篇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故事的标题《书签》实际上标记的是一种文学流派的结点;故事最后,警察对杰森的惩罚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了怀疑、思考、批判之后,断定了其延续能力的终结。旧的文学传统已完成了其孕育新文学形式的使命,作者和读者都必须暂时将其搁置,才能继续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路。库弗本人也曾明确表示:“我很少有耐心读那些被过分赞誉而实际上只是重复三百年来旧形式的东西。一读到打破规则、打破传统、改变旧方法、不局限于传统、不囿于前代人强加给我们的信仰、神话及其梦幻的东西,我就很激动。”[2]
那么,为什么总有新的流派在文学史中更迭?为什么文学创作不能沿着已被认可的模式恒常走下去?文学创新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客观推动作用,还有没有更为微观、更为主观化的需求?换而言之,在传统文学中被既定为“受众”的读者们在文学创新的过程中有没有其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创新过程?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二、读者需求与创新需求
德国文论家尧斯首次提出了“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概念,它指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将读者与作者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期待与假设。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是接受理论的首要特征。该理论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悲剧对观众的“净化”(catharsis)功能的论述。其后的贺拉斯不仅认为观众是作品艺术性的终极裁定者,而且认为“对话性”是文本的固有属性:特定观众的反应引导着创作过程。朗基努斯也在他的《论崇高》中表示,文学作品真正的崇高体现在受过教育的读者群给予的持久一致的认可。王尔德在他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艺术真正反映的并非生活,而是观赏者。这既是对艺术模仿论的颠覆,又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读者反应论的到来。
之后的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思想理论都为该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哲学基础。胡塞尔首先区分了“现象”(phenomenon)与“客观事物”(object),并认为只有被人们感知到了的事物才能被称作“现象”,所以“客观事物”不能存在于意识对物质的能动感知过程之外。胡塞尔继而提出他的艺术观点:作品的成形依赖于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的审美能力,文艺作品不可能存在于一个“缺乏审美能力”的人的世界中,也不可能先于读者的接受而存在,即“无感知,不艺术”。
海德格尔在重新审视时间与“存在”的关系后,提出他的艺术观点:“艺术的本质是一种起源,是真理成为存在、成为历史的一种独特方式。”[3]716他认为艺术是揭示并且传达真理的方式,而真理一旦得以表述,便成为“存在”,继而转变为存在的“历史”。在此艺术的历史功能论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端都是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众多的陌生与精彩……艺术的发生,便是历史的开端。”[3]717
作为对形式主义的反驳,接受理论反对作品本身有其独立于受众之外的形式与意义,而是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能动行为放到与作者的创作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尧斯正面反驳了文本的客观性,他认为,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接受过程是这部作品美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受众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则无从谈起”。伊瑟尔也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文本本身,还要包括读者对文本的回应。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应该由“两极”(two poles)构成,其中“艺术”这一极是由作者创造的,“审美”这一极则是由读者的感知创造的,而作品的文学价值恰在“两极之间”,通过作者与读者的交融而存在。同时伊瑟尔又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能够“挫败读者的预测”,即突破既定“期待视野”的束缚。只是重复旧说的作品必然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
库弗的短篇《帽子戏法》(The Hat Act)是接受理论最好的例证。作者在此篇中形象展现了受众对作品的反应和接受程度如何在绝对意义上左右作者的创作活动;创作者在受众需求的驱动下,不得不努力进行创新实践。在这篇小说中库弗采用了剧本形式,讲述了一场魔术表演,包括舞台展示内容与观众相应的反应。尽管有些表演内容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行的,但是后现代的夸张与悖谬特征仍使得文本具有极高的生动性、可读性。魔术师以从帽子里拿出一只兔子为开端,继而不断尝试难度更高的戏法,甚至把自己的助手乃至自己的脑袋从帽子里拽出来。这一系列大胆的尝试实际上是在观众的驱使下进行的,因为每当一个把戏结束后,观众都会有“下一个会更精彩”的期待,并且如果期待没有得到满足,观众就拒绝鼓掌。这便是“期待视野”的效果:受众的反应并不是随机的,而总是要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期待与假设的基础上的,因而“期待视野”也会因时期的不同或者受众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以《堂吉诃德》为例,同一部小说,在骑士时代是一部历险佳作,而换到作品本身的时代,便成了对骑士小说的辛辣仿讽。
事实上,在《符号与旋律》中,库弗也确实写下了“致塞万提斯”的篇首语。库弗之所以如此尊崇塞万提斯,是因为其在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中阐述了丰富的、开创性的小说理论,如他从否定角度谈小说的独特性:不借助于经典,不受古代法则的约束,体现出创作上的自由;表现想象的艺术,不追求精确,无需证明;不是说教的工具,不是伦理研究,也不是神学;不是哲学,不用来传达思想。作为塞万提斯的忠实粉丝,库弗感慨道:“您(塞万提斯)曾经感受到的乐观、纯真和存在种种可能性的氛围已经消逝殆尽,宇宙的大门正再次向我们关闭。和您一样,我们似乎正站在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开启的地方。”[4]44
尧斯用“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一词形容既定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的差距,并指出这种差距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的逐渐被理解而渐渐消失。伊瑟尔也说:“我们前瞻,也回顾;做决定,也改变主意;形成新的期待,落空时为之震惊;我们质疑,深思,接受,或拒绝;这就是recreation的动态过程。”[3]726“recreation”一词一语双关,可以解释为“娱乐消遣”,亦可以解释为“重新创造”。文本的解读与审美活动恰是这两个词义的合二为一,既是娱乐活动,又是创造过程。因此,伊瑟尔坚持认为,在阅读过程中,主体是读者而不是作者,同时读者也是思考行为的主体。
在《帽子戏法》接下来的情节中,或是因为对自己助手的失望,或是因为自己戏法库存的枯竭,魔术师开始感到暴躁不安。最终,他把帽子扔到地板上,跳上去,踩死了还在帽子里的助手。原本给人带来新奇与欢乐的剧本终于演绎成一出黑色喜剧:凶手被当场处决;一张大板竖立起来,用大写字母写着:演出结束,抱歉不能退款。对于故事的结尾,读者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魔术师真的踩死了帽子里的助手,结局就是悲剧的;魔术师踩死助手与最后竖起的板子一样,都是演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魔术师的创新尝试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或者入戏太深酿成悲剧,或者表演精湛堪称完美。而无论读者选择哪种解读方式,实质上都是在完成伊瑟尔所说的“recreation”的过程:既把阅读当作娱乐活动,又在选择中再次创造了文本。
这个短篇是《符号与旋律》的最后一篇,是库弗给文学创新这个主题量身设计的一个剧本,可以当作全书升华主题的收官之作。通过戏剧化的表演设计,库弗意在用此篇提醒创作者们,旧的艺术形式必然要在新流派的冲蚀下黯然失色,最终失去艺术受众的兴趣与关注;对新奇作品的期待与渴望是观众和读者的合理诉求,更是鞭策艺术创作者不断创新的动力;作家如果不进行创新实践,一味重复旧制,其作品便会失去色彩与生命力。此外,库弗也在警示创新之路上的求索者们:在创新探索的过程中,不可急于求成或偏颇执拗,否则便如结尾解读之一,终适得其反,难以自拔。以乔伊斯为例,《尤利西斯》被公认为现代主义流派的巅峰之作,但在其后的《为芬尼根守灵》中,作者似乎陷入了后现代的偏执中无法自拔,一味致力于语言的隐晦性与隐喻效果,最终使该文本成为文学史上最伟大却又最让人难以读懂的作品之一。
三、作家库弗的创新实践
关于情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它应该是只有一头(beginning)、一身(middle)、一尾(end)的一个整体,头是起因,身承上启下,尾则一定是最终结果。后现代的另一代言人罗兰·巴特则在他的著作《S/Z》中首次将文本划分为“读者文本”(readerly text)与“作者文本”(writerly text)。在阅读“读者文本”时,读者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在阅读“作者文本”时,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合著者”,必须自己去选择分析、排列组合、建构故事。无数的读者成就了同一个文本无尽的可能性。尼采则更进一步地认为,因果的定向逻辑本来就不存在,如“针刺——疼”是因果,但反过来“疼——发现针”也是因果。不仅如此,“疼”的结果也可能是发现一个钉子、一个针头,甚至一只蜜蜂……读者能动确定文本的过程,实际就是读者与作者的合作与互动过程。王尔德也在他的文学批评中表达了“文学的本质是纯粹主观”的观点,因此拒绝了作者创作意图的权威性:作品一旦问世,便有了自身独立的生命力。
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综合了诸多思想激进的哲学家的理论(如尼采对于真理的质疑、弗洛伊德对于主体意识的批判、海德格尔对于存在论的再次审视),建立了解构主义理论体系。解构主义首先否认了西方哲学长久以来默认的“罗格斯”权威,在拒绝绝对真理的同时,也拒绝“罗格斯中心主义”,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拒绝承认文本的中心。
短篇小说《保姆》(The Babysitter)是库弗文学创新实践的典型。与前两个短篇不同,在这篇小说中,库弗并没有显性或隐性地嵌入任何关于创新的理论主张,而是运用碎片化(fragmentation)、自我抹除(self-erasing)、超链接(hyperlink)等手法,完全颠覆传统文学中顺理成章的因果逻辑、历时叙事,将传统的“作者文本”改造为更有能动性的“读者文本”。在故事情节上,既无中心人物,也无中心线索,甚至没有明显的时间顺序,可以说是“去中心”手法的代表之作。故事分为108 个小节,读者只能在整体上明白大致是一系列安排在晚上7:40 至10:00之间的情节片段,却无法为整个情节作一个概述,甚至任何为这些片段排序的尝试都只能是徒劳心力,因为作者不断地用之后的片段否定之前片段中的情节,例如:男主人是否在宴会中途返回了家?保姆的男友到底有没有来找她?男主人是在幻想还是现实中强奸了保姆?保姆是诱奸了小男孩还是把他淹死在了浴缸里?甚至结尾也是相互矛盾的对立:“你听到那个关于保姆的新闻吗?”[1]238似乎证明所有暴力混乱的片段只不过是与情节进展无关的一则新闻;紧接着“你的孩子被杀害了,你的丈夫跑了,你的房子彻底毁了”[1]239,似乎悲剧真实地发生了。
这种自我抹除的写作方法一次次地突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实现了伊瑟尔所谓的“挫败预测”(frustrate our expectation),用“情节轰炸”迫使读者进行积极式阅读。这种阅读模式废除了作者与读者、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是作者的主观意识与读者的主观意识相互协商的过程。所以伊瑟尔说,阅读活动实际上瓦解了寻常概念中的主客观对立;或者说阅读活动本身就是辩证的:作者的主观与读者的自我、虚构的文本与读者的现实世界相互交融。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解构主义进一步否认了“超验的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s),肯定了“滑动的能指”(gliding signifier),并以“love”这个词为例:在与宗教相关的语境中,“love”可以诠释为“为上帝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在其他语境中又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而任何词语都只是一个隐喻,“除了语境别无他物”,能指与所指之间永无确定的对应关系。
这种非对应性在《保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爱她,她爱他”这样的句子多次出现,但语境中却并未明确指示“他”或“她”是文本中的哪个角色。读者即使努力进行积极的分析与筛选,也始终只能推断出可能的所指,而无法确定唯一的所指。由“滑动的能指”建构出的“流动的文本”,更加具有随意性,也更加富有生命力。这也正印证了伊瑟尔的观点:文本的阅读是一个创意活动的过程;恰是阅读活动赋予了文本生命力,“使文本的内在活力得以展现”[3]724。
这种语义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文本阅读的过程也有着两面性特征:一方面,不同读者的不同逻辑与推断交织成一个文本的“阐释网”(a network of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s),令文本展现出无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没有哪种解读是真正意义上科学的、合理的或者权威的,任何一个阐释都只是整个阐释网中的一个线条而已。伊瑟尔以星空为例:文本中的“星星”是固定的,但是连接“星星”的线条是可以变化的,因而不同的人看到的就可能是不同的星座。所以,文本“不是自我生成了意义”,而是发起了能够构造意义的“活动”(performances)。
伊瑟尔还指出了阅读活动的两个特点:(1)它是短暂的;(2)它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阅读过程多半不是一气呵成的,会有暂停和继续;另一方面,已经被阅读过的文本也很有可能被再次阅读。在第一次阅读中,读者对文本是完全陌生的,阅读活动以预测为主;而在第二次阅读过程中,读者就很可能关注到之前没能把握住的,包括文本内部与文本外部的双重关联性。综合来看,阅读活动揭示了文本潜在的多重关联性,文本的生成实际上是在读者第一次的预测行为与第二次的反思行为中完成的。伊瑟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的阅读经历实际上映射了我们的人生经历,因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会不断地寻找与我们人生经历相似的“一致性”(consistency)。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情节安排,或者选择与能指对应的所指时,我们也在潜意识中遵从这种一致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是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一个人的经历与秉性,阅读文本则是认知自我的过程。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经历中。
那么是不是所有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合理的呢?文本解读的相对性延伸至何处?无限性又止步于哪里?就此,伊瑟尔提出了“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的概念;费希则提出了“理想读者”(intended reader)的概念。“隐含读者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文本的结构之中,体现着由文本本身而非以经验的外部现实所设定的所有诱因。”[5]404“理想读者”具备作者所期望的教育背景、独立思维、关注焦点、语言能力、人生经验等条件。可见,无论是“隐含读者”还是“理想读者”,在实际阅读活动中都只能是读者中的小众。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设定文本解读的合理性与相对性:以“理想读者”用“隐含读者”的方式得出的文本阐释为参照,一方面鼓励不同阐释的多面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要尽力规避过于牵强主观的阐释。
四、创新的时代特色
尽管《保姆》是活页文本这一文学体裁的经典代表,但事实上库弗并不是活页文本的首创者。活页文本出现在20 世纪50 年代,之后法国作家Marc Saporta、英国作家B. S. Johnson 都有尝试创作。《保姆》更高的创新价值在于文本中娴熟的超链接手法的运用,使得碎片化了的文本内部仍有着微妙的平滑过渡。
超链接一般出现在网络文本中,通过点击,读者可以迅速获得需要参考的相关信息或者文章。那么库弗是如何在纸质文本中自如地嵌入超链接的呢?“他给她的背上打香皂……香皂滑到了水里,落到了他的两腿间……‘帮我找找,’他对着她的耳朵低语……‘没问题,’宴会主人说,‘你丢了什么?’”[1]222如此,“帮我找找”这句话便成了在不同小节中重复出现的超链接。如果设置在网络文本中,那么通过点击这个超链接,读者就可以实现在不同场景之间的切换:男主人的家中、男主人参加的宴会中、男主人的幻想中。同样作为超链接使用的还有“阿司匹林”一词,分别在6个小节中出现,有些是真实场景,有些仍是男主人的幻想。
解构主义的巅峰也许在于德里达创造出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并赋予它“不同”“区分”“延迟”等多重含义,并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交流”中产生的,“言语”的地位高于“书写”。在他的文章《柏拉图的药房》(Plato’s Pharmacy)中,“pharmakeia”一词的对应翻译有着诸多可能:毒品、药品、毒药、补救、秘方、春药等。只有通过在“交流”中的“区分”,一个词语在语境中的意义才能得以确认。另外,在解构主义看来,任何一个词的意思都远远延伸到这个词本身的“存在”之外,对一个词的解释必然牵扯到一个巨大的关系网。
文学词语的解读更离不开语境与语义相互交织构成的语用关系网。在纸质文本中灵活插入超链接,不得不说这是库弗最为独特、最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手法。一方面,超链接把文本中相关的要素巧妙联系起来,使得文本中“延异”部分的含义有了可参考的相关语境。另一方面,超链接使得活页文本并非完全散漫无章,其大大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同时也使得故事的双重结尾有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关于保姆杀害孩子的新闻是场景切换的超链接,在男主人家的电视中和宴会上的电视中共时播放,或者宴会上电视中播放的新闻就是男主人家发生的惨案。
库弗的这个短篇意在告诉创作者们,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内涵上,更可以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上。艺术创作可以借助科技的突破以实现自身的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阅读需求与阅读模式。
五、结语
通过对库弗的三个短篇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库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者型作家。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他都极力主张文学创新实践,并且敢于、善于用突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库弗的创新思想并未导致他走向极端的狭隘论,相反,对于文学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创新的土壤,传统的价值不容小觑;但是当培育出新的审美之后,大胆摆脱传统的束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方可延续文学的生命力。
第二,库弗能准确把握住文学革新的核心动力。读者的认可程度是衡量文本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的标准,只有读者感知到了的文本才是活的文本。但同时库弗也认识到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催熟,因而作者不可一味迎合读者。
第三,库弗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受到20世纪60 年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影响。在库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的影响:“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得到淋漓尽致的阐释,“去中心”的文本也体现出库弗精湛的解构技能。
第四,库弗能敏锐觉察到科技的进步给文学实践带来的影响。文学创作与科技创新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在作者的创新追求中得到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