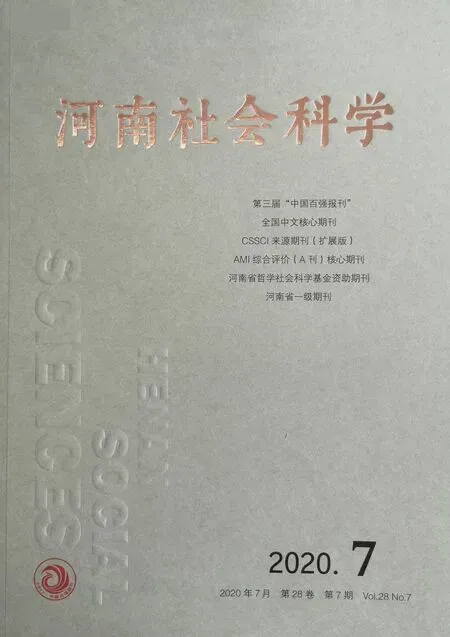季札论《郑》《卫》平议
周 群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秦汉以前的郑卫之音(或称郑卫之声)因其“美听”“宜于众人之耳”,一时影响远胜于雅乐,但自孔子“郑声淫”,到朱熹“郑、卫之乐,皆为淫声”,郑卫之音都被视为淫声秽辞。“郑声淫”似成定谳,而被视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而稍前于孔子的季札在鲁国观乐时,与孔子对郑、卫之音的认识则不尽相同。研究季札的《郑》《卫》之论,既有助于探寻孔子文艺思想的来源,又对全面地认识郑卫之音不无裨益,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史学意义。
一、乐耶?诗耶?
吴王余祭继位不久,季札带着通君嗣的目的聘问中原诸国。到鲁国时请观周乐,鲁国使乐工遍歌《雅》《颂》与列国之《风》,其间季札一一予以评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郑》《卫》并无“淫声”之评。季札观乐之时,孔子尚年幼。因此,季札对《郑》《卫》之音的评论,正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郑》《卫》之音的另一个历史坐标。《左传》和《史记》对其都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其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是:
(鲁)为之歌《邶》、《鄘》、《卫》,(季札)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①
春秋时期诗乐互为表里,《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可见,“诗三百”是兼诗、乐、歌、舞为一体的。唐人孔颖达更谓之:“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工也。”可见,他们都认为《诗经》诗乐同具。对于季札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出聘鲁国时“请观于周乐”,所“观”的内容,一般也认为是诗乐一体的。如刘勰云:“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瞽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文心雕龙·礼乐》)但也有学者认为“郑卫之音”中的音与诗是分开的,如戴震云:“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其诗也。郑卫之音非郑卫诗,如靡靡之乐、涤滥之音,其始作也,实自郑、卫桑间、濮上耳。然则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义甚明。”③马瑞辰也认为“郑之淫固在声而不在诗”④。但是,季札所观当是诗乐一体,因为“为之歌”,必有歌辞,而非徒乐。唐人孔颖达认为季札所闻,乃是“取诗为章”,所论较合情理:
《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长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诗为章,则人之情意,更复发见于乐之音声。出言为诗,各述己情。声能写情,情皆可见。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神瞽大贤、师旷、季札之徒,其当有以知其趣也。⑤
季札是一位博识贤者,在听乐之前当已熟谙徒诗。这当与季札之父寿梦的期许有一定的关系。据《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第二》载:“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哉,礼也。’”⑥钟离之会是吴文化与中原文化一次重要的交流契机。但在这次盟会中,季札之父寿梦因疏于礼乐而遭遇交流不畅的尴尬。寿梦厚爱季札,⑦因此,让其多习礼乐,诵咏徒《诗》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文可传而声难达。因此,季札观乐当是在吴时已知乐歌之词,至鲁而听其雅音,以与原诗对应。
但季札观乐的评论,为何时有猜测语气?如闻《邶》《鄘》《卫》时,谓:“是其《卫风》乎?”我们认为原因概有三:一是因为吴、鲁之间方言有别,吴国所在的南方方言与中原的方言相去甚远。诚如柳宗元所言:“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⑧所谓“楚越间”,正是句吴之所在。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史记索隐》注曰:“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此言自号句吴……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⑨可见,柳宗元所谓“楚越间声音特异”,就是指吴语独特难懂。二是行诸歌唱,比言谈更加难以听懂。因此,闻歌而后,季札时有猜度之意,当是不明歌辞的具体内容,而仅得其大概而已。三是演奏之时极可能是先未通报乐名,因此而有“是其《卫风》乎”的疑问。缘乎此,评述季札论《郑》《卫》,当参证《国风》中的相关内容。
二、《卫》分为三之谜与《郑》《卫》之别
《左传》及《史记》中对季札观《郑》《卫》的记载,在文献学方面最早提供了关于《邶》《鄘》《卫》关系的信息。《诗经》中《邶风》《鄘风》和《卫风》分列,但是,后世往往将《邶》《鄘》《卫》视为一组,三者皆为卫诗,如朱熹《诗集传》云:“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鄘之地。”⑩但朱熹对于邶、鄘既已入卫,诗皆写卫事,又为何系故国之名的原因则存疑未解。其实,对《邶》《鄘》《卫》作一体论始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季札观乐时,“为之歌《邶》、《鄘》、《卫》”,季札感叹道:“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将《邶》《鄘》《卫》视为一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卫风》的面貌,这在相关的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⑪但北宫文子所引乃《邶风·柏舟》第三章中的两句,并不在《卫风》之列。对此,杜预的解释是:“此《邶风》刺卫顷公,故曰《卫诗》。”⑫但这仅仅陈述了表象,而未涉及《邶风》中的诗歌何以刺卫顷公,亦即《邶》《鄘》统汇于《卫》、归为一组的原因。更何况,对于该诗的创作旨趣,一般认为并非如《毛诗序》和杜预所说的“刺卫顷公”,作者当是一位女子。朱熹谓其为“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⑬。宋人王柏也认为该篇既不是“仁人不遇,小人在侧”之作,也不是庄姜所作,云:“以兄弟不足依据,而叹其不能奋飞,此闾巷无知之言也。”⑭因此,《诗经》中卫诗分编,或邶、鄘、卫三国同风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对这一问题进行正面探索的当数顾炎武、魏源等人,他们认为卫国存诗最多,是汉儒将其一分为三。如顾炎武曰:“邶鄘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⑮但何以分之?顾炎武谓之:“邶、鄘、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鄘》、《卫》。”⑯清人贺贻孙则云:“邶有邶音,鄘有鄘音,卫有卫音,所得之地不同,故其乐之音亦异。随地审音,别而为风,至其言卫事则一而已矣。”⑰意思是一分为三是因为“三音”不同。但据顾炎武所言,邶、鄘、卫“相距不过百余里”⑱,果如其然,音分三类,似乎仍难以理解。魏源则干脆得出这样的结论:“邶、鄘、卫之不可分,犹曰殷商,曰荆楚。”⑲亦即邶、鄘、卫同义。虽然后世对于何以分为三名众说不一,但季札观乐为后世对《邶》《鄘》归《卫》的讨论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历史坐标。
季札观《郑》《卫》作出的即兴评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郑》《卫》作区别论。《郑》《卫》之音向被视为同类。孔子虽然“放郑声”而并未言及卫,但这在后世学者看来仅是“举甚言之”。对此,朱熹论述得甚为详细: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⑳
可见,在他们看来,郑卫虽然程度有别,但本无二致,皆是淫声的代表。朱熹曾引张载之言,谓卫国人的性情或轻浮,或柔弱,或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郑诗》放此”㉑,似乎卫为因而郑为果。可见,在正统的儒家学者看来,郑、卫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礼记·乐记》等文献中将郑、卫归于一类,描述了其令人惊悚的危害:“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㉒
但季札观乐时,对于《郑》《卫》的评价并不一致。当其闻《邶》《鄘》《卫》之歌时,了无贬意,皆为赞叹之言。除对其审美效果的赞叹之外,还有内容方面的赞美:“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杜预注之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卫康叔、武公德化深远,虽遭宣公淫乱、懿公灭亡,民犹秉义,不至于困。”对于“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史记集解》贾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难,武公罹幽王、褒姒之忧,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㉓《国语》亦记载,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于国,恭恪于朝。当然,亦有说者怀疑武公有杀其兄恭伯代立的劣迹。但《史记索隐》以及崔述等人认为其兄恭伯乃自杀,证据之一便是季札在观乐时对卫康叔、武公令德的由衷赞叹,如崔述云:“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于弑兄之贼也。”㉔不难看出,季札对卫风的赞叹,与其表现卫康叔、武公德化深远具有直接的关系,亦即其审美价值是与诗乐丰厚的内涵相关联的。但《诗经》之《邶》《鄘》《卫》风中直接赞美卫康叔或武公之德的作品并不多,得到普遍认同的似乎仅《淇奥》一篇。《左传·昭公二年》“北宫文子赋《淇奥》”,杜预注:“《淇奥》,《诗·卫风》,美武公也。”《毛序》亦云:“《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就此而言,季札闻歌《卫》,仅闻《淇奥》一首也不无可能。这篇诗歌称颂了“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德,“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之质,“宽兮绰兮,猗重较兮”之品,“充耳琇莹,会弁如星”之貌。《毛序》谓其“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称颂其自警自省之德,这样的解释或许也受到季札“忧而不困”的启示。对武公的称颂既美其形又美其德,尤其是描绘其“锻炼以精,温纯深粹,而德器成矣”㉕,与季札所叹的“美哉!渊乎”其意正同。可见,季札叹卫风之“微言”,恰成后世论《卫》的重要渊薮。但季札之论全是赞美之辞,又与郑、卫同列的传统观念迥然有别。
与论《卫》迥然不同的是,对于《郑》,季札虽然肯定了其审美价值,但言其内容则皆为贬评,这在闻列国之风时仅有《陈风》与其相似。
季札闻《郑》而憾其“细已甚”,由此而使“民弗堪”,遂作出国“先亡”的推论,可见“细已甚”危害之大。对于季札之谓“细”,孔颖达认为是“为政细密。”云:“居上者,宽则得众。为政细密,庶事烦碎,故民不能堪也。”㉖但这样的解释是基于儒家政教为本文艺观的立场,似乎难以说通。因为“为政细密”褒贬难判,与其后的“民弗堪”、国“先亡”的贬意不尽相符。同时,歌辞一般比较简约,表达“细已甚”难度甚大。其实这很可能是季札观乐时秉持的中道方法,表达其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审美愉悦与功利致用的平衡。亦即,他认为《郑》之诗乐的情感委婉细腻,愉悦(亦即“美哉”)有过,而功利致用不足,易诱使民众过分享乐而荒其本业。据考古学研究,郑卫之音在声乐方面多用繁声促节,采用新的音阶㉗。同时,除金石之外,大量的丝竹乐器得到了应用。《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齐国如此,郑、卫之乐当更加柔婉琐细,表现手法也更加丰富多姿。这才是季札既称其“美”,又谓其“细已甚”的原因。对此,清人陈启源《毛诗稽古篇》的论述亦可参证:“淫者,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于星言淫,于雨言淫,于水言淫,于刑言淫,于游观田猎言淫,皆言过其常度耳。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有节焉,郑声靡曼幻眇,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者导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㉘同样,这在历史文献中得到了证实,《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杜预注云:“五降而不息,则杂声并奏。所谓郑、卫之声。”㉙由此也可以看出,季札观乐对于郑卫之音的认识虽然与孔子不尽相同,但追求中和、追求艺术服务于政教还是一致的。这是从乐的角度而言。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也留有“细已甚”的些许痕迹。事实上,现存《郑风》中确实多有描写极细腻的作品,如《将仲子》诗,传情达意,婉转曲折。虽然《诗序》认为该诗是讽刺郑庄公之作,但自宋代郑樵以来,学者多认为其是一首表现男女情爱的诗歌,所写的乃一篱落之间的女子,既难抑与仲子之情,又畏惧父母、兄弟、国人之言,不敢轻身以从。虽然短短数句,但情感表达则一波三折,欲迎又拒,欲拒还迎,曲折细腻堪称“细已甚”。可见,虽然季札观乐以知政为宗旨,但其闻《郑》声则主要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论述的。因此,季札称颂其“美”,实质是肯定了其审美愉悦的功能。当然,即使是如此明显的论乐取向,也往往受到儒者的曲解,如孔颖达正义云:“‘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孔颖达将审美与诗乐的政治功能完全统一。但这样的疏解很难解释既有“美哉”之叹,为何又有国之先亡的猜度,显然不合季札之意。不难看出,季札评《郑》,其实是对审美愉悦与艺术社会功能作区别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论乐对艺术独立性问题已有所涉及,这是孔子乃至儒家诗乐理论中鲜有论及的。
三、斥“淫”缘由、叹“美”意义与季、孔相因
孔子所说“郑声淫”,成为后世论“郑卫之音”的圭臬。但对于“淫”的诠释众说不一,或谓之“淫色”“淫邪”,或谓之“过甚”“过之常度”。就后者而言,季札所谓“细已甚”颇合其意。但论者多以其为“淫色”“淫邪”之意,遂有乱世之音的恶评。就此而言,季札论《郑》《卫》时了无其意。这为我们了解郑卫之音提供了一个与儒家学者不同的重要历史信息。季札论《郑》《卫》虽是即兴之言,但又有近乎史实的一面。事实上,《左传》等文献中对《郑风》的使用多明郑国之志,如《左传·昭公十六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蘀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㉚
郑国的六卿所赋的诗歌都表达了郑国的意向,若为淫声,岂能引以自况,且韩宣子闻之欣喜并认同。可见,郑卫淫声之说,不但在季札的品评中了无踪影,见之于史乘的也并非淫邪之声所能概括。
为何时人运用《郑风》以明志,而孔子还力斥郑声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与孔子所在的鲁国历史文化有关。鲁国有承祧与维系西周礼乐文明不隳的独特责任。据《礼记·明堂位》载:“成王以周公为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㉛当雅乐的地位受到挑战之时,其他的诸侯国尚可容忍,但鲁国则不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制礼作乐乃周公的重大贡献,鲁国是诸侯国中独享天子之礼乐的国家,因此,他们更不能容忍礼崩乐坏。缘乎此,我们便能够理解孔子“放郑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乱雅乐”,即如同“恶紫之夺朱”一样。这与其后的荀子等人有所不同,荀子排斥郑卫之音,是因为其能“使人之心淫”,因此他提出“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㉜。荀子与《礼记·乐记》中的观点颇为相近,认为乐之清正或淫邪关乎国之治乱,而孔子则以维护西周雅乐的正统地位为职志。因此,他删诗正乐,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㉝。但是,孔子胶执于正统并不能改变礼崩乐坏的趋势,根本的原因是西周之礼乐已经固化为僵死的程式,而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郑卫之声既承绪了殷商之乐成熟的基因,同时又受礼的束缚较少。郑、卫、齐、宋等国既非王畿之地,亦非鲁国那样以承祧礼乐正宗为己任,因此,雅乐的束缚与影响力相对较小,郑卫之音作为民间音乐能够得以发育与广泛流播。
比较而言,在对郑卫之音一片挞伐之声中,季札对于郑卫之音较为平和的评论便显得尤为难得。郑卫之音的流行打破了西周雅乐定于一尊的不利局面,促进了灵活多样的音乐的发展,使音乐自然地抒写情感,而不仅仅是教化的工具,这是音乐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向。因此,季札对于郑卫之音的“美哉”之赞,在后代文人中也得到了承续。唐代白居易便认为艺术有其独立性,他在《复乐古器古曲》中云:“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矱》、《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㉞孔、荀等人的崇雅之论并不能改变郑卫之音的流行,这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雅乐乃宫廷庙堂之乐,并不能反映下层百姓的情感与生活。因此,郑卫之音不可无,不可抑。其二,雅乐因为是礼之辅,而礼又是森严不可僭越的,这就决定了雅乐也必然是僵化板滞之乐。这也就无怪乎魏文侯闻之而欲睡了。而当艺术失去了愉情悦性、抒发情感这一最基本的功能,而仅存隆礼敦化功能之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必然会窒息艺术的生命。因此,冯梦龙云:“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㉟他将山歌与郑卫之音相联系,承认了“情真而不可废”。亦即自由灵活地表达情感,乃是艺术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季札之论又有与孔子相通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追求中和之美。孔子论诗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以中和为美。这也是季札观乐时品歌论乐的核心取向。除其在论《邶》《鄘》《卫》时所说的“忧而不困”之外,在孔子之前,季札在论《豳》时已有“乐而不淫”之评,论《颂》时也有“哀而不愁”之评,在论《颂》时更是以“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十四个相同的句式,状写了《颂》在内容方面持节有度、音律方面“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的和谐之美。其二,以乐观政、以诗观政的功利文艺观。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其中的“观”,就是通过诗歌观风俗、知盛衰,这是儒家文艺观的重要特征。而季札观乐时不但在论《郑》时从“细已甚”,推想到“民弗堪”,乃至对其国祚的忧虑;而且整个论乐过程都是通过诗乐以知一国之盛衰、君德的高下。其三,季札在肯定郑卫之音具有审美愉悦功能的前提之下,也特别推崇雅乐。这固然从其“请观周乐”的目的可以看出,同时,他在品鉴论述之时,对于《颂》有极致之评。当然,季札的崇雅倾向也是与其功利文艺观相通的,因为《颂》与《风》相比较,更真实直接地记录了时代的特征,《大雅》《颂》堪称史诗。因此,季札对于《颂》的极度推崇,也体现了重观世功能是其文学观的首要特征,这与孔子的思想并无二致。季札观乐在孔子知事之前,孔子谓“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294页),可见其对季札的敬意。据记载江阴的季子墓旁,曾有“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之碑,亦即“十字碑”,相传为孔子所书。虽然博雅如欧阳修尚不能判其真伪,故而见录于《集古录》,“以俟博识君子”㊱。尽管此碑真伪难稽,但季札论乐对孔子的文艺思想有诸多启迪,孔子对季札甚为推敬则是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观乐时的诸多即兴之论,对儒家文艺观实有先发之功。而对于郑卫之音的些许融通之评,则体现了季札宽广的文艺视野与襟怀。
注释:
①⑪⑫[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九《襄公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1121、1167、1168页。
②吴毓江撰:《墨子校注·公孟》,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690页。
③《戴震全书》之三十二《东原文集》卷一《书郑风后》,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六册第230页。
④《毛诗传笺通释》卷八《郑风总论》,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⑤㉖[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十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96、1098页。
⑥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⑦《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史记》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9页。)
⑧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与萧翰林俛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8页。
⑨㉓《史记》卷三十一,第1446、1453—1454页。
⑩⑬《诗集传》卷第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8页。
⑭《诗疑》卷一,清通志堂经解本。
⑮⑯⑱⑲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巴蜀书社,第86页。
⑰《诗触》卷一《邶风鄘风论》,清咸丰敕书楼刻本。
⑳《诗集传》卷四,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㉑《诗集传》卷第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页。
㉒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1页。
㉔崔述:《考信录》卷八,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㉕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一《淇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7页。
㉗冯洁轩通过新郑城出土的六枚春秋时代甬钟的测音结果发现,“不管从新音阶或旧音阶的角度来看,它的隧音和鼓音结合起来,已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论郑卫之音》,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1期)。而周乐则是五声音阶。郑、卫据于殷商故地,故其音乐受其影响。
㉘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一《卫灵公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8页。
㉙《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昭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01—1202页。
㉚《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三《昭公四》,第1411页。
㉛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842页。
㉜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乐论》第二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页。
㉝《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第1936—1937页。
㉞白居易:《白居易》卷六十五 策问四《复乐古器古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65页。
㉟《叙山歌》,载《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㊱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