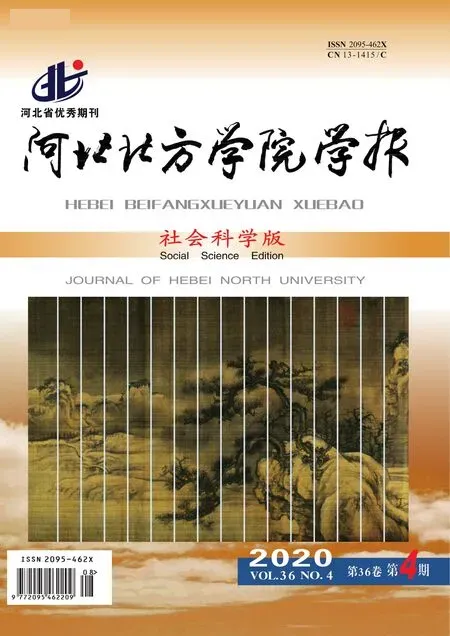《远山淡影》中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救赎
赖 婷 婷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远山淡影》是日本作家石黑一雄28岁时完成的处女作,曾获得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纪念奖。小说通过一个二战后移居英国的日本女人悦子的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讲述了其大女儿景子自杀后,小女儿妮基来英国乡下看望自己,以及20多年前在日本长崎和佐知子母女交往的故事。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探讨了人性的阴暗及其独特的讲述方式,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震惊文学界。译者张晓意评论:“这部小说的很多东西成了他日后的标志:如第一人称叙述、回忆、幽默与讽刺、国际化的视角等。”[1]248目前,国内关于《远山淡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书写、身份认同和不可靠叙事等方面,较少涉及小说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视角。基于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叙事学理论,探讨叙述自我对“现在”的追忆视角和远、近距离经验自我视角的转换运用,探究叙述自我以此进行心灵忏悔和救赎的隐蔽意图与曲折历程。
一、叙述自我视角与远、近距离经验自我视角的交替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和故事人物同一,叙述者“我”即叙述自我,通常以回忆的方式讲述过去的“我”,即经验自我的故事。“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2]叙述自我既可以用“现在”的追忆视角感知故事或审视经验自我的经历并进行叙述干预,也可以用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故事。为了厘清叙述者以哪一个“我”的视角来感知故事,需要区分视角和叙述。学者申丹“用‘视角’指涉感知角度,用‘叙述’指叙述声音”[3]。一般而言,小说中所有的叙述声音都是叙述者发出的,而视角既可能属于叙述者,也可能属于故事中的人物。因此,采用多种视角感知故事是叙述者的一种叙述策略。
《远山淡影》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由叙述者“我”即“现在”的悦子讲述过去的“我”即正在经历事件的悦子发生在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与叙述自我的叙述行为同一年的4月,小女儿妮基来英国乡下看望经验自我的那5天。这一时空中的经验自我在时间上距离叙述自我较近,因而被称为近距离经验自我。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多年前,经验自我在二战后的日本长崎与佐知子母女交往的那个夏天。这一时空中的经验自我在时间上距离叙述自我较远,因而被称为远距离经验自我。这两个故事均由几个事件组成,在每个事件的开头和结尾,叙述自我常采用“现在”的追忆视角引出往事,而在具体事件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自我大多以经验自我正在经历事件的视角感知事件。小说中的事件主要讲述经验自我和他人的对话与交往,而以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的对话场景增强了临在感和真实感。此外,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自我还通过“现在”的事后视角审视远与近距离经验自我的经历,并发表观点与看法进行叙述干预。如小说第一章开头叙述自我先采用“现在”的追忆视角,概述妮基来英国乡下看望近距离经验自我的大致情况以及引出近距离经验自我和妮基相处的第二天关于景子的一段对话,然后采用近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他们具体的对话过程。“直到来的第二天她才提起景子。那是一个灰暗的、刮着风的早晨,我们把沙发挪进窗户,看雨水落在花园里。‘你指望过我去吗?’她问。‘我是说葬礼。’‘不,没有。我知道你不会来。’”[1]3-4在此,叙述自我的视角通过表示时间距离感的“那”体现出来,近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则通过人物对话的当下感表现出来。第一章后半部分叙述自我在叙述远距离经验自我与佐知子母女的交往故事时,先采用“现在”的追忆视角叙述了20多年前日本长崎的战后重建、远距离经验自我的生活状态和远距离经验自我刚开始认识佐知子的情况,然后采用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远距离经验自我与佐知子具体的交往过程。“那时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因为我记得我边往前走边叫她。佐知子转过身站住、等我追上她。‘什么事’,她问。‘找到你太好了’,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女儿,我出来时看见她在打架。就在水沟旁’。”[1]可以发现,作者通过表示时间距离感的“那时”“我记得”以及人物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呈现出两种视角的区别与转换。
《远山淡影》的叙述自我在交织叙述中叙述远与近距离经验自我的故事。叙述自我常在近距离经验自我正在经历的事件中穿插远距离经验自我的故事,使近远距离时空的不同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叙述自我的视角和两个经验自我的视角也在不断地交替与切换。叙述者之所以这样叙述,原因与景子在出租屋上吊自杀这一核心事件有关。3种视角的交替运用,一方面强调了叙述自我和近距离经常陷入对往事的纠结和梦境的事实,暗示了叙述自我和近距离经验自我内心充满混乱,一直忍受着创伤之苦。另一方面也为叙述自我重组回忆,重新面对和审视远距离经验自我的愧疚提供了线索和机会。
二、叙述自我对远距离经验自我视角的理想化虚构
在远距离时空叙事中,叙述自我主要运用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佐知子母女的故事,叙述自我塑造了渴望去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不关心女儿的佐知子、在战争中留下心理创伤而变得自闭的万里子以及对万里子更为关心的远距离经验自我3个人物形象。佐知子在生活中不太关心女儿万里子:没有送万里子去上学,还经常留她一个人在那个破旧的小木屋里。当悦子告诉佐知子她女儿在和别人打架时,佐知子认为这种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万里子因目睹一个女人将婴儿淹死留下了内心阴影,佐知子对此却采取漠视的态度。每次万里子说因见到了那个女人而感到害怕时,佐知子都认为她在胡编乱造。最终,万里子变成一个不爱与人交流的自闭的孩子。佐知子渴望跟美国男人弗兰克去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却不在意万里子根本不愿意去美国,虽然她一直强调自己做任何事都会先考虑万里子的利益。远距离时空中的悦子不仅在家庭中是一个传统的温顺的妇女,且在与佐知子母女交往中不止一次提醒佐知子要多关心万里子。每次万里子跑出去,她都会问佐知子要不要去找她,遭到拒绝后,悦子总是独自出去找万里子。在佐稻山那次远游途中,悦子对万里子的关注远胜于佐知子,她不仅主动给万里子买望远镜,在她们回去的路上还主动给万里子钱支持她玩抓阄。可见,作为旁观者的悦子比佐知子更关心万里子,她与佐知子对万里子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叙述自我之所以讲述佐知子母女的故事,是因为佐知子其实是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的投射,万里子则是景子的投射。沈安妮在《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抉择之难——就石黑一雄获奖对话唐纳德·斯通教授》一文提到,《远山淡影》中的日文名“Sachiko”的汉字有两种写法——“幸子”和“佐知子”,更常用的写法为“幸子”。中文译本采用的是另一种写法“佐知子”。“根据名字的原意,幸子与悦子的含义基本相同,即喜悦快乐的孩子。石黑一雄在这一细节上暗示了她们两人身份的一体,而两者的命运更是对其名字的讽刺,因为她们自身连同她们的女儿,既不快乐也不幸福。”[4]所以,叙述自我省略了远距离经验自我与景子在长崎的生活和移居英国的经历,而以佐知子与万里子母女的故事代之。远距离经验自我和佐知子对待万里子的态度形成的巨大差距,暗示了远距离经验自我对万里子的关心其实是叙述自我渴望补偿女儿景子的心理投射,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及其形象是叙述自我对远距离经验自我的理想化虚构。处于“现在”的叙述自我在巨大的心理创伤和潜意识的心理防御机制下,不自觉地将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他者化。但透过理想化虚构的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叙述自我得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并审视他者化的佐知子对待万里子的态度,从而审视过去的自己对女儿景子造成的伤害。理想化虚构的远距离经验自我在与万里子接触时不自觉地会将她与景子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将两者混淆。小说中,悦子两次去寻找万里子,万里子对悦子手里分别拿的绳子和提着灯的杆子感到很害怕,每次都询问悦子拿那个做什么。这显然和景子死的方式有关,因为景子是在漆黑的出租屋上吊而死。当佐知子收拾东西准备带万里子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时,万里子坚持要把她的猫也带走,佐知子一气之下将万里子的猫扔进了河里。悦子去河边找到万里子并安慰她说:“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1]224此处,叙述自我表面的冷静叙述笔调失去控制,暴露出叙述不可靠性下其深藏的内心痛苦。远距离经验自我的分裂的两部分界限终于模糊,逐渐合二为一,万里子被还原成了景子。
将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他者化暗示了叙述自我当初选择去英国时的自私动机,使用理想化虚构的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远距离时空故事,表达了叙述自我希望通过理想化虚构的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对待景子的态度进行间接观察和审视的隐蔽用意。她没有考虑景子的意愿,执意带景子去英国,导致景子在英国一直生活得不开心,直至最后在出租屋上吊自杀。这正是叙述自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的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但在景子的死亡面前,又不得不去面对。“作为悦子的投射,佐知子代表着悦子所不能认同的那一部分自我。悦子之所以在景子死后回忆起这段友谊,而不是与景子之间的往事,是为了避免对自我的直接暴露、观察与批判。”[5]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叙述自我为什么在远距离时空叙事中两次发出如下的叙述干预,强调自己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1]46,“回忆,我发现常常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毫无疑问,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1]201
三、叙述自我对近距离经验自我经历的叙述干预
在近距离时空的叙事中,叙述自我主要采用近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感知近距离经验自我与妮基的故事。另外,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自我常采用“现在”的事后视角审视近距离经验自我和妮基的相处过程,不断对与景子相关的话语进行解释或评论的叙述干预。透过近距离经验自我的视角,叙述自我表面上似乎在讲述近距离经验自我与妮基的故事,但透过叙述自我的多次叙述干预,可以看出实际上景子才是她的关注重心。如叙述自我在第一章所言:“也许不单单是这里的安静驱使我女儿回伦敦去。虽然我们从来不长谈景子的死,但它从来挥之不去,在我们交谈时,时刻萦绕在我们心头。”[1]4
最初,叙述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非常强烈,不愿承认是自己的自私选择导致景子最终自杀,因而反复出现自我逃避和辩解的叙述干预。但随着近距离时空叙事的不断推进,叙述自我的叙述干预也渐趋沉默,最终在近距离经验自我的坦诚话语中承认了自己对景子的愧疚。小说第一章的第一个场景叙事是近距离经验自我与妮基关于景子之死的一段对话。之后,叙述自我以“现在”的追忆视角不仅回忆了媒体对景子上吊自杀的报道,而且对妮基来看望近距离经验自我的意图进行叙述干预,认为她“是来安慰我说我不应对景子的死负责”[1]5。叙述自我在下一段发出“如今我并不想多谈景子,多说无益”[1]5一句叙述干预,以此来逃避景子之死后,就开始了对佐知子母女故事的叙述。当妮基因为自己的房间对面是景子的房间而睡不好觉向近距离经验自我要求换房间时,叙述自我又进行了叙述干预,即对景子过去住的房间、她与家人的紧张关系以及她上吊自杀的那个房间的情景进行了解释和补充。在此,叙述自我第一次描述了自己脑海里一直出现景子上吊自杀的恐怖画面,但她的心理防御和逃避机制很快压制了稍稍坦露的心迹:“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画面的恐怖从未减弱,但是我早就不觉得这是什么病态的事了;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久而久之就会熟悉最痛的部分。”[1]237当近距离经验自我告诉妮基她多次梦见公园里的一个小女孩时,叙述自我对此的叙述干预是:“这也许表明我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我肯定从一开始就怀疑——虽然不确定是为什么——这个梦跟我们看见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跟我两天前想起佐知子有关。”[1]65以叙述自我的视角将近距离经验自我与远距离经验自我联系起来,叙述自我肯定近距离经验自我已意识到这个梦与那几天回忆起佐知子有关,但却没有道出梦中的那个女孩其实是景子,而是通过后文妮基的话点出:“我想你是指她。景子。”[1]121近距离经验自我很快否定了妮基的说法,并且认为梦中的女孩是万里子。但在最后一章,近距离经验自我最终通过一张印有长崎港口的日历说出:“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1]237之后,小说没有再出现叙述自我的叙述干预。此处叙述干预的沉默和叙事不可靠性表明,叙述自我通过近距离经验自我的话承认了远距离时空叙事中的佐知子和万里子就是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悦子和景子。
第六章后半部分叙述自我关于景子的叙述干预出现了3次。叙述自我结束前半部分的远距离时空叙事转换到近距离时空叙事时,她的第一句话是:“如今的我无限追悔以前对景子的态度。”[1]111叙述自我第一次如此诚恳地承认自己对景子的自杀的愧疚。但当叙述自我追忆起景子离家6年期间切断了与她的所有关系时,叙述自我又出现了辩解的叙述干预:“我是为了她好才一直强烈反对她的。”[1]111当妮基赞赏“我”当初离开日本的行为时,叙述自我的叙述干预再次出现:“再者,她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在长崎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二郎努力为家庭尽到他的本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称职的丈夫。而确实,在他当女儿父亲的那七年,他是个好父亲。不管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如何说服自己,我从不假装景子不会想念他。”[1]114但很快叙述自我又补充道:“不过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愿再去想它们。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再想这些也没用了。”[1]114-115叙述自我对过去作了短暂的反思和忏悔后,又压抑了这种反思和忏悔,仍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考虑景子的利益。第三次是在近距离经验自我表示想见妮基的朋友却遭到妮基的沉默回应时,叙述自我对景子和妮基性格上的许多共同点进行了一番解释的叙述干预。但当叙述自我提到景子之死时,叙述自我经过短暂的反思和忏悔后又开始了逃避:“我并不像我丈夫那样,觉得可以把原因简单归咎于天性和二郎。可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想也没有什么用了。”[1]119-120直到最后一章妮基离开的那天,妮基对近距离经验自我说父亲谢林汉姆应该多关心景子时,近距离经验自我回答:“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1]228之后,叙述自我没有再进行逃避和辩解的叙述干预,表明叙述自我透过近距离经验自我的话直接承认和面对了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对当初不顾景子意愿执意带她来英国,最终导致她自杀的愧疚。
近距离经验自我呈现的在与妮基相处中的多个涉及景子的事件,为叙述自我对景子的关注提供了叙述干预的线索和机会。叙述自我从一开始的难以言说,到后来对景子的多次提及中逐渐引出内心的反思和忏悔。虽然逃避和辩解的叙述干预也总是紧跟其后,但最终透过近距离经验自我的坦诚话语,叙述自我以叙述干预的沉默直接承认和面对了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的行为给景子带来的伤害,完成了在近距离时空叙事中进行心灵忏悔与救赎的曲折历程。可以讲,叙述自我通过叙事建构出新的自我和意义。叙事对受过精神创伤的人具有重要作用,“对叙事者来说,叙事是一种人格的重构过程。在叙事的过程中,人们重新整理自己的经验,当情节片段连接和组织成完整的故事时,隐藏在情节后面的意义便凸现出来,潜意识中的观念被推到意识的前台。许多问题在这过程得到澄清,从而建构出新的自我”[6]。
《远山淡影》的叙述自我围绕双重回忆不断建构叙事迷宫,通过对3种视角的独特运用,表达出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进行心灵忏悔和救赎的曲折历程,从而在叙事中建构新的自我和意义。在远距离时空叙事中,叙述自我采用理想化虚构的远距离经验自我视角间接观察和审视他者化的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对景子的伤害,表达叙述自我想以此进行反思和忏悔的隐蔽意图。在近距离经验自我视角感知的与景子相关的事件中,叙述自我以“现在”的事后视角不断进行半是反思与忏悔,半是逃避与辩解的叙述干预,最终通过叙述干预的不再出现直接承认和面对了真实的远距离经验自我对景子带来的伤害,完成了在近距离时空叙事中进行心灵忏悔与救赎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