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麟天文科普作品的特征及其教育价值发微
[编者按]
加强科普作品评论,总结创作经验,是繁荣科普原创的必由之路。对科普名家作品的鉴赏,更是评论活动的应有之义。近年来,科普创作界开展了一系列对科普名家的研讨活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于2016年12月主办的“加强评论,繁荣原创——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就是其中影响颇广的一次活动。
卞毓麟先生是天文学家,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科普理论家。他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年,1998年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专事科技出版事业。著译《星星离我们有多远》等图书30余种,科普类文章约700篇,作品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文章多次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
研讨会是对卞毓麟先生科普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将研讨创新繁荣科普创作落到实处、推动科普原创再上新台阶的契机。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在研讨会上强调,特别希望借此契机,在总结科普传播、科普创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科普原创作品、科普创作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做出更大的业绩,为我国科普事业多作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钱旭红会上指出,当下科普创作不易、科普名家难寻,社会的科普文化氛围亟待增强,针对此现状,十分有必要加强对已有科普作品的关注与评论。承办单位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决议在研讨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论文征集活动,正式出版卞毓麟《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见本期封底书讯)。该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卞毓麟作品的写作特色、风格,用寄语篇、思想篇、风格篇、影响篇、档案篇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示了卞毓麟的科普工作。中國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在代后记中表示,以卞毓麟为代表的一代投身科普创作的科技工作者,内心具有厚重的社会使命感,这将激励更多后辈在科普的道路上耕耘、前行。
文集中,叶永烈等多位专家对卞毓麟及其科普创作留下寄语;专家们围绕卞毓麟对科普创作的担当精神、卞毓麟科普作品对科学精神的发扬、对科文交融理念的实践以及作品中的科学史要素、科学家形象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年逾八旬的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知名的脉冲星专家吴鑫基以“同行同好看门道”为题撰文,介绍了卞毓麟的科普如何使天文界受益,为何说教育专家向中学生推荐阅读《星星离我们有多远》是慧眼识真金,乃至他本人如何受卞毓麟的影响走上科普创作之路,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恰在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可以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常读常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次研讨会或许远远不够。随着近年来科普教育、科幻教育的发展,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注意到卞毓麟作品这一宝库。本期“名家赏析”特邀来自南京、北京的两位语文特级教师分别从创作、教学等角度切入对卞毓麟作品的解读,以飨读者。我们笃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卞毓麟作品也必将会迸发出更大的时代价值。
卞毓麟有一本书《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出版后曾有记者问他:“这本书讲天文,却时而谈到历史,时而谈到艺术,时而又谈到宗教。您是怎么把这么多东西捏到一块的?”卞毓麟回答说:“并不是我把它们捏到一块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而已。”[1]274笔者认为,他科普作品中“科文交融”的理念、境界和新的知识创新①,正是这一“整体”的化身。
卞毓麟如是解释“科文交融”:“有意识地把科学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大文化的框架里融进科学的精华”[2]。他把这当作是自己科普创作的自觉追求,追求一种科文互通、亦科亦文的全新境界。他说: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应该让读者“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1]274。他多次引用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表示希望跨越科学和人文割裂的鸿沟,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1]271,走出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造成的“半个人”(梁思成语)的窘境。这也是一种知识创新,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契合时代对人发展的要求。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认为,人类知识本质上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寄托。人只有相信某个知识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才会认为这个知识是真实的、客观的、值得追求的。“信念”和“寄托”很能说明卞毓麟“科文交融”理念对其创作的指导意义,他也以辛勤的探索和丰硕的成就,实践了自己的理想追求,从而在百年中国科普创作序列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是怎样在科普创作中实现“科文交融”追求的?这使他的科普文本具有哪些鲜明的特质呢?
一、展示探索的叙事结构
许多人称赞卞毓麟是说故事的高手,《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讲了一个精彩的天文探索的故事。怎么理解“天文探索的故事”?这本书中混合着三种表达模式,一是发现过程模式,二是人物故事模式,三是原理解说模式。三种模式中,前两种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故事,可是第三种模式,即书中大量的对天文探测原理解说的文字,也是故事吗?是的,它也是故事,是另一种形态的故事,准确地说,是以故事为基本背景和依据转化而成的科学表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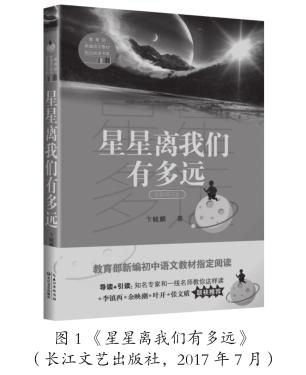
美国写作教育专家托马斯·纽柯克(Thomas Newkirk)认为,我们的理性依赖于叙述,“叙述是人类心灵的一笔财富,是我们内心不可缺失的理解力,它近乎一种本能”[3]33。他断言“所有优秀的作品,内部的结构都是叙述”[3]19。他引用写作专家唐纳德·莫瑞(Donald Murray)的观点,优秀的应用文中有“创造与隐藏”:作者“懂得如何运用每个应用文本中潜在的叙述,懂得何时在文本中创造叙述,又何时让它隐藏于信息之后”[3]19。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学术文章、科学文本的深层结构都是叙述,即使是实验报告也不例外。《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一书中那些看似理性冷峻的科学文字,同样是在讲故事——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以一个探索者的立场,用满足我们好奇心与求知欲的方式去讲述科学发现的故事。我们阅读这些文字,跟随着作者,遥望天外璀璨的星辰,亲历问题的探索现场和解决历程,心灵奔向远方。
故事的本质是揭示出事物内在的因果联系,而这个因果联系在书中表现为一种问题意识,一种探索意识。从地球的大小到地月的距离、地日的距离,再到地球与近星的距离,然后到地球与遥远恒星的距离,最后到达地球与球状星团、河外星系的距离,而全书的结尾,则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一百多亿光年外的太空深处,引向人类的未来,形成一个开放式结尾。作者不断通过测量方法、测量工具、测量手段的迭代,揭示观察结果与实际距离、人类认识与宇宙实际大小的因果联系。“星星离我们有多远”是全书的标题及叙事主轴,如同一首宏大交响乐中的主题乐句,不断重复变奏,不断递进,以达高潮。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围绕着它,层层设问,不断回顾,总结深化,形成一个整体,形成特殊的节奏,引人入胜。全书中一个一个问题隐藏着“期待-解决”的内在结构,构成一种紧张感和冲突感,让我们获得一种在场的感觉,由此带来推动阅读的力量,推动着读者不断地往前走,让我们理解科学探索的艰难和曲折。
这种问题意识不仅表现在全书宏观的架构上,也表现在章节的微观处理上。我们用《再来一段插曲:银河系和岛宇宙》中《银河系的真正发现》这一篇加以说明。这篇文章由两方面的内容组合而成:一是英国德裔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的天文探索故事和成就,二是人类认识银河系的历史。第一部分通过赫歇尔一生的追求和他妹妹帮助他研究的动人情景,说明了赫歇尔一生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天文学史巨人的原因。第二部分写出了他对银河系结构的探索以及后继者的新探索。全篇以“银河系到底有怎样的结构,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来架构安排。作者在后半部分三个段落的结尾处安排意思相仿的语句:“后来弄清,赫歇尔的这些数字仍比真实情况小了许多”“但比起如今我们所知道的,这又是一个太小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依然太保守”,通过这三个段尾关键句不断否定,层层加以拓展,最后以“如今我们知道银河系的形状大致如图43”一句,展示我们今天认识到的银河系的示意图,给读者完整清晰的印象。这篇文字紧紧扣住标题中“真正”两个字,不仅清晰还原了人类认识银河系的历史進程,而且通过“期待-解决”的叙事结构,写出了人类认识宇宙波澜壮阔的进程,给人跌宕起伏的阅读感受。全书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接一个“期待-解决”的叙事结构,构成了人类认识太空、认识宇宙的宏大思想历程。
这种叙事结构中蕴含着真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并非亘古不变的真理,它是通过不断质疑、不断否定而突破教条、持续追求的过程;科学并不必然意味着真理,而是追求真理的产物,是可以证伪的求知过程。从“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到太阳系的真正发现;从赫歇尔发现银河系结构,到雅各布斯·科尔内留斯·卡普坦(Jacobus Cornelius Kapteyn)的继续研究,再到埃德温·鲍威尔·哈勃(Edwin Powell Hubble)查明“旋涡星系”的本质并发现哈勃定律,到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的“宇宙大爆炸”模型及其天文观测的支持,最后到遥远的超新星和类星体的发现,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化,永不停止。书中多次提到,在艰难的天文探测中,探测数据不断修正,研究结论不断更新,永无停止的那一天,永无最终答案和终极真理。由此可见,这种深藏文中的叙事结构预示着问题的走向和思维的律动,包含着对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质的深度理解,可以帮助读者领悟科学思想的发展,领悟科学精神的真谛,给人行动的力量和指导。
二、启迪智慧的解说策略
卞毓麟写这本书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之一,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把我们普通人非常陌生、几乎无感的天文现象、观测原理表达出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他当然会娴熟地运用定义、分类、图表这些理性思维的工具。除了这类工具之外,他还擅长在科学文本中说故事,采用比喻、拟人以及生活场景、日常经验的细节类比或对比,讲清相关原理和知识。
作者常用比喻这种方式,把抽象的知识和原理变成我们熟悉的事物,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将月亮比喻成“天灯”,将光年比喻成“量天尺”,将秒差距比喻成“更长”的“量天尺”,将分光视差法比喻成“巨尺”,将造父变星比喻成“更远”的“量天尺”,将各类变星比作“太空中一支支标准的蜡烛,或是一盏盏瓦数固定的天灯”,将量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比喻成规模宏大、历程漫长的“接力跑”。
作者多次运用拟人手法,让那些遥远陌生的天体现象和天文原理变得亲切可感,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介绍谷神星这颗小行星时,作者说“可是论‘辈分的话,月球还得管‘谷神星叫‘叔叔”。一个拟人的称谓,让我们理解了小行星谷神星诞生的时间,亲切可感;在介绍造父变星半径时大时小、星体一胀一缩时,将它拟人化为“喘着粗气”,还调皮地假设把所有造父变星移到同样的距离上比较,说“‘体格强壮,容光焕发的那些造父变星,会不会喘得不那么匆促呢”;他说双星像舞伴那样互相缠绕,说恒星喜欢群居,有明显的“抱团”倾向,也会“生长老死”,正在“逃离”我们……把一个个神秘的宇宙恒星特征用我们熟悉的生活化的方式解释出来,让读者理解。
这一个个比喻和拟人,就是一个个微型叙事,用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生活场景讲述仿佛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故事,让我们获得一种在场感甚至即视感,让那些遥远陌生的东西能够与读者当下的个体存在联系起来。
令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常常在解说一些高度抽象、难以理解的天文发现和知识时,运用现实生活中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经验进行类比或者换算比较,给人阅读上的快感。
《测定近星距离的艰难历程》中《泛舟泰晤士河的收获》这一篇,作者介绍了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雷(James Bradley)泛舟伦敦泰晤士河的一次奇妙经历。他由雨伞在雨中倾斜程度找到了困扰着自己的恒星位置偏移的原因,并从这个生活事例中他意识到,天文学家的望远镜是“伞”,恒星射来的光线则是“雨点”,而行走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地球”。望远镜必须像雨伞一样朝着地球运动的方向略微倾斜,这才能使星光笔直地落到它的镜筒里。由此,布拉德雷发现了“光行差”,为后来人们找到恒星视差打下基础,作出贡献。这既是一个天文发现的逸事,又能说明科学发现的某种道理:用熟悉的生活现象进行恰当类比,找出两者的共同性,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规律。宇宙膨胀是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如何让普通读者理解这种日常看不见摸不着、显得高深莫测的宇宙规律呢?作者用了生活中吹气球的例子:一个表面沾了许多面粉颗粒的气球,我们往里吹气,随着气球不断膨胀,从表面任何一个粉粒上望去,都可以看见其他的颗粒离自己而去,作者拿这个我们生活中的事例说明星系普遍存在的、彼此退行互相远离的图景。这样,宇宙膨胀变成了我们普通人都可以理解的知识,带给我们一种豁然开朗、突然发现的快乐。宇宙的这种超级膨胀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原因又何在呢?作者带领我们展开想象,回溯宇宙诞生的过去,一窥大爆炸宇宙理论的雏形。那时,宇宙间所有的物质紧紧地挤在一起。有人把这个密度极大、体积极小、温度极高的“原初原子”称为“宇宙蛋”,它在一次无与伦比的爆炸中炸成碎片,形成无数后来的星系,至今仍在飞散之中。这里,作者带领读者一起利用日常生活经验做了一场“思想实验”,描摹了宇宙大爆炸的情景。作者表达的精妙之处在于,他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宇宙的初始状态,而且让我们有一种代入感,仿佛亲身参加了这次前沿的宇宙探索,激活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给人科学方法的引领。书中这类充满智慧的知识原理解说还有多处,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时有发现的乐趣、创意的快感。
作者还常常运用想象,进行数量的转化和比较,带领读者思考,避免枯燥概念引起昏昏欲睡之感,使读者突破认知极限,将天文知识主动消化吸收。谁能说清楚1光年有多远?作者这样带领我们想象:把地球直径缩小10亿倍,于是地球成了一颗直径只有1.3厘米的小“葡萄”;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本来是1000千米左右,这时缩小为1毫米;将1光年按同样的比例缩小10亿倍,却还有9000多千米,相当于北京到巴黎的真实距离那么远。伴随着长长的喟叹,读者跟随作者亲历了这一发现,并深受震撼。
为什么作者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在于作者不仅心中有知识,而且眼中有读者。他知道读者在理解这些天文学知识过程中会产生哪些疑惑、遇到哪些困难,在强烈的读者意识的驱动下,选择并确定知识叙事的策略,化难为易,化陌生为熟悉,化枯燥刻板为妙趣横生。运用叙事策略成为作者讲述天文知识时的拿手好戏。
三、摇曳生姿的图表数字
本书中共有72张插图、8张表格,它们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另一种重要的文本样式。把如此众多的插图和表格组织在文字之中,构成了卞氏天文科普文章的一大特色。卞毓麟非常重视图表的作用,他在“作者的话”中特别介绍这些插图的收集与绘制过程。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些插图使全书图文并茂,增加阅读的体验感,帮助读者理解文字[1]175。但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忽略了对其文本特征和思维开发价值的思考,而这恰恰是关键之处。
书中图表占比最大的是科学原理类图表,其次是天文学家的肖像或天文史料类插图,还有各类星体的图片或照片。第一类图表,主要功能是与文字互相配合,辅助说明各种“量天尺”的原理,增加文字的清晰度,便于读者理解;第二类插图形象地展示天文史上先驱者探索的足迹,让人仿佛徜徉在天文史画廊之中;第三类插图展示浩瀚星空、璀璨天体美丽的形象,给人以现场感、浸润感,让读者陶醉在天文之美中,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
最值得研究的是第一类图表的特点和作用。比如图2(原图28),我们如果去掉这幅示意图,仅仅用文字来表述,那么缺少几何训练的人若要在脑子里清晰复现“视差”就会比较费劲,原文表达的清晰度也会下降。而现在图文互补,便简洁而又准确地说明了文字表达的利用“视差”测量恒星距离的原理。图3(原图33)是对正文中半人马座α星的形象展示,它犹如在文中增加了一个阅读链接,既生动地说明了古人命名半人马座α星的原因,也保证了行文的流畅简洁,大大增加了文本的信息量。图4(原图35),这幅图回答了文中的疑问,解释说明光源的视亮度与观察者距离平方的反比关系。其实就算去掉这幅图也并不影响正文的阅读,可是放在这却产生奇妙的效果:阅读文字可以使我们“理解”知识,而看懂了这张图之后,我们就产生一种“发现”的快乐,一种思维被激活的高峰体验……这一幅幅的插图是一次次的探索实验,引领读者思考其中的原理,体会探索的过程,丰富了科普文本独特的阅读美感。不会读科普类文章的人遇到数据、图表常常跳过去,会读的人则会在这里盘桓逗留,获得深度体验。因为需要图表的地方往往涉及到一些深奥的原理,理解上存在挑战,因此研读图表可以增进我们对文本中知识的理解。
卞毓麟科普作品中数字使用频繁,它同样有独特的功能。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留心那些时间数字,常常有惊心动魄之感。不必说“光年”“天文单位”“秒差距”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长长的天文数字给人的冲击与震撼,也不必说一代一代天文学家观察计算每一点推进背后的坎坷与艰辛,就讲我们比较熟悉的时间数字,也是摇曳生姿。作者总是特别写下那些关键的时间,其中有些是艰难时刻,有些是成功瞬间,还有些是转折点。“又过了1500年,才有人第一次用视差测量比月球更远的天体的距离。”“事情的转折点,是在1912年。”“1838年1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贝塞尔(Friedrich Wilhelm Bessel)终于宣布:‘这颗星星视差是0.31″。这相当于16.6千米以外的远处看一枚一元硬币所能见到的大小。”
细心观察,你会发现,看似普通的数字背后是有故事的,甚至这些数字就是故事本身。作者常常提到人物的年龄,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青少年时期就有所建树的科学家是多么才华横溢,光芒四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6歲时观看了一次日食,从此开始转向天文学和数学。”“他(贝塞尔)21岁便利用1607年以来的观察结果,重新计算了哈雷彗星的轨道,这使他很早就出了名。”“1782年11月12日夜晚,约翰·古德里克(John Goodricke)观测到了大陵五逐渐暗了下来,并发现当它的亮度下降到正常亮度1/3时,又重新亮起来,直至复原……面对这种奇怪的现象,这位当时才18岁的少年毫不张皇……”笔者还注意到,作者在说起这些天文巨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他们观察研究的年限和生命长度,比如:“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受命继任直到1742年与世长辞。”“(贝塞尔)担任这座天文台的台长直至去世。”“他(亨利·诺里斯·罗素,Henry Norris Russell)从1912年35岁开始,长期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天文台台长,直至70岁退休。”“(哈罗·沙普利,Harlow Sharpley)1921年长期担任哈佛学院天文台台长,直到1952年。”结合人物的生卒时间,可以看出他们往往一干就是20年、30年,甚至在心爱的岗位上结束一生。作者没有添加更多评价性文字,却用数字说明了一切。
四、朴素通透的语言风格
卞毓麟多次提到他的科普文章追求文字规范流畅而生动,绝不为盲目追求艳丽而堆砌辞藻。确实如此。他的文章准确而严谨,流畅而生动,内敛而妥帖,朴素而通透。
卞毓麟非常推崇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多次在文章中表达他对阿氏写作成就和表达特色的钦佩及欣赏。阿西莫夫曾用“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作比喻,说明自己写作的独到追求。“有的作品就像你在有色玻璃的橱窗里见到的镶嵌玻璃。这种玻璃橱窗本身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却无法看透它们。”“至于说平板玻璃,它本身并不美丽。理想的平板玻璃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理想的状况是,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拦。”[4]267我们常有一种误解,觉得这种看似白开水般的语言表达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审美价值,殊不知这种乍看平淡无奇、实则内里波澜起伏的表达乃是一种语言运用高境界的体现,绝非“通俗易懂”几个字所能概括。难怪阿西莫夫会不无嘲讽地调侃:“如果谁认为简明扼要,不装腔作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建议他来试试看。”[4]245因为“写得明晰比写得华美更加困难”[4]267。
《太阳离我们多远》之《金星凌日》中,第四段典型地反映了卞毓麟科普创作的语言风格。
哈雷提出观测金星凌日来推算太阳的视差,是在1716年。但是他本人却未能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因为金星凌日不是经常发生的。那时,最近的两次金星凌日也须等待到1761年和1769年才会来到。哈雷虽然是一位长寿的天文学家,活了86岁,但于1742年去世了。天文学家们为了观测1761年和1769年的金星凌日,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组织多个远征队到世界各地去,希望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观测。可惜,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损害了观测的精度。1761年金星凌日时,各观测队求得的太阳视差数值差异很大:有的小到7.5″,有的大到10.5″。但是,天文学家们不屈不挠,重新努力,使1769年的观测大有进步。这次观测之后一共发表了200多篇有关太阳视差的科学论文,其中大多数结果都在8.5″~8.8″之间。法国天文学家潘格雷(Alexandre-Gui Pingré,1711—1796)综合分析全部资料后,于1775年公布了最后结果:太阳的视差为8.8″。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可惜当时人们并不重视它。
文章的语言特色除了表达严谨准确之外,还有叙事上的一波三折。作者运用了两个“但是”与两个“可惜”,先说哈雷无法参与此次观测的遗憾,再说其他天文学家观测不准确,接着说第二次观测大有进步,最后说观测的结果不被当时社会重视。这四个转折性词语,既真实地反映了利用金星凌日测定太阳视差的曲折历史,叙述上也一波三折,富有悬念感,增加了阅读的快感,让人体会到卞毓麟文章富有张力和起伏的内在之美。
如果深入到语段内部,我们发现,许多看似平常的语句中大有故事,同样给人美感和联想。《通向遥远恒星的第一级阶梯》之《恒星光谱分类》中有这样两段:
如此浩瀚而精细的分类工作,大部分是由皮克林的助手坎农女士(Annie Jump Cannon,1863—1941)奋力完成的——这位两耳几乎完全失聪的女性乃是美国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天文学家。
坎农按照恒星的表面温度(可惜,限于篇幅,本书不能详细介绍如何测定恒星的温度了)由高而低的次序,重新调整了主要光谱类型的顺序。
请注意第一段中破折号后一句话,这个句子达到了没有一个多余字的精准地步!读者在咀嚼细读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此句于不动声色之中所表达出来的太多的言外之意。而第二段括号中一句话,又给人悬念感,让我们想到这其中会有多少精彩的故事。像这样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的语言表达,散落在书中各处,让读者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关键部位的词语运用更具匠心。在《再来一段插曲:银河系和岛宇宙》一章中,讲到河外星系时,作者专门提到麦哲伦舰队发现的“大麦云”和“小麦云”。作者写道:“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星系世界中,大小麦云乃是银河系的近邻。大麦云离我们‘只有16万光年,小麦云离我们19万光年。”接着作者抓住“只有”这个词,设问提引下文:“在‘16万光年这样巨大的数字面前,为什么还要加上‘只有这样的词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数以百亿计的河外星系中,像大小麦云离我们这么近的确实为数极少。距离我们100万光年以内的星系总共不过十来个而已;而那些遥远的星系,则往往要以10亿光年来计算他们的距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里“只有”这个词不仅表达准确,而且揭示其中隐藏着的秘密,让行文有波澜起伏之妙。作者抓住这个词做文章,介绍了河外星系与我们之间的远近距离,写得极有特色,充满趣味。
朴素通透似乎意味着简单,可细细品读后却发现它很不简单。这不是艺术的缺席,恰好相反,达到这一点需要更高的技巧。这是一种“元风格”,具有直接感,自自然然,没有任何中介的扭曲,有一种内在之美。“这个过程不是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将伪装、过度和焦虑通通拋开”,“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5],表现出对读者的坦诚,对真理的敬畏,对科学的尊重。
笔者认为,卞毓麟天文科普作品的文本价值被低估了。造成低估的原因,是我们对科普文本的偏见。传统上一般认为科普就是用形象生动的形式和手法,把科学知识“包装”起来,以便普及科学,而其语言和表达,则价值不大。殊不知,科普并非简单的文学包装和新闻宣传,而是知识创新——创造新的知识形态和传播方式,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况且在科普日益成为主流阅读的今天,科普文本已经开始重视其独立的文本价值,国内外已有诸多成功的实践。在这方面,卞毓麟富有本土原创意味的科普文本具备范式意义。他的作品是优秀的普及型科学著作,又是具有科学底色的质量上乘的文学作品。它超越了科学与人文的简单拼接和混合,而是二者融合,生成新的文本特点,具备新的教育价值。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贡献思考,给卞毓麟作品新评和重估,借此纠正传统偏见,并向卞毓麟表达敬意。
□ 作者简介
曹勇军,南京市第十三中学语文教师,江苏省首批正高级教师。现任江苏省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南京市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中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推广工作。论著有《语文,我和你的故事》等。
参考文献
[1]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
[2]尹传红.科学情结人文关怀——访卞毓麟[J].科普研究,2007(1):77.
[3]托马斯·纽柯克.所有的写作都是讲故事[M].董蓉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33.
[4]阿西莫夫.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M].黄群,许关强,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0.
[5]米歇尔·奈豪斯.科学随笔写作指南:如何写好科学故事[M].张志敏,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①本文认为卞毓麟科普作品并非简单“转述”现成的天文知识,而是一种富有个人创意的知识表达,具有服务公众的新的传播形态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