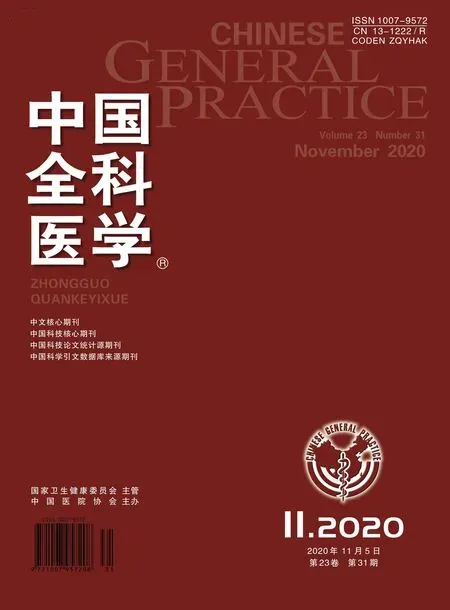大洋彼岸的涛声:新型冠状病毒下的挑战与反思
充满变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代下的转变
生活会呈现给我们无数次转身。有的意料之中,期待并华丽;有的则猝不及防,悲怆且骇悚。
从婴儿到儿童,从青少年到成人,从衰老到最后的死亡,这是生命路上的转身。在每个里程碑,以及向新的里程碑的每次转身,都有独特的挑战。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再到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最后加入工作者的行列,不断地结交和失去朋友,不断地建立关系和撕破脸皮;实现了成功,也遭遇了失败。
这些人生阶段的转变是有某种确定性的,它是按照“通过仪式”来完成的。可以预料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个年级地走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这些教育系统,会经历一个或多个工作,甚至会更换几种职业。可以预料到我们将与一个或多个伴侣交往,也许会组建家庭,也许会买栋房子。我们可能直接存钱,或把钱放在养老金里,等退休后有足够的钱用。
当然,无法保证或确定这些事情都会按部就班地发生。
这些人生转变的发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而不是发生在眨眼之间。不过,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这让我们所有人措手不及,没能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应对其影响的准备。转变可以像冰川融化那样极其缓慢,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的转变却疾如闪电。从以往的来去自由到现在的活动限制,从群体聚集到社交隔离,从就业到失业,从经济独立到寻求救济,从去中小学和大学校园接受教育,到待在家里对着电脑在线学习。
人的境况需要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才得以发展和生存。
如果少了可预见,多了不确定,我们就会变得恐惧、焦虑、沮丧,甚至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担心永久失业,担心失去积蓄,担心失去人的意义、健康和生命。
临床心理学家Myrna Weissman教授,是开发治疗抑郁的人际关系疗法的专家。她认为某些触发因素是导致发生抑郁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丧失或悲伤、转变、人际冲突。
现在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包含所有这些触发因素,而其他的情况通常只有一个或两个触发因素。我们正在目睹巨大的生命损失,数十万人的丧生。
巨大的生命损失让我们沉入悲伤。我们现在悲伤和渴望的,是那些习以为常的曾经。无疑,过去肯定不会再有。正如我们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知道,交税和死亡是确定发生的,生活中的改变也是绝对要发生的,我们目前经历的就是巨变。
我们曾计划并期待着和朋友一起喝咖啡或吃饭,组织家庭聚会,参加体育活动,去剧场看戏,或者就是简单地带孩子去当地的游乐场。这场大流行剥夺了我们的这些快乐。视频会议上喝的咖啡根本就不是那个味道。
那些失业的人,他们因失去安全而感到悲凉,他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
这个转变已经超大规模地以光电的速度发生了。当我们把丧失和悲伤叠加到巨变中,并把它们置于封闭的孵化器内,我们面临的将是人际冲突的可能。
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就有可能出现抑郁大流行,随着封闭时间的延长,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甚至内乱。
我们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是保持封闭状态,以延迟或预防病毒的传播;还是解除封闭,以防止经济崩溃、精神疾病和社会动荡?
我们现在仍处于封闭的早期阶段,而且也是在学生放假期间,所以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封闭状态还不太难受。但是两三个月后,情况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不确定性。重要的是,决定何时解除封锁,鼓励重返工作岗位,而且还要避免第二波感染。这需要“所罗门的判决”。让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的领导人们,按照最佳的证据行事,并有智慧行事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确定性的措施。
设定好每日目标,在有限的时间内享受户外活动,坚持实施室内健身方案,补上那些曾被搁置的家务,通过电话或数字媒体与朋友联系,在需要时寻求心理支持,并时刻警惕手卫生和社交距离。
我们要对我们的卫生系统和公共卫生措施保持信心。澳大利亚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相对较低。我们必须把绝望化为希望,把希望化为欢乐,坚信这场疫情必将过去。
译者注:judgment of Solomon,所罗门的判决:取自犹太圣经故事,两个女人都声称是一个婴孩的母亲,于是所罗门判决把孩子切成两半,每个女人得到一半。结果是说谎的女人同意所罗门的裁决,而真的母亲恳求把剑收起,把孩子给对方。所罗门的判决是比喻决策者用智慧做决定。
rites of passage,通过仪式:法国民族志学家甘纳普提出的术语,指人从一个群组离开加入另外一个群组要经过的仪式。人生的阶段如同一个个房间,这些是确定的。我们在人生中转换,就像在不断更换房间,然而房间是通过走廊连接的,所以这个过程必须通过走廊,这就是本文中Piterman教授说的rites of passage。穿过走廊是转换的必须过程,穿过走廊到另一个房间,是人生中的某种确定性。文中谈到婴儿、儿童、青少年、青年、成人、老年、死亡。这些都可以比喻为房间。连接这些房间的是各个通过仪式,比如降生、满月、抓周、上小学、成人礼、高中毕业、上大学、大学毕业、订婚、结婚、生子、退休、葬礼,这些都是通过仪式。通过仪式可以有3个阶段,以及相应的3个具体仪式:分离(separation stage)是与前阶段的脱离,仪式称为前礼(preliminal rites);中间的是过渡阶段(transitional stage),仪式称为礼拜或门槛礼 (liminal or threshold rites);进入新阶段是结合阶段( incorporation stage),仪式称为后礼(postliminal rites)。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代下的伦理
通常说的伦理学,具体说的医学伦理学,是在某特定情形下,决定什么样的做法是正确和公正的。
某做法对某个体可能是正确的,但对群体可能不是正确的,反之亦然。因此,当出现新事物,或旧事物再次出现时,常常会有伦理学的辩论和讨论。我们在协助自杀问题上已经经历过这种辩论,在人工流产和安乐死问题上,则一直在辩论中。
这些辩论是漫长的,立法上的改变可能是缓慢的。
涉及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伦理问题早已浮出水面,不过当初我们没时间辩论。现在,诸多改变已经付诸实施,伦理学辩论也正在以各种方式展开。
伦理学是建立在某些原则之上的,因此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代,审视这些伦理学原则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原则包括:权利与义务,自主权与家长制,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我们的民主社会得到立法和法治的保护,其中规定了某些自由。这些自由包括行动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仪式自由和表达自由。
作为个体和社区,我们有权利享有这些自由,而且政府有责任保护这些自由。在出现大流行并在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力削减或移除这些自由,并在公众健康受到威胁时,考虑行使这项权力。
政府在削减我们的自主权时,可能采用家长制的做法。不过政府会为自己做法的正确性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保护群体的健康,才以削减个人权利作为代价。
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方法,以个人的最大利益为代价,来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显然,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不赞同这种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有些人在实行禁令期间,大群地聚集在沙滩上,办聚会,到处旅行。这是个人主义最糟糕的表现,没有顾及在管理大流行时的集体主义需要。
如果这些人感染了病毒,他们是否仍然有权利得到治疗?依照医学伦理标准,医学工作者是否有责任给这些人施治?
当涉及医护工作者、健康工作者,以及在第一线处理和运送患者的司机等其他人员时,就会有特定适用的权利。健康工作者有权利在安全的、有保护的环境中工作。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健康工作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们中很多人正在死亡。
我们已经见到塔斯马尼亚州的健康工作者感染所造成的影响,两家医院因为工作人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检查结果阳性而被迫关闭。病毒传播到当地社区所造成的影响是超出想象的。缺少个人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就是将卫生专业人员置于不安全的环境中,这违反了职业健康和安全立法,并可因此导致对雇主采取法律行动。
很显然,为了给危重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准备好可提供高浓度氧气的呼吸机,并准备好重症监护病床是非常必要的。在澳大利亚,正在筹建多达4 500张的重症监护病床,并已获得7 500台呼吸机。
这些安排依据的是数学模型的测算,并考虑到通过其他社区措施而使病毒感染曲线减缓上升的情况。这些社区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社交隔离、经常洗手、使用手消毒剂,以及在某些场合佩戴口罩。
作为卫生专业人员,我们有责任为确保患者的生存而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服务。然而,如果服务需求太大,正如美国或欧洲那样的情形,或者澳大利亚可能出现的情况,呼吸机和重症监护病床的提供不能满足需求,那么我们就会出现“有限资源分配”的伦理问题。这就给医学专业人员,特别是给所有的医生,带来噩梦般的伦理困境。
谁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谁不能得到?谁可能活下来,谁基本上会死?采用什么标准来化解这个两难境地,做出正确和公正的决定?1位70岁患糖尿病和肺气肿的获诺贝尔奖的病毒专家,与1位40岁被判终身监禁的囚徒相比,谁的命更有价值?如果那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患老年痴呆症呢?
对这类话题的伦理学辩论和讨论,经常是在抽象的功利主义者与道德主义者之间进行。不过职业的伦理专家自己往往不涉及生或死的决定。幸运的是,大多数医生也不做生或死的决定。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改变了这一切,特别是要让一线的医生去做生死决策。因为缺乏资源,所以要尽快地做出生死决策。很有可能,这种决策是在不知道患者是否有过好的生活,是否有过生前预嘱的情况下做出的。
如果我们在富裕的西方经济体中也遇到生命支持设备短缺的问题,那么请设想一下贫穷的非洲国家、太平洋岛屿上的邻国,以及印度面临的困境。那里的医生将要做出怎样的决定。我们澳大利亚要给他们分享我们当下过度存贮的呼吸机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把伦理学辩论提升到此时此刻的高度,不再停留在“如果那样会怎样”的空辩上。全球化已经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成为可能。现在,不是谈个人主义的时候。
我们必须寻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式的、集体的决策,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处理这次危机,从而让我们继续前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代……那我们呢?
我们是谁?我70多岁,划归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高危类别里,我已经采取了各种必要措施,把自己的危险降到最低。我深深地感觉到,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我应该属于被放弃的人,被划归在可有可无那一类。很多像我这样的年龄,以及比我更年长的人,也可能会这样想。不过,即便是我有幸得到了最好的照顾,而且在目前的澳大利亚,我非常有可能得到最好的照顾,我死亡的可能性也在5%~10%。
我已经暂停面对面的接诊患者,转而采取了从专业角度来讲效果并不好的远程医疗咨询方式。我离开人群密集的墨尔本市中心,去300 km之外僻静安全的海滨房暂栖。我认为自己很幸运。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之所以拥有这些,是因为之前已经付出了长期的努力。
从新闻里我震惊地看到,世界各地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们在遭受着什么。他们在老年照护机构孤独地、没有尊严地死去,或者在自己家孤独地死去;如果走运,可能会被送到医院,但在入院后不久死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曾被揶揄为“婴儿潮一代的清除剂”。看看那些在宽敞的海滨度假胜地的年轻人的行为,我能理解为什么要创造出来这个词,并且直接指向我们这些曾被认为幸运地拥有一切的一代人。
我每次在清晨散步时,都会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可是那些浑身冒汗、喘着粗气的慢跑者们,就这么从我身边跑过,从未想到或考虑他们会给我或其他人带来危险。有些人就站在步行道上聊天,从未考虑到挪开一些让我通过。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跟他们其中一位说说理,他却对我说:“大家全是这样的……”。这些大家是谁,是谁聚集在沙滩上,是谁在组织聚会,是谁在无视居家防护的法令?
我敢说大多数这些人都比我年轻得多。他们是千禧一代,X一代,Y一代,Z一代。我相信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祖母或祖父死去,但不知不觉中,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些老人活得实在太奢侈了,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也许还有度假屋,而且还有养老金。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准备好分享这些收获。最后,大自然找到了一种可以派发正义的方式。
毫无疑问,有些人在走极端,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看作是大自然对婴儿潮一代忽视社会大环境的报复。他们很生气,他们的敌意受到特权感的驱使,即在规避风险时遭遇的不公正感,这种不公正感在歌曲《那我呢?》的副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
“那我呢?这不公平。我受够了,现在我想要我的那份。你看不出来吗,我想活下去。
但你得到的比你付出的多。”
在关注了“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之后,我现在想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广泛社区。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反应,以及我们走过这场改变生活的大流行的旅程。
最初,是他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第一次听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在2019年12月底或2020年1月初。那时它局限在中国的湖北省武汉市,我们被告知那里采取了封城措施,以防止病毒传播。我们也有些担心地关注每天的死亡人数,但这在当初影响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之前也有过疫情,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也曾在中国出现并得到控制。所以这次什么好担心的呢?
然后,可能是我们的事了。随着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报告了病例,澳大利亚也报告了几例从武汉市来的旅行者病例,澳大利亚政府在2月初对中国关闭了边境。那时候澳大利亚担心的是经济,因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学生,因此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澳大利亚出现了恐慌性抢购,大家对厕所纸展开了莫名其妙的攻击。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玩笑,以及有创意的油管视频。
接下来,肯定是我们的事了。新出现的病例数量逐渐增加,主要是2020年2月和3月初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返回的居民,这显示我们这边可能面临一场大流行。在制定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南、提出洗手建议、禁止大型活动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采取着拉锯式的行动。最后在2020年3月的下半月实施了自我隔离和封城。
我们迅速地调整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模式,包括采用远程医疗咨询。为了防备大量感染患者的涌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新建4 500张重症监护病床,配备了7 500台呼吸机,并订购大量个人防护设备。
再往后,就不仅仅是我们的事了。我们看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遍了欧洲、英国、美国,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我们看着那些飙升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曲线,我们再想想自己……
我们是幸运的。当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写《幸运之国》时,他不知道有什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过,就我们目前的感染率和病死率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非常棒。
从今往后,我们要走向哪里?我们在进入深渊。失业率狂涨,因长期限制造成的社会紧张,心理健康问题,对经济造成的后果,加上对第二波感染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困难时期和微妙阶段。
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用集体的客观需要取代了个人的主观欲望。
我们只有通过保持集体的、合作的和协作的方法,使“我们”的需要优于“我”的欲望,才能成功地度过下一阶段。
我们可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挑战,但不能没有支持
时光荏苒,梦境再来
那时的我 希望满怀 生命澎湃
——《悲惨世界》音乐剧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部著名音乐剧里面的这段歌词,一直萦绕着我们,因为我们这些深陷于隔离的众生们,已经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花时间沿着梦境回溯到过去,与当下相比,曾经的拥有是多么的美好。我们一边回味着过去,一边与朋友和家人进行着电子化的连接。我们也知道这只是触摸、拥抱和亲吻的蹩脚替代品,只是某种触觉参与而已。
我们生活在希望中。这种电子化接触不久还会再回来的,特别是美国新出现的那些糟糕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危重患者被失败的医疗系统雪崩般地淹没。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是幸运的,也给我们这些医学界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全科医生反思的机会,通过汲取以往的巨大教训而去想象未来,注意到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今天就是明天的过去,是昨天的未来。
虽然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性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但有几点是肯定的:病毒不太可能消失,我们可能会经历第二波感染;即使我们没有被第二波感染,病毒也可能会待在社区里,继续感染脆弱人群,就像多年来流感病毒所做的那样。
我们在控制细菌感染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应对病毒感染方面,除了使用疫苗预防感染之外,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仍至少还需要几个月才能研制出一种可靠的疫苗来对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且,冠状病毒肯定存在发生新突变的可能,这将会带来更多的挑战。
我们最近的经历表明,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特别是如纽约那样高楼耸立的大都市,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影响。在澳大利亚,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以及每个家庭占地四分之一英亩(1 012 m2)的设计,有助于我们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就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言,全科医生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全科医生采用的是联邦和州卫生部及专业机构制定的指南,旨在保护医生、诊所工作人员和患者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指南的建议包括在可以得到个人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尽量地使用这些设备;对疑似病例进行筛查,并转诊给新型冠状病毒监测中心、当地的病理检验所,或者医院。
全科医生们花了很多时间回答担心、焦虑的患者提出的问题,许多全科医生已经改用远程医疗咨询。
迄今,澳大利亚确诊的病例数量还没有超过8 000人,大多数全科诊所很可能一个阳性病例都没有见到过,但关于缺乏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的投诉却无处不在。似乎我们还没有从2008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吸取教训。现在可以打流感疫苗了,许多原本担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远离全科诊所的患者,主动回来要求注射流感疫苗,甚至有些患者自认为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在诊所停车场注射疫苗。
很多全科医生,特别是年纪大的和面临危险的医生,也包括我自己,已经改成远程医疗咨询,在我们等待对这种与患者交流方式的效率和效果研究时,我们也对这种看病方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在我看来,远程医疗咨询的价值是有限的,它可能是一种短期措施,可用于管理一些心理问题、识别需要管理的临床问题、管理一些显而易见的皮肤病问题、给熟悉的患者开药或安排实验室检查;不过它无法替代面对面的接诊、身体检查,也做不了类似测血压这么简单的事情。
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病患者,由于害怕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在疫情期间一直不来全科诊所或医院就诊。这样的话,慢性病发展出并发症,或没能发现癌症的风险,远远大于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风险。
随着禁令的逐渐放宽,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患者涌进诊所。他们给辅助检查和专家服务带来的压力,远远大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增多带来的压力。
我们生活在南半球的人,很快就会暴露在随冬天而来的感冒和流感的季节。出现感冒或流感症状的患者可能会担心他们得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种情况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便是我们告诉患者如果有症状就要待在家里,并拨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热线电话,但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患者来诊所看病。那么,我们要继续执行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措施吗?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我们至少维持到10月份?
在这种背景下,会有许多潜在的医学法律和职业健康安全问题涌现出来。今后,那些没有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的诊所工作人员,是否应该接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诊所员工可能会因为暴露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中而对诊所提出诉讼。如果工作人员是病毒携带者,并感染许多患者,那么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因此现在的关键,是保证能优先地对所有诊所员工进行检测。
全科医学服务是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给患者提供服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经济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我们面临的是大规模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再加上长期的社交隔离措施本身,也能造成毁坏性的后果,特别是对那些本已脆弱的家庭关系,后果尤为明显。
全科医生很可能会接诊大量患有各种心理社会问题的患者,从失眠症、焦虑障碍、适应障碍到重性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家庭暴力问题及其后果也日益紧迫,这可能会增加儿童行为障碍的发生率。
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以及其他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持续的,是深远的。它已经并将继续给全科医生带来挑战,其中一些挑战就像病毒本身,是不可预见和不可预测的。
与其他医学专科相比,全科医学更经常地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要满怀信心地,在社区和政府的支持下,准备好应对这些挑战。
译者注:quarter acre block,澳大利亚标准的居民私家宅地面积。四分之一英亩的一块地,相当于1 012 m2。这既是澳大利亚人的梦想,也是澳大利亚的土地政策。Piterman文中提到这个政策,是在说它让居民居住的很分散和独立,不利于传染病的传播。
原文见:https://www.chinagp.net/Magazine/Content/show/id/5816.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