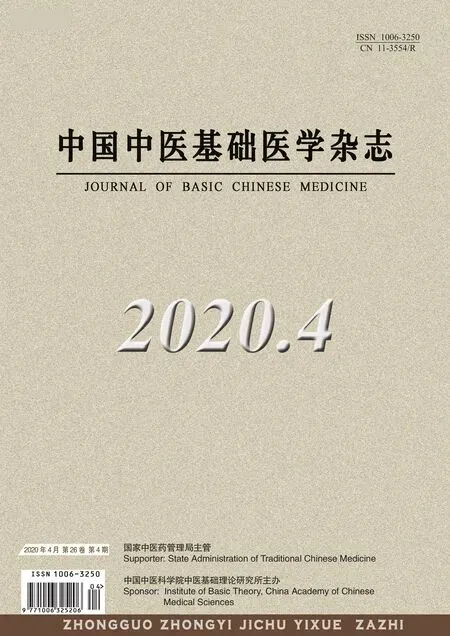从SARS到禽流感与COVID-19谈中医药防疫的研究思路及其意义
邱模炎,黄苏萍,裴 颢,王怡菲,闫二萍,刘淑娟,邹 浩,熊莉莉
(1.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 100102; 2.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州 350122; 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北京 100082; 4.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 100015; 5.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2003年以来,SARS、禽流感、甲流、鼠疫到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中国政府以及业务主管部门在防治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业务主管部委也出台了相应的技术指导方案。但是我们认为,在流行之初由于对这些传染病以往的临床经验积累很少,尽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是在未实际进行足够样本的临床观察、缺少足够的“中医四诊”资料的前提下,盲目推测其证候和出台治疗方药,似属不妥。诚如清代温病大师吴鞠通所言:“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医药参与SARS、禽流感和新冠肺炎防治的研究思路进行反思,目的是为了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防治。
1 从中医疫病学体系特色探讨其研究思路
中国传统种痘术和大量文献中所记载的中医防治烈性传染病的多样性手段以及伤寒论、温病学、疫病学的形成和发展史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医学在研究传染病方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我们认为该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色[1]。
(1)重视临床研究,突出辨证观和整体观。既重视普遍性规律的研究,又不排除不同疫病的特殊性。如张仲景《伤寒论》、吴又可《瘟疫论》、余师愚《疫疹一得》等。
(2)重视中医病名、病因、病机、症状学、舌诊、脉诊等理论和临床基础研究,如《伤寒论》《温疫论》《疫疹一得》《伤寒温疫条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3)重视多样性的防治手段研究,并致力于取得“一病一法”防治方法的探索,前者如《松峰说疫》,后者如《温疫论》等。
(4)重视疾病传变规律和论治方法、选方用药规律的研究,如《伤寒论》《温疫论》《疫疹一得》等。
(5)重视诊断与鉴别诊断和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研究,如《伤寒论》《温疫论》《疫疹一得》《伤寒温疫条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6)重视疾病发病规律、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和孕妇、小儿等特殊群体发病与论治特点以及疫病流行预测和独特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疫论》《疫疹一得》《伤寒温疫条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从学术争论的角度而言,由于长期的“寒温之争”,促进了温病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基础,形成了互为羽翼的伤寒论和温病学,形成了与内伤脏腑、气血津液辨证相比翼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体系[2]。禽流感的中医定性应该是通过逐步深入的临床观察,组织中医外感热病学专家进行论证;或通过动物实验研究,采用“以方测证”的研究思路进行探讨,后者可以立即进行,前者可以组织中医外感热病学专家对定点医院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积累病例,与动物实验结果相互印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中医药研究更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尤其是中医、西医、中兽医、民族医的通力协作。我们建议:多部门联手,有关管理部门如中医药管理部门、兽医管理部门、疾病控制与防疫部门等,应抛开部门之别,通过联席会议尽快达成共识,充分利用资源,实施中医药等实验研究。中西医联手共同开展临床研究,中医的介入应当从发病早期开始,才能真正从中医角度探讨其发病、证候、传变规律以及中医和(或)中西医结合的疗效。医学家、防疫学家、兽医学家与气象学家、天文学家等联手,共同探讨其发病与流行因素,为解决中国传统预测学、运气学、周易学等种种学术争议提供契机[1]132-137。
2 从中医药参与研究得失探讨今后研究思路
回顾2003年春夏之SARS的防治过程可以看到,积极开展SARS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群众对中医药防治SARS均寄予厚望。广东省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制定了有关中医诊疗和防治方案[3];“863”计划、科技部专项课题以及各省市所进行的中医药治疗SARS的研究项目等中医防治SARS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及其并发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民族医药在防治SARS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多方位展现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独特优势。但是,至今有关SARS的认识,如中医病名、传变规律、证候特点、分期分型、辨证方法、成药应用、中药药理等仍未形成共识。从风靡一时的非典中药预防“八味”处方的争议,以及基于西医提高免疫力而采用黄芪、太子参、虫草制剂等进行SARS预防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可以看出,目前大多数的观点强调预防疫病应遵循中医辨证预防方法,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我们认为,通过认真总结中医药参与SARS防治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将为防治新发疫病的研究思路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的看法是,中医药参与的研究思路,其核心思想与我们在SARS期间提出的建议一致,即中医药防治研究的思路必须突出中医传统研究特色[4-6]。
根据《松峰说疫》的论点[7],从SARS、禽流感、甲流、鼠疫到新冠肺炎等疫病首先应当辨明属于寒疫、温疫(瘟疫)、杂疫哪一范畴。就SARS和COVID-19而言,是属于温疫中的温热类疫,如暑燥疫、温毒疫等,还是属于湿热类疫,目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更可叹的是,将其归于风温、冬温、春温的观点比比皆是[4,8]。将疫病的发病与伏邪温病的发病等同起来的观点也不少。我们在SARS和COVID-19爆发初期都曾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建议在中医临床科研和救治中,采用数码相机、舌诊仪、脉象仪等收集客观的病历资料。如SARS从目前的报道中,主要是舌诊方面,面诊仪的客观资料基本未能留下。遗憾的是在舌诊资料中,动态观察者少,而且由于介入过晚,应当可以认为大多的舌诊资料为SARS中后期,以及采用输液治疗和应用激素治疗后的舌诊,并非完全是SARS患者舌象变化的本相。可喜的是,广东省中医药的经验、北京市胸科医院的经验(健康报,2003年6月4日第7版)、北京中医药大学张晓梅的65例临床观察(中医药专家谈SARS.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等为我们提供了SARS早期和(或)演变过程中宝贵的、较为全面的中医“四诊”资料。“四诊”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石,没有客观的第一手临床资料,任何分析只能是纸上谈兵甚至是臆测。这也是我们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中医研究SARS、禽流感、COVID-19等烈性传染病也应该遵循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原则,避免急躁心理、急功近利甚至照搬西医模式,邯郸学步。创新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否则为无源之水。如过多地争议SARS的中医“新名称”,或言“肺毒疫”,或言“肺疫”,或言“金疫”等,不如采用“SARS”之通用名称,既有利于临床实际,也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中医药防治SARS的科普工作,认真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思路,汲取以往的教训,力争在NPC的中医证候演变规律的研究中有所突破,形成共识。我们建议组织全国参加过SARS中医临床治疗和研究的专家以及外感热病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等,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学术思想,集思广益,科学总结,制定出中医防治COVID-19的“国际”级方案。
中医药参与SARS的研究结论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肯定性评价,是中医学的又一骄傲。但总结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以下不足之处可以作为目前开展中医药防治COVID-19的研究借鉴:一是中医药研究介入过晚,未能在SARS流行早期形成全国中医药研究的“一盘棋”;二是重药轻医,重视中药筛选的投入,而基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足,重新陷入“寒与温之争”“温与瘟之争”“湿与温之争”以及“毒”等中医概念扩大化的倾向较为普遍[9];三是中医外感热病学专家主持重大课题者不多[1]129。
3 中医药参与防治与研究具有广泛的意义
对中医药参与SARS、禽流感以及COVID-19防治和研究的学术和政治意义,可以说已经形成共识,我们在SARS爆发期间也发表了有关看法[1]130。现以提要形式简述如下,旨在抛砖引玉。
(1)将提高中医药在中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
(2)将为发挥中医药在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中的作用提供决策依据;
(3)将为打破长期的国际堡垒提供机遇,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4)将为解决中医温病学、疫病学中的“三大学术争议”(温病与瘟疫、伤寒与温病、新感与伏邪之争),尤其是“温病与瘟疫”之争提供契机;
(5)将促进中医疫病学、外感热病学或中医传染病学的学术发展;
(6)将为解决中国传统预测学、周易学、运气学等是否科学的学术争议提供契机。
此外,通过中医、中兽医跨学科的联合攻关,势必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兽医学(中兽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