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巨人,一面是婴孩
高博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在20世纪西方文坛引起人们争论最多的人物之一,福特就曾把他形容为“仁慈的谋杀者”,暗示出庞德自相矛盾的性格。作为西方文坛巨擘、英美现代诗歌的创始人,庞德不仅发现并培养了艾略特、乔伊斯、海明威、劳伦斯等一大批诗人和作家,而且还翻译了中国儒家“四书”和《诗经》,出版了英译中国古诗集《华夏集》,把中华古典文化介绍到西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庞德的人生也有过不小的“污点”,他曾经极其狂热地为法西斯主义站台并一味地支持反动、落后的经济理论。
庞德其人
一头浓密惹眼的白发,一对湛蓝深邃的眼睛,一双雕刻家般有力而灵巧的手,庞德无论是待在他桑艾姆布罗吉欧的公寓里(脖子上还围着我们熟悉的、用玉米须织成的围巾,上面印着“一切与众不同”),还是沿着威尼斯圣格雷戈里奥的滨河路漫步,他的身上总散发出一种高贵的气质,这种气质与生在尚礼国度松柏林里的孔子颇有渊源,似乎还可以追溯到更加遥远的伊根黑水湖畔的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那里。可就是这样一位谦恭有礼、文质彬彬的人,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屡遭人们的诘难。但丁在流放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今天他的坟墓静静地矗立在拉文纳圣方济各教堂附近,显示着对变化莫测命运的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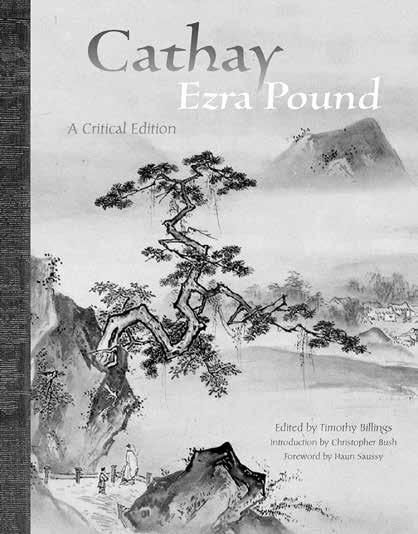
庞德1885年10月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海利。他不满16岁就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后获得硕士学位。1908年,他乘一艘装运牲口的轮船奔赴欧洲,并定居伦敦,此后又迁居至巴黎和意大利的拉帕罗。“二战”期间,他在罗马电台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宣传,攻击美国的作战政策,因而被指控叛国罪。1945年,美军将他逮捕,回国受审,之后他精神失常被送进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12个春秋。获释后庞德回意大利居住,1972年11月1日病逝于威尼斯。
在欧洲,庞德广事交游,并以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从事着创作活动。他到英国不久便成了伦敦文坛的领袖。庞德的一生似乎处处表现出与众不同,常常引起轰动。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我行我素,乐意当个“特殊学生”;到伦敦后,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引人注目;就算是在比萨拘留营的露天囚笼里,他也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人们都称他是一个怪杰,令人捉摸不透:他对犹太人恨之入骨,却又和某些犹太人亲如手足;他发起过不少文学运动,比如意象主义和旋涡主义,但不久又将它们统统抛弃;他以发现和培养新人为己任,满腔热忱地帮助过很多青年文学家,可他对自己的儿子却毫无感情,冷若冰霜;他大骂战争的愚蠢,却又说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是公正的。
文学艺术“巨人”
庞德才华横溢,精力非凡,他一生写了至少70本书,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自1908年在威尼斯自费出版第一部诗集 《灯光熄灭之时》起,他就笔耕不辍,诗歌、散文、译作等频频问世。诗集《人物》使他获得一定的声誉,《诗章》则是他的毕生之作。他从1915年开始创作这部宏伟的长达117章的现代史诗,以“诗章”的形式分期发表。这部长诗涉及文学、艺术、建筑、神话、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内容十分庞杂,其中心思想是描述“高利贷”(暗指近代金融资本)为万恶之源。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诗章》里還专门阐述了中国的儒家哲学。
此外,庞德颇有语言天赋。他早期研究诗歌时就或多或少地学习了9种外国语言。他旁征博引,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多种 “外语”成分,《诗章》中就出现了18种外国文字。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难怪英美读者都抱怨《诗章》晦涩难懂。
庞德在文学上的才华还可以从他与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的交往当中体现出来。庞德与叶芝在伦敦相识。那时的爱尔兰诗人年近半百,作品选集已经出了8卷,并且获得了广泛赞誉。叶芝的诗歌对庞德的早期作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庞德很快就开始走自己的路,突出自身风格。堂皇的辞藻、华丽的虚饰、貌似壮丽而无实际意义的形容词、边缘模糊的意象等等在庞德的诗歌中不再占有任何位置,取而代之的是由他开启的“讲究精确的时代”。各种艺术也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庞德的知识及诗歌给叶芝留下了深刻印象,叶芝开始按照庞德创作所遵循的理论原则来进行变革。1913—1915年,庞德给叶芝当了三个冬天的私人秘书。在一封给爱尔兰民间传说女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叶芝这样评价庞德:
我从他(庞德)那里得到的批评给我以新生;我把那首写塔拉的诗改造成了一个新的东西,我抛开了背上的弥尔顿模式,正带着新的信心从事写作。埃兹拉是两个批评家中比较高明的一个。他脑子里装满了中世纪的知识,他帮助我脱离开现代抽象的概念,返回到具体的事物上来。和他讨论一首诗就好像你把一个句子改成方言,一切都变得清晰自然。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叶芝开始尝试创作新型诗歌。10年之后的1922年,叶芝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起来,这是庞德第二次帮助举荐诺贝尔奖人选了。此前,为了让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得候选人的资格,庞德和叶芝曾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很久以后,另外两位跟庞德联系密切并从中受益的作家——艾略特和海明威,也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为了表示敬重和感激,艾略特更是将他的不朽长诗《荒原》题献给埃兹拉·庞德——“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匠人”。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庞德本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除了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庞德对音乐始终怀有浓厚兴趣。他在年轻时就参加过许多歌剧演出,还尝试作曲和创作歌剧,甚至与别人密谋过掀起一场音乐革命。
政治经济上的“婴孩”
庞德的人生是在一个沉疴痼疾的乱世中度过的,他一辈子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以前,他很少对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而“一战”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的好友、法国雕刻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死于战争,庞德当时在伦敦正热心于现代主义的旋涡运动,他觉得战争粉碎了他的艺术梦想。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已不是暂时现象,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已势不可挡。面对着如此众多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庞德的救世热情被激发起来,于是,他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相关著作。此外,他还积极写信并会见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府官员,通过报纸、电台等多种传媒来宣传他的思想。现在细读起庞德的相关著述,我们发现他的看法虽不乏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精准批判,但从总体上看观点大都庞杂零乱,甚至有不少低级错误。

举例来说,庞德经常会根据某些不完整的历史和原则来妄下结论,而且他的认识是散漫随意的,其中不乏他自己的偏见和一时的热情。比如,庞德坚持认为货币改革是当务之急,那么凡是能够证明其观点的经济学知识才被看作是有用的。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有时碰巧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更多时候则失大于得,遗珠之憾是常有的事。再比如,他对银行的研究常常只停留在对其早期历史的考察,而不顾及其发展史;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史、对19世纪美国的经济史以及20世纪工业国家经济史的研究更是断章取義,以自己的个人偏好来解释材料。更为荒谬的是,他对掌握的文献也经常不加甄别,往往在学术界公认是错误的、废弃不用的材料,他却如获至宝,信以为真。这样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如果尚可把庞德的经济思想视为“婴孩”般的稚嫩,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他的政治观点上,则会发现他的想法近乎不切实际。1933年1月30日,庞德在意大利见到了墨索里尼,当时“墨索里尼和庞德”的新闻标题几乎登上了拉帕罗所有报纸的头条。这次会见对于庞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他被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彻底征服了。这一点可以从《诗章》的文字中得到证实。在《诗章》中,庞德不吝溢美之词地高度赞颂了墨索里尼对国际形势的“精准把握”。庞德发表这一评论时正值他获准拜访罗马的威尼斯宫殿,而此前已有很多人的参观要求被政府拒绝。庞德把他已完成的30篇《诗章》奉送给墨索里尼,当墨索里尼读完之后,庞德被领到了他的面前。不难想象,彼时庞德心中对如此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是多么兴奋。更为可笑的是,在见到墨索里尼之后,庞德似乎患上了一种“妄想症” ——由幻觉而产生的自负情绪。他幻想着自己不再是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文人墨客,而是一个在为全人类进步和世界繁荣奔走呐喊的时代英雄。出于这样的心理,1939年他到美国时也曾提出与罗斯福总统谋面,但遭到拒绝。而只要回到意大利,他便可以随时写信给墨索里尼,和他讨论问题,在意大利他写的东西就是权威。
庞德后来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和经济上,而不再是艺术。那时的庞德,急切地想为自己的付出求得回报,实现一种拥有影响力的假象。因此,在随后的日子里,庞德还是不断地寻求与墨索里尼进一步会面。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不但没能如愿以偿,还在1943年被意大利政府突然解职,而就在被解职的几个月前,墨索里尼才终于对庞德的某些想法产生了些许兴趣。但墨氏与庞德见面的邀请信在庞德返回拉帕罗之后才被送到他在罗马入住的酒店——显然,这封信来得迟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