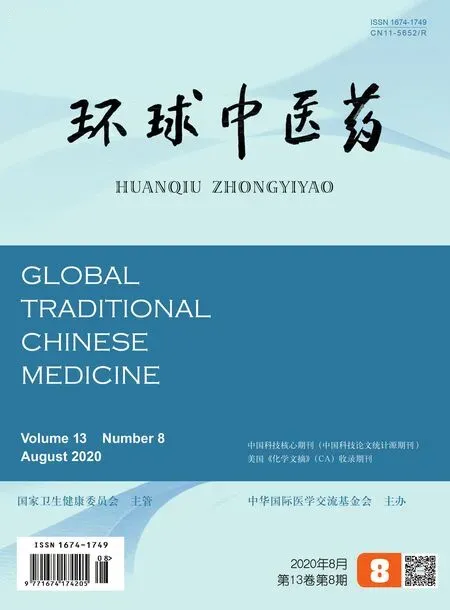崔红生教授以“和调气机”为纲治疗支气管哮喘经验述要
秦芳芳 毕伟博
目前,西医认为支气管哮喘是发生于气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是一种异质性的疾病,它是由多种细胞及细胞组分如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以及气道上皮细胞等参与支气管哮喘的发病过程[1-2]。支气管哮喘在中医上归属“哮病”范畴,是一种发作性的痰鸣气喘疾患,发作时喉中有哮鸣声,呼吸气促困难,甚则喘息不能平卧。哮病的发生为痰伏于肺,每因外邪侵袭、饮食不当、情志刺激、体虚劳倦等诱因引动而触发,以致痰壅气道,肺气宣降功能失常。若长期反复发作,寒痰伤及脾肾之阳,痰热耗灼肺肾之阴,则可从实转虚,在平时表现肺、脾、肾等脏气虚弱之候[3]。崔红生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笔者跟师抄方,受益匪浅,现结合医案,将崔红生教授“和调气机”为纲的治疗经验述要如下。
1 枢转气机、和调阴阳是治疗的总纲领
“百病生于气”(《素问·举痛论篇》)源于古代元气论的认识,这里的气是指气机而言,意思是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气机升降失常有关。中医认为人体气机运行无处不在,肝在左主升、肺在右主降为气机枢转的外轮,脾胃中州为枢纽中轴,心火下潜、肾水上承、水火既济等,以上升降出入、如环无端的运行是气机枢转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肺主人体一身之气,主治节气机,反过来说,其他脏腑气机失和,更影响整体中的肺脏系统气机运行。崔红生教授发展了《金匮要略》中“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的理论,在支气管哮喘乃至其他肺系疾病的治疗中,提倡从脏腑体系整体高度,枢转气机,和调阴阳,促使肺气和降,病气平散,临证时,病机和治法千头万绪,循着“和调气机”的纲领,可使理法方药从容不乱。
2 大气存于胸肺之中,和调胸肺气机至关重要
在理论层面,崔红生教授认为肺为“气”之所居,胸肺之中更是“大气”所在,肺系疾患发病首先在于“气机失和”。生理上,“诸气者皆属于肺”(《素问·五藏生成篇》),病理上,“诸气膹郁,皆属于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气、血、津、液等对肺脏影响最大的是气分。崔红生教授推崇喻嘉言、张寿甫之“大气”理论,认为胸肺中阳气,“胸中包举肺气于无外”(《医门法律》)而行治节,即“大气举之”(《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之意。
崔红生教授哮喘治疗中“和调气机”之法有三:其一,治外邪引触时,升散气机以“达邪”。在实际中,肺气失和有时存在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往往有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哮喘发病以外邪引触而起时,虽然体质等内在因素不可忽视,但初起时主导因素仍在于外邪,然而神丹甘遂不可合而饮之,故而,此时治则主要在于“达邪”。辨其寒热,遣方用药,崔红生教授多以麻黄、苏叶、荆芥、防风等药祛风达邪,促气机发散升越,则肺气自然宣利,哮喘自平[4];其二,治肺气上逆时,和降气机以平喘。以肺气上逆为主导因素者,或喘、或干咳,痰黄痰少不易咳出。气有余便是火,此时辨证多属肺气挟痰热上逆,或兼有外寒束内热的病机,治疗以降逆气、清肺气为主,崔红生教授多合参寒热病象,以麻杏石甘汤、青龙汤等方加减化裁;其三,病日久,肺气出现怫郁时,往往在利气的基础上考虑“燥”的因素。崔红生教授提出的支气管哮喘从燥论治与一部分支气管哮喘患者出现气机郁滞、伤阴化燥的病机相吻合,在学术上和临床上均有指导意义[5]。喻嘉言有感于“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即创立清燥救肺汤以“治诸气郁、诸痿喘呕”。崔红生教授推崇喻氏清燥救肺汤及其“诸气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的理论,在临证时,凡久病肺气怫郁和伤阴化燥的支气管哮喘患者,注重和调肝气及肝胃之阴,多选用沙参麦冬汤、贝母瓜蒌散、过敏煎等加减[5]。
3 少阳厥阴气机运行与支气管哮喘密切相关
3.1 时间医学与外轮气机
历代医家对支气管哮喘多有论述,在继承“肝肺相关”“从肝论治”“调肝理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以脏腑、八纲辨证体系为本,合参三焦、六经、气化等学说,崔红生教授丰富和发展了和调“外轮”的治法以及相关理论。对于支气管哮喘的病机,崔红生教授曾从时间医学角度进行研究和阐释。正如全球哮喘防治创议曾指出的,支气管哮喘多在凌晨,即寅时左右发作。寅时乃“肝旺”之时,肝肺气机不调可由肝失疏泄、肝郁化火或肝血不足导致,最终出现气血失和、升降失常、肺气上逆,从而引发支气管哮喘。因此支气管哮喘多发生在凌晨时期,崔红生教授提出“治重在肝,调肝理肺是为常法”[6]。肝肺同调,恢复肝之和升、肺之和降,恢复气机调和、阴平阳秘、安和无病的状态,和调“外轮”,这是崔红生教授“和调气机”为纲的重要部分。《伤寒论》提出的“欲解时”是六经辨证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对此尚存在争议,崔红生教授认为少阳、厥阴欲解时亦在寅时左右的凌晨,提示少阳、厥阴气机运行与支气管哮喘密切相关。
3.2 和调少阳枢机
临床中,崔红生教授和调“外轮”之法大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为“和调枢机”。肝,体阴用阳,气属少阳,而少阳为枢,是气机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调节少阳枢机是崔红生教授治疗哮喘的重要思路,首先是柴胡剂的应用,崔红生教授在研究和应用恩师武维屏教授“调肝理肺法”代表方“哮喘宁”的基础上[7],主张辨证灵活应用柴胡剂治疗哮喘及咳嗽变异性哮喘,选方时不拘泥于经方,还选用时方,如柴胡疏肝散、大柴胡汤、小柴胡汤、过敏煎、四逆散、丹栀逍遥散等临证化裁。柴胡剂治支气管咳喘,自古已有之,《伤寒论》中提出“胸胁苦满……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小柴治咳值千金”出自许叔微的名言,而崔红生教授的思路在于抓住枢机不利、肝肺气机不和的关键,以和调疏降为法,灵活应用,无论风阳妄动、气逆气郁,无论三焦气滞变生风、火、痰、瘀、虚等等,随证加减治之。其次是对于兼有情志因素者的治疗,崔红生教授又从心身医学角度发展“从肝论治”的理论,研究中医藏象概念的“肝”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关系,对于哮喘或兼有情志因素者,提出“从肝论治”的很多治法,比如加减应用四逆散以疏肝理气、半夏厚朴汤以解郁化痰、丹栀泻白散及龙胆泻肝汤以清肝泻肺、天麻钩藤饮以平肝清肺、一贯煎以养肝润肺等[8]。
3.3 和调厥阴风木
崔红生教授“和调气机”之外轮的第二个层次在于和调厥阴风木,以及和调阴寒阳热之错杂。激素依赖型哮喘是由于支气管哮喘患者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对其产生依赖性而造成的,一旦撤减激素或停用激素即可引起哮喘复发。崔红生教授认为激素依赖型哮喘的基本病机特点为阴虚风动、寒热错杂,正符合厥阴主证,以乌梅丸加减治疗激素依赖型哮喘取得了较好疗效;在临证时,又根据激素撤减过程的不同阶段,明辨其寒热虚实,随证用药,比如肾阳虚者,合四逆辈;肝肾阴虚者,重用白芍、乌梅等;气血虚者,重用参、归;偏热者,重用黄柏、知母、黄芩之属[9]。燮理阴阳又与心肾水火既济或失济相关,随病程、病候、气机变化调整方略。
4 调护脾之和升与阳明胃之和降的中枢
4.1 和降胃气
《素问·咳论篇》提到“聚于胃、关于肺”,《素问·逆调论篇》言“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故肺胃气当同降,胃气和降失调可上逆犯肺,致肺失宣降,因而阳明胃失和降与支气管哮喘发病相关。崔红生教授认为,此医理为中、西医所共通,比如西医所论哮喘中胃—食道反流的因素即是。胃—食道反流可看作是诱发夜间哮喘的原因之一,典型者伴胸骨后烧灼、疼痛,呕恶泛酸,舌红、苔薄黄、脉弦,崔红生教授常用旋覆代赭汤合半夏厚朴汤加减以和降胃气,疗效显著[4]。
4.2 和调脾土
太阴脾土为肺金之母,又脾之健运、清阳之升是运化浊阴的前提,是故古人有“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的说法。伏痰为哮喘发病的宿根,崔红生教授认为,无论在哮喘的发作期亦或缓解期,和调脾土、升清降浊、培土生金皆是澄源之法。在哮喘发作期,症见胸憋气短、脘痞纳呆、痰多白粘,舌淡、苔腻、脉细滑,崔红生教授常以麻杏二三汤加减治之;在哮喘缓解期乃至其他肺系疾病迁延不愈时,若病机属浊阴在上不得清降,症见神疲气短,纳呆痰多,舌淡、苔腻、脉沉细者,崔红生教授常以“温药和之”为法,得温则清气升,用参苓白术散、六君子汤、苓桂术甘汤等温脾升清[4]。
总之,和调胸肺大气,和调外轮少阳、厥阴之气,和调中州枢纽等是“和调气机”的主要部分。有时一法单用,有时多法合用,针刺之法有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之奇,内治之法有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巧,和调气机之妙在于疏右以调左、和中以清上等等,可启迪后学。
5 验案举隅
案一:患者,女,39岁,初诊。主诉:咳嗽伴喘息1周。现病史:患者1周前受凉后咽痒干咳,痰少,为白色粘稠痰,后遇冷时有发作喘息气促,可自行缓解。夜间加重,时有喘鸣,伴胸闷、气短。纳呆便溏,舌淡,苔白腻水滑,脉濡。肺部听诊:两肺可闻及呼气相哮鸣音。于外院行肺功能检查诊断为支气管哮喘,为求中医治疗前来就诊。既往慢性咽炎病史。初步诊断:支气管哮喘。辨证:肺脾气虚。处方:北柴胡15 g、防风6 g、乌梅12 g、醋五味子10 g、诃子6 g、地龙10 g、钩藤12 g、生黄芪20 g、炒白术10 g、炙枇杷叶10 g、炒苏子10 g、清半夏10 g、姜厚朴10 g、炙甘草6 g、桔梗6 g,水煎服,日1剂。嘱其喘息发作时按需吸入沙丁胺醇,其他中西药物停用。服药1周后,症状明显减轻,发作次数减少,效不更方。调治两周,夜间已不发作,每周发作次数小于两次。
按 患者肺脾气虚,肺虚则皮毛卫外不固,脾虚则伏痰宿根不化,一遇风寒之邪由皮毛而入,引触宿根,逆于肺络,肺气上逆,则发为喘鸣咳嗽。故用过敏煎加地龙、钩藤等收敛肺气,同时疏降肝气调外轮以助和降肺气;又以桔梗甘草汤、半夏厚朴汤加减开肺之郁气,防其敛降太过;佐以黄芪、白术健运升清,以制伏痰。以上组方和思路都充分反映了崔红生教授“和调气机”为纲的学术思想。
案二:患者,男,65岁,初诊。主诉:咳嗽3周,发作性喘憋2天。现病史:患者3周前因受凉出现咳嗽,干咳,呈阵发性,咳吐白色泡沫样痰,2天前凌晨3点40分从睡梦中憋醒,有濒死感并伴随呼吸困难,持续近十分钟后缓解。既往支气管哮喘病史5年,病情控制尚稳定。平素急躁易怒。舌暗,苔白腻,脉弦细。西医考虑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予解痉平喘、止咳化痰等相应治疗后,患者症状未见明显改善,仍于凌晨3~4点左右出现憋醒,咽喉紧箍感,崔红生教授认为厥阴病欲解时(从丑到卯上),与凌晨3~4点相应,考虑夜间喘憋症状为阴阳失和、枢机不利,乌梅丸化裁。处方:乌梅20 g、细辛3 g、桂枝10 g、黄连10 g、黄柏10 g、当归10 g、椒目10 g、附子6 g、麦冬10 g、五味子10 g、白芍20 g、钩藤30 g、木蝴蝶10 g、诃子10 g、地龙10 g、炙甘草6 g,共5剂,水煎服,日一剂。服药一周后,患者诉夜间未再发作喘憋,咳嗽咯痰症状明显改善。
按 患者发作喘憋具有明显的时间特点,每次于凌晨3~4点发作,这段时间与《伤寒论》中所说的“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相吻合,崔红生教授认为两阴交尽、一阳初生之经为厥阴,当阴阳相互转化时如出入气机不相顺接、枢机不利,则可出现气机升降失和、肺气上逆而出现咳嗽、喘憋等症,因此厥阴病可从和调阴阳、和解少阳枢机论治[10]。本医案在乌梅丸的基础上加入诃子、木蝴蝶、五味子、麦冬可敛肺止咳、养阴利咽,加入地龙、钩藤可解痉平喘,芍药、甘草共用柔肝酸甘化阴,解痉平喘。诸药共用,共奏和解枢机、调和阴阳、降逆止咳平喘之功,阴平阳秘、枢机得疏、升降和合,则喘憋可平。以上辨证思路再次反映出崔红生教授“和调气机”的重要学术思想。
——肝与枢机密切相关对肺之影响*
——保养肺气 春捂秋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