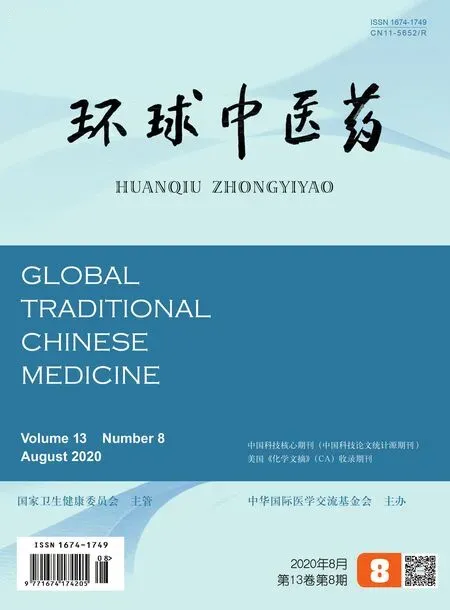王肯堂论治中风病思想探略
陈亮 马岱朝 唐勇 张展峰 潘平康
王肯堂,字宇泰,又字损庵,江苏金坛人,为明代著名医学家。中风病是一类以突然昏仆、神识昏蒙、半身不遂、偏身麻木、口舌歪斜、语言謇涩或不语为主症的一类疾病。王氏论治中风思想见于个人所撰《证治准绳》及个人所撰或他人编撰的《医镜》《医论》《灵兰要览》等著作。这些著作详辨中风的病因、病机及治疗,笔者对王氏论治中风病的论述加以归纳总结,略作探讨。
1 对中风的病因强调正虚邪中、真气不周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篇》)。“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篇》)。《诸病源候论·风病诸侯上》中也指出:“偏风者,风邪偏客于身一边也。人体有偏虚者,风邪乘虚而伤之,故为偏风也。”人体起防御作用的卫气虚弱,不能正常卫外而易为外邪所中。足太阳膀胱经为人体之藩篱,上额,交巅,络脑,下项,若为外邪侵袭,则太阳经气不利,营卫不通,脑络郁阻,易发中风[1]。“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灵枢·刺节真邪》)。意指若机体卫气不固,营卫两虚,肢体失于温养,风邪可乘虚而入,侵袭机体,客于脉络,阻滞营气血濡养肢体,发为偏枯[2]。人体正气先虚,即王氏所谓“内气之虚”和“真气不周”是导致中风的根本内在原因;“真气者,经气也”(《素问·离合真邪论篇》)。王氏所谓的“内气”指脏腑之气,“真气”可以理解为经络中流动的经气。遭受以风为主导的外邪侵袭,则是中风的发病的外在原因。王氏继承了前贤对中风病“正虚邪中”的病因认识,认为卒然中风,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虽由外风之中,实因内气之虚”[3]。并指出“身之表里上下积虚之处,气不灌流,一为风中,肢体便废”[3]。可见王氏认为“内气之虚”是中风发病的主导原因。流行于经络中的真气是“内气”的外延,经络是“内气”营养、防御功能的发挥通道,真气虚因此成为外邪入中的直接原因。若平素饮食起居、情志、嗜好等原因消耗脏腑阴精气血,内气不足,使经络中真气虚衰并腠理疏松,一旦为贼风所袭,真气不但失于防御,更不能灌流发挥营养躯体作用,便会病势如破竹,致“卒然颠扑”之症。
2 对中风的病机重视心、胃、肾与冲任的功用
2.1 心藏神、心主血脉的功能失常是中风病的体现
王氏谓心乃“天真神机开发之本”,“心者元阳君主宅之,生血主脉[4]”。“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心主神明,与中风病发病的机理及症状密切相关。中风病主要对应现代医学脑血管疾病,常见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包括肢体不遂、言语不利、感觉麻木、失语、精神症状等,古人对通过对这些症状的观察,提出了诸如《千金方》记载的“偏枯”“风痱”“风癔”“风痹”等症状的描述。因此,“心主神明”是神经系统功能的高度概括,中风病必然会见到心主神功能失常的症状。
心藏之神有广、狭两义。就广义而言,心主神的生理功能,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心通过广义之“神”调控人体整个生命活动,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调控中枢。“心藏神”(《素问·宣明五气篇》),“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这些指出了心藏神的功能对五脏六腑、肢体官窍,甚至全部生命活动的总体调控作用。其二,作为“神”下一层次的魂魄、志意从不同层次构成人体的调控与感知系统。“随神往来者谓之魂”(《灵枢·本神》)指“魂”与神一同发生,对神的调节功能具有辅助作用。“并精出入者谓之魄”(《灵枢·本神》),指魄的是在父母之精结合时产生的。“魄之为用,能动能作,痛痒由之而知也”(《类经·藏象类》)。可见“魄”是心所藏之神中主管并调制肢体、官窍固有活动,感知人体痛温觉,触压觉的功能。《灵枢·本脏》又言“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指“志意”对心理活动中的精神情绪、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机体对外界的感知的调适等方面的能力。其三,“志意”“专直”则“五脏不受邪”的卫外作用。“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灵枢·本脏》)。此处再次说明了“志意”对感知、精神、情绪的调控作用,还补充了“志意”能调动人体的防御能力,使人体免于感邪。就狭义神而言,心司意识、精神、思维、情感等心理活动的作用,正如《灵枢·本神》所说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谋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可见,心为狭义神的运行器官,通过感知周遭信息的“任物”的形式产生相应的心理活动。
通过以上心神的功用推断,中风病的病程中,可见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可见“十二官危”的脏腑功能失常,如中风后应激性溃疡导致的便血等。第二,可见肢体活动、痛温等感知异常,另外可见神识不清、精神涣散、喜笑不休、癫狂等症状。如王氏认同刘河间“心火暴盛”之说,“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郁瞀,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5]。即王氏所谓“中风将发之前,未有不热者,热极生风”[6]。第三,外邪侵袭为外风致病的公认原因,心神不藏,“志意”欠“专直”,可使防御低下,五脏更易受邪。《素问·刺禁论篇》言:“心部于表。”其中“部”字体现心与表的关系。日本学者森立之注曰:“心火阳气充足于皮肤,故心部于表也,部是分配部别之意。”表明了心与表的密切关系。外风侵袭人体,首先袭表,若心气虚弱,邪气可直接伤心[7]。可见通过这条途径,外邪直犯于心,促使中风发病。第四,心开窍于舌,舌是心的功能的重要体现部位,舌为心之苗,舌主发音,是人的思维体现于外的直接器官。中风后的言语謇涩、舌歪,是心神失常的直观体现。
除心藏神的功能外,“心生血”。心与血液的化生密切有关,即脾胃转化的水谷精微物质上输于心肺,经心火的温煦变化而赤为血液,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有“心生血”之说。张景岳《类经》指出:“肾之精液入心化赤而为血。”心通过加工转化肾精而参与血的生成。心主血脉,心气推动血液循行于脉中,周流于全身。四肢百骸受气血的濡养,正如“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中风入经络,邪气独留,血失于濡养肌肉筋骨,则见肢体不遂,皮肤血充养,则麻木不仁。
2.2 胃气的作用与中风发病有关
王氏又认为胃乃“谷气充大真气之标”[4]。《灵枢·刺节真邪》言“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指出胃能使谷气填补真气充养周身。“胃者,五脏之本”(《素问·玉机真脏论篇》)。“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然胃不能独立行使其转化谷气的功能,必须与脾相互配合,完成五谷的收纳腐熟、受气取汁、化生精微的过程。《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曰:“脾者,土也,治中央……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四肢肌肉皆为其运化水谷精气以滋养之。”并曰“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王氏在论治四肢不举时,认为此证“有虚有实,实者脾土太过,泻令湿退土平而愈,虚者脾土不足,十全散加减,祛邪留正”[4]12。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则气血充足,反之,脾胃虚弱致气血不足,进而影响肢体官窍的濡养。脾胃不足可致痰湿内生,引起朱丹溪所谓“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的病机转化。阳明属胃,“治痿独取阳明”是《内经》对痿病制定的基本方法,阳明受纳水谷精微,化生气血,阳明经脉总会于宗筋,宗筋具有约束关节而滑利关节的作用。因中风与痿症都具有肌肉无力、关节活动不灵的表现,从阳明胃入手,对中风的论治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脾胃腐熟食物为谷气功能正常,则真气能周流四脏三焦、上下内外,且邪不易侵袭。反之,真气不充,外邪侵袭,进而不能周流于经脉濡养肢体则发偏枯不遂,不能分布于五脏则发不能言语等症。
2.3 肾虚及肾络与冲任的经络联系循行参与中风发病
《素问·脉解篇》记载:“内夺而厥,则为暗痱,此肾虚也。”刘河间《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诸证门》有“肾水虚衰”之说,“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二足废而不能用,肾脉虚衰……地黄饮子主之”。王氏注重肾虚与冲脉在中风病机中的作用,通过冲任之脉与肾的联系,来认识肾虚和口不能语、足不能行之喑痱的关系。如其所言“夫肾者藏精,主下焦地道之生育,故冲任二脉系焉。冲任二脉与少阴肾之大络,同出肾下起于胞中,冲任为十二经脉之海,冲脉上行者,渗诸阳,灌诸精,下行者,渗三阴,灌诸络而温肌肉,别络结于跗。肾虚而肾络与胞脉内绝,不能上通于喉咙则喑,肾脉不上循喉咙挟舌本,则不能言,二络不通于下则痱厥矣”[4]12。此处肾络指足少阴肾经,胞脉包含冲任二脉。任、冲二脉皆起于胞中,经肾的大络也起于胞中,因此任、冲、肾经通过胞中相联系。
任脉总任一身之阴经,调节全身阴经的气血。“任脉者……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素问·骨空论篇》)。从循行路线来看,咽喉、头面等局部的言语障碍、面瘫病症与任脉有关。冲脉为“血海”。“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入腘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伏于出跗属,下循跗,入大指间”(《灵枢·逆顺肥瘦》)。冲脉“其上行者,渗三阳,灌诸精。其下行者,渗三阴,灌诸络而温肌肉,与阳明宗筋会于气冲。因言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证治准绳·杂病·痿》)。冲脉与阳明相会,故可间接影响宗筋束利关节的作用。冲脉分布于软腭、咽喉、膝踝、趾等部位,与发音、下肢、足的正常活动相关。肾藏精,内寄元阴、元阳,对全身起滋养与温煦作用。足少阴肾经循行于下肢,“起于小趾之下,斜走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灵枢·经脉》)。冲任之本在肾,肾虚之精水亏耗为本,肾气不足,冲任空虚失于灌输濡养为标,构成了王氏中风病之肾虚——冲任失调学说。赵献可创立的命门学说,认为命门处左右两肾之间,乃肾间动气,命门右旁的小窍为相火,命门左侧的小窍为真水,肾间动气、真水、相火为荣养肢体的气血之根。故赵献可对肾虚致中风有以下论述:“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干也。人之气血荣养乎四肢也,犹木之浆水灌溉乎枝叶也。木有枝叶,必有根本,人之气血,岂无根本乎?然所谓气血之根本者何?盖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而火与水之总根,两肾间动气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源……今人纵情嗜欲,以致肾气虚衰,根先绝矣,一或内伤、劳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触,皆能卒中。”以此理解肾虚中风的病机颇为允当。
3 对中风的分类突出中经络
张仲景首次将中风以症状分类,《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言:“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在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藏,舌即难言,口吐涎。”他将“不识人”和“舌难言”归入中脏腑,以此分别中经络与中脏腑。李东垣将中风分为中血脉、中腑、中脏,故王氏谓:“中风当如东垣法。”[4]9同时又受龚廷贤“中腑者为在表,中脏者为在里,中血脉、中经络俱为在中”的影响,王氏沿用龚廷贤“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中经之分焉”的分类[9]。但王氏对中风分类的鉴别,更为精细,提供了详尽的鉴别诊断症状,并突出中经络在各类中风病中的地位。
经络是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因此中经络的波及范围远较仅累及面部的中血脉为广,因此见肢不能举,口不能言等症。经络是脏腑联系全身的纽带,同时经络与血脉相互联系,邪气在经络、血脉、脏腑三者间相互传递。同时内脏疾病信号可以通过经络反应于体表。经络中流注真气,真气不周是风邪侵袭人体的直接原因,因此经络是风邪袭击人体致中风发病的门户,也是邪气在脏腑、血脉、上下内外传递的中介,因此王氏尤为重视中经络。如人体感受风邪后,可以通过血脉→经络→腑→脏的次序由浅入深逐渐加重,表现出中血脉→中经络→中腑→中脏的症状。王氏倡导的中血脉、中经络、中腑、中脏的疾病严重程度的层次分类,提纲挈领,对于把握中风的病程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有利于领会中经络在中风病的地位。
4 治疗上讲求解表、攻里、行中道
龚廷贤曰:“在表者宜微汗,在里者宜微下,在中者宜调荣。中腑者,多着四肢,手足拘急不仁,恶风寒,为在表也。”[9]中风病的治则,王氏总结为“解表、攻里、行中道”[4]10三法,即中脏可下之,中腑可汗之,中经可补血养筋,中血脉可养血以通气。王氏同时常配合调气顺气、攻痰清热、培补真气等方法。
4.1 发汗祛风
中风病“内虚邪中”之说,自金元之后逐渐淡化,鉴于医界对中风病机认识的转变,“外风”学说已逐渐减少甚至不再为目前的中医学者所认同,前人有关“外风”的理论及治风方药也渐渐被忽略[10]。黄元御《四圣心源·中风解》曰:“中风证,时医知有外邪……张景岳愚而妄作,创非风之论,是敢与岐黄仲景为敌也。”中风病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多有气血两虚的体质特点,且该病多发于冬春交替的季节,正值风邪当令之时,这符合正虚风中的致病特点[11]。由于从外风立论对中风病有确凿的临床疗效,迄今仍然有医家在临床应用。治疗上,对于中脏,王氏常以防风、荆芥祛风。对于大便秘结者,三化汤中的羌活,也体现了疏散外风的目的。中腑者兼有表证者,常用麻黄发汗,羌活、防风、荆芥祛风。中腑外可见六经之症者,以河间之法,宜祛风发表为功用的加减小续命汤分经论治;中经络治以羌活、独活、防风、细辛疏风;中血脉以秦艽升麻汤中的升麻、干葛、秦艽、白芷、防风、桂枝祛风散邪,外用方以酒煎桂枝取汁外敷患侧面部以温通经脉。
4.2 通腑泻下
《中藏经》在中风病的治疗中采用通腑泻下,如《中藏经·论治中风偏枯之法第三十九》曰:“人病中风偏枯,其脉数而面干黑黧,手足不遂,言语謇涩,治之奈何……在中则泻之……泻,谓通其塞也。”[12]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第十》中用三化汤治疗中风病中脏者。泻法自古作为祛邪的有效方式之一,王氏采用下法论治中脏与中腑,如《证治准绳》中提到:“有热盛生风而为卒仆偏枯者,当以河间法治之……或大便闭塞者,三化汤下之。”[4]三一承气汤主治“中风僵仆,风痫发作”。《医镜》记载中脏者宜大黄、枳实、厚朴泻下;中腑,内有便溺之阻隔,根据病情选择峻猛的三化汤、三一承气汤,或滋润柔和的麻仁丸;若兼有便秘,先解表后攻里。泻下之法用于中风病,源于《内经》时代,兴盛于金元,繁荣于明清,在当代得到了规范化推广及广泛临床应用[13]。
4.3 调血顺气
气与血密切相关,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血充足,经络通畅,气血荣养四肢。血虚不荣,气虚推动无力,继而血行瘀滞,形成瘀血。另外,脏腑功能紊乱,气机逆乱,输布运行津液失调,津停为水湿化痰,痰浊等病理产物由此产生,与瘀血一起,构成中风发病的主要病理因素[14]。李东垣曰:“中风为百病之长,乃气血闭而不行。”明代楼英认为:“中风皆因脉道不利,气血闭塞也。”王氏引用戴原礼《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中:“治风之法初得之即当顺气,及其久也,即当活血,此万古不易之理。久患风疾,四物汤吞活络丹愈者,正是此议。”[15]因气滞血瘀是导致中风发病的关键致病因素,王氏赞成以顺气活血之法治疗中风病。王氏在治疗上,中腑以陈皮、枳实、苏梗顺气;中经络为在中,按照“在中者宜调荣”[9]的思想,中经络外无六经表证之见症,内无二便之阻隔,为血不能养筋所致,治以四物汤养血荣筋;中血脉以清阳汤中的红花、苏木活血,或以四物汤佐以红花养血活血,同时以枳壳、乌药、香附、陈皮通气。
4.4 攻痰清热
《杂病广要》曰:“中风证,卒然晕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声,或口眼喎斜,手足瘫痪,或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语……昏乱晕倒,皆痰为之。”[16]《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风》谓中风:“多痰多热,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法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救其标,次当治本。”[17]历代医家常用清热涤痰开窍治疗中风之挟痰挟火,内闭经络的“阳闭”证。对于卒然昏倒、昏不知人、痰涎蕴盛者,王氏主张以麻油、姜汁、竹沥调服苏合香丸,或服至宝丹,或服活命金丹。中脏者宜服瓜蒌仁、杏仁、苏子姜汁、竹沥祛痰。痰涎蕴盛者,宜吐痰治法,主张以皂角、白矾所制的急救稀涎散或石绿、冰片所制的碧霞散催吐其痰。中脏热极生风、心火暴盛者,治法以清心降火,“心火既降,肝木自平,此实则泻其子之法也”[6]。予以大剂清心汤或泻心汤。朱丹溪指出“半身不遂,大率多痰”[18],因此祛痰通络可治疗中风肢体不遂。王氏主张中腑者以竹沥祛痰;中经者以南星,半夏、茯苓、黄芩、姜汁、竹沥治其痰;中经络以胆南星、半夏、茯苓、黄芩、姜汁、竹沥治其痰;中血脉加姜汁、竹沥祛痰。
4.5 培正填虚
因“真气不周”是中风发病的内因,故培补真气为中风病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王氏提倡以“黄芪助真气者也,防风载黄芪助真气以周于身者也”[4]10,且推崇人参的使用,谓人参“能补五脏之正气,正气复则邪气除”[6]2417,又曰“通血脉,助真阳,非大剂人参不可”[6]2441。对于中风病见口开、手撒、遗尿的脱证,病情危殆,王氏认为治疗当以“速用大料参芪接补之,及脐下大艾灸之”[4]9,以回阳益气,固脱救阴。肾虚所致的痱喑之症,调养宜地黄饮子以填补肾气之虚。偏枯、音喑,总由“真气不周而病者也”[4]10。故又一法,以黄芪为君药,人参、白芍、当归为臣以益真气而养血。
4.6 中风之预防及预后调摄
王氏在《证治准绳》中引用薛己的预防论述:“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帷幕可也。”[4]12即遵守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恬淡虚无”“形劳而不倦”,戒“七损”的经旨,方可“持满”肾精,固气血之根,有助于真气的保养,预防中风病发生。《灵兰要览》记载中风将发之预防,以黄芪、人参、防风补五脏正气,助真气周于全身,辅以橘红、木通顺气,当归、红花养血理血,山栀清热。若外邪或内邪已去,则以“行中道”之法予以羌活愈风汤,此方养心神、补肝肾、清湿热、祛风邪,王氏建议此方宜常服以调摄预后。
5 结语
由于王氏所处时代对中风认识的局限,王氏所论述中风病包含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语言謇涩或失语、神识昏蒙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包含现代医学中脑血管疾病、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病、面神经麻痹等一类疾病,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医学的卒中。王氏吸纳了河间肾水亏虚,心火暴亢,故心神昏冒的认识;继承李东垣本气自病等认识,提倡“正虚风中”的观点。因所处时代所限,著作中尚未提及“类中风”“非风”“内伤积损”等概念,可见其学术思想未受同时代的张景岳学术思想影响。但“外风”说的确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历代有大量的验案证实了小续命汤、风引汤、大秦艽汤、侯氏黑散等方剂治疗中风病的有效性。有学者提出,外风因素至今仍需引起重视,因为外风存在不容置疑,尤其是在治疗效果不佳或中风后遗症的辨治中要有外风的概念,并认为基于营卫失调理论的外风学说,在中风病的病机中不可忽视[11]。因此,在内风学说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仍需审视外风学说在中风病治疗中的作用。王氏从心藏神、心主血脉、胃气、肾虚及肾络与冲任的经络联系循行来认识中风的病机。王氏提供了中风分类的详尽的鉴别诊断症状,突出中经络在各类中风病中的地位。王氏为辨治中风病提供了详尽的治疗方案,通常汗、下、补血、助真气、攻痰、祛风、顺气、调血等方法联合使用。王氏对中风病的论治思想与方法,对当今中医临床治疗中风病仍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继承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