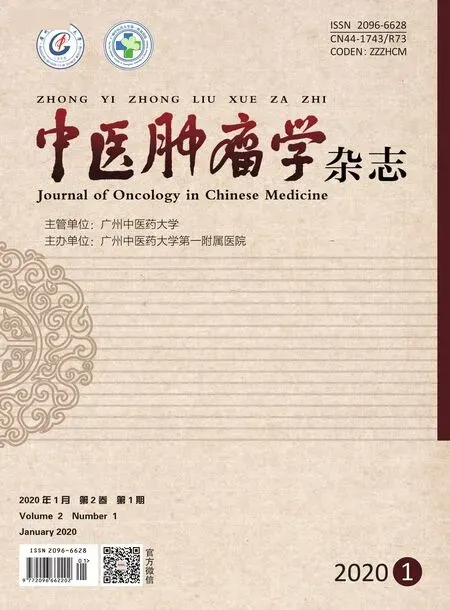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发病机理及诊疗现状
黄晓蒂, 梁子成, 田莎, 王茜, 田雪飞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为我国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诊断技术的提高,PLC早期确诊率显著提高,而外科手术治疗为早中期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PLC术后治疗主要以防治肿瘤转移复发为主,而手术创伤带来的一系列炎症反应,使肝癌术后患者5年肿瘤复发率高达40%~70%。因此,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关注术后康复治疗,缓解术后后遗症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据报道癌因性疲乏(Cancer Related Fatigue,CRF)是肿瘤术后及其治疗期间最常发生和最令人痛苦的后遗症状之一,癌因性疲乏比睡眠失调、过度劳累导致的“正常”疲劳更严重、更持久、更令人虚弱,而且不能得到有效缓解[2],CRF在肿瘤患者的总体发生率可达到19%~99%,且贯穿于肿瘤发生、发展及其治疗的全过程中,在肿瘤幸存者完成治疗后该症状可能仍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3-4]。本文就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发病机理及诊疗现状进行综述。
1 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发病机理
1.1 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现代医学认识
癌因性疲乏的发病因素尚不明确,可能与肿瘤治疗、生活习惯紊乱、情绪紊乱、患者身体情况等有关,发病与否及严重程度与手术治疗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5]。肝癌术后的贫血、细胞因子分泌失调、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失调、5-羟色胺(5-HT)神经递质水平失调、三磷酸腺苷(ATP)含量的改变等都是导致癌因性疲乏发生的内在原因。迄今为止,认为细胞因子分泌失调,特别是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失调是癌因性疲乏发生的主要发病机制[6]。
1.1.1 肝癌术后炎症与癌因性疲乏
肿瘤炎症本身对于肿瘤的发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项基于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建立的一种新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的研究中,探讨了炎症在肝癌预后价值中的重要地位[7]。肿瘤炎症可通过刺激神经免疫信号通路参与癌症相关疲乏的发生。机体为维持体内稳态,肿瘤的周围产生促炎症细胞因子,促炎因子可以通过刺激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发出信号,产生疲乏症状和其他行为变化。有研究发现,由肿瘤产生的促炎症细胞因子所介导的周围炎症反应是癌症相关疲乏的潜在机制,用药物阻断促炎细胞因子TNF-α之后,肿瘤患者的疲乏症状也获得明显缓解[8]。外科手术的治疗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炎症反应的发生与发展,Cata JP等[9]的研究发现原发性胆道癌或转移性肝癌术后炎症和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的标志物,如血浆IL-6和皮质醇浓度可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峰值。
1.1.2 肝癌术后神经内分泌紊乱与癌因性疲乏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重要部分,通过对糖皮质激素的调控作用影响参与调节体内多个器官的应激反应,HPA轴参与细胞因子的产生,研究表明HPA轴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HPA轴可通过影响炎症反应,导致疲乏症状的产生[10-11]。由于情绪心理压力、肿瘤治疗以及生活规律改变的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呈现出皮质醇反应迟钝,使得相关细胞刺激因子产生升高,可能是导致炎症过程加剧的基本机制[12]。研究发现,因手术期麻醉可影响机体免疫系统刺激下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造成免疫系统迟钝而促使肿瘤的复发与发展[13]。
1.1.3 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其他可能机制
肝癌术后细胞免疫系统的激活,包括白细胞数量的增多都在加速着肿瘤患者疲乏症状的发生[14]。另一种可能是癌症发病过程中炎症加重与病毒的重新激活有关,最近一项关于乳腺癌的研究发现,癌症患者巨细胞病毒(CMV)抗体滴度升高与疲乏有关[15]。众所周知,原发性肝癌患者多伴有肝炎病毒复苏,很有可能是肝癌手术后激活炎症反应引起疲乏的潜在机制之一。
1.2 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中医学认识
“痨者劳也,劳损气血而为病也”,癌因性疲乏中医发病机制主要是正气不足,阴阳气血亏损,脏腑虚损伴有夹痰、夹湿或气血瘀滞[16]。肝癌的慢性消耗以及手术治疗对于肝癌患者正气的冲击,加重了肝脏的虚损。肝脏长期虚损影响着肝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导致肝脏中气血逆乱,瘀滞、痰饮湿阻形成。因虚致实,虚实夹杂,痰饮湿的形成进一步遏阻气血的正常运行,从而导致机体进一步虚损,难以恢复。这种恶性循环形成了肝癌癌因性疲乏症状的复杂病机,导致癌因性疲乏症状较其他疲乏症状更为持久,不易缓解,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与治疗。聚类分析研究发现癌因性疲乏的主要证型为:肾阳虚证、肝气郁结证、脾胃阴虚证、寒湿困脾证、肺气亏虚证、脾气亏虚证[17]。病位在肌肉,脾主肉,故脾的虚弱,气血生化不足,是疲乏的主要病机。
2 现代医学对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治疗
肝癌手术影响患者术后疲乏发生的因素主要是贫血和抑郁,针对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患者改善炎症微环境、调节神经内分泌等需求,现代医学主要的治疗手段是抗贫血与抗抑郁治疗。
2.1 抗贫血与癌因性疲乏
肝癌术后患者,术中大量出血,术后部分肝脏切除肝血窦贮存血液总量减少,血液循环系统异常运行,机体供氧、营养功能及肝脏解毒功能减弱,产生乏力、困顿等不适症状。异体输血是缓解症状最快的方法,临床上肝癌术后必要时会采取异体输血的方法以迅速填补术中大量出血的空缺,达到治疗癌因性疲乏的目的[18]。此外,王文红[19]等通过临床研究发现,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具有显著改善疲乏的效果,实验组采用健脾益肾化浊汤治疗肾性贫血,患者的疲乏症状得到较好改善,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增加血红蛋白量,达到抗贫血效果,从而减轻疲乏症状。由于手术的打击,巨噬细胞的活化和各种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加,进而导致内源性EPO合成不足,抑制骨髓中红系前体细胞的分化,以及铁代谢的改变,临床治疗上可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血小板生成素(TPO)、白介素11(IL-11)处理。
2.2 抗抑郁与癌因性疲乏
抑郁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会导致患者体内细胞因子水平失衡与体液系统紊乱,其原理包括:降低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活力、生成更多的IL-1与IL-6等。杜春燕[20]通过研究270例肝移植患者的多维度疲乏症状量表发现,抑郁与疲乏存在密切关系,长期处于抑郁状态容易导致机体免疫下降,加重患者病情。在长期抑郁状态下,患者极易产生疲乏症状。有学者研究发现氯胺酮可以应用于抗抑郁治疗,临床疗效较好,其抗抑郁的机制可能与下调IL-1β和IL-6的水平有关[21-22]。针对肝癌术后产生的疲乏症状,临床治疗上可结合抗抑郁手段进行交叉治疗,干预炎症微环境及调整神经内分泌,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2.3 综合护理与癌因性疲乏
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包括生活节律调控、心理护理、家庭护理干预等。荣玲[23]以80例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为对象,对观察组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通过SF-36、herth希望量表获得数据并分析发现,延续性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试验组的现实态度、积极行动及社交关系,提高生命质量。何珊珊等[24]对124例肝癌患者进行分组心理护理试验,以Piper疲乏量表、焦虑自评表、抑郁自评表检测,进行护理干预的实验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肝癌术后患者可采取综合护理措施进行干预,结合心理疏导、适量运动,加强沟通交流可以降低肝癌术后癌相关性疲乏发生率,缓解肝癌术后患者癌因性疲乏症状,配合术后治疗。
3 中医对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治疗现状
在中医治疗方面,针对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方法主要有药物疗法,情志疗法,运动康复疗法、针灸疗法及五音疗法等,其主要依据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发生发展的相关病因病机展开。
3.1 药物疗法
根据癌因性疲乏的肾阳虚证、肝气郁结证、脾胃阴虚证、寒湿困脾证、肺气亏虚证、脾气亏虚证的六大临床证型,主要治法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3.1.1 健脾益胃散寒法
肝癌患者术后大伤元气,元气耗伤,调节脏腑功能能力下降,针对脾胃阴虚证、寒湿困脾证、脾气亏虚证所形成的脾虚性术后癌因性疲乏,采用健脾益胃散寒法可迅速恢复元气,促进脏腑正常运转。黎汉忠[25]通过Piper疲乏量表收集数据,分析发现采用健脾消积汤治疗患者,治疗组的情绪功能、角色功能、躯体功能、物理症状和整体健康状况均优于对照组,阳国彬等[26]运用薯蓣丸治疗恶性肿瘤化疗患者43例,发现薯蓣丸可减轻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疲乏程度(治疗组缓解率88.37%vs对照组65.12%,P<0.05)。刘永叶[27]将补中益气汤运用于CRF患者治疗,取其补气健脾、益胃生津之功效,采用疲劳症状测量表评价变化,发现治疗组评分低于对照组,且恶心呕吐等消化道不良反应明显得到减轻。
3.1.2 补肺益气法
肝癌术后患者气虚可表现为肺气损虚,百脉失司,浊气无以排出,癌毒内郁所形成的肺虚性癌因性疲乏,采取补益肺气法,起到促进体内外清浊交替、缓解术后疲乏的功效。刘志勇等[28]在临床研究中通过60例癌症患者对比发现中成药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甲地孕酮对于晚期癌症患者CRF具有良好的症状改善效果,其30例联合用药组行为、情感、躯体以及认知状况等方面都得到改善,其中医作用机制取参芪扶正注射液的补益肺气、驱邪扶正之效,其分子机制可能与转化生长因子-β1、肿瘤坏死因子-α的表达相关。
3.1.3 疏肝养肝法
肝癌术后患者情志抑郁,肝失疏泄,血行不畅,津液输布障碍,脏腑筋脉失养,且肝气郁结,癌毒内盛,肝郁化火,生痰致瘀[29]。诸多病理产物,如火、痰、瘀等,进一步阻滞经脉,加重疏泄障碍,形成恶性循环,此时应用疏肝养肝法可切断恶性循环,取得较好的治疗术后癌因性疲乏成效。徐国荣[30]通过观察128例癌因性疲乏患者,实验组应用中成药阿胶黄芪口服液治疗,数据显示:实验组的KPS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等都优于对照组,且发现黄芪的提取物可明显降低血清ALT、AST和减少HA、TNF-α含量,调节免疫功能,消除肝脏炎症,改善肝功能,提示其对癌因性疲乏患者疗效良好且临床安全性高的优势。冯正权[31]在临床中使用四逆散加减以疏肝养肝,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储真真[32]运用疏肝养血法治疗癌因性疲乏,应用柴胡疏肝散合四物汤加减,以柴胡疏肝散理气活血,四物汤生血养肝,患者肝气郁滞症状与肝血虚症状皆得到有效减轻。可改善肝癌术后患者本虚标实的状况,阎丽珠[33]在临床治疗癌因性疲乏中运用益气疏肝法治疗癌因性疲乏,处方用药以四君子汤为主方并加以疏肝理气药,具有良好收效。
3.1.4 补益肾阳法
肝癌患者术后肾气受损,摄纳无力,肺中自然清气无法正常下纳于肾,肾阳虚损,失于温煦,阳虚不振,精神萎靡,生殖、气化功能减退,出现呼多吸少、动则气喘等症状,在术后肾虚性癌因性疲乏治疗的过程中,补益肾阳法意义重大[34]。刘莲方等[35]认为肾为人之根本,癌因性疲乏的治疗应把握以肾为切入点的方向。李志明[36]通过观察60例癌因性疲乏患者发现,健脾益肾法的治疗组在行为维度、认知维度、感觉维度等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王沁[37]研究67例癌因性疲乏患者,发现运用益肾化瘀解毒方的观察组中,骨痛、贫血缓解率达95.8%,厌食症状改善率10%。宋和新[38]将龟鹿二仙膏应用于肾阳虚患者,使患者肾阳得以滋养,精神倦怠、肢体乏力等肾阳虚症状得到减轻,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3.2 情志疗法
中医认为情志病是情志活动异常的疾病,情志活动是人体脏腑精气对外界刺激的应答;肝癌术后CRF患者身体长期处于疲乏,易并发情志不遂,或心生烦闷、肝火旺盛,或意志低沉、气机郁滞,气血运行失常,津液代谢受阻,机体失于濡养,则易形成虚证。同时气机郁滞,津液代谢异常,癌毒内盛,郁积化火,焦灼阴液,形成虚证。此时患者情志失常,且身心疲惫,容易导致抑郁发生,极大地降低了肝癌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张辉等[39]将130例CRF患者分组研究发现,在常规临床治疗基础上加入中医情志疗法措施,采取针对性手段,如言语开导法、移情易性法、情志相胜法、情志制约法、顺情解郁法、释疑解惑法等,有利于减缓患者疲乏程度,提高患者KPS评分与后续治疗依从性,李禹其[40]对44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中医情志护理,通过开导式、转移式、情胜式、静式等心理调节方法减轻患者的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且观察组术后并发症为54.5%,远低于对照组的79.6%。
3.3 其他疗法
BANZER W等[41]发现,运动疗法可通过增加患者的肌肉力量、提高患者的有氧适能及其心理社会功能等,缓解术后CRF患者疲乏症状。修闽宁[42]研究发现,八段锦运动能辅助减轻CRF患者疲乏的程度,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邱萍等[43]通过观察71例癌因性疲乏患者临床研究发现,八段锦联合中医情志护理可以改善癌因性疲乏及焦虑、抑郁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上运动疗法改善CRF的可能机制是通过刺激垂体β内啡肽的分泌,发挥β内啡肽增强机体对强刺激的耐受力、生理镇静的功能,从而减轻CRF的相关症状[44]。金玲[45]研究发现,子午流注择时五行音乐可减轻胃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症状,提高其睡眠质量。
另一方面,中医针灸在治疗癌因性疲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临床可通过针灸治疗方式可通过对肿瘤直接作用、肿瘤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不良反应和并发症以及改善患者心理状况等方面来有效改善患者的癌因性疲乏症状,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46]。焦培娟等[47]经过研究发现针对足三里、三阴交、合谷等穴位进行每天6次,每次1分钟的周期性按压可明显改善CRF症状。
此外,基于中医相生相克原理的五音疗法,具有调神、悦心、舒肝、解郁的功能,可以通过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减轻肝癌患者的疲乏症状[48]。陈苏娟等[49]通过研究64例中晚期癌症患者,对比研究发现在综合性中医护理针对性加入角、徵、宫、商、羽对应属性的肝、心、脾、肺、肾5套音乐,发现干预组的负面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癌因性疲乏状况得到明显减轻(P<0.05)。
4 小结
肝癌术后炎症微环境的形成、神经内分泌的失调及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等诸多因素下,都会导致术后癌因性疲乏的发生。中医认为,肝癌手术一定程度上损伤患者正气,正气不足、气血阴阳虚损,导致疲乏症状的出现。目前针对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主要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是补充激素以对抗炎症反应、药物调节神经内分泌以及在辨证基础上中医药的使用。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综合护理、有氧运动与中医导引术、针灸及五音疗法等。在目前已知的治疗手段下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由于其发病因素多样、发病机制复杂、患病个体差异大,单一的治疗措施并不能取得长效持久的效果。输血、使用激素等治疗措施见效快但副作用大,而中医药治疗手段疗效较好,在CRF的治疗中特色鲜明,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本文系统总结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综合治疗手段,以冀为日后开展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相关研究、形成肝癌术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规范诊疗方案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