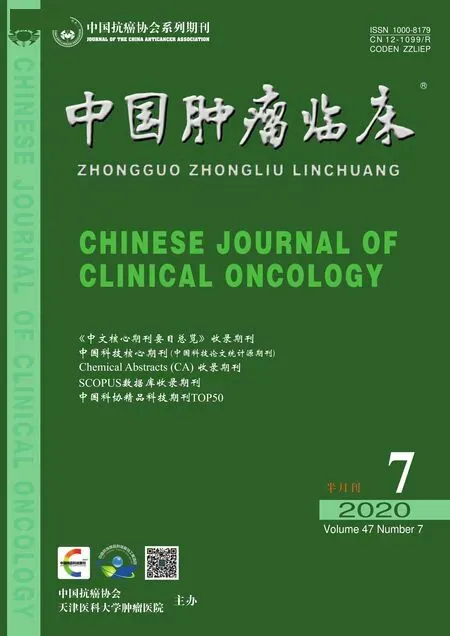单羧酸转运蛋白家族介导乳酸转运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汪婷婷 何永文
肿瘤细胞产生和生存的内环境,称为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其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治疗存在深远影响。TME不仅包括肿瘤细胞本身,还有其周围的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等各种细胞,也包括附近区域内的细胞间质、微血管以及浸润在其中的生物分子等[1]。TME在生化和生理特征方面具有自身特点,比较典型的为缺氧和酸中毒[1-2]。肿瘤细胞为了在贫乏及不断变化的营养环境中满足快速增殖的生物合成与能量需求,改变代谢模式,进行代谢重编程,即使在有氧条件下也优先利用糖酵解来获取大部分能量,有氧糖酵解被称为“Warburg 效应”[3]。缺氧可进一步增强TME 中肿瘤细胞的糖酵解过程,导致大量乳酸产生[4]。单羧酸转运蛋白(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s,MCTs)为溶质运载蛋白16(solute carrier 16,SLC16)家族的一部分,主要功能为介导质子耦连的乳酸等单羧酸类物质的跨膜转运。MCTs可将细胞内的乳酸转运到胞外,防止由于乳酸在胞内蓄积引起的糖酵解抑制,从而维持肿瘤细胞的高糖酵解表型,同时转运到胞外的乳酸降低TME的pH值,维持TME的酸性状态;另一方面,其可将TME 中的乳酸转运到胞内,用作氧化型癌细胞的代谢原料以及肿瘤血管生成的信号传导物质[5]。因此,作为转运蛋白的MCTs 与肿瘤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不仅参与调控肿瘤细胞能量代谢和TME 酸化,还通过介导乳酸转运来促进血管生成和诱导免疫耐受,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MCTs概述
MCTs为SLC16基因家族编码的一类转运蛋白,由具有细胞内N-端及C-端的12个跨膜螺旋结构和第6及第7螺旋结构之间的大胞质环组成[6],其包含14个成员,主要定位在细胞膜上,在细胞器膜中也有表达,亚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表达调控、组织分布、细胞内定位以及对应底物和抑制剂的亲和性。MCTs家族成员本身未糖基化,但MCT1-4需要与糖基化的辅助性蛋白(basigin/CD147或embigin)结合,才能维持其活性。MCT1(SLC16A1)、MCT3(SLC16A8)、MCT4(SLC16A3)优先与basigin/CD147结合,MCT2(SLC16A7)优先与embigin结合。MCTs家族的14个成员中,MCT1-4表现出质子耦连的单羧酸类物质的转运,包括丙酮酸、乳酸、酮体以及短链脂肪酸(丙酸和丁酸),转运方向完全由质子和一元羧酸盐在胞膜两侧的浓度梯度决定[7];MCT8(SLC16A2)为甲状腺激素转运体;MCT10(SLC16A10)是芳香族氨基酸转运体;MCT6(SLC16A5)参与了包括布美他尼(bumetanide)在内的一些药物的转运,但其天然底物尚未明确;MCT7(SLC16A6)参与禁食时肝细胞对酮体的向外转运;MCT9(SLC16A9)是肉毒碱(carnitine)的向外转运体;MCT12(SLC16A12)为肌酸转运体;其余成员的功能尚未明确[6,8]。每个组织中不同MCT亚型的表达模式与其在该组织中的代谢作用相匹配。几乎所有组织中均有MCTs,使得一种组织中产生的乳酸、丙酮酸和酮体可用于另一种组织。如肝脏脂肪酸进行氧化代谢时产生的酮体,经MCT1或MCT2进入血液,被神经元、骨骼肌和心肌再经MCT1或MCT2吸收,用作代谢燃料[9]。另外,不同的MCT亚型在糖酵解型细胞和氧化型细胞之间协调转运乳酸,以满足代谢的需求。在骨骼肌中,表达MCT4的糖酵解型白色肌纤维为表达MCT1的氧化型红色肌纤维提供乳酸;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表达MCT1和MCT4的糖酵解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为表达MCT2的氧化神经元提供乳酸[7]。此外,MCT1还可以介导某些药物通过肠、肾的上皮细胞膜以及血脑屏障[9]。因此,在生理状态下,MCTs在维持组织稳态及细胞代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MCTs在肿瘤中的表达
近年来研究发现,MCT1、MCT2和MCT4在多种类型的肿瘤中异常表达,并参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研究证实MCT1在恶性胶质瘤、乳腺癌、宫颈癌、胃癌、口腔癌、非小细胞肺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和Burkitt 淋巴瘤、皮肤鳞癌、软组织肉瘤、胆管癌中表达上调[10-19],在前列腺癌中表达下调[20]。MCT4在乳腺癌、食管癌、口腔癌、非小细胞肺癌、皮肤鳞癌、肝细胞癌、宫颈癌、恶性睾丸生殖细胞肿瘤、软组织肉瘤和胆管癌中表达上调[10,12,14-16,18-19,21-26],在弥漫性大B 细胞淋巴瘤和Burkitt 淋巴瘤中表达下调[13]。MCT2在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中表达上调[12,20],在肝细胞癌中表达下调[27]。MCTs在肿瘤中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增殖、迁移等恶性生物学行为和肿瘤的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可成为评估恶性肿瘤预后的指标。Huhta等[22]在对食管腺癌的研究中发现,MCT1、MCT4在正常上皮、Barrett 黏膜、非典型性增生及癌组织中的表达呈线性增加;MCT1的低表达与淋巴结转移阳性、远处转移阳性、高肿瘤分期相关,MCT4的高表达与远处转移阳性相关。Liu 等[21]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和Western blot检测骨肉瘤组织,发现MCT4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其高表达与骨肉瘤的远处转移和复发呈正相关,MCT4低表达的患者总生存期明显高于高表达组。Zhu等[23]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到MCT4在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中表达升高,其高表达与肿瘤大小、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肿瘤复发密切相关;使用siRNA敲低OSCC 细胞系中MCT4的表达量后,发现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行为均受到抑制,其增殖的抑制与p-AKT和p-ERK1/2的下调相关,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减少可能是整合素β4-SRC-FAK和MEK-ERK信号的下调导致。深入了解MCTs 家族在肿瘤组织中异常表达的作用和机制,能为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3 MCTs介导乳酸转运对肿瘤的影响
肿瘤组织中,糖酵解细胞的主要代谢产物为乳酸,其是氧化癌细胞的主要代谢原料,也是重要的信号传导物质,与肿瘤组织的血管生成和免疫耐受相关。目前研究表明,MCTs介导乳酸转运可通过参与肿瘤组织中细胞之间的糖代谢共生、促进血管生成及诱导免疫耐受等方面调节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
3.1 MCTs介导乳酸转运促进肿瘤组织细胞糖酵解与代谢共生
有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中表达MCT1的氧化型癌细胞能吸收表达MCT4的糖酵解型癌细胞分泌的乳酸盐[28],随后的多项研究也证实了该现象[29-31]。与葡萄糖相比,氧化型癌细胞倾向于使用乳酸作为氧化原料,这样使得葡萄糖更易被糖酵解型癌细胞利用。因此,糖酵解型和氧化型癌细胞存在共生关系,之间相互调节对能量代谢物的获取,肿瘤组织中的这种合作关系称为“代谢共生”[28]。近期研究证明,肿瘤组织的代谢协同作用还涉及基质细胞: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进行糖酵解,为癌细胞的氧化代谢提供原料[32]。Martinez-Outschoorn等[33]研究发现,在基质小窝蛋白-1下调的肿瘤中,癌细胞诱导邻近的CAFs代谢重编程,使CAFs进行有氧糖酵解,产生大量的乳酸和(或)丙酮酸。这些代谢物被转运到邻近的癌细胞中进入三羧酸循环,增强氧化磷酸化,进而产生更多的ATP。乳酸或丙酮酸的分泌和再摄取是由MCT1/4介导的。Whitaker-Menezes等[34]把MCF7乳腺癌细胞和正常成纤维细胞进行共培养,观察到MCF7细胞促进正常成纤维细胞向CAFs转化;并且发现单独培养时,MCF7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均不表达MCT4,共培养时癌细胞可特异性诱导CAFs中MCT4的表达。此外共培养时MCF7细胞中MCT1被特异性上调;在原发性人类乳腺癌样本中也获得相似的结果。癌细胞和基质细胞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称为“逆Warburg效应”[32]。上述研究表明,MCTs介导乳酸转运在肿瘤组织细胞的糖酵解与代谢共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3.2 MCTs介导乳酸转运促进肿瘤血管生成
在氧化型癌细胞和内皮细胞中,乳酸通过MCT1流入,被乳酸脱氢酶1氧化生成丙酮酸,成为促血管生成的胞质信号。丙酮酸通过抑制脯氨酰羟化酶(prolyl hydroxylases,PHDs)发挥促血管生成作用。PHDs为一类依赖氧、α-酮戊二酸和Fe2+催化的非血红素、铁依赖性双加氧酶[35],能将2个羟基转移到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氧依赖域的402和564位脯氨酸残基上,使HIF-1α羟基化,羟基化的HIF-1α会被泛素-蛋白酶水解复合体降解[36]。在此分子背景下,丙酮酸与α-酮戊二酸竞争,抑制PHDs的活性。在癌细胞和内皮细胞中,PHDs被抑制后,解除对HIF-1α的羟基化,避免HIF-1α因羟基化而被降解,使HIF-1α得以积累并与HIF-1β结合形成二聚体,激活肿瘤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和内皮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的转录[36-39],VEGF-A和bFGF均为促血管生成因子,与内皮细胞表面表达的受体特异性结合,可刺激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40]。在内皮细胞中,PHDs可负向调控核转录因子κB抑制蛋白激酶(inhibitor of κB kinase,IKK)的表达和活性。IKK磷酸化核转录因子κB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κB,IκB),导致其随后被泛素化并通过蛋白酶体途径降解。在静息状态下,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过与IκB紧密结合而被隔离在细胞质中,PHDs被抑制后,IKK的表达和活性上调,使IκB蛋白磷酸化随后被降解,解除对NF-κB的抑制,释放的NF-κB转位进入细胞核,调控多个靶基因的表达[41],引起包括促血管生成因子白介素-8(interleukin-8,IL-8)的转录[37,42]。在肿瘤中乳酸经MCT1转运至氧化型癌细胞和内皮细胞,通过抑制PHDs激活转录因子HIF-1、NF-κB,增强肿瘤细胞VEGF-A和内皮细胞VEGFR2、bFGF和IL-8的表达,促进血管生成。
有研究发现,在常氧条件下,氧化型肿瘤细胞中的乳酸激活HIF-1,但在Warburg型肿瘤细胞中不激活;MCT1的抑制阻断了乳酸诱导的氧化型肿瘤细胞中HIF-1的活化[39]。研究者使用具有氧化代谢活性的人子宫颈鳞癌细胞系SiHa和进行有氧糖酵解的人结直肠腺癌细胞系WiDr,发现SiHa细胞比WiDr细胞表达更高水平的MCT1;此外MCT抑制剂α-氰基-4-羟基肉桂酸(αcyano-4-hydroxycinnamate,CHC)可完全阻断SiHa细胞中乳酸诱导的HIF-1α蛋白的表达;RNA干扰导致的MCT1沉默也可抑制乳酸诱导的HIF-1的活化。因此在氧化型肿瘤细胞中,乳酸摄取为触发HIF-1信号通路的上游事件,MCT1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Vegran等[37]研究发现,肿瘤细胞经MCT4释放的乳酸可能被内皮细胞经MCT1吸收,并通过NF-κB/IL-8信号通路刺激血管生成。研究证实内皮细胞经过MCT1摄取的乳酸可诱导IL-8的表达;乳酸诱导IL-8依赖于NF-κB途径;肿瘤细胞经过MCT4释放乳酸可刺激IL-8的产生,同时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和灌注;使用MCT1和(或)MCT4抑制剂可能干扰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间乳酸的微妙交换,间接减弱IL-8对肿瘤血管发育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糖酵解型癌细胞产生的乳酸可激活促血管生成转录程序,诱导肿瘤内新生血管的形成,MCTs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3.3 MCTs介导乳酸转运诱导肿瘤免疫耐受
在肿瘤中,乳酸通过抑制T细胞增殖、树突状细胞成熟和NK细胞活性来抑制抗癌免疫。Fischer等[43]研究发现,活化的T细胞增殖时进行糖酵解,并通过MCT1输出乳酸;由于乳酸的转运方向是由细胞膜两侧的浓度梯度决定,因此肿瘤微环境中积累的乳酸会阻碍这些细胞的乳酸外排,从而干扰T细胞的代谢和功能。Puig-Kröger等[44]报道了乳酸抑制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monocyte-derived dendritic cell,MDDC)的表型和功能,其机制与乳酸钠抑制NF-κB的活化进而削弱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MDDC表型和功能的成熟相关。Brand等[45]研究发现,癌细胞中乳酸脱氢酶A引起的乳酸增加可抑制肿瘤浸润T细胞和NK细胞中细胞因子的产生,特别是γ干扰素;还能抑制T细胞和NK细胞的功能,诱导T细胞和NK细胞凋亡。
4 MCTs抑制剂在肿瘤治疗中的潜在应用
随着MCTs在肿瘤发生、发展、侵袭、转移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MCTs抑制剂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CHC被用来进行了大量的体外和体内实验,对MCT1、MCT2和MCT4均有抑制作用,其作用的敏感性MCT2>MCT1>MCT4[7,46];然而,CHC除了可以抑制MCTs外,还可以抑制线粒体丙酮酸载体和阴离子交换蛋白1[6]。其他已知的MCTs抑制剂中,4,4′-二异硫氰基芪-2,2′-二磺酸(4,4′-diisothiocyanatostilbene-2,2′disulfonicacid,DIDS)不可逆地与MCT1和MCT2上的赖氨酸残基结合,使转运蛋白失活,但不作用于MCT4。有机汞化合物,如对氯汞苯磺酸通过干扰MCT1、MCT3、MCT4与辅助蛋白CD147的相互作用来抑制其表达和活性,但不影响MCT2[7]。AR-C155858和AZD3965为MCT1和MCT2的有效抑制剂,但不作用于MCT4[47-48]。化合物AZD3965,目前作为一种抗癌药物,正在进行前列腺癌、胃癌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Ⅰ期临床试验[6]。目前尚无MCT4选择性抑制剂的相关报道。
如前所述,糖酵解型和氧化型肿瘤细胞存在共生关系,其相互调节对能量代谢物的获取。糖酵解型癌细胞产生的乳酸为氧化型癌细胞的代谢底物,当MCT1 控制氧化癌细胞对乳酸的摄取时,靶向MCT1可导致乳酸内流受损,氧化型癌细胞中代谢从以乳酸为底物的氧化磷酸化转变为以葡萄糖为底物的有氧糖酵解,从而导致缺氧癌细胞因持续性的葡萄糖剥夺而死亡[28]。其选择性是由于同一肿瘤中氧化型和糖酵解型癌细胞的代谢相互依赖性:氧化型癌细胞通过改变底物来适应MCT1的抑制,依靠代谢共生的糖酵解型癌细胞则不能。Sonveaux 等[28]使用Lewis 肺癌细胞(LLc,其在细胞膜上表达MCT1)建立小鼠肺癌模型,在此模型中应用MCTs抑制剂CHC可导致肿瘤生长迟缓,以及广泛的肿瘤中央区坏死;在WiDr细胞(进行有氧糖酵解的人结直肠腺癌细胞系)中也可观察到类似情况。此外Sonveaux 等[28]还发现抑制MCT1可使肿瘤对放疗更敏感,采用MCT1 抑制或(和)6-Gy 照射处理LLc 小鼠肺癌模型,单独治疗时,对肿瘤生长的影响相似;联合治疗时,对肿瘤生长的抑制显著提高,超过单独治疗时两者效益的叠加。MCTs介导糖酵解型癌细胞的乳酸向外转运,是重要的pH调节因子。抑制MCTs 功能可以酸化糖酵解型癌细胞的胞质,诱导死亡。Hanson 等[49]研究发现,用CHC 或MCT1和MCT2 抑制剂AR-C155858 结合MCT4 敲低阻断所有3个MCT分子(MCT1、MCT2、MCT4),可显著抑制乳酸的外排,降低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内pH值,从而诱导细胞死亡。
5 结语
MCTs为细胞向内和向外转运单羧酸类物质的主要通道,是细胞内外pH调节的关键因子及维持肿瘤细胞高糖酵解表型和酸抵抗表型的重要参与者,在TME的代谢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不同肿瘤类型中表达高低的差别、在肿瘤间质中的表达及作用、在肿瘤免疫耐受中的相关机制等方面亟需进一步的研究。目前,MCTs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乳酸的转运上,对其他单羧酸类物质(如丙酮酸、酮体等)转运的研究尚少。此外在MCTs抑制剂方面,MCT亚型选择性抑制剂尚未明确。
综上所述,MCTs为维持TME稳态的关键因子之一,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其作用的相关机制,有助于开展针对MCTs的靶向治疗,为肿瘤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