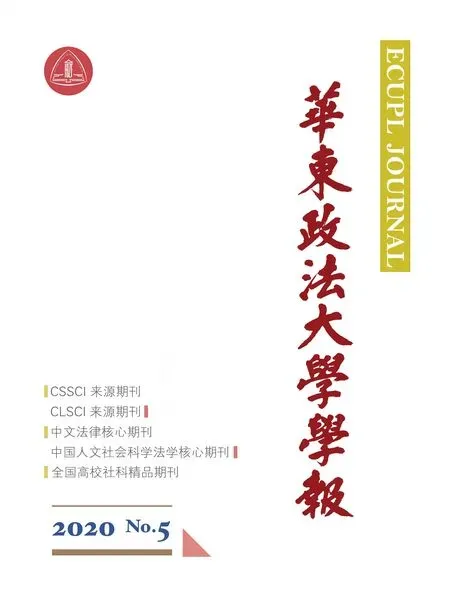《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起草过程、规范含义与解释实践
刘海林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法是一部全国性法律,也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作为全国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具有抽象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宪制性法律,基本法由作为有权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必要时进行解释,是推动基本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保障。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实施中涌现出来的法律问题很大一部分都和基本法解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作为规范基本法解释的主要条款,集中体现了香港普通法制度和原则与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衔接与融合。
基本法实施以来,香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时地解释基本法,解释对象既包括基本法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也包括非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针对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作出过五次释法,〔1〕解释的条款包括《香港基本法》第22 条第4 款和第24 条第2 款第3 项、附件一和附件二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第53 条第2 款、第13 条第1 款和第19 条以及第104 条。解释的条款均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在这五次释法中,有四次释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只有第四次释法由于涉及作为国家行为的国家豁免原则的适用而由香港终审法院主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是两种法律解释制度首次主动实现衔接,是基本法起草者所设想的基本法解释机制的应然运行状态。因此,这次释法被认为是香港终审法院积极履行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有利于基本法的正确理解和贯彻实施。〔2〕参见《全国人大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解释草案举行发布会》,来源: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document/995102/995102.htm,2020 年5 月25 日访问。
随着基本法实施的不断深入和基本法解释实践的不断增多,围绕基本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学术讨论和研究愈益丰富。从研究主题来看,内地学界的现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研究基本法的解释体制及两个释法主体释法权力的性质、地位及相互关系,从而证成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正当性;另一类则是研究基本法的解释方法、程序和技术,从而说明解释权冲突的现状、根源及其化解。从学术史角度看,学界讨论的主题曾经历了从“基本法解释权”和“基本法解释体制”到“基本法解释机制和解释原则”的转向。综观已有研究,反映立法者意图的基本法解释条款的起草过程并没有获得深入考察。
讨论基本法解释有关问题,首先就要全面地理解基本法的规范含义与立法原意,而理解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规范含义,首先需要了解记载该条款形成过程的权威立法资料,从起草委员会讨论这一条的具体过程中把握规范体系的原意与精神。〔3〕参见韩大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 条的形成过程及其规范含义》,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1 期,第15 页。香港回归以来,围绕《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产生的相当一部分争论是缘于脱离基本法文本,对《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立法原意的误读,以及香港法院未能适应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转变,在解释基本法过程中脱离宪法,从而做出违背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的解释。基于此,本文拟在考察《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起草过程的基础上,阐释其规范含义,并通过分析围绕《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所产生的基本法解释方法之争,试图指出能够有效缓和两种法律解释制度的张力的路径。
二、《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起草过程
要正确理解《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规范内涵和立法意图,有必要详细考察《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起草过程。通过回溯基本法起草者在基本法解释条款的变迁过程中的争论和共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正本清源,化解基本法实施中的争议。
1985 年3 月29 日,彭真在接见港澳记者时指出,“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尚未讨论,我想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为特别行政区是由宪法诞生的,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是由全国人大成立的。”〔4〕《彭真昨谈香港基本法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载《大公报》1985 年3 月30 日第1 版。虽然此时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尚未提上日程,但中央对基本法解释权问题的回应,已经为即将开展的基本法起草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1985 年7 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起草委员会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香港开展咨询活动。此间,针对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条款,香港社会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随后,姬鹏飞在访港期间明确指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解释权理所当然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贯彻执行基本法的过程中有一定解释权的问题将在制定基本法时加以研究解决。”〔5〕《基本法解释修订权理所当然属于人大》,载《大公报》1985 年12 月22 日第4 版。这为后来的基本法解释条款的草拟指明了基本方向。〔6〕香港基本法起草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1985 年7 月至1986 年4 月);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1986 年5 月至1988 年4 月);基本法草案形成阶段(1988 年5 月至1989 年1 月);从基本法草案到通过阶段(1989 年2 月至1990 年4 月)。参见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50-552 页。
(一)第一阶段:香港法院获得解释基本法的有限授权
1986 年4 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结构(草案)》,初步确定了《香港基本法》的大纲,但此时尚未形成基本法解释条款的雏形。尽管如此,在此次会议上部分起草委员还是提出建议,希望未来的基本法解释条款能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较大的解释权力和解释范围,特别是涉及特区的内政事务上。〔7〕参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部分起草委员对基本法结构(草案)的意见》,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9 页。随后,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具体负责草拟基本法解释条款的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专题小组提出了该条款的初稿,共有三款内容。〔8〕该条初稿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中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对基本法的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引用该条时,即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参见《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的工作报告》,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14、15 页。其中,第1 款规定原封不动地被基本法的正式文本所采纳,因为这样的规定严格遵循了中央一直强调的符合宪法的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属于中央权力等原则要求。第2 款明确了香港特区法院可以对“基本法中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但同时也把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的范围限定于“基本法中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而对于自治权范围之外的条款,香港法院无权解释。根据第3 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所有条款都可以作出解释。对于有关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香港法院虽有解释权,但其最终解释权仍归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由此可见,在基本法解释条款的初稿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得到全面体现,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范围则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专题小组内部对第2 款内容也存在保留意见,有的委员认为香港法院的解释范围可不限于“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9〕参见《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的工作报告》,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15 页。
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专题小组并未对有关基本法解释的条款作任何调整,因为起草委员的意见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有的委员认为,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上是无可否认的,但第2 款规定香港法院只可以解释“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是不必要的。因为既然基本法的所有条款都是香港的根本法,香港法院在有必要时应该都有解释权,所以“自治权范围内”的限制可以考虑删去。并且,如果香港法院的解释是错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最后的解释进行纠正。有的委员则认为,规定香港法院对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是必要的。因为基本法不是一个纯粹地方性法律,它规定了许多有关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内容,如果完全由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进行无限制的解释,那么这解释不但影响香港,而且可能影响到全国,因此这是欠妥的。而且在香港回归后,香港终审法院有终审权,其判决为最终判决。如果香港法院审理的涉及国防、外交及中央管辖的事务的案件不正确,将无法得到纠正。〔10〕参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委员们对基本法序言、总则及第二、三、七、九章条文草案的意见汇集(1987 年5 月22 日)》,第31-34 页。
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专题小组提出的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条款仍未发生变化。因为解释权的问题比较复杂,起草委员们提出的各种方案都还不够成熟,尚需要作进一步研究。〔11〕参见《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的工作报告(1987 年8 月22 日)》,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7-9 页。不少委员尝试在两种对立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折中意见。例如有的委员认为,香港法院必须有权解释基本法,没有解释就无法审理案件;在自治范围以内的条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将解释权授予香港法院;在自治范围以外的条文,香港法院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12〕参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委员们对基本法序言和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章条文草稿的意见汇集(1987 年9 月2 日)》,第74-77 页。有的委员认为可以将第2 款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中有关该案的条款进行司法解释,其解释不影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的最后解释权。”〔13〕《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的工作报告(1987 年8 月22 日)》,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2 页。这样既赋予了香港法院对基本法所有条款的解释权,又维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终解释权,获得了专题小组的认真考虑。
(二)第二阶段: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授权获得拓宽
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专题小组提出的草稿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14〕参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各专题小组拟定的各章条文草稿汇编》,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76 页。
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对基本法的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引用该条时,即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的条款进行解释。如果案件涉及基本法关于国防、外交及其他由中央管理的事务的条款的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对案件作出终局判决前,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由上可知,原第3 款内容被前移至第2 款,同时增加一款内容作为第3 款。第3 款规定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所有基本法条款进行解释,取消了原来规定的仅可以对“自治范围的条款”进行解释的限制,解释范围得到极大拓宽。但同时要求香港法院对“基本法关于国防、外交及其他由中央管理的事务的条款”的解释在终局判决前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对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构成了一定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第3 款规定的香港法院的提请解释机制并不影响第2 款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何时候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对香港法院均具有拘束力。
1988 年4 月26 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整理出了《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该稿中关于基本法解释的条款较前一稿未作变动,但也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15〕例如,有的委员建议“香港法院可以对基本法的所有条款进行解释”,“针对基本法中关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全权进行解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各专题小组的部分委员对本小组所拟条文的意见和建议汇辑》,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102 页。
(三)第三阶段:香港法院获得解释基本法的高度授权
自《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咨询委员会的配合和协助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征询意见工作。随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专题小组对基本法解释条款再次进行了重要修改。一是,将《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69 条第2 款“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由于此项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涉及的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不作解释,扩大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二是,根据第169 条第3 款,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其条件必须是该条款的解释“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及只能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从而使得香港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不致太多。〔16〕参见《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专题小组对条文修改情况的报告(1989 年1 月9 日)》,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1989 年1 月,第8、9 页。
(四)基于《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起草过程的总结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围绕基本法解释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讨论,其核心议题是基本法解释权配置和解释机制问题,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是否享有基本法解释权,解释权范围如何界定以及有权主体如何解释基本法。梳理基本法起草过程可知,起草委员会就有关基本法解释的条款的讨论在前期主要集中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配置,特别是香港法院的解释权范围问题,后期则主要集中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的衔接与协调。
基本法起草伊始,起草委员针对基本法解释权的配置的分歧很大,有的委员认为基本法主要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因此应当采取普通法的办法,将基本法的解释权全部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17〕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法律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专责小组编:《基本法解释及修改权最后报告》,1987 年3 月14 日。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67 页。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终没有采纳这种意见,因为这不符合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我国宪法规定,解释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但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香港特区将保留普通法制度,按照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惯例,法律又是由法院解释的。基本法的条文如何设计才能既符合宪法的规定,又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使两种不同法律制度的根本矛盾在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中能得到协调和统一,〔18〕参见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7 页。是起草委员会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经过长期讨论、广泛咨询和反复修改,最终在1990 年提出了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从而既保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又有利于香港特区行使其自治权,既可使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的理解有所依循,又不致由于不准确的理解而作出错误的判决。〔19〕参见姬鹏飞:《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有关文件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0—1991 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版,第83 页。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正式文本并未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的程序机制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了秉持普通法思维的部分人士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享有主动解释基本法的权力的质疑。事实上,在基本法起草前期,该条款一直包含“全国人大常委会如对基本法的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引用该条时,即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这一规定,并且该规定被置于第1款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后,这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是在基本法起草后期,为了扩大香港法院对基本法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的解释权,上述规定被后移至第3 款规定中,成为香港法院提请释法的机制的一部分。
此外,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解释基本法时所采用的解释原则和方法的冲突,可能引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衔接机制失灵的问题,基本法起草者并未进行深入讨论,基本法条文亦未作规定。〔20〕参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法律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专责小组编:《基本法解释及修改权最后报告》,1987年3月14日。这是回归以后学界和实务界围绕《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规范阐释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规范含义
《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共有四款规定,其中前三款内容主要涉及基本法解释权的配置和有权主体的解释权的衔接,第4 款规定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前置征询机制。与前三款相比,第4 款规定的含义简明而具体。基本法解释实践中的争议主要围绕第158 条前三款规定展开,因此下文将重点探讨第158 条前三款的规范含义。
(一)第158 条第1 款的规范含义
在《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的草拟过程中,只有第1 款在起草之初便已确立,此后再未发生变动。因此,第158 条第1 款在立法目的上具有确定性和相对独立性,其规范含义不受第158 条的其他规定的影响,因而可以不用结合第158 条的其他规定进行理解和阐释。
1.基本法解释权的归属
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规定符合宪法规定的法律解释体制,并且这一规定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始终成为讨论其他各款内容的基础和前提。第1 款规定中的“属于”一词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解释基本法的主体的唯一性,基本法解释权被一般性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和尊重普通法传统的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将基本法解释权授予香港法院。基本法这种并未直接将基本法解释权授予香港法院,而是由全国人民大会将基本法解释权授予香港法院的制度安排,是协调两种法律解释制度的结果,也是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发生效力的重要体现。
第1 款规定中的“属于”一词还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对基本法的全面解释权。在“刘港榕案”中,曾有意见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可以在香港终审法院依据《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第3 款提请释法时才可以解释基本法,但终审法院并未接纳这种意见,而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普遍和无条件限制的。在该案中,梅师贤法官在补充意见中明确指出,《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依照《宪法》第67 条第4 项的规定,订明基本法的全面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1〕刘港榕及另外16 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FACV10&11/1999.这通过上述基本法起草过程的考察也可得印证。
2.基本法解释权规范的根本依据
《香港基本法》第11 条第1 款规定,根据《宪法》第31 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这说明,基本法规定的在香港特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符合《宪法》第31 条的精神,〔22〕参见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88-90 页。为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区别于宪法规定的有关制度提供正当性支持。其理论逻辑是,“香港特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为依据乃是宪法第31 条的授权,是宪法同意这样做的”。基本法在宪法允许的情况下,对宪法作了许多变通规定。〔23〕参见许崇德:《简析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载《中国法学》1997 年第3 期,第23 页。亦可参见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63 页。但有关基本法解释的条款显非如此。第158 条第1 款的条文并未进行有别于宪法规定的法律解释体制的设计,而是严格遵循了宪法规定的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否定了部分起草委员和香港社会曾经提出的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香港法院的意见。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基本法解释权的根本依据是宪法第67 条第4 项。
(二)第158 条第2 款的规范含义
第158 条第2 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由《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可知,在基本法起草后期,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为了扩大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而对基本法草稿中的原规定作了重新草拟,形成了上述第158 条第2 款规定,而基本法草稿中的原规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的条款进行解释”。从“可以……解释”到“授权……自行解释”,关于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的第158 条第2 款的规范含义发生了根本变化。
考察第158 条第2 款中“授权”的含义,不得不首先考察整个《香港基本法》中“授权”的含义。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国奉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因此,特别行政区拥有的权力是高度自治权而非主权意义上的绝对权力,高度自治权由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基本法本质上是一部授权法,从基本法文本来看,基本法条文中有大量授权条款。在立法技术上,这些授权规范具有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有不包含“授权”字样的授权规范,〔24〕例如,在《香港基本法》“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一章,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也有直接明文规定“授权”的授权规范。〔25〕《香港基本法》文本中共有13 处出现“授权”表达。不考虑不包含“授权”字样的授权规范,仅从直接明文规定“授权”的授权规范看,基本法中的“授权”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某项权力本来归属于中央,经由基本法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由基本法对中央的权力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间进行再分配,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行使权力而无须经中央再具体授权,中央一般不行使已经授予出去的权力,也不得撤回授权,除非修改基本法。〔26〕《香港基本法》第2 条关于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的规定,即属此类。二是,基本法规定中央可向特别行政区具体授权,中央拥有是否授权以及如何授权的决定权,也可以收回已经授予出去的权力。〔27〕《香港基本法》第20 条关于中央可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他权力的规定,即属此类。很明显,第158 条第2 款中的“授权”具有上述第一种含义。此外,第158 条第2 款中的“自行”一词表明,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可按照普通法原则进行解释。
(三)第158 条第3 款的规范含义
第158 条第3 款共有四句规定,第一句涉及香港法院对基本法关于特别行政区非自治范围内的条款的解释权,后三句涉及香港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机制,包括香港法院提请释法的要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依香港法院的释法提请而作出的解释的效力。除了最后一句“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的含义较为明确外,该款内容中的其他每句规定都曾因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引发争论。例如,针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的规范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终审法院曾经就作出了不同的理解。相比之下,该款规定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和“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尚未得到充分的规范阐释。对此,下文将做出一些尝试。
1.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非自治条款的主动解释权
《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并未直接规定,在香港终审法院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不提请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主动解释基本法,但这并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必要时主动解释基本法。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来就享有主动对基本法关于特别行政区非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的权力。〔28〕在“刘港榕案”中,资深大律师张健利认为,除非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司法提请,否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主动对基本法作出解释。当然,这种观点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因而也不为香港终审法院所认同。参见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刘港榕及另外16 人,FACV 10&11/1999.《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该条第1 款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在第2款接着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如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据此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所有条款都可以主动进行解释。但后来经过向社会征求意见,为了扩大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基本法(草案)》将原第2 款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不主动解释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但是,第3 款第1 句规定“香港法院对基本法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也可”一词表明,与自治范围内条款不同,香港法院对于非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虽然有解释权,却不可以“自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对非自治范围内的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和主动解释权。
2.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
从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条款的变迁可知,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范围经历了从受高度限制到获高度授权的转变:从香港法院仅限于“对基本法中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且不享有最终解释权,到“可以对基本法的条款进行解释”但不享有最终解释权,再到“对基本法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和“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针对基本法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虽享有全面解释权,但在具体行使时会基于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而一般不再解释,由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自行解释;针对基本法关于特区自治范围以外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主动进行解释,但为了尊重普通法地区的法院享有法律解释权的传统,而授权香港法院“也可”进行解释。因此,香港法院对基本法全部条款都具有解释权,香港法院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体现了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和对普通法制度的尊重。
3.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的效力
第158 条第3 款第3 句规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终审法院的提请释法而对基本法作出的解释,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动释法对香港法院是否有约束力,基本法并未做明确规定。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一次主动释法中即已明确,“本解释公布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时,应以本解释为准”。〔29〕《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9 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第214 页。香港终审法院在后来的“刘港榕案”“吴小彤案”等案件中也一再申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 条第1 款作出的解释对香港法院具约束力”。
香港终审法院尽管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但并不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过程中所使用的解释原则或方法亦具约束力。其认为,解释法律是法院的职责,在解释基本法时,其必须引用在香港发展的普通法。香港法院根据普通法解释基本法时的任务是确定法律文本表达的立法原意,而并非仅确定立法者的原意。〔30〕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庄丰源,FACV 26/2000.由此,在实践中,第158 条第3 款规定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的含义并不包含香港法院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原则或方法为准。
香港高等法院原审庭在立法会议员违法宣誓案(亦称“梁游案”)中指出,“《宣誓及声明条例》的有关条文在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的解释影响下而作出适当诠释,其意思及法律效力也与《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的含义相同”。针对当事人主张的香港法院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所作的解释的约束,法院称“有没有该解释,法庭得出的结论都一样”。〔31〕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and another v. Yau Wai Ching and others,HCMP 2819/2016.因此,香港高等法院既未回应人大解释的效力问题,也未直接依据人大解释作出判决。胡锦光教授认为,香港高等法院在对基本法非自治条款进行解释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已进行解释,香港高等法院则没有必要再作出解释,应当直接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作出裁判。此次香港高等法院在判决中故意不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而又作出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判决,这一做法违背了基本法的规定。〔32〕参见胡锦光:《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2 期,第67 页。对此,香港终审法院在本案终审中作出纠正,依据人大解释作出了判决。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香港法院是有约束力的。〔33〕梁颂恒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律政司司长,FAMV 10/2017.由此可知,第158 条第3 款规定的“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应该理解为香港法院在以后的案件审理中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裁判依据。
四、《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方法论之争及其化解
伯恩·魏德士说,任何法律适用者都应该注意,方法问题是宪法问题,它们关系到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分立。在解释宪法与法律的时候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对被解释的规范的内容具有很大的影响。〔34〕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04、305 页。作为享有基本法解释权的主体,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方法上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基本法规范的内涵和最后的司法判决,这不仅会影响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权和其他权力分支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随着基本法的正式实施,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开始不时解释基本法的有关条款。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原有的司法制度和原则得以延续,这包括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等。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仍然依循普通法的解释原则和方法,这与内地所秉行的法律解释原则和方法存在根本差别。在案件不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事务或者中央管理的事务,而仅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时,两种解释思维和解释方法的差异性可能并不会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关系产生很大影响,但案件一旦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两种法律制度的隔阂与对立的态势则逐渐显现。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终审法院在解释方法上的互动
回归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行使基本法解释权过程中的首次直接互动乃是缘于“吴嘉玲案”。〔35〕虽然马维騉案的核心议题之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所成立的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问题,其本身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但由于香港高等法院最后在判决中作出了临时立法会合法的判断,最后并未引发可能出现的宪制危机。在“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在解释有关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的基本法条文时,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其所坚定遵循的普通法的解释思维和解释原则。在“吴嘉玲案”终审判决作出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释法作出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澄清了《香港基本法》相关条款的立法原意,并且明确指出,终审法院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从而引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动释法。〔36〕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指出,终审法院1999年1 月29 日的判决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该有关条款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终审法院在判决前没有依照《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第3 款的规定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而终审法院的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故决定释法。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根据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37〕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并非仅运用原意解释这一种解释方法,也会在必要时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但在基本法解释方法问题上,原意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强调的解释方法,也是与普通法解释原则相对的内地法律解释方法的标志。
在2004 年有关政改问题的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出,按照基本法附件一第7 条中“如需”修改的立法原意,如果2007 年以后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立法会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不作修改的情况下,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理应适用附件一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规定;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理应适用附件二关于第三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规定和附件二关于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的规定。〔38〕参见李飞:《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4 年第4 期,第268-270 页。在2005 年有关行政长官任期问题的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指出,按照立法原意明确行政长官缺位后产生的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为原行政长官未完成的剩余任期,使得在2007 年香港特区可以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循序渐进地发展香港的民主,从而逐步创造条件向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迈进。〔39〕参见李飞:《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5 年第4 期,第304-306 页。
在2016 年有关议员违法宣誓问题的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引述邓小平对“爱国者”的标准的定义指出,在《香港基本法》具体条文起草过程中,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的原则与香港通行的就职宣誓制度结合起来产生了《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香港基本法》颁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其制定的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临时立法会等的产生办法中,都规定行政长官参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必须拥护《香港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这也说明,对于《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规定的“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中央一直理解为既是依法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40〕参见张荣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 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6 年第6 期,第1058-1061 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运用原意解释方法对《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作出了诠释。〔41〕肖蔚云教授曾指出,虽然在基本法条文字面上并没有出现“爱国者”一词,但从基本法许多内容和立法原意上却充分体现了“港人治港”应以爱国者为主体的内容,基本法专门写了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等都要依法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包含了爱国爱港的意思,是邓小平同志主张的体现。肖蔚云教授还指出,基本法的起草高度依赖对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的反复学习、研究,基本法文本体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精神。参见肖蔚云:《全面理解基本法立法原意》,载香港《大公报》2004 年3 月16 日。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次释法所采纳的解释方法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尊重基本法文本的字面含义,同时也强调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宗旨和精神,反对将基本法的文字表述和立法原意、宗旨割裂开来。〔42〕参见肖蔚云:《论实施香港基本法的十项关系》,载肖蔚云、饶戈平主编:《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三年实践》,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6 页。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终审法院在阐释其解释基本法的原则和方法时也声称,法院解释法律的任务是诠释法律文本所用的字句,以确定这些字句所表达的立法原意。但其又明确指出,立法原意不同于确定立法者的原意,法院的工作并非仅是确定立法者的原意,而是要确定所用字句的含义,而在这过程中需要考虑该条款的背景及目的。〔43〕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庄丰源,FACV 26/2000.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强调对立法原意的尊重,但二者对立法原意的理解和探寻立法原意的方法可谓均大相径庭。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数次释法对立法原意解释方法的强调,并未促使香港法院在以后的案件中削弱对普通法解释原则的坚持。
在“庄丰源案”中,香港终审法院首先认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 年针对基本法有关条款所作的解释对本案所涉第24 条第2 款第1 项的解释不具有约束力。但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已经明确,《香港基本法》第24 条第2 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 条第2 款的意见》(下称《筹委会意见》)中,特区政府希望香港法院能够基于普通法解释原则的灵活性将《筹委会意见》纳入考虑,从而正确诠释第24 条第2 款第1 项的含义,但香港法院通过“内在材料”和“外来材料”的区分及基本法“制定前的材料”和“制定后的材料”的区分这些技术手段,排除了对体现基本法立法原意的《筹委会意见》的参考适用,而是将基本法其他条款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规定作为“有关条款的背景及目的来诠释文本字句”。〔44〕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庄丰源,FACV 26/2000.在后来的“外佣居港权案”中,特区政府再次指出,《筹委会意见》作为“外在材料”对理解案件所涉条款的立法原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香港终审法院坚称,《筹委会意见》对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没有约束力,从而拒绝通过《筹委会意见》去考察基本法相关条款的立法目的。〔45〕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v.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and Another,FACV 19/2012.
(二)香港法院普通法解释方法的理论基础
鉴于香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坚持普通法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强调客观解释的立场而回避原意解释方法,有学者将这种法律现象形容为基本法的“普通法化”。〔46〕参见林来梵、黎沛文:《反思香港基本法的“普通法化”现象》,载《明报》2016 年4 月12 日。基本法是一部成文法,基本法的“普通法化”的实质就是成文法的“普通法化”。普通法地区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关注成文法如何规定,又重视成文法律应当如何规定。也就是说,通过目的解释、遵循先例等普通法原则,香港法院可以在法律解释中对制定法进行实质改造并将其纳入普通法。
这种法律现象的存在并非缺乏正当性基础。从道德基础看,基于保护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正义观念,香港法院对于基本法关于人权和自由保障的条款通常选择宽松的和目的性的解释,在探寻立法目的时即使选择参照《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外来资料,也不选择能够反映立法原意的权威性历史文件。这也是香港法院在系列居港权案件中面对判决可能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坚守普通法解释原则的主要原因。从法律传统看,基于立法意图的可及性、法律确定性等因素,普通法对使用外在材料作为法规释义的辅助资源一向持较为疏远或拒斥的态度,香港普通法沿袭了这种司法传统。〔47〕参见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使用外在材料作为法规释义的辅助工具》,来源:https://www.hkreform.gov.hk/chs/publications/rstatutory.htm,第36-46、52、53 页,2020 年6 月25 日访问。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不唯在香港地区存在,在其他普通法地区也较为常见。〔48〕参见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使用外在材料作为法规释义的辅助工具》,来源:https://www.hkreform.gov.hk/chs/publications/rstatutory.htm,第146 页,2020 年6 月25 日访问。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先生曾在向内地介绍香港普通法时指出,普通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适应性和弹性,普通法能够因应环境情况而调节改变。〔49〕参见马道立:《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一名香港法官的个人意见》,在北京国家法官学院所作的演讲辞(中文译本),来源:https://www.hkcfa.hk/sc/work/engagement/index.html,2020 年6 月25 日访问。在解释作为宪制性法律的基本法的规范上,普通法的这个特征更为明显。因此,普通法解释方法并不等于就是客观目的解释方法。一方面,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会选择采用多种解释方法,而非固守某一种解释方法。〔50〕参见王千华:《香港基本法研究中的普通法和大陆法问题》,来源:http://basiclaw.zijing.org/2017/0103/726238.shtml,2020 年6 月11 日访问。这是普通法地区的法院在法律适用中解释法律的常见现象,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地采用多种而并不一致的法律解释方法,由此也缺乏能够精确描述法院如何适用法律的法律解释理论。〔51〕参见[加]杰夫·霍尔:《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普通法方法的胜利》,李明倩译,载《法律方法》第23 卷,第37、38 页;[美]安东宁·斯卡利亚:《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蒋惠岭、黄斌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18 页;D.A.S Ward, “a criticism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in the New Zealand courts” New Zea land Law Journal 293 (1963).另一方面,原意解释方法在普通法系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确定制定法规范的含义时较为寻常地将诉诸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作为解释原则。〔52〕参见[美]安东宁·斯卡利亚:《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蒋惠岭、黄斌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43 页。
尽管存在不少对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方法的质疑和批评,香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仍旧坚持普通法司法传统。〔53〕有学者认为,此举是为了避免司法的自主性和以普通法为基础的香港法律制度受到侵害。参见陈弘毅、罗沛然:《香港终审法院关于〈基本法〉的司法判例评析》,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 年第3 期,第96 页。因此,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只要“一国两制”原则保障香港法院依据基本法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它就有足够的自由决定其所采用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并为其所欲采用的解释原则和方法作出合理化论证。〔54〕参见[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议会立法、法条解释、先例原则及法律改革》(第6 版),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14 年版,301、302 页。回归以来的香港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香港基本法》的合宪性解释
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款共做出过五次解释,只有第一次和第五次是因应香港法院审理的有关案件而主动作出的,其他三次释法或不涉及司法案件,或是应香港法院提请释法而作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针对基本法关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法院的两次主动释法,其解释客体也都是基本法关于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
笔者认为,法律解释制度和方法的差异性是两地法律和司法制度差异性的组成部分,是“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体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应当适度包容两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摩擦和冲突。这种适度包容应以不影响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为界限;一旦超越这一界限,为了维护宪制秩序的稳定,解释原则和方法的冲突必须得到防范和弥合。为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和尊重两种制度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须审慎、克制行使全面解释权,而香港法院亦有宪制责任防止或减少基本法解释权运行冲突的产生。当在不影响香港司法制度的独立运作和不减损香港法治的前提下能够通过调整解释原则和方法避免解释权运行冲突时,香港法院更应当积极履行这一宪制责任。
宪法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55〕参见胡锦光、刘海林:《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变迁及其意义》,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第8 页。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不能脱离宪法,不能一味坚持运用普通法的解释原则和方法,而导致法院的解释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冲突的情况出现。例如,香港终审法院曾在“吴嘉玲案”中通过解释宪法有关条款最后得出了“特区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去审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这一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的结论。〔56〕吴嘉玲、吴丹丹诉入境事务处处长,FACV 14/1998.
香港法院在适用基本法时,必须正确理解基本法的规范内涵,而这就有必要从宪法层面理解基本法,否则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基本法的含义,特别是在基本法的含义存在分歧时,就更需要从宪法的层面上理解基本法。在解释《香港基本法》的过程中,香港法院应当对基本法进行合宪性解释,也就是说,基本法的解释也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指导,当通过原意解释、目的解释等不同的解释方法而使基本法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时,应尽可能选择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法。〔57〕参见韩大元、张翔:《国家意识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研究》,载饶戈平、王振民主编:《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论丛》(第1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 页。
五、结语
基本法凝聚着基本法起草者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基本法文本是基本法起草者达成广泛共识的体现,也是基本法起草者综合权衡各种社会意见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基本法实施中出现的大多数法律问题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都已经获得基本法起草者的广泛讨论和充分思考。因此,要解决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应当回归基本法文本,考察基本法相关条款的规范内涵,寻求法理上的共识。基本法解释权和解释机制的相关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基本法文本的规范阐释获得理论解答。《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对基本法解释所作的制度安排,正是基本法起草者在反复权衡各项因素后对内地和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衔接的结果,是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制和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的相互融合在基本法上的最直接体现。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新宪制秩序下,有必要从宪法出发去认识《香港基本法》第158 条对基本法解释有关问题所作的制度性安排,也有必要通过确立基本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原则去缓和基本法解释实践中的解释方法的冲突。推动围绕基本法第158 条所形成的基本法解释机制的良性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基本法解释制度维护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作用,从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