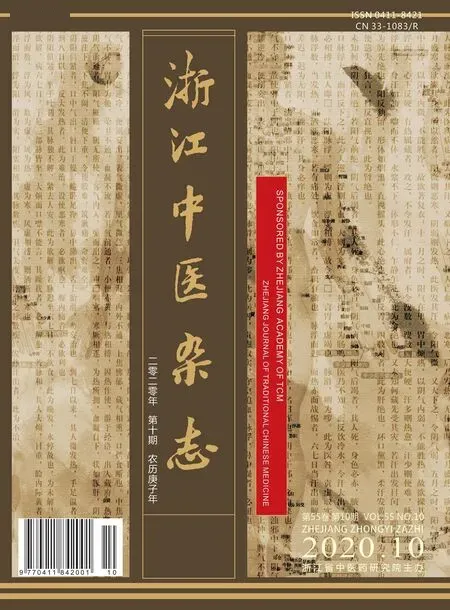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
李佳嘉 夏鳌安 余 谦 汪紫虹 李如辉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是中医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探讨者甚众,本文尝试从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这一崭新的角度,力图将有关认识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推向新台阶,以冀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离、合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理性依据。
1 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存在着特殊性
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迄今最为经典且最具权威的论述当推恩格斯,“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1]。就原子论哲学与西方自然科学而言,正如童鹰所说:“由于原子学说的复兴,原子学说中所包含的微粒思想和其他思想,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整个近代科学发展时期,便成为孕育出近代各种科学理论的思想土壤。”[2]在这里,哲学是作为一种思想背景因素通过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的指导而发挥其支配作用的,是“隐藏”在特定自然科学理论形态背后的强大的思想力量,其作用形式是深藏不露的,甚至于是潜意识的,因而,其影响只有透过自然科学理论的具体表述本身进而把握其理论实质的层面上才能得到体认与窥视。鉴于这一观点的普遍意义并广为接受,笔者称其为“哲学对自然科学影响的共性原则”(以下简称“共性原则”)。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学科主体属性为自然科学)的关系,毫无疑问地遵循并体现着“共性原则”,透过中医理论具体表述层面,人们无不为其背后浓重的中国古代哲学精神而感叹,中国古代哲学同样也曾作为一种思想背景因素通过为中医学研究提供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的指导而发挥其支配作用,是“隐藏”在中医学理论形态背后的强大的思想力量。正如印会河所说:中医学“用当代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3]。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又绝不局限于“共性原则”,因为,人所共知的中医学理论浓重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色彩又是显在的,普遍见诸于理论表述层面。中国古代哲学既是“隐藏”于中医学理论形态背后的决定医学精神实质与方向的“无形观念”,又是显在地将其自身的概念、原理、结论等直接地编织于中医学理论具体表述的网络中,并最终固化成为中医学“理论之网”上的“绳线”与“纽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这一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存在着特殊性。
2 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特殊性的具体体现
以原子论哲学及其对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的影响作为参照系,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哲学概念成为中医学“理论之网”上的“纽结”:中医学概念赖以发生的途径是复杂的,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与改造,就《黄帝内经》一书所见,如精、气、形、神、阴阳、五行等与中医学自身实践而发生的概念相嫁接便产生了大量新的医学概念,于此,李如辉等[4]已有详论,恕不赘述。而后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哲学概念继春秋战国秦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渗入医学领域,体用、升降、气机、气化等在宋明医籍中更是屡见不鲜。
尽管道尔顿也曾经直接将哲学的原子概念迁移到化学领域,创立举世闻名的化学原子论,“如果说,古希腊原子论还是一种哲学理论的话,那么道尔顿的化学原子论则完全是一种科学理论了”[5]。但这在西方科学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事例了。
由此,“大量的哲学概念涌入医学理论中”[6]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之一。
2.2 哲学理论成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除了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外,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乃中医学进行说理的无法取代的工具,“运用哲学原理对医学问题进行广泛的说明”“把哲学观念作为医学理论的体系构架”[6]。
反观西方科学史,尽管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尝试,如波义耳就曾“试图以原子学说来解释化学反应”[2],但并没有获得成功,更不用说理论体系的构建。可见,作为中医学说理工具的中国古代哲学则是其对中医学影响特殊性又一内容。
2.3 哲学理论成为中医学理论发生的推理前提:在中国古代哲学天人一气、天人一体、天人一理等命题下,执哲学命题推导出中医学的某些具体的理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于是,“援物比类”在中医学理论构建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人右眼不如左眼明”、心化赤为血、心包络“代心受邪”、肺气“肃降”、脾主升清、脾为后天之本等理论无不藉此途径而发生。于此,李如辉等[4]曾有一文专论,故从略。
西方科学史上虽然也能看到诸如此类的运用,如布鲁诺在1584年以后发表的基本著作中,也曾从天体与人体的类比中,以行星绕日的循环运动提出过人体中的血液循环的猜想[7]。但由于在原子论哲学内部找不到逻辑支撑,这种运用从来不曾被看作是顺理成章的,受制于此,故难以得到发展。
众所周知,中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便形成了理、法、方、药为构成要素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较之西医学明显是“早熟”了。无独有偶,在梁漱溟[7]先生看来,中国古代哲学同样有着“早熟”的特征,史实也确实如此。中医学的“早熟”现象堪称世界科学技术史之奇迹,而造就这一奇迹的,除了先贤们在医学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材料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早熟”的中国古代哲学,其中,尤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代表。综合前文三点不难看出,倘若没有“个性殊强”[7]与西方哲学“适成一种对照”[8]的中国古代哲学,倘若没有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形式,编织中医学“理论之网”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概念(“纽结”)不足与叙述工具(“绳线”)缺乏的困境而落空。如果说哲学概念成为中医学“理论之网”上显在的“纽结”,有效地克服了由于医学实践的有限所衍生的概念数量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哲学理论成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成功解决了编织中医学“理论之网”的“绳线”问题,那么,哲学理论成为中医学理论发生的推理前提便是既提供“纽结”又提供“绳线”。于此可知,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早熟”及其对中医学影响的独特形式,为两千多年前编织中医学“理论之网”的努力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条件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2.4 数量可观的医哲“两栖”性质的研究群体:以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深刻性论,当首推道、儒二家,既为道家又为医家、既为儒家又为医家的情形,即道医、儒医“两栖”性质且数量可观的研究群体,又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特殊性的另一个极为突出的标志。兹分述如下。
2.4.1 道、医兼修:习道者大凡兼能明医,《抱朴子·杂应篇》曾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据有关统计,六朝道医占当时全部医生总人数的28.7%[9]。《汉书·艺文志》的“七略”,其中“方技略”又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而房中、神仙都与道术密切相关,占据了中医药文献的半壁江山。而《道藏》收录的医药书籍,占《道藏》内容的70%以上[10]。故自古就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之说,它充分反映了道教“尚医”的历史传统。
2.4.2 亦儒亦医:《图注八十一难经·序》言:“未有通乎医而不通乎儒者也。”纵观中医学的发展,一方面,大儒也多能兼医甚至于通医。《医说·医功报应》云:“季明其儒医之良者也。”《续医说·医书》云:“余近见赵继宗《儒医精要》一书,驳丹溪专欲补阴以并阳,是谓逆阴阳之常经,决无补阴之理。”中医学术群体——儒医,便指有着一定文化素养的医者,或宗儒、习儒的医生和习医业医的儒者。
一方面,如皇甫谧、张洁古、朱丹溪、滑寿、高武、李中梓、汪昂、薛雪、刘完素、李时珍、喻嘉言、吴鞠通等均为弃儒从医而在中医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名家。《格致余论·序》云:“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另一方面,历代大医也不乏大儒,“医圣”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皇甫谧曾多次受到晋武帝召见授官,然其辞请不就而执意从医;孙思邈,《旧唐书》称其“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在当时即享有盛名。
西方医药学尽管也存在有医哲“两栖”性质的学者,如阿拉伯炼金术的主要代表人物贾比尔·伊本·海扬是一个与陶弘景一样的药学家和医学家。贾比尔的继承人、另一个著名的炼金术士士拉泽同样也与中国炼丹家一样兼通药学与医学。而阿拉伯炼金术、医学与哲学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阿维森纳同样也具有中国炼丹家的特色。[2]但该性质的群体在西方医学史上较之中医学在数量上、影响上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
3 结论
综上,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是一个真实命题,这对于挣脱以“共性原则”论哲学对自然科学影响的单一、狭隘的思维陷阱,克服以“共性原则”抹杀“特殊性”的弊端,对于理解并认同文化哲学、科学、医学的多样性、多元性、多形态性等具有普遍价值。②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其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使得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构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努力获得了成功。③独特形态的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赋予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独特的理论形态。④中医学理论的临床实效,为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影响的特殊性的价值提供了终极依据,这将强有力地引导对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积极的评价,而不是相反。主张将哲学与中医学进行剥离等观点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