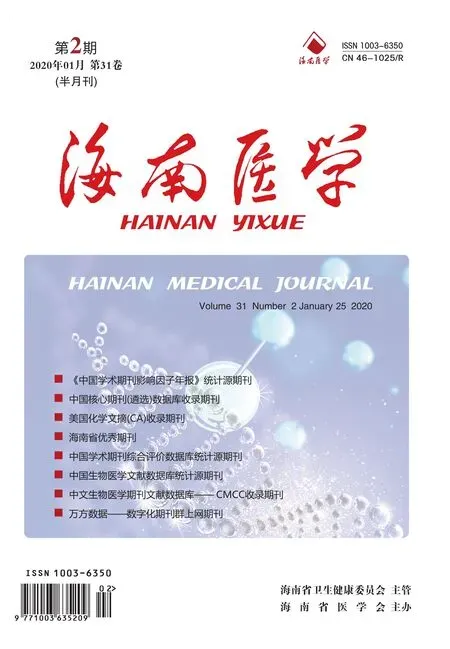急性胰腺炎近十年针刺治疗研究进展
李淑娜,李义
遵义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贵州 遵义 563000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指由多种病因引起胰酶激活,导致胰腺局部炎性反应发生,可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改变[1]。临床上表现为急性、持续性腹痛(偶无腹痛),多数患者血清淀粉酶活性增高≥正常值上限3倍,可存在胰腺形态改变,总体死亡率为5%~10%[1-2]。临床上常用的西医基础治疗包括禁食、胃肠减压、给氧、维持电解质酸碱平衡、抑制胰液分泌、应用抗生素等。中医在AP急性期予以疏肝解郁、清热化湿、通腑泻热、祛瘀通腑、回阳救逆;缓解期予以疏肝健脾、益气养阴等[3]。但单纯西医治疗或中医治疗都有其局限性,而中西医结合治疗AP已在临床上取得良好治疗效果,成为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法。其中针刺辅助治疗AP在镇痛、促进胃肠蠕动、抑制炎症反应、保护胰外器官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4],且该治疗方法已纳入《急性胰腺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3)》,并沿用至2017年版。但针刺辅助治疗AP在针刺方法、针刺时间及针刺穴位方面仍无较统一的标准,以下对近十年针刺相关研究概况进行了简单总结。
1 针刺疗法
针刺辅助治疗AP常用的针刺方法主要有毫针、电针和水针疗法,这三种针刺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联合使用。2013年AP专家共识意见推荐针灸治疗常用穴有足三里、内关、中脘、胃俞、脾俞、下巨虚、胆俞等,也可酌情选取期门、阳陵泉、血海、合谷等穴以增强疗效[3]。但因临床上患者病情不同,施针者经验、习惯存在差异,故临床选穴不尽相同,治疗效果也有差异。
1.1 毫针疗法 毫针刺法指利用毫针刺入或刺激腧穴经络以防治疾病的方法。足三里穴是毫针疗法辅助治疗AP最常用的穴位之一。在针灸学理论中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具有调和肠胃、通利气机、行气导滞的作用。《针灸大全·四总穴歌》提到“肚腹三里留”,即腹痛应首选足三里穴。另外,《医学入门》也有“腹痛轻者只针三里”的说法。毫针针刺足三里治疗AP在缓解腹痛、腹胀等方面的疗效显著。现代研究发现,西医常规治疗辅以毫针针刺足三里治疗AP不仅可缓解肠梗阻症状、缩短平均住院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而且在降低血淀粉酶、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及白细胞计数方面也有良好的效果[5-6]。另一项研究发现,针刺足三里还可以提高鼻空肠管的置管率,便于早期开展肠内营养,有利于胃肠道功能的恢复[7-8]。除此之外,针刺辅助治疗AP在降低死亡率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证实:刘清红等[9]使用升清降浊针法治疗49例AP患者,发现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针刺上、下巨虚、足三里、阳陵泉、合谷、天枢、大横、关元、丰隆、太冲等穴位辅助治疗AP,不仅可缓解其临床症状,缩短患者住院日,更可以降低AP死亡率。
1.2 电针疗法 电针疗法是以毫针疗法为基础,加以微量低频脉冲电流的一种治疗方法,其主治病症大多与毫针疗法主治病症相同。电针最常用的穴位有足三里、天枢、中脘、下巨虚、内关、胃俞等。《针灸大成》中提到“腹内疼痛,内关、三里、中脘如不愈,复刺关元、水分、天枢”。《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有“大肠病者取巨虚上廉”的记载。此外,《针灸玉龙经》、《玉龙歌》、《胜玉歌》等也有“腹痛兼闭结,支沟奇穴保平安”的说法。但与毫针相比,电针强度及波形可量化,可控性更强,操作也更加便捷,而且产生的治疗与麻醉效应比手针更为有效[10],故近年来电针辅助治疗AP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电针辅助治疗AP在促进胃肠功能恢复、镇痛及促进炎症恢复方面效果显著。有学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实: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予以电针刺激足三里、中脘、合谷、内关、梁丘等腧穴辅助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合并麻痹性肠梗阻,可明显改善患者腹痛、腹胀等肠梗阻体征,促进炎性指标和淀粉酶的恢复,缩短SAP的病程[11-12]。袁雯静等[13]也通过研究发现:电针刺激双侧足三里、内关、中脘、上脘等穴位,配合恒旋磁场治疗SAP可有效缓解疼痛、促进胃肠道蠕动、抑止炎症反应、改善循环并减少SAP的并发症及后遗症。普通针刺足三里、丰隆、上下巨虚、中脘等穴位,合并电针刺激足三里、合谷、下巨虚、支沟,发现针刺治疗AP可明显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缩短住院日并加速患者恢复[14]。而且单纯电针刺激足三里穴、支沟穴也可明显缓解SAP伴麻痹性肠梗阻患者的腹部痛胀情况[15]。除此之外,电针在保护胰外器官方面也有不错的效果。有学者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及“俞募配穴”等理论,通过动物实验证实:电针刺激AP模型大鼠的肺与大肠经俞募穴肺俞、大肠俞、中府、天枢可以促进AP模型大鼠胃肠功能恢复,从而达到防治肺部病理改变的目的[16-18]。
此外,在电针辅助治疗AP有效的基础上,有学者对比了针刺腹部穴位及四肢穴位治疗AP效果的优劣,发现在西医基础治疗上配合电针刺激腹部上脘、中脘、下脘、梁门等穴位配合电针刺激合谷、内关、足三里等穴位都在缓解患者腹痛、腹胀程度及减小腹围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但电针刺激腹部穴位组缓解腹痛的治疗效果更显著[19]。虽然目前临床上很少采用单独针刺腹部穴位或四肢穴位治疗AP的方法,但对于一些不适合腹部穴位与四肢穴位同时针刺的AP患者(如局部皮肤感染、肢体缺如等)仍有一定意义。
1.3 水针疗法 水针疗法指在穴位、经络等部位注射一定量药物,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水针疗法不仅可以刺激穴位并发挥药物的药理作用,由于药液在穴位中存留时间较长,还可以起到增强与延长穴位的治疗功能的作用[20]。水针疗法通常选用周围肌肉组织丰富的穴位,有利于药物的吸收。临床上最常用的穴位为足三里穴、胃俞穴等。穴位注射一般选用具有调节胃肠道功能药物如黄芪、山莨菪碱、甲氧氯普胺、新斯的明等。现代研究发现:足三里注射黄芪、甲氧氯普胺、新斯的明、维生素B1等药物都可促进AP患者肠鸣音恢复,缓解肠麻痹症状,增强AP患者抵抗力[21-26]。胃俞及足三里注射山莨菪碱或甲氧氯普胺,都对AP患者肠功能恢复作用明显,能够有效缩短患者痛苦,减少复发率,加快患者肠功能恢复,对临床治疗AP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7-28]。
2 针药结合
针药结合是指对同一患者、针对同一病症同时予以针灸和药物等治疗措施,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29]。因其在治疗AP中能发挥针刺及药物的双重作用,在改善胃肠动力、镇痛、抗炎、减少AP并发症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已被临床广泛应用。在药物选择方面,中药常采用具有清热化湿,利胆通腑、逐瘀、除满消痞、回阳救逆作用的药物。西药除常规治疗外,常选用具有镇痛、减少胰腺分泌、保护胰腺细胞等作用的药物。
研究发现中药灌肠例如清胰汤、小承气汤、大黄等,配合针刺足三里、天枢、内关、中脘等穴位,可明显缓解AP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促进胰腺形态复原及淀粉酶恢复,降低白细胞计数,缩短住院时间,减少继发感染[30-35]。胡峰等[36]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针刺双侧足三里穴配合大承气汤联合微量生长抑素持续泵入对SAP肠麻痹治疗有较好效果,并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的机率。崔东等[37]发现针刺天枢、大肠俞,配和巨虚、曲池、合谷、腑会、中脘等穴位联合参附注射液静脉输注可明显改善患者肠胃功能,有效缩短腹痛时间、胃肠减压时间,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从而控制其病情进展,总有效率为94.74%。白玉君等[38]通过研究发现针刺胰腺穴、脾俞等穴位配合清府降浊中药汤剂,联合使用奥曲肽治疗AP,可有效改善AP的临床症状,还可避免西药常规治疗的副作用,增强疗效,缩短平均住院日。有学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使用右美托咪定联合电针刺激神庭、足三里等穴位可获得良好的阵痛效果,可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量[39]。新斯的明注射足三里穴联合中药灌肠、胃管内注入或外敷,可有效缩短AP患者腹胀、腹痛时间,促进患者排气、排便,减轻体内炎症反应,减少并发症,提高治愈率[40-44]。
3 针刺治疗AP的机制
中医认为AP多由腑气不通所致,属“胃脘痛”、“腹痛”、“鼓胀”等范畴[45]。脏腑功能失常,气机逆乱,出现气滞、热结、津枯、气虚等,而致胃失和降,大肠传导失利,腑气不通,气聚作胀,胃肠功能受到抑制。针刺辅助治疗AP,具有增强清热解毒、通腑攻下、化瘀止痛、和胃止呕、疏肝利胆等功效[46]。粟多海等[5]采用针刺足三里的方法辅助治疗AP,达到健脾和胃、通腹化痰、升降气机、扶正培元、生发胃气、燥化脾湿等功效,从而改善胃肠的蠕动功能。刘清红等[9]通过针刺上、下巨虚、足三里、阳陵泉、合谷等穴位,达到了胃健脾降逆、通腑化痰、升降气机的功效。
西医认为AP发病的机制繁多,目前临床上较认可的机制有胰酶自身消化学说、炎性因子学说和自由基学说等[47]。针刺辅助治AP主要是通过重建促炎-抗炎平衡、改善胃肠道通透性并促进胃肠道蠕动、保护胰外器官、镇痛等方面来发挥作用[3]。
3.1 降低炎症反应 AP时多种致病因素致胰腺细胞损伤,最终导致介质的瀑布反应的发生。其中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8、IL-10、CRP等发挥着主要作用[48]。针刺可通过调节炎性介质来重建促炎-抗炎平衡,从而有效降低炎症反应。有研究证实:电针刺激足三里、合谷、支沟、天枢等穴位可以增高IL-10、缩胆囊素八肽(cholecystokinin,CCK)8及IL-4水平,下调TNF-α和IL-6水平,降低CRP从而诱导抗炎作用的发生[49-50]。针刺太溪穴与飞扬穴可通过减少IL-8,增加IL10,增强抗炎反应,从而减轻炎症反应[51]。有学者发现电针刺激肺经、大肠经俞穴及募穴可增强抗炎反应,通过升高IL-10水平,下调TNF-n、TNF-q、IL-6等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减轻中性粒细胞在浸润,重建促炎-抗炎平衡,抑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活性,降低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抗氧化,从而减轻SAP大鼠胰腺病理损伤[16]。冯勇等[30]对72例AP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清胰汤保留灌肠结合针刺胰俞、脾俞、胃俞等穴位可降低TNF-α、IL-6和IL-8等的表达。
3.2 改善胃肠道通透性,促进胃肠道蠕动 胃肠屏障的破坏常常导致胃肠菌群移,而胃肠菌群移位可导致多种并发症,是AP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代研究证实:AP的西医常规治疗配合针刺足三里穴可恢复胃肠黏膜的屏障功能,抑制炎症反应,促进胃肠功能恢复[52-53]。柴芩承气汤改良保留灌肠联合新斯的明足三里穴位注射可迅速缓解麻痹性肠梗阻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肠道功能恢复,从而改善预后[54]。
3.3 保护胰外器官 SAP的过度炎症反应可能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及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 systemic organ failure,MSOF)的发生,影响全身多器官的功能。其中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可引起进行性的低氧血症和呼吸窘迫,是SAP病程早期主要的死因之一。电针肺与大肠经俞募穴可刺激胃肠肽类激素的释放,减少MPO以及MDA的生成,减轻肺损伤[17];有学者发现针刺肺、大肠、脾经穴位及其背腧穴,可抑制巨噬细胞炎性蛋白-2(MIP-2)mRNA的转录及翻译过程,并抑止血清MIP-2蛋白的合成,从而达到减轻肺损伤的目的[18,55]。
3.4 镇痛 AP患者大多伴有持续性的腹痛,针刺通过神经递质、神经调质、神经肽、细胞信号分子和炎性介质等多种生物活性分子共同发挥镇痛作用[56]。电针通过抑止外周和中枢分泌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来抑制疼痛。这些包括阿片类药物,其使外周伤害感受器脱敏并减少外周和中枢的促炎细胞因子、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减少中枢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亚基GluN1磷酸化[57-58]。
4 总结
综上所述,近10年来针刺辅助治疗AP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存在以下问题:(1)目前临床试验研究病例数较少,缺乏大样本的临床试验;(2)针刺穴位无统一规范,难以推行至基层医院;(3)中、西医中对AP都有明确的分型,但临床上缺乏对不同类型AP的针刺方案;(4)针刺手法、穴位定位难以控制,留针时间也不尽相同,故难以比较不同针刺处方治疗效果的差异;(5)针刺辅助治疗AP的机制研究尚未清楚。笔者认为应根据AP的不同分型遴选出有针对性的优良的针刺处方,并进行推广,此举有利于广大AP患者的恢复,并能促进针灸辅助治疗AP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