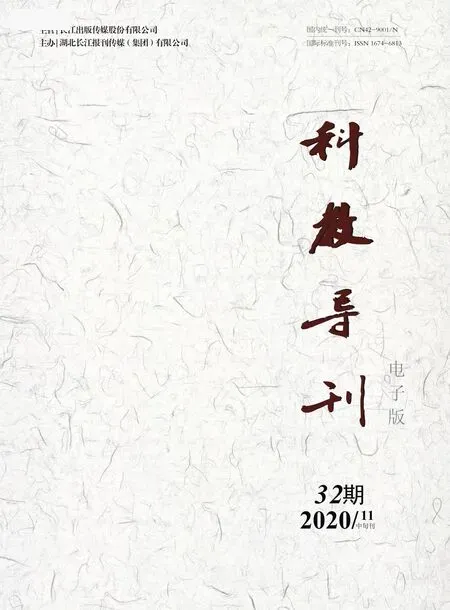“同意”与“强力”维度下中国儒家与法家的霸权理论的比较
盛 喆
(诺丁汉大学 英国·诺丁汉 NG7 2RD)
霸权一词在汉语语境下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国是唯一将其用作官方术语使用的国家。这个术语的诞生与发展同样根植于相应的时代背景:东周以后,周天子虽然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他不但没有足够的实力号令分封的臣子,而且其名下的封臣们无论与王室有无血亲关系,也都不满足于受周王控制,并且各自发展壮大势力。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封建体系和维护相应伦理的礼乐制度都在逐步瓦解崩溃。而且自从郑庄公战胜周天子后,周王室的声望跌落谷底,再无力阻止诸侯相争。相对于旧秩序中的领导者周天子的头衔“王”,以诸侯为主体的领导者的称谓便是“霸”。因此,“霸”这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以“王”作为至高领导者的旧秩序的崩溃以及领导权力的下移。但是,作为旧政治秩序的领导和象征的周朝及周天子本身还存在,霸主迎合了遵奉既定秩序的社会心理需要。所以霸主并不公开否定王名义上的领导地位也不完全颠覆当前政治秩序,而是以维护王室的名义讨伐异己,即“尊王攘夷”。自齐桓公已降,强大的诸侯开始重整天下秩序,“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战争与会盟成了霸权的主要形式。
对于霸权这种现象,儒家学派总体的态度是不赞赏的,从《论语·季氏》的著名论断“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对于霸权的定义:天下无道的产物。这个结论也可以被认为社会规范丧失的结果。因为“名”这个概念本身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要素之一,与政治中的等级规范息息相关。“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已有社会规范下头衔和权柄具有唯一性,而王作为当时秩序下正统的领导人,行使权力具有正当性;而霸主并没有王的头衔,却行使本应属于王的权力来统领和自己在地位上本应是平等的其他诸侯,这本身是一种僭越。所以相对实至名归的王权是正当领导权,霸权的正当性就显得不足。但另一方面,孔子对于霸权政治的设计者管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单纯从这两句来看,在孔子的视角下霸权在现实中的作用并非对于社会秩序的彻底破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文明存续。而且孔子本身就生活在权力更下移的“陪臣执国命”时期,社会的混乱和危机相较诸侯称霸时期有增无减,因而霸权在孔子的概念中兼有积极和消极两面。而孟子的观点则将“王道”和“霸道”至于对立面。在孟子的定义中,王道是用德行让人心悦诚服,霸道是用暴力让人被迫臣服,即《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让人被迫臣服和心悦诚服,二者结果哪个更胜一筹就很明显了。这种划分方法一定程度上被后来的荀子继承。“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但是对于霸的地位,虽然荀子还是将其至于王之下,但没有像孟子一样单纯通过德治和力治来将二者对立。相反,霸是介乎于最正统、令人臣服的“王”和完全依靠暴力的“强”之间的一个折衷统治方式,在这种统治方式之下霸主仍需要交好诸侯来获得支持而非全然的暴力强迫。另外荀子对于霸权的作用认识更加辩证:霸主对于农业经济发展、人才选拔、明确行赏有促进作用,是无王之时的最好选择。所以综合三位儒家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霸是一个相对于王的相对概念,虽然未必是一个很坏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最好的设计。
法家对于霸道的态度与儒家有较大不同,商鞅本人的著作没有将霸道和其他政治构想做系统对比,但《史记·商君列传》生动地记载了商鞅的三分法: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被引荐给秦孝公时分别讲述了帝道和王道,秦孝公全然不感兴趣,第三次宣讲霸道之后才被孝公采纳。从这个顺序上来来看,商鞅主观地优先倾向于选择圣贤之道,当圣贤之道行不通的时候才最后选择霸道。从结果来看,商鞅的行为深化了霸权的实践:集中权力、鼓励耕战、重视刑罚,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战胜诸侯。这与之前霸主仅是领导诸侯已经有了本质区别。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就从逻辑上批判了前人主张的王道思想。《五蠹》中韩非用仁义亡国、尚武兴盛的现实和守株待兔的寓言证明了历史走向;优秀的君主应该遵循这个规律而不该妄想王政复古。这个观点在韩非的著作中被反复强调,如《显学》中“固不道仁义”、《六反》中“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在韩非看来宣扬道德的王道并不光荣,崇尚武力的霸道也并不可耻。如果说商鞅仅把霸道妥协之后的权宜之计,为王道还留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韩非则彻底破除了对王道的迷信。
西方的“霸权”一词出现于古希腊。“Hegemonia”本意指城邦联盟领导者。但是霸主本身也是联盟的成员,这个头衔仅是一种荣誉,在地位上与其他成员平等。因此,霸权起初不包括对他人的强制干涉,而是来自平等成员自愿让渡的领导权,不涉及对成员的胁迫。与霸权相对的概念是“帝国”,它代表着高权威与力量以及对他人的强制性。在这里“强力”作为界定霸权的第一个维度。但霸权本身也涉及力量这个因素,要彻底让他人保持自愿的原则也不可能。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城邦时代晚期)人们不再渴望平等,要么统治要么被奴役。而且希腊当时存在两个强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这两者争夺霸权的结果就是“战争无可避免”。此后,霸权概念长期沉寂,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提及。基于“强力”这个逻辑,特里佩尔定义霸权是介乎“统治”和“影响”之间的一种“格外强大的影响力”并最终“以支配告终”这个定义在《韦氏新世界大辞典》被采用,霸权的定义便是处于支配地位。而作为“霸权”比较物的“帝国”相对应的则是“统治”,吉登斯定义统治为“致力实现和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而葛兰西对霸权有着迄今最深刻的认识:霸权领导力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霸权是广泛同意的集体意识的产物。他认为强力本身并不能压倒同意,而霸权本质上则是强力的对立。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思想受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虽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没有直接写到霸权,但马基雅维利重视以力量为基础、争取人民广泛支持的统治方式,如君主需要拥有充足的财力、强大的军队,并不结怨于人民。
如前文所述,在古希腊的二分法中帝国代表更高级的权力,在特里佩尔的三分法中统治位列霸权之前。如果将这两种分类方法对比,帝国代表统治的最终形态,那么霸权代表的支配则是尚未达到能够直接统治的绝对强力或者是强力正在通向统治的中间状态。所以,霸权和帝国并非全然对立互不相干的两种形式,而是有联系甚至可以转化的,“帝国和霸权乃邪恶的孪生兄弟”,甚至霸权国本身的目标就是建设帝国。但是与帝国不同的是,霸权对于制定秩序尚有和其他弱小国讨论的余地,最终整个集体达成一致。作为回报,弱小国可以在霸权主导的体系之下确保自身的安全。这种同意是基于换取安全的交易所得,而非帝国的强制所致。所以,只要“同意”存在,霸权存在一种契约关系。
如果将“强力”和“同意”两个维度代入,会发现儒法两家思想的交锋点在于“强力”和“同意”何者为先。除了孟子激进否定“强力”之外,孔子和荀子仍然对“强力”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辩证看法。比如,孔子论述强国的三个条件中“强力”的要素占据了两个——“足兵、足粮”。但如果不能兼顾,“同意”要素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足兵、足粮”还是需要让位于代表“同意”的“民信之矣”。可见“强力”在孔子的构想中并非必要条件。而在荀子的三分法中,虽然肯定了霸的强力是次于王的较好选择,但从“王”到“强”的堕落过程其实也就是“同意”逐渐让位于“强力”的过程。另外相比于孟子定义霸内涵是纯粹的强力,荀子指出了霸的根本在于诚信——“信立而霸也”。关于“强力”和“同意”谁是本源的问题,荀子的最终答案在《议兵》篇中。此篇中他对比了战国的精锐之师和春秋霸主,然而这些都不敌“汤武之仁义”。“强力”与“同意”两个要素高下立判。从这点上来说,儒家的理念与葛兰西类似,偏向“同意”。霸权主导本身仍需要让从属的多数人满意,因而霸权一定程度上具有良善的多元性和契约性。对于儒家思想来说,“强力”这个要素在理想状态下、或者在“同意”这个理念推向极致以后是可以放弃的。这一点与葛兰西认为略有区别,后者认为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若无同意,不可想象;若无强力,不可实行。
法家思想更加具有现实主义。商鞅和韩非,无论前者在理念上是否还对帝王之道存有幻想,二者在方法论上无一不是将“强力”发挥到极致。其中最典型的商鞅变法中以耕战为本、崇尚军功这种对强力的推崇。这种推崇强力的结果就是形成了社会性的功利主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全体国民对于势利的皈依这一集体行为。显然在此情况下争取他人自主的同意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同意”完全被裹挟,这也就是“强力”的最终胜利。所以安德森评价法家将暴力与意识形态、强力与同意二要素纳入了一个统一的体系。
参照西方对于霸权和帝国的二分法,法家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实际上一方面实证了霸权和帝国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因为法家思想的最用在现实结果就是铸造了一个统一帝国;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当“强力”能够完全裹挟“同意”的时候,霸权就会发生质变。但除了对于霸权本身特性的讨论,儒家和法家都没有将霸主当成他们政治构想的目的,面对相同的社会问题让他们的思想终点和历史使命是一样的——完成统一,因此霸权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必要阶段。所以,与其说他们对于霸权的不同认识是基于对“同意”和“强力”的不同侧重,不如说他们是对于“帝国”如何“统治”有本质性分歧,即“强力”或“同意”何者能够维持服从。儒家的理想是将“同意”推向极致,也就回归了儒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德治,并将其作为治国之道来遵守。法家同理,将“强力”推向极致,除了军事武力,还要遵从以法为教、吏为师这样兼有教化性和强制性的非人格化权威。
“同意”和“强力”的兼有的霸权,并非中国古典政治构想中的顶层设计。但是反过来,单纯强调其中某一要素以期超越霸权建立帝国也不可行。儒家始终没有重新创造出完全天下归心的凝聚力。而法家虽然成功地凭借强力创立了帝国,但单纯以强力治理的秦朝只维持了14年。并且随着对世界概念的扩充,单纯的强力维系就意味着将武力投射到各个地方,因此任何国家想依赖绝对的武力是不可能的。而霸权这一概念本身虽然会因为时间、地域不同有具体不同的表现。但是有些表现并非没有关联,尤其在核心构成的两个要素上的矛盾,这在儒家和法家的不同理论中已经可见一斑。同时霸权作为一种一个兼有自愿性质的“同意”和强迫性质的“强力”的领导权,霸权国和其他成员之间的主从关系是自愿还是被迫就很难界定。因此,霸权也不是一种最终令所有人满意的秩序,同样也不会是政治设想构建的最理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