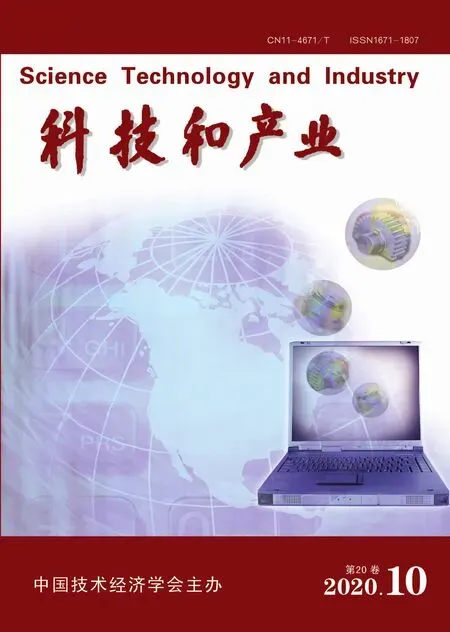中美在职消费计量问题研究述评
贺镜帆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 广汉 618307)
随着我国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问题的报道相继浮出水面,高管在职消费成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在美国,高管在职消费项目已纳入企业高管薪酬总额,金额超过10 000美元的在职消费将在高管薪酬中予以披露。而在我国,高管在职消费尚未取得“合法化”地位,企业也并未有关于在职消费的相关披露,这为学者们研究在职消费带来了难度。在这些关于在职消费的研究文献中,如何对在职消费进行计量,却各不相同。本文将围绕在职消费的计量问题展开述评。
1 中美在职消费的界定与披露
在职消费,无论是美国的SEC,还是中国财政部,均未对在职消费进行明确的定义。然而,在2006年美国SEC发布的一项关于高管薪酬披露的新规定中,对在职消费的界定以及披露均作了详细的要求。关于在职消费的界定,SEC的判断标准有三条。第一,项目是否整体地且直接地与工作相关,若是,则不属于在职消费;第二,是否产生了直接的或非直接的个人方面的利益,若否,则不属于在职消费;第三,这种利益的提供在员工之间是否具有无差异性。若无差异性,则不属于在职消费。关于在职消费的披露,SEC对在职消费的披露起点作了新规定。新规定要求,若高管的在职消费与其他个人福利之和超过10 000美元,则该在职消费必须按种类在“所有其他薪酬”栏目中予以披露。同时,若某一项在职消费的金额超过了总的在职消费与其他个人福利金额之和的10%,或某项在职消费的金额超过了25 000美元,则该项在职消费必须在附注中予以披露。
SEC将高管在职消费纳入了高管薪酬的范畴,要求上市公司予以披露,意味着高管的在职消费被“合法化”与“透明化”。这意味着在职消费属于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在职消费的激励作用。这与传统的在职消费仅是“管理层侵占公司利益的手段”[1]传统观点不同。与美国SEC关于在职消费详尽的界定与披露不同,在我国,并没有出台关于在职消费的界定的规定,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也未被要求予以披露,尽管事实上高管在职消费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然而,目前我国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尚处于灰色地带。
2 美国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计量
当前,在以美国的公司为样本对在职消费进行研究的文献中,对在职消费的计量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以高管所享受的某一项在职消费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有Yermack[2]与Rajan and Wulf[3]。其中Yermack是以公司为企业高管提供私人飞机作为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而Rajan and Wulf分别采用了公司为CEO提供的飞机使用情况,为CEO提供的汽车使用情况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指标。以在职消费的某一项目进行研究,必须是这一项目在在职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同时,该在职消费项目在许多公司都有提供。如在Yermack研究的样本公司中,在披露的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项目中,公司为企业高管提供私人飞机使用情况是所有在职消费项目中频率最高,涉及金额最大的项目,且在其研究样本中发现有78.1%的公司拥有自己的飞机。同时,这种计量方式比较适合深入探讨某项在职消费的提供与公司高管及公司自身特征之间的关系。如Yermark发现,公司为高管提供私人飞机,与公司是否具有远距离的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显著相关。而Rajan and Wulf发现公司为CEO提供飞机,与公司总部所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显著相关。然而,这种计量方法的缺点是,以在职消费的某一项目替代了所有的在职消费项目,以部分替代了总体,因而计量出来的金额小于在职消费的实际金额,金额替代具有不完全性。第二种方法是以报表披露的CEO、CFO等前五位高管在职消费的金额之和作为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计量金额。如Grinstein et al.[4],便是采用此法,研究了新规则披露前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变化。采用这种方法的还有Andrews et al.[5],Chia-Ying Chan[6]等。这种方法计算的高管在职消费金额,应该是最接近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真实金额。因为按照SEC的规定,只要高管的个人在职消费与福利之和超过10 000美元,均需要在报表中分项目予以披露。因而,按照此种方法,除了个人的在职消费与福利之和低于10 000美元的没有计入进去之外,其他的在职消费项目均计入进去了。三是以报表披露的CEO、CFO等前5位高管在职消费的项目数作为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Andrews et al.,Chia-Ying Chan的文章中均有采用。以在职消费的项目数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这种计量方法并不一定准确,因为公司为高管提供的在职消费项目数越多,并不意味着在职消费的金额越大,而在职消费的项目数越少,也不意味着在职消费的金额越低。因而,该种方法只能作为在职消费计量的一种辅助方法。
3 我国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计量
在我国,并没有关于在职消费界定的明确规定,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也并未要求披露,这为在职消费的计量带来了难度。鉴于在职消费的隐蔽性,学者们从企业“管理费用”或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下的明细项目中选择一些方法进行计量。具体做法有:
3.1 明细费用之和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指标
采用明细费用之和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指标,这种做法最早来源于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7],他们将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下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这八项费用之和作为了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参照这种做法的还有卢锐等[8]、罗宏等[9]、陈冬华等[10]、周玮等[11]、刘银国[12]、冯根福等[13]等。除此之外,Adithipyangkul, Alon and Tianyu Zhang[14]也采用了明细费用之和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指标,然而,与陈冬华等不同的是,他们选取了餐饮、旅行、交通、通讯、娱乐费等支出之和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
采用明细费用之和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指标,包含了企业由于正常的经营活动而进行的花费,因而,这些费用之和计算出来的金额,高于企业实际在职消费的金额。同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表附注中,这些费用有些公司并未予以披露,有些披露了部分,这为收集资料带来了困难,容易导致企业间由于资料收集的不完整而不具可比性。
3.2 残差法
由于用八大费用总和包括了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费用,Weiluo et al.[15]以及李宝宝和黄寿昌[16]提出了用扣除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费用的残差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残差法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管理费用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中剥离出其他费用,使残差能正确地反映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金额,这方面Wei luo et al.与李宝宝和黄寿昌的估计模型并不相同。李宝宝等对在职消费的估计模型如下:
先将管理费用对销售收入做回归:
ADEj,t=β0+β1REVi,t-1+β2REVi,t+β3REVi,t+1+εi,t
(1)
其中,ADE:企业的管理费用;REV:企业销售收入。
将回归后的模型(1)中的截距项定义为管理费用中的固定性要素,将剔除固定性要素之后的管理费用称作变动性管理费用,然后将变动性管理费用与反映正常经营活动费用的一些变量进行回归,如下:
DADEj,t/SALESj,t=β0+β1(ASSETj,t/SALESj,t)+β2M/Bj,t+β3MAGSIZEj,t+β4ln(EMPLOYEEj,t)+β5MEETINGj,t+β6COMMTITTEj,t+β7LOCATj,t+εj,t
(2)
其中,DADE:变动性管理费用;ASSET:总资产;M/B:市净率;MAGSIZE:管理层人数;EMPLOYEE:员工数量;MEETING:股东大会次数,董事会次数以及监事会次数之后;COMMTITTE: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的设立情况;LOCAT:地域因素。
对模型(2)分年度按行业进行回归,回归后的残差ε(异常管理费用率)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
上述模型是将在职消费认定为变动管理费用扣除企业一些正常经营活动费用的残差。在考虑与正常经营活动费用相关的因素时,考虑了员工人数、规模等因素。然而,我们认为,该模型有几处不妥。一是该模型将在职消费排除在企业固定性管理费用之外,认为仅是一项与收入相关的变动性费用,我们认为不妥当。事实上,有些在职消费项目与企业的收入并没有联系,相反却与高管自身特征相关。如企业高管的小车费,可能更多的是与企业高管的住所离公司距离的远近相关。公司为CEO提供私人飞机与CEO是否具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相关,与公司总部所在地理位置是否偏僻相关。二是该模型在剔除其他相关费用时,忽略了某些费用,如与存货管理等相关的一些管理费用,企业与政府部门、客户、供应商往来等发生的一些关系费用等。三是在该模型中,将股东大会、董事会次数及薪酬委员会等的设立情况作为影响变动性管理费用的因素。我们认为,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相关会议费用的发生并非是一项与收入相关的变动性管理费用,因而,列作影响变动性管理费用的因素不妥当。
Weiluo et al.的方法与李宝宝和黄寿昌不同,他们采用了两种方法来估算高管在职消费,一是从管理费用中剔除其他相关费用后的残差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另一种方法是从现金流量表的明显项目中扣除相关费用后的残差。其模型如下:
(3)
其中,Mexpense: 管理费用-(坏账+无法实现的利得+存货损失+高管人员直接薪酬)
Δsales:销售收入的变化
PPE:固定资产净值
Inv:存货净值
Lnemployee:员工人数对数
模型回归后的残差作为高管在职消费的计量
模型(3)是从管理费用中剔除其他相关费用,将计量后的残差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这与李宝宝和黄寿昌研究方法相同。不同的是李宝宝等中在职消费是从变动管理费用中剔除其他费用后的残差,而Wei luo et al.是从扣除异常损失及高管直接薪酬后的管理费用总额剔除其他相关费用后的残差。在模型(3)中,根据管理费用包含的内容,考虑了与折旧相关的管理费用因素(固定资产净值)、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的管理费用(销售收入增量)、存货管理导致的管理费用(存货)、与员工相关的管理费用(员工人数)以及规模因素(资产)。但是,在该模型中,遗漏了列为管理费用的无形资产研发支出项目,同时,按照新准则规定,企业的坏账也不在“管理费用”中核算,而是在“资产减值损失”中。最后,在考虑管理费用中的其他相关费用因素时,忽略了地域因素,以及企业为了自身的生产发展而建立的一些关系费用,如企业与政府部门、客户、供应商往来等发生的一些关系费用等。
Weiluo et al.的第二种方法是从现金流量表的其他明细项目中剔除相关费用后的残差。如模型(4)所示。
(4)
Mpay: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项目中收集了五类项目,包括差旅费、娱乐费、小汽车费、相关福利项目(包括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国外培训等费用)、行政特权费用(包括办公费、董事会费、通讯费等)。其他变量与模型(3)相同。
模型(4)收集了现金流量表中的差旅费、娱乐费、小汽车费、相关福利项目、行政特权费这五类明细项目,然而,这五类项目有些企业并未在现金流量表附注中披露,有些企业只披露了部分项目,从而使得数据资料不易获得。同时,在考虑其他相关费用因素时,存在与模型(3)相同的缺点。
4 结论与展望
由于在职消费在我国与美国的规定不同,从而在职消费在计量问题上体现了差异性。目前,美国的学者对在职消费的计量主要采用了三种方式:一是以高管所享受的某一项在职消费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这种计量方式比较适合深入探讨某项在职消费的提供与公司高管及公司自身特征之间的关系,但该方式要求该项目在在职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且该在职消费项目在许多公司都有提供。而这种方式的缺点是以在职消费的部分替代总体,金额替代具有不完全性。第二种方式是以报表披露的CEO、CFO等前5位高管在职消费的金额之和作为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金额。这种方式计量的在职消费,应该是最接近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真实金额,然而在我国却并不适用。第三种方式是以报表披露的CEO、CFO等前5位高管在职消费的项目数作为公司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这种计量方法并不一定准确,因为公司为高管提供的在职消费项目数越多,并不意味着在职消费的金额越大,而在职消费的项目数越少,也不意味着在职消费的金额越低。因而,该种方法只能作为在职消费计量的一种辅助方法。在我国,关于在职消费的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的明细项目下的八大费用之和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但是这八大费用中,通常包含了企业由于正常的经营活动而进行的花费,因而,其金额往往高于企业实际在职消费的金额。同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表附注中,这八大费用有些公司并未予以披露,有些披露了部分,这为收集资料带来了困难,容易导致企业间由于资料收集的不完整而不具可比性。二是以残差法对在职消费进行计量。然而,如何从“管理费用”中剔除在职消费之外的费用,使残差能恰当反映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却是当前残差法计量的难点。
关于在职消费的计量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值得去研究。比如,当前的在职消费,学者们均是从“管理费用”或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明细项目中提取,而在职消费是否有可能反映在了其他费用项目中?如“销售费用”中是否存在?“在建工程”或其他资产成本中是否存在?如何从这些项目中提取在职消费?同时,在采用残差法对在职消费进行计量时,当前的研究仅考虑了剔除正常的经营活动费用这一项,而企业的管理费用中是否还包括在职消费与正常经营活动费用之外的费用,如企业与政府部门建立的关系费用?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关系费用?这些关系费用应该如何去衡量?而在计量方法上,除了总和法与残差法,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对在职消费进行计量?这些都是未来对在职消费进行计量时所需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