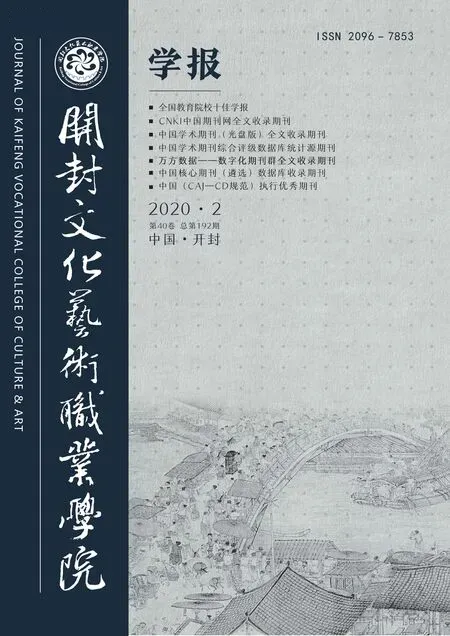苦难下的忍耐和反抗
——论《灿烂千阳》中女性生存意识的觉醒
刘奥梦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女性的生存处境
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从事实性和可能性两方面把握生存的观点。事实性是人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可能性则指人超越本能。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处境……不是就生理而言,而是同时就身心两方面而言的。”[1]202因此,生存意识可以理解成“处境意识和追求意义的结合”。人永远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处境,因为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总是会被某种处境所局限,因此处境意识主要是指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即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生存环境本能的、惯性的反应;而追求意义是一种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生命活动以及社会的、精神的期待。作者在小说中向我们展现了阿富汗女性普遍的生存困境,苦难是小说中女性人物生存世界的底色。无情的战火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尤其是因战争导致的极度贫困更是将本就艰难的阿富汗人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并且,小说中展示的阿富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至上的国家,大多数女性只能在男人的庇护下生存,她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父亲、丈夫或儿子,女人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女性的生存权利遭到了残酷的践踏,这便是小说中女性的处境。
二、女性的忍耐——处境意识
上文提到,生存意识可以理解为“处境意识和追求意义的结合”,其中处境意识主要指个体在生存的过程中对自身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的生存环境本能的、惯性的反应。小说中的一位女主人公玛利亚姆由于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影响,她在面临自身苦难命运时总是表现出默默忍耐的性格特征。而与玛利亚姆生长环境不同的另一位主人公莱拉,虽与她有不同的性格,但在面临自身所处的苦难现实时,为了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也不得不暂时忍耐不公的命运。面对这样的生存处境,两位女主人公生存意识的核心都是忍耐。
玛利亚姆的苦难根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病态的原生家庭,二是不幸的婚姻。在小说设定的社会背景下,私生子是一个不被社会接受的身份。主人公玛利亚姆是一个私生子,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她从小就和母亲住在远离市区的山上。因为身份的低微和不幸的婚姻,母亲把对男人以及对现实的怨恨都强加给了玛利亚姆,把不幸都归结于命运,她经常对玛利亚姆说:“这就是我忍受这一切所得到的回报,你这个打碎了传家宝的小哈拉米。”[2]156(哈拉米即私生子)这让玛利亚姆在童年时期就背负了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也正因为这样,玛利亚姆在以后人生重大事件的选择上都表现出忍耐和妥协,而这就是她以后不幸婚姻的根源。玛利亚姆的母亲死后,十五岁的玛利亚姆不得不嫁给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男人拉希德。当然,婚姻的初始,玛利亚姆是感受到了“幸福”的。她听从拉希德的指示,穿上了阿富汗女人的传统服饰布卡,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只有两只眼镜露在外面。此时的玛利亚姆正享受着丈夫拉希德给予的保护——她认为这是丈夫对妻子的保护。然而,这短暂的“幸福”在玛利亚姆经历了六次流产以至于丧失生育能力之后便消失殆尽。从此,她成为丈夫施暴的对象,挨打和辱骂成了家常便饭,这种情况在拉希德的第二个妻子莱拉来了之后变得更糟,丈夫的暴打成了那样“程序化且习以为常地进行着。没有诅咒,没有喊叫,没有哀求,更没有意料中的尖叫,只剩下蛮有条理性的殴打与被打”[2]201。玛利亚姆成了任丈夫宰割的羔羊,而这时的玛利亚姆只能忍耐这一切的不公和苦难。因为唯有忍耐,她才能活下去。
另一位主人公莱拉的不幸来自战火的摧残和妥协的婚姻。与玛利亚姆不同,莱拉出生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中,就出生而言,莱拉是幸运的。她度过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注定她的一大段人生都脱离不了战争。当两个哥哥战死之后,母亲精神渐渐崩溃了,莱拉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莱拉的幸福本来近在咫尺,因为曾经安土重迁的母亲答应逃离阿富汗,但此时一颗炸弹瞬间改变了莱拉的命运。炸弹夺去了她父母的生命,莱拉也身受重伤,曾经温馨的家庭就这样毁于一旦,这也是莱拉苦难命运的开始。伤重的莱拉就这样走进了拉希德的生活。为了得到年轻貌美的莱拉,拉希德编造了莱拉的初恋情人身亡的谎言,这让莱拉十分绝望。而在这时,莱拉发现自己腹中有了初恋情人的孩子,“莱拉此时也陷入了生存选择之中,在这样的生存天平上,离开还是留下成为了一个难题”[3]。但是,为了保住这个生命,莱拉屈从了拉希德,因为当时的她只有嫁给拉希德,她和腹中的孩子才能生存下去。
三、女性的反抗——追求意义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说过:“一个深受不幸与苦难折磨的人,他虽然有了这些苦难和不幸,但他宁愿还是他自己,而不愿成为没有灾难的别的什么人。他宁愿选择苦难与不幸,也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存在。”[4]那么,证明自身存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不仅仅是自身的生存,更是超越了个体生命以外的意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证明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活着,还在于对他人和社会的价值。这种生存的自觉行为,是一种具有本真状态的向死而生,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存意识的觉醒。
小说发展到最后,两位女主人公生存意识的核心渐渐由忍耐转变成反抗和追求。主人公玛利亚姆是作者胡赛尼从众多阿富汗女性中提取出来的一个典型,她具有女性所有的美好品质,同时,在小说中,她也是生存意识觉醒的女性代表。但是,她的觉醒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她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处于追求生存的最低阶段,即活下去。她的生存意识由忍耐转变到反抗的源头是莱拉的女儿阿兹莎。阿兹莎唤醒了玛利亚姆心中强烈的生存意识,所以莱拉策划第一次逃跑时,玛利亚姆充当了跟从者,她希望莱拉和孩子能够逃离她们共同的丈夫拉希德的控制。在拉希德对她们施暴并且欲置莱拉于死地的时候,玛利亚姆勇敢地举起铁锹打死了丈夫,并且独自承担罪名。她终于作出了反抗,她作为女性生存个体的意识终于觉醒了,并且在打死丈夫的那一刻达到了最高点。玛利亚姆在短暂的一生中忍辱负重,忍受着降临到她身上的所有不幸,最终用爱和宽容拯救了与她同病相怜的莱拉,这其中散发着人性的光辉,照亮了莱拉以后的生命之旅,她将永远活在莱拉和女儿的心中,她们将会用一生来缅怀玛利亚姆。
小说中另一位女主人公莱拉,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的生存意识一直处于一个良性的上升阶段,在面对不幸命运时,她不会像玛利亚姆那样只是一味地忍耐,她会进行有力的反抗,反抗的种子一直在她心中潜伏着。莱拉有坚韧的个性,她的坚韧尤其体现在为了让尚未出世的孩子获得一个尚且可以的生存环境,她毅然地嫁给了拉希德。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忍耐和妥协,她从未放弃过对苦难命运的抗争,她不断地寻找通往新生活的道路。她一面忍受着丈夫的暴力,一面为女儿争取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当丈夫殴打玛利亚姆时,她也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在丈夫的重压下,莱拉从未放弃过斗争,她策划并实施了两次出逃,这意味着莱拉对男权的反抗,对女性自由权和生存权的追求。
四、生存意识觉醒后的意义
在《灿烂千阳》中,作者清楚地认识到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环境是不同于西方女性的,两者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去甚远。作品中女主人公玛利亚姆对男权的压迫没有声泪控诉,没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利。但是,觉醒后的玛利亚姆却成为阿富汗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她最终没有像她的母亲一样用自身的灭亡来默默承受甚至认可男性的权利以及不幸的命运,她用行动打破了母亲所奉行的观念——用忍耐来承受所有的不幸,她“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其伟大的人格,实现了最终的精神救赎,同时将阿富汗女性崛起的希望传递给了像莱拉那样的新女性”[5],这正是玛利亚姆生存意识觉醒之后的意义和价值。
阿富汗战争结束以后,莱拉放弃了安稳舒适的生活,选择回到祖国阿富汗成为孤儿院的一名教师,向孩子们传授知识,用知识和文化来充实自己,把爱和希望带给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和人民。在小说的最后,莱拉不仅重拾旧爱获得了幸福的婚姻,而且得到了工作的权利,并踏上了回报社会的旅程,这也是莱拉作为生存个体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玛利亚·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