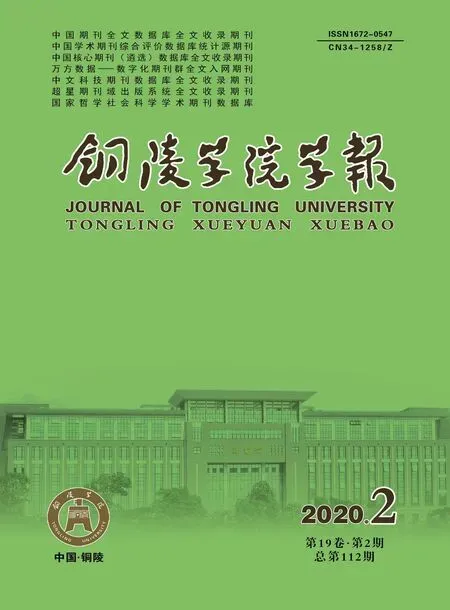儒家伦理视阈下布兰琪的悲剧人生
姚 瑶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欲望号街车》是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扛鼎之作,该剧接连荣获普利策奖、纽约剧评人奖和唐纳德森奖三项美国最重要的戏剧大奖。阿瑟·米勒曾评价这部戏剧:“只看了短短几分钟,我就认识到这出戏、这个制作已经向另一个戏剧世界敞开了大门。[1]”威廉斯那别具一格、独具匠心的戏剧语言艺术,错峰奇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设计,既给读者带来一种沉浸式的阅读快感,又给观者以当时美国时代背景折射式的启迪。
纵观国内学界对《欲望号街车》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两方面特点。一是过分着墨于整部戏剧的故事结构的建构分析亦或是威廉斯高超的戏剧语言运用,就事论事的痕迹明显,不能给学界同仁或者有志于从事戏剧创作的业界人才提供多角度的灵感激发。二是文化自信的元素较少。长久以来,国内学界热衷于拾起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工具去解析《欲望号街车》这部伟大的戏剧作品,但受众观者又主要是国内学人,非掌握相当的专业知识,断不能做到“以无厚入有间”的顺畅理解。细读整部戏剧,不难发现,田纳西·威廉斯力图解决的是对女主人公布兰琪悲剧人生的伦理探索。而中国儒学在伦理方面具有精深且丰富的阐释途径,因此,以儒家伦理的相关理论来解析该部戏剧,不仅能更深层次地挖掘布兰琪的悲剧成因,同时也可以充分展示该剧所隐匿的伦理启示和道德规范。
一、千金小姐的堕落与伦理身份的骤变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2]”《欲望号街车》中女主人公布兰琪的伦理身份集中体现于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两个方面,包括女儿、妻子、教师、“情人”。这些身份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致使女主人公逐步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
就家庭身份而言,布兰琪历经了“为人女”和“为人妻”两个人生关键时刻。剧中,不论是从她刚出场时与白种女人尤妮斯的对话,还是她的自身妆扮、生活习惯及男主人公对她所在家族物质财富的固有印象,都可以看出布兰琪从小出生于一个环境优渥的家族。身为庄园主的千金小姐,理应从小由家中父辈来安排接受“贵族”式的教育,成为礼貌高雅、心智聪颖、自信自爱的女性。而“为人父止于慈[3]”,慈爱是父辈之德,既为人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但布兰琪家庭成员关系混乱糜败,生活亦淫乱不堪,因此长辈皆疏于对子女的培养和管教,布兰琪也顺势在此环境下自然生长。所谓“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4]”布兰琪脱离“贵族千金”这一人设的预定轨道,全凭自己的真实性情渐渐成长,虽然看似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实则某些原始欲望已悄然露出端倪。由于出身高贵、相貌迷人,布兰琪成为周围人赞美和艳羡的对象,而她也视其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养料,随即衍生出对各种形式之“美”的无限渴望。当布兰琪遇到风度翩翩的诗人艾伦时,前者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领略到诗人生活的清新高雅,第一次感受到崇拜他人的兴奋之情,第一次萌生出对“情爱”的幻想。艾伦的出现使布兰琪陡然意识到不同身份的人在生活上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让她开始向往内涵之“美”。与艾伦的结合既实现了布兰琪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同时也是她的身份意识生平第一次被强有力地激活。
当布兰琪正沉浸于诗人之妻的新奇身份中时,却无意间发现了丈夫艾伦的同性恋行为,她亦由此急速踏入了另一条生活的河流。从温室般的家庭被迫逃离后,布兰琪心怀忐忑地步入了社会。最初,她在小镇劳雷尔谋得英语教师的工作,开启了她作为一个庄园主女儿始料未及的生活。然而,微薄的薪水无法负担起她的物质需求,繁琐的教学事务也令她无所适从。一次偶然的机会,布兰琪收到了镇上倾慕者的礼物,自此她便利用自己的美貌作为资本,委身于不同类型的陌生男人。为了麻痹内心的孤寂和苦闷,改变无所依靠的处境,布兰琪逐步沦落成小镇上人尽皆知的“大众情人”,最终因与自己未成年的学生有染而被赶出劳雷尔。就社会伦理而言,布兰琪兼具教师与“大众情人”的身份,而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势必会引起伦理身份的错位和伦理秩序的混乱。究其根本缘由,是因为布兰琪的意识中自始至终都缺少恒定有效的道德机制的管控,而此种机制在中国儒学字典中简要概括为“礼”。礼是社会秩序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调节了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诚如《荀子》中所述:“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4]”可见,礼是人们行为的尺度和行事的依据,人如果不依礼而行,便无法在社会上立身成名。剧中的布兰琪做人处事皆以自己的喜好、欲望为先,没有主动用“礼”去节制自身日常行为的意识。因而,生活中各种矛盾冲突对其随时都是一种考验,并不时让其陷入灵与肉撕裂的边缘,由此导致其迈向混乱乃至于极端的深渊。
显而易见,从千金小姐到“大众情人”,这种身份的骤变展现出布兰琪刻意用纵欲来排遣生活的忧愁和命运的多变,但她还未曾意识到身份转变所可能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关于伦理身份,儒家的“五伦”可谓是经世致用的伦理理论。“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种不同的伦理关系中,每一伦都包含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每种角色都有与该角色相对应的道德规范”[5]。《欲望号街车》中,布兰琪身处不同的伦理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她只是一味地从各种角色中获取荣誉、虚荣、利益等有利元素,从未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纵然她的血亲、丈夫、同事等等都有品德或行为上的瑕疵,但她作为自身价值实践的主体,并没有认清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反而时时以消极、逃避、自弃的方式回应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如若她对家中亲人多一份人性关怀,对自身欲求多一份合理管制,给丈夫一次解释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减震的空间,安守不同伦理身份所应恪守的伦理规范,那么迎接她的也许不会是剧中呈现的那种如无根之萍般的流浪生活,更不会由此接续产生如此这般左冲右突的伦理困境。
二、“白色的森林”:爱情幻想与伦理困境
通观整部戏剧,可以看出作者田纳西·威廉斯总是将丰富的笔端对准剧中女主人公遭遇的重重伦理困境。Blanche Dubois(布兰琪)取自法语,意为“白色的森林”。“白色”象征着布兰琪纯真、善良但又脆弱的一面,“森林”则象征其内心各种欲望交织在一起的隐秘世界。布兰琪个人性格所呈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与她的多重伦理身份遥相呼应。多重角色迭次切换中既有痛苦撕裂的迷茫,但更多体现的是她所经历的伦理混乱,而伦理混乱会进一步导致伦理困境的产生。
剧中,布兰琪每次面临的伦理困境皆与其不同伦理身份环境下的爱情幻想息息相关。在第一段与诗人艾伦的婚姻中,基于她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基于对初为人妻的向往,布兰琪选择了绝对地相信生活、相对光明、相信世间的一切美好,相信这个世界会始终对其报之以歌,相信她可以一直这样天真烂漫且无忧无虑地过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折射出布兰琪纯真善良的性格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这段婚姻中隐匿着某种疯狂的心态,因为艾伦的俊美和才华对她有着无以复加而又难以名状的魅力,“她简直连他踩过的地面都膜拜不已![6]”因此,当她偶然间发现艾伦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竟然是一名同性恋时,布兰琪内心惊愕不已,情绪混乱几近崩溃。理想中“王子与公主”般的爱情刹那间被按下了停止键,随之她也不得不面临着伦理两难的困境:究竟是结束婚姻还是将错就错。从“仁义”层面上说,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仁爱”和“道义”是对婚姻初衷最理想化的解释,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实践者维系和经营婚姻的智慧。如果布兰琪遵从这种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她便会以“仁者爱人”的精神来寻找丈夫成为同性恋的真正原因,进而客观、理智地审视他们的婚姻,毕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7]。但从“利己”角度来考虑,布兰琪对艾伦的疯狂爱恋没有得到相应的回赠,那么凭其“爱之深恨之切”的执拗态度,势必造成更加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一切发生的是那么果不其然,又是那么理所当然,布兰琪不具有“智者不惑”的人生历练经验总结,遇事必然也不会有“致中和”的智慧考量,凭本能、凭本性是其唯一而又别无他法的选择。
尽管布兰琪的婚姻困境随着丈夫的离世暂时告一段落,但是逃往其胞妹斯黛拉家中后所面临的新的处境却更加复杂和棘手。被逐出劳雷尔小镇后,位于新奥尔良埃里西安地段穷人区的斯黛拉家成了布兰琪在这世上仅存的、唯一的“伊甸园”。即便自己伤痕累累、一无所有,布兰琪在外人面前也总是显得那么矜持与优雅,仿佛在她身上根本不曾发生过些许苦难,她依然是生活在贝拉里夫庄园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庄园主女儿。然而,妹夫斯坦利却对布兰琪居高临下的姿态和装腔作势的做派极其不满,于是暗中调查这位贵族小姐来此穷乡僻壤的真正原因。布兰琪与斯坦利两人相互厌恶,却又互相吸引。前者需要后者填补情感世界的虚空和肉体上的欲求,后者则是贪婪前者高贵优雅的气质和摄人心魄的美貌。此刻,向自己的欲望妥协还是向现实妥协成为布兰琪的另一伦理困境。世人皆有爱与被爱的权力,但男女之间的关系应“发乎情,止乎于礼”,而“礼”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所谓“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4]329,言下之意,人需要将道德修养作为规范欲望的天平。如若布兰琪单纯因为欲望之“美”而逾越礼法、人伦的界限,那么妹妹的家庭秩序会受到重创,届时布兰琪也会遭受伦理规范的惩罚。但是,如若她不能尽快依附于某位男性,并且构建属于自己的归宿,那么本就没有安全感的布兰琪必然倍感自己无处容身、无所皈依。这段基于人性本能欲望的畸形情爱幻想再次将她推向两难的困境,使她在生活上窘态毕露,在心理上进退维谷,剪不断,理还乱。
历经情感挫折和现实打击的布兰琪已经接近心如死灰的边缘,这从她接连不断的酗酒以及难以自制的紧张中可见一斑。而米奇的翩然而至对她而言无异于绝处逢生时那一道微弱的曙光。他是布兰琪自婚姻失败后遇到的第一个“绅士”,因为他的温和敦厚在周围的野蛮粗俗的映衬下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米奇被布兰琪高雅的形象和不俗的谈吐深深地吸引并迅速对其萌生爱意。相应地,她也从米奇对她的崇拜与追求中再次体验了久违的愉悦之情和虚荣之心。在某次约会时,米奇讲述了自己的浪漫爱情故事,作为回应,布兰琪也向他诉说了过去不幸的婚姻。当米奇听完她的凄惨往事后,温柔地说:“你需要一个人。我也需要个人。可不可以——你和我?[6]”[这类似求婚的话语一瞬间照亮了布兰琪原本已黯然无色的生活。但是,米奇作为她精神和物质的拯救者,既让她重新点燃了爱情的希望之火,同时也使她再次面临了伦理两难的困境:是否该将她自己的真实经历坦诚相告?毕竟在与米奇交往的过程中,布兰琪刻意隐瞒了实际年龄和堕落往事,而诚信却是为人处世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8]”可见,诚实、信用是人类交际活动有序顺畅的根本保障。从长远意义来看,如果布兰琪继续带着厚重的面具伪装成高洁的淑女,那么她仍然会停留在阴暗的角落里承受着各种谎言所附加的恐惧和焦灼。随着真相揭晓的那一刻,她也必然因失信于他人而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会沦落至无处容身的悲惨境地。但从现实情况出发,如果她此时将自己过往的事实真相和盘托出,那么米奇极有可能对她生出厌恶之情并且背弃他们二人的婚约。而米奇好比是布兰琪“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可以帮她摆脱过去、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在失去诚信抑或是失去新生的艰难选择中,布兰琪陷入了深深的两难境地。
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对爱情充满向往和期盼,对世界还怀有深深的眷恋,才使布兰琪步入无法自拔的伦理困境。她仿佛一头受伤的小鹿在捉摸不定的命运世界里一通乱撞,根本不懂得如何运用世间的伦理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又称为“五常”)可谓融合了中国人丰富的处世智慧和核心的伦理价值,是社会独立个体应该拥有的五种最基本的道德修养。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该剧逐一呈现了这些道德修养给布兰琪带来的连锁反应,因为如何解决种种困境最终还是取决于她对其自身伦理价值的定位:是不顾人伦道德的任何羁绊,只求坐享其成、浮生若梦,终日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还是力求达到仁义、守礼、理智、诚信等为人品德的根本,以此与过去的自我彻底作别、与未来的新生挥手相望?无论布兰琪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自身部分甚至是整个利益的损失。正是由于难以权衡上述选择的利弊,布兰琪才会屡次面临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时踌躇不前。
三、“天堂福地”:伦理选择与悲剧人生
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2]”在《欲望号街车》一剧中,伴随着各种伦理困境的产生,女主人公布兰琪必然面临着各种伦理选择。这些选择不仅使整个戏剧情节紧凑、高潮迭起,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田纳西·威廉斯“言不尽意、意不尽情”的道德教诲方式。可以说,该作品以布兰琪悲剧人生的凄惨落幕令观众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道德觉醒。
布兰琪最初面临的伦理选择是是否继续保持“诗人妻子”的伦理身份,这不仅关乎她个人的名誉、虚荣,更是她今后物质生活最根本的保障。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布兰琪,从儿时直至少女初期都在极度被呵护的状态下长大的,是绝对的温室里的花朵。她习惯于各方云集的赞美之声,热衷于高雅奢华的社交场合,钟情于诗词典故的艺术氛围。当她遇见风度翩翩的艾伦时,立刻对其年青英俊的相貌和才华横溢的性情着迷不已,继而与后者“金童玉女”般的结合更是将布兰琪推至幸福的云端。可幸福的时光却总是那么离奇的短暂。自己引以为傲的丈夫竟然是同性恋,此种“出其不意”的命运安排让她顿时惊惶失措、无所适从。中国传统儒家将个人先天之所予谓之“性”,将后天之所历谓之“命”。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其中“命”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也能理解为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9]。因为挫折教育的天然缺乏和单纯执拗的性格使然,布兰琪仅凭着本能的冲动便在某次舞会上无情地揭露了丈夫的私隐,以至于造成了她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艾伦饮弹自尽。丈夫的突然自杀是布兰琪始料未及的,而亲人的相继辞世、家族产业的消失殆尽、经济来源的急剧匮乏,这些接踵而至的灾难如同噩梦般彻底改写了她的命运。自此,布兰琪不得不开始一段她之前从未经历的全新生活。但可悲的是,她既没有顺应个人命运起伏的客观规律,又未曾意识到主观努力对于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不敢直面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竟以放纵肉欲来释放内心的压抑和填补物质的需求,这种极端行为在文明社会里必然带来各类伦理问题的层层叠加,最终使其在劳雷尔丧失了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与体面。
由于无节制的糜烂生活使得布兰琪很快臭名昭著,所以她被迫去投奔世上唯一的亲人——妹妹斯黛拉。新的环境让布兰琪的精神与肉体得到了稍许放松,但过往的遭遇使她对这个世界持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并形成了犹如凌霄花般的攀援习惯,进而令其再次将自己置身于伦理选择的漩涡。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兰琪的闯入无疑是扰乱了斯黛拉家庭伦理的正常秩序,甚至是破坏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虽是同胞姊妹,斯黛拉却独具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特点。家道中落后,她选择与时为军士长的斯坦利私奔,很快便适应了新奥尔良穷人区的生活。而后者长期生活在兵营及底层社会,塑造出强壮有力的体格和随性不羁的性格。“活在当下”是他们维系婚姻秩序的不二法则,而仍然“怀念过去”的布兰琪明显与其格格不入。继续躲在自欺欺人的虚幻世界里还是勇敢面对现实,艰难的伦理选择已悄然呈现于寄人篱下的布兰琪面前。所谓“不知礼,无以立也”[8],“礼”作为一套规则体系,既是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规范。结合布兰琪的实际情况,唯有摆脱种种虚无缥缈的往日情怀,尽快让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运行规则和处事要求,才能在这个最后的容身之所获得久违的安全感。然而,妹夫斯坦利或明或暗的暧昧举动以及原始野性的男人味,激发了她几近消失的虚荣心,也挑起了她对两性情爱的欲望和幻想。难以自控的布兰琪开始尝试着引诱斯坦利,全然将两者的伦理身份和家庭的伦理规范抛诸脑后。此种乱伦行为不仅使斯坦利严重破环了婚姻伦理中的契约精神,也会让布兰琪因为“失礼”和“缺礼”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随着妹妹与丈夫家庭矛盾的逐步加深,布兰琪的“他者”形象便愈发显得格外醒目。斯坦利本就对她的突然造访及几乎肯定的长期居留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而后者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表下也仿佛隐藏了太多的秘密。当斯坦利着手调查事实真相并偶尔不怀好意地试探时,布兰琪只能通过抽烟、酗酒来安抚敏感的神经和紧张的情绪。躲在厚重的面具下,她用伪装的高贵与坚强来抚慰她即将无处安放的灵魂和身体。即便是遇到温暖她、爱慕她的“好男人”米奇时,她仍然选择将她堕落的往事尘封于心底,因为她天真地认为只有完善自己的伪装,才能紧紧地抓住米奇这“最后一根稻草”。从这个角度来说,布兰琪执着于那斑驳的面具其实是想早点摆脱傍人门户、身不由己的生活。但“不知言,无以知人也”[8],言下之意,“论辨思议之是非得失,生于心而发于言”[8],所以从人的言谈当中即可分辨他的人格、了解他的过往。布兰琪来到妹妹家中之后,一直以面具示人,不仅编造了各种虚无缥缈的谎言,连自己的年龄也刻意隐瞒,甚至时时立于昏暗处以防别人看清了自己早已青春不在的相貌。因此,不论妹妹斯黛拉还是“未婚夫”米奇都沉浸于布兰琪亲口描述的虚幻世界里,并对其“不幸的过去”充满同情和怜悯,认定她是被命运所负却能圣洁如白莲花般的女人。最为讽刺的是,在别人无法辨清布兰琪真实人性的同时,她自己也由于堆积的谎言时常陷入思绪混乱和困惑的状态,不明真假,不辨是非。而知道真相后的斯坦利立刻将其公布于众,此举彻底扯下了布兰琪赖以生存的“面具”。继众叛亲离后,布兰琪今后的生活也完全不明所从来,亦不知所去。
不难看出,布兰琪的悲剧始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族千金到委身于他人的“大众情人”,她始终游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丝毫不愿认清生活的真相,更拒绝接受现实的残酷。但是,唯有“知命”,人才能主动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积极主动地去实现最高的人生价值;唯有“知礼”,人才能利用合理、合法、有利的条件来达到立身处世的最高目标;唯有“知言”,人才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且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由此可见,布兰琪既不能拓宽生命的长度,也无法调整生命的亮度,那么她注定在自欺欺人的虚幻世界里和畸形欲望的不断膨胀中饱受煎熬。米奇的出现曾让她幻想着可以再次做回正常人,再次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她尝试由内而外地向光明的那边靠近。但知道真相后的米奇愤然离开,不留一丝余地,此刻本就万念俱灰的布兰琪却又遭到斯坦利的无情强暴而变成精神上的“失心疯”,最终走向了她真正的“天堂福地”——疯人院,全剧亦由此落幕。
四、结语
田纳西·威廉斯借助《欲望号街车》一剧,通过分层展示女主人公布兰琪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而给予观众丰富的道德启示,同时也达到了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2]”总而言之,威廉斯用他那极其敏锐的笔端,勾画出布兰琪矜持虚荣而又悲壮可叹的矛盾人生画面:幻想与现实的对立、本性与文明的冲突、绝望与欲望的共存。女主人公在与残酷现实的本能对抗中穷其一生、耗尽精力,其伦理悲剧宛若空谷回音,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即便威廉斯没有在剧中为布兰琪的悲剧人生设计出明确抑或是切实的解决方案,但该剧所凸显的伦理价值已润物无声般地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因此,整部剧既是那时那刻美国社会人文风俗的全画幅呈现,又体现了威廉斯“芥子纳须弥”的高超智慧。而布兰琪的伦理悲剧则时刻提醒着人们:处于各类矛盾交融交锋的时代,唯有以正确的伦理观为基础,做到正视自身、权衡利弊、大胆取舍,才能直面命运的困难和挫折,实现自己最美好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