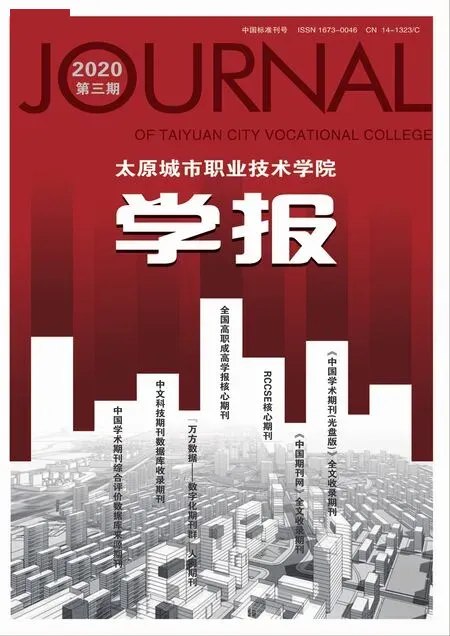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后现代主义视角
■孙 毓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在西方,翻译研究大约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注重文化转向。受其影响,翻译理论也开始努力突破原中心语的框架范围,进行译入语取向的探索。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随之被纳入了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的范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一种方法论。它既注重政治批判,也强调文化的介入。文化转向在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发展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的兴盛。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这几个流派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译者主体性的阐述。
一、后现代主义与翻译理论
(一)后现代主义的源起与发展
关于后现代究竟何时出现这个问题说法不一,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起初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它是一个由一系列观念组成的复杂术语,19世纪7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一词被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开始经常使用。学术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主要理论家们都反对用任何固定的形式来对他们所坚持的主义进行界定或者规范,因而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很难用精准的定论来概括。后现代涉及到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宽泛,包括工艺、艺术、建筑、时尚、音乐、影视、文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这些不同的领域都反对以特有的方式来继承原有的或者既定的理念,因此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他们都提出了各自领域内成体系的论述。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由具有不同特点的多项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这种融合性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涵盖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绝非几句话就能对它进行公式化的界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哲学和建筑学是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领域。哲学史上的不同学者都对相似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境况进行过各自的解说,但都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概括性的文本。大致说来,法国的解构主义算是其中能够将后现代主义在总体上做大致性表述的一个哲学文本了,它解构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解构主义认为对既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存在无限多层次解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表征或者符号都存在着多方面的意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用哪种意义对其进行解读就要看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反映了。
(二)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兴盛
在翻译理论方面,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已经影响到诸如解构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以及女性主义翻译观等的理论建构。认识论上是对本质主义哲学观当中语言意义单一性与固定性的否定[1]。我们说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并不是把翻译理论归属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只是借助于或者说结合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或者理论框架而兴起。当前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在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对翻译理论和研究整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是多种艺术主义的融合,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趋向性、解构而非建构的破坏性,因此国内的一些翻译理论学家遇之绕道而行。先不说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如何,单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许会对建构中的翻译学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由解构主义方法论为基石,涵盖了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这就会对受缚于本体性研究、遵循语言的线性逻辑规约的传统翻译理论带来巨大的质疑和冲击,它同时也能促使人们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对翻译理论进行思考。也正是受此影响,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展现出高度的协作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将研究拓展到翻译的外部,出现了现代翻译研究的第一次转向——文化转向。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转向的表现主要就是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2]。
1.解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解构主义兴起于法国,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德里达出版了《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确立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消解,具体来说,它应该看作是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进行的否定,之所以称“解构主义”,是因为它否定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几个重要的概念。同时,对语言提出了挑战,代表人物主要有德里达、本雅明和韦努蒂。解构主义自产生后被应用于学术界诸多领域,其中包括翻译领域。
解构主义对语言、意义的本质进行了论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将意义视为中心,认为意义先于语言而存在,将语言和意义分离,强调所谓的“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德里达提出的“延异”这一说法粉碎了这一幻想。德里达认为,意义并非产生于语言之前,而是“延异”嬉戏(the play of différance)之后产生,“延异”是意义产生的条件。由此而言,符号的意义、文本的意义都不是确定的,我们所捕捉到的意义只是在某个语境下的、暂时的意义。如此,意义不能同语言分离,更不是先于语言而存在,这种解构下的意义就不可能毫无损坏地从一种语言中提取出来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也就是说某一语言状态下的意义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用另一种语言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任何一个文本都包含多重意义,对其进行的任何一种解读都不能穷尽文本的意义。推而广之,德里达突破传统的思维,主张用“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来代替翻译,也就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3]。德里达的意义不确定论颠覆了意义确定论,同时对翻译的新诠释中翻译不再是意义的“等值”转换,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诠释解构主义过程中,翻译理论家们将传统翻译研究领域扩展到哲学、历史等层面,同时也拓展了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
2.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萨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首次将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了研究范围,将研究中心由文本形式转移到了文化政治上,显示了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倾向[4]。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者定位于殖民文化和相关联的前国或者附属国文化,旨在殖民文化的独立复兴,其中也包含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文化交流与对话。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确实意识到了世界范围内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的比例失衡状况,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化。以东方为代表的弱势文化和以西方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受到广泛关注。由此观点而言,翻译活动实际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殖民化的过程。为了消除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扭曲理解,展现东方殖民地语言与文化,抵制西方霸权主义的侵略,后殖民主义翻译家提出了相应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如霍米米巴巴提出“杂合”翻译策略,即翻译时将两种语言与文化的特征融和在一起,优势互补,呈献给读者原有文化基础上的优化文化。再比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即翻译时译者要将语言和文化差异传递给读者,为了消除文化霸权现象,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特意使用不透明、非地道的翻译表达方式。
3.女性主义
起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质疑西方传统中将男女割裂、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话语体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形成于上个世纪末,产生于加拿大,是将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结合的翻译理论。一直以来,关于翻译的女性气质话题经久不衰,它包括不同文化间的性别角色的差异及其不同的表达方式等。其代表人物有弗洛托、西蒙、张伯伦、斯皮瓦克、哈伍德等。纵观历史,不分种族地域,女性历来地位低下,相应的女性在翻译时以及翻译中女性的地位也很低下。女性主义翻译观旨在消除翻译中对女性的歧视,进而重新认定原有文本和已有译本的地位。成功的翻译不仅是语言使用的过程,还必须考虑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因素。基于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突出强调使用女性特有的语言展现独特的女性心理和在社会中的整体建构,转变女性的一直以来卑微的形象。同时将文化等因素考虑在内,从整体大背景下突出女性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解读。
二、传统翻译理论框架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这一主观能动性首先是以尊重翻译对象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展现其能动性,也就是在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创造性。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译者主体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主体性包括译前主体性和译中主体性。译前主体性是指译者翻译之前对翻译文本、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的考量;译中主体性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的理解、阐释以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等。
众所周知,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忠实”,认为翻译是忠实基础之上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传递。“忠实”的标准显然就是突出了原作的中心地位,任何翻译都要以原作为基准进行语言转换和信息的传递。原作及原作者被赋予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威。这样译者翻译时就要严格忠实于原作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从属地位。译者就是原作者的传声筒,自己基本陷于失声状态,主体性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甚至压制。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受原作者、原作、译者本身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严重影响主体性的发挥。基于这种状况,韦努蒂提出术语——译者的隐形,呼吁翻译界让译者“现身”,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主体意识的强化
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主体意识对应的是笛卡儿与康德式倡导的理性的主体性原理,以及强调主体性实践的带有中心性的现代主义文化,而后现代文化,比如詹姆森指出的那样,是一种远离中心化或者说是一种主体零散化的实践过程[5]。看似矛盾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意识确实在以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中得到了强化。
(一)解构主义是在文本之间、文本与译者之间的互文关系中去构建意义
对于文本的意义,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互文性和非原始性的特点。意义具有开放性,是因为意义本身具有不断扩散的特性,这样任一文本的意义就会同其他的文本形成互设的关系,存在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中。从意义的互文性我们可以看出,不存在最初的或者恒定不变的意义。这也是意义非原始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不会有任何一个译文文本的意义与原文的意义完全相符,由于文本的意义的开放性、互文性和非原始性的特点,翻译一个文本,就必须追根溯源,联系它之前的各种相关文本,并加以引用。这种情况下,就无从谈起忠实或对等。解构主义构建下,译者无法挖掘到已有的意义,译者的翻译实际是一种基于原文本的建构行为,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不断修改完善。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形成的解构主义理论用于翻译实践中,使译者从从属和被遮蔽中解放出来,肯定了译者的作用,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凸显了译者积极的主体性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译论认为译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模仿者,而应是积极主动的创造者,应该主动地把握和占有原文
后殖民主义体系下的译者在对受殖民地的“统识性”(hegemonic)翻译中,译文文本就是对殖民统治者强势文化的重新塑造、对受殖民统治的践民形象的重新刻画。基于此,后殖民主义者主张以另一种方式释放译者的主体性,既能够纠正“他者”文化被贬抑的形象,又可以借助于抵抗式的“混杂”策略反对殖民主义的“统识性控制”[6]。在后殖民主义翻译中,殖民主体充当了译者这一主体,他们是话语权力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其话语权力推广扩大,对被殖民者实施权力布控,使被殖民者臣服于他们的殖民统治,而翻译就充当了他们的殖民工具。这样后殖民主义翻译的译者就可以发挥主体性,为所说的“他者”文化正言。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论述基本一致
它是将性别因素纳入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认为译者主体性“是以争取女性的平等和尊严为起点,并不将译者、译本打入次一等级的观念,力求戒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那部分陈旧意识”[7]。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女性特有的角度出发,对原作和译作的关系进行论述,突出强调译者主体性,并对其加以补充阐释,同样拓展了翻译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者认同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或文化交流,还认为翻译是实现女性译者主张的手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另一个角度突破传统译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译者的性别,从不同的角度彰显译者的主体性。
综合以上三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意义都存在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中,文本和语言具有同质关系,无形之中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对意义的解读过程中,倡导突出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强调翻译中的女性意识;而后殖民主义译论认为译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模仿者,而应是积极主动的创造者,应该主动地把握和占有原文。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框架下的这几种翻译理论从不同的思考角度对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相同方向的诠释,即强化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四、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突出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相应地解决了翻译与意识形态、性别、文本阐释等问题,使我们进一步理解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主体意识之下的包含各种因素、力量的语言操作过程。后现代主义框架下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翻译理论的研究问题上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共同倡导强化译者的主体意识。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解读译者主体性,既有助于还原殖民主义在其文化交流中的真实境况,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了解译者活动的积极作用,深化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还有助于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推动翻译理论的建设。总之,后现代主义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应用于翻译研究,正在不断促进中国乃至西方以及整体翻译理论的完善,推动着翻译学的全面发展。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