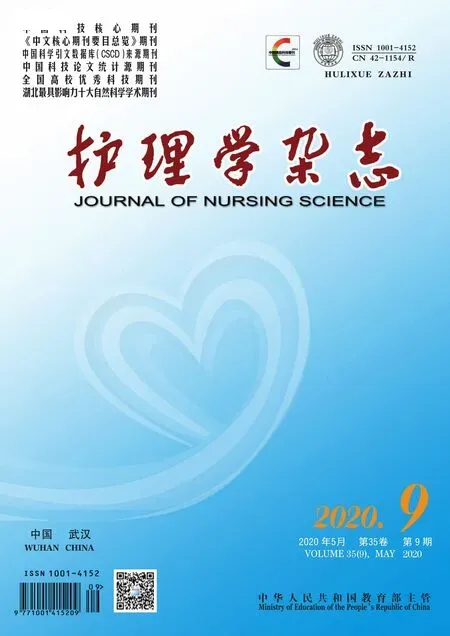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研究进展
王硕,吕利明,刘培培,杨昕宇,朱礼敬
2018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公布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乳腺癌位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患病人数占女性癌症总病例的24.2%[1]。我国乳腺癌发病率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中位年龄48~50岁,50岁以下约占57.4%[2]。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许多患者可以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5年生存率不断提升,乳腺癌“幸存者”已发展为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美国医学会(Institute of Medicine)认为癌症幸存者涵盖“从疾病确诊之时直到生命结束”这一时期的患者,包括初步诊治、过渡、持续生存三个阶段[3]。经过疾病确诊和一系列治疗等急性应激以后,乳腺癌幸存者面临着躯体改变、角色适应、社会融入等多方面挑战,容易出现自卑、抑郁等负性情绪,在人际交往中常常选择自我封闭、退缩和疏远,甚至出现社交焦虑、社交回避等问题,难以融入社会群体,并因此感受到孤独、无助和无意义感[4-5]。这种“社会疏离”状态不仅降低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其癌症复发率及长期存活率,甚至导致家庭及社会功能障碍,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6-7]。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研究不断深入,而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较少。本文对社会疏离进行概述,从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等方面总结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研究现状,为今后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社会疏离概念及测量工具
社会疏离最早由Biordi等[8]提出,认为社会疏离是与“归属感”相悖的被动“脱离感”,是个体脱离自己所在组织后主观体验到的情绪感受。随后,Carpenito-Moyet[9]指出,社会疏离是群体(或个体)的社交意愿得不到满足,并伴有孤独、寂寞或者无意义感等消极情绪的一种状态,该定义着重于疏离者心理感受的描述。而Finelay等[10]则认为社会疏离应考察客观行为改变,故包括社会性疏离和情感性疏离两个方面。其中,社会性疏离包含社交网络范围(如经常联系亲友的数量)及社会接触频率(如联系亲友的频率)等客观指标,情感性疏离包含孤独感等主观情绪体验。从上可以看出,目前关于社会疏离的定义尚无统一的界定,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社会疏离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遭到他人的消极对待(如无视、拒绝),未能与外界进行良好的互动,由此产生孤独和无助等消极情绪状态,并表现出冷漠及拒绝等消极行为的现象,既包含个体的主观感受,如社交焦虑、孤独感等,也包含个体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社会互动减少的客观行为改变,如社交回避等。
社会疏离目前尚缺乏成熟、通用的测评工具,研究者多根据社会疏离的内涵和行为表现选择相应的量表进行测评,目前较为常用的是ELSA社会疏离指数(ELSA Social Isolation Index)、Lubben社会联系量表简化版(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6,LSNS-6)、社会规定量表(Social Provisions Scale,SPS)和友谊量表(Friendship Scale,FS)等。ELSA社会疏离指数由Shankar等[11]根据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数据而编制,评估个体与亲友的接触频率以及社会活动的参与状况。当前主要用于老年人、膝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社会疏离的测量[12]。LSNS-6由波士顿大学网站提供,分为“家庭模块”和“朋友模块”两部分,通过评估与亲友联系的疏密程度对社会疏离进行筛查[13]。以上两个测评工具仅采用某些客观指标对社会疏离进行测量,缺少主观感受体验的评估。SPS由Russell等[14]编制,其依恋子量表可从情感上衡量个体与他人的疏离程度。也有研究者认为,SPS侧重于疏离者主观体验的评估,缺乏对客观行为变化的测量,因此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疏离的内涵[15]。FS由Hawthorne[16]编制,包含6个条目,从社会性疏离和情感性疏离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疏离的内涵,现已广泛应用于老年人、腰背痛患者。此外,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S)[17]、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ubscale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Scale,SAS)[18]、UCLA孤独感量表(Loneliness Scale)[19]也常被研究者作为社会疏离的测量工具,但均从主观或客观某一方面反映社会疏离状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可采用多个量表结合使用的方式,如李文涛[20]综合应用社交回避、社交焦虑和孤独感量表测评残疾人社会疏离现状。
2 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现状
乳腺癌幸存者在整个生存期会面临择业、婚姻、生育、社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因现存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其发展机会、职业竞争力等均处于弱势,导致社会融入困难,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因此其社会疏离状况成为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从社会参与、社交状况、是否重返工作岗位以及孤独感体验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乳腺癌幸存者的社会疏离问题。如Alicikus等[21]研究显示,多数乳腺癌幸存者不愿直视自己的身体与瘢痕,不敢去沙滩,不敢穿大领口夏装,在社交场合表现得不自信,以致不愿意或回避参加日常社交活动。Jakobsen等[4]对11例乳腺癌患者访谈发现,大多数患者治疗后社交活跃度降低,社会活动参与减少。国内研究也显示乳腺癌幸存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碍,如刘凤兰[22]发现,36.3%的乳腺癌术后患者会减少与家庭成员及社会接触,很少参加集体活动,12.5%从来不进行家庭外活动。林玉珍等[23]对282例乳房缺失患者调查发现,其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高于我国健康人,这与侯胜群等[24]的研究一致。此外,对中青年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对其融入社会、提高个人成就感和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人群重返工作岗位的情况不容乐观。Lee等[25]研究显示,在确诊后的3年内,288例乳腺癌幸存者中仅107例(37.1%)重返工作岗位。国内调查显示,57%的乳腺癌幸存者在诊断及治疗后会选择在家休养而不是恢复原有工作,30%未退休者中只有5%重返工作岗位[26]。孤独感是评估社会疏离的重要情感指标,国外学者将其描述为“可察觉的社会疏离”。Rosedale[27]的定性研究显示,乳腺癌幸存者在确诊及治疗后感到家人、朋友的冷落和疏远,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孤独感加重。
3 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
3.1人口社会学因素 年龄、婚姻、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均是影响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年轻、未婚的女性乳腺癌幸存者更容易发生社会疏离[23,28],可能因为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正处于学习、工作、生活的黄金时期,在各方面都担任着重要角色,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对其造成身心双重创伤。此外,相对于已婚患者,未婚患者面临择偶,社交活动更加丰富,诊断及治疗带来的躯体改变对其打击更大,使其趋于回避社会交往。Cobo-Cuenca等[29]研究发现,有伴侣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生活满意度较高,而离婚或丧偶患者有更多的孤独感,社会疏离发生率更高。需要经常外出应酬以及对形象要求较高的职业女性在患病后往往回避外出及社交活动,社会疏离程度较重。如国内研究发现,个体经营者的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相对较高[22]。Kroenke等[30]发现,文化程度、经济地位高的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发生率较低,原因可能为文化程度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理智、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突发事件,经济地位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林玉珍等[23]研究显示,高学历及高收入人群的自尊水平较高,且具有更高的精神生活追求,感知到的社会疏离较重。因此,文化程度以及经济状况对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
3.2身体意象改变 身体意象是个体对自身外表的主观印象,是通过自我观察和观察别人对自己身体的反应而建立的心理认知[31]。乳腺癌患者术后面临乳房缺失这一形象改变,加之公众由此产生的歧视和疏远,患者感知到的病耻感较重,影响其正常的社会交往。因此,身体意象的变化是导致社会疏离的直接原因。质性研究表明,乳腺癌术后患者因不满意自己胸部的瘢痕和整体外观而选择回避日常社交活动,以掩盖或隐藏乳房缺失,最终导致交际圈缩小,社会功能下降,造成孤独、封闭[21,31]。Suwankhong等[31]访谈20名40~79岁泰国女性,她们在术后因对自己的外形失去信心而产生病耻感,逐渐减少社交活动而孤立自己。侯胜群等[24]研究也发现,非保乳手术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水平明显高于保乳手术者。此外,放化疗引起的头发、眉毛脱落和瘢痕、色素沉着等皮肤改变,也会影响患者的身体意象,使其对社交产生恐惧。因此,对形象要求较高的乳腺癌患者可推荐乳房重建,或指导佩戴义乳等方式弥补形体的缺陷,同时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形象指导,如佩戴假发、头巾等掩盖脱发的困扰,做好面部护理以预防皮肤损伤,增强患者的自信心,保持正常的社会活动。2010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已将术后乳房重建纳入乳腺癌综合治疗[32]。
3.3负性情绪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会影响患者的认知,使其对治疗和预后悲观,长期处于自我贬低的状态,并加重对躯体不适的感受性,回避与他人的交往,社会参与困难。Puigpins-Riera等[33]研究发现,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社会疏离得分与焦虑、抑郁具有高度相关性,即焦虑、抑郁情绪越重,越容易发生社会疏离。国外一项定性研究表明,与死亡的持续联系会增加乳腺癌患者的焦虑和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会抑制其社会交流,导致社会脱节[6]。国内调查发现,中青年乳腺癌幸存者抑郁得分越高,社会参与程度越低[34]。提示医务人员在对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问题进行干预时应重视心理因素的影响。
3.4社会支持 家人及朋友等社会支持可以增强患者的情绪认同感,减轻日常生活活动负担,并提供积极的应对信息和资源,提高其生活质量,减少社会疏离的发生。Trusson等[35]研究指出,因为癌症会加深对疾病和死亡的脆弱感,61%的健康人表明会选择避开癌症患者;此外,52%的乳腺癌幸存者提到,有时候他们的朋友或家人会避开他们,这使他们不愿外出参加团体活动。Hinzey等[5]研究明确指出社会环境与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相关性,外界提供的信息、资源、情感支持越多,患者感知到的疏离感程度越轻,与他人互动越频繁。Yildirim等[36]研究也显示癌症幸存者的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因此,通过举办同伴支持、以夫妻为中心的团体活动等,提高乳腺癌幸存者的情感、社会支持,对促进其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更好地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5其他 疾病造成的躯体不适以及治疗不良反应对乳腺癌幸存者的工作及社会活动具有负面影响,导致其社会参与减少,进而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疏离。Sleight[37]对9例乳腺癌幸存者访谈发现,原来喜欢参加娱乐活动的患者在患病后因为疲乏、缺乏精力而选择在家睡觉、看电视,避免外出活动;某些适龄工作患者由于疼痛、虚弱等停止工作,部分患者因躯体不适导致工作能力下降而被解雇,社会融入度下降。此外,乳腺癌患者治疗后多伴随头晕、健忘、难以集中注意力等现象,Jakobsen等[4]研究发现,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为了避免发生尴尬的场景往往选择回避社交场合。鉴于以上研究结果,医务人员在进行社会疏离问题干预时,应重视患者疲乏、疼痛等症状护理,提高其躯体功能。
4 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干预措施
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增强社会支持、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躯体状况等方面对乳腺癌幸存者的社会疏离问题进行干预,以团体干预方式为主,包括以下几种。
4.1综合性团体心理治疗 团体心理治疗是指通过团体活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团体氛围、团体治疗师的引导、激发与唤醒,在团体中获得情感支持,增强归属感、认同感、亲密感等积极体验,引导个体探索个人价值、发现共同情感,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38-39]。综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包含心理教育、压力管理、支持性治疗及放松训练等多项内容,是目前采用最多的团体心理干预方式。Fukui等[38]将5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每周1次、每次1.5 h、为期6个月的团体心理干预,包括健康教育、应对技能训练、压力管理和心理支持4个方面,具体内容有提供缓解癌症压力与疾病治疗的相关知识,帮助其应对身体形象的改变和复发恐惧,增强与家人、朋友、医生的沟通技能,指导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孤独感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朋友的互动频率以及互动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Heiney等[39]研究中,实验组接受名为“STORY(Sisters Tell Others and Revive Yourself)”的团体心理治疗,干预以电话会议的形式进行,每周1次,每次90 min,持续8周,包括患者个人故事分享,提供治疗、自我形象、压力管理等方面的信息,组织家庭、社会关系的应对训练,改善了患者的社会疏离状况。团体心理治疗具有效率高、影响力大、后续效果好的优点,近几年已广泛应用于癌症患者心理社会问题的干预。但该治疗方式需要干预者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应选取专业的心理治疗师领导实施。
4.2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 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Supportive-Expressive Group Therapy,SEGT)是以存在主义为导向、以情感为中心的认知心理疗法,由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等多学科人员组织,引导小组成员讨论和表达各种相关主题,如控制疾病症状、获取社会支持、处理对复发和死亡的恐惧等[40]。Tabrizi等[40]将81例乳腺癌幸存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参加每周1次,每次90 min,为期12周的支持性表达讨论组,会议主题包括提供应对疾病和复发恐惧的心理知识,阐述压力管理和疾病应对策略,制定未来康复计划,鼓励小组成员积极参与并进行情感表达,建立新的社会支持。干预结束后实验组的孤独感得分显著降低,社会功能明显改善,8周后随访显示,两组得分仍有统计学差异,说明支持性表达对改善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具有长期效果。Brandão等[41]对26例乳腺癌幸存者进行为期16周的支持性表达团体干预,内容包括促进情感表达、鼓励接受身体形象的改变、增强应对技能、改善家庭和社会支持,干预结束后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了解患者的感受,结果发现患者的满意度较高,他们认为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有所提升,应对疾病的方式更加积极乐观,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也得到改善,与他人的互动增加。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有助于患者宣泄负性情绪,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增强社会支持,这使他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下降,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增加。然而,当前研究中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的干预时间、频率以及小组人数、规模各不相同,最佳的干预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4.3基于正念的团体心理治疗 正念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不做任何判断的集中注意方式。正念团体治疗通过团体内的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观察、学习和体验中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增强心理灵活性和社会适应能力[42]。Dobos等[42]对117例乳腺癌幸存者进行正念团体干预,内容包括基于正念的冥想、瑜伽、生活方式指导以及认知行为训练,共11周,每次120~150 min,每周1次,干预结束时及3个月后随访的社会功能得分较干预前显著增加,表明正念团体干预改善了患者的社会疏离状况。Carlson等[43]将271例乳腺癌幸存者分为正念团体实验组、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正念团体干预包括正念冥想和瑜伽练习,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包括团体支持和情感表达,对照组接受压力管理训练,干预时间均为每周1次,每次90 min,共12周。干预结束时及12个月后随访显示,正念团体实验组社会功能以及情感、信息等社会支持得分均高于支持性表达小组治疗组和对照组,说明正念团体干预对社会疏离具有积极的干预效果。分析原因可能为正念团体干预在增强社会支持的同时,培养了患者的心智,促进其保持灵活、接纳和存在,更加平和地应对疾病,减轻社交焦虑和恐惧,社会联系增加。
4.4其他 Floyd等[44]Meta分析指出,团体运动干预通过骑自行车、跑步、跳舞、太极等有氧运动和抗阻力训练,改善了患者的疲劳、焦虑、抑郁等身心问题,同时,小组形式的运动干预为患者提供了社交互动的机会,可以满足乳腺癌幸存者的心理社会需求,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减轻社会疏离水平。同伴支持是具有相同生活环境和经历的特定人群之间通过经验移情和信息共享为目标人群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45],同伴支持更容易让患者获得情感共鸣,满足其信息需求,增加整体幸福感。Power等[45]对8例乳腺癌幸存者进行每周1次,每次2.5 h,为期7周的同伴支持干预,干预人员由康复效果好并经过同伴支持专业培训的乳腺癌幸存者、乳腺癌专科护士、志愿者组成,提供缓解淋巴水肿、上肢功能锻炼等康复信息,交流、分享疾病康复经验,干预后患者重返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家庭、社会功能有所改善。
5 小结
目前我国关于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①社会疏离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定义,其内涵及外延仍需进一步探讨和梳理。目前较为公认的是社会疏离包含社会性疏离和情感性疏离两个方面,但当前关于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研究多局限于其中某一方面,缺少全面、整合性研究。未来应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综合考察乳腺癌幸存者的社会疏离现状,从个人、家庭及社会层面深入分析其特点及影响因素,为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干预工作提供依据。②尽管国内外对社会疏离的研究不断深入,但仍缺乏成熟、通用的测评工具,无法准确、全面对其进行评估。今后应根据社会疏离的内涵和特征开发、研制信效度高的测量工具,尤其是针对乳腺癌人群的特异性量表,以便准确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疏离状况以及客观评价干预工作的有效性。③当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多为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缺少深入的质性研究以及相关干预性研究。今后应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了解乳腺癌幸存者社会疏离的特点,并借鉴国外经验,从疾病、心理、社会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社会介入工作,以提高该人群的生存质量,促进其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