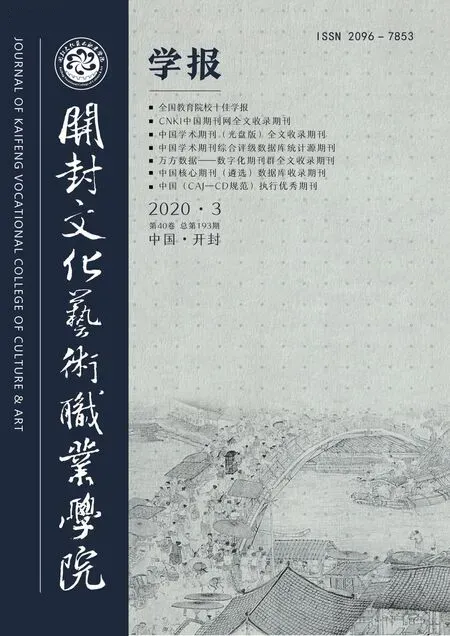明清戏曲中的诗学理论
——以“诗言志”与“诗缘情”为例
强 朵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戏曲在本质上属于叙事文体,然而,中国古代戏曲又被称为“剧诗”,其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诗歌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1]16的观点奠定了我国古代文论一元论的基调,即所有文体的源流和本质是相同的,并由此派生出形态各异的文体。众所周知,词是由诗歌发展演变而来的,其实戏曲也是由诗歌所派生出来的。明代戏曲家臧懋循就曾说过:“所论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其源本出于一。”[2]162到了近代,姚华在其戏曲文论《曲海一勺》中把诗歌比喻成是强大的树干,而南北诸曲及其衍生出来的剧种,则是这个树干上的众多分枝,“综之,北曲以乐府为宗,南曲以诗余为祖,丛流溯源,强为断代,实则与乐府诗余,皆诗之所出也。以诗视乐府,以乐府为诗余,以诗余视曲”[3]162。姚华把戏曲称之为“诗余”,认为曲承于诗,由此可见戏曲与诗歌之间的关系。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强调的是文学艺术的政治教化功能。此外,自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4]后,“诗缘情”便成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的另一重要命题。“诗缘情”注重情感的抒发,主张遵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实际上,“情”与“志”都是从心而发,但“诗缘情”更侧重于表达脱离礼乐文化的制约而回归到情感本身的文学理想。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对于“言志”与“缘情”的讨论或者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绝大部分人限于在诗文的范畴里讨论这一问题,很少有人会涉及戏曲。事实上,作为“诗余”的戏曲也能体现出传统诗学中的“言志”与“缘情”理论。
一、明清戏曲中的“诗言志”理论
“诗言志”强调礼乐精神对情感的净化与提升,要求诗歌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258的中正之美,强调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实际上,“言志”理论在戏曲中也有很明显的表现。
明代初期的戏曲有着浓厚的伦理教化色彩,这与当时统治阶级推行程朱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元璋大力推行程朱理学,表现在戏曲方面则是他对标举风化、有益人心的《琵琶记》给予了高度认可:“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6]95
所谓上行下效,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代弘治年间的邱濬投统治者所好,创作了《五伦全备记》等传奇。《五伦全备记》从题目上来看就表现出浓厚的教化色彩,文章开篇为“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若于伦理不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6]95。在作者邱濬看来,伍子胥的传人伍伦全及其异母兄弟伍伦备等人既是忠臣孝子,又是夫妻和睦、兄友弟恭、朋友信任的五伦典型。作者创作这样的传奇作品,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主要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喜好,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统治的目的。由于《五伦全备记》牺牲了作品的审美性而一味追求对民众的教化,违背了艺术的真实性,因而被明人斥为“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7]239。
“言志”这一诗学理论在清代戏曲中也有所体现。《桃花扇》中李香君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孔尚任所追求的中正之情。剧中李香君的痴情和前代戏曲中的衷情女子形象有很大不同。之前戏曲中的女子绝大多数或是衷情于自己的爱情,或是衷情于自己的丈夫。但在《桃花扇》中,李香君衷情于国家民族,在这一点上就体现了孔尚任对情感的态度:情不能过度,应表现中正之情。孔尚任在其所写的《桃花扇小引》一文中认为,传奇“旨趣实本于《三百篇》”,应“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为目的,并进一步阐述他创作《桃花扇》的目的是“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8]1。孔尚任明确提出传奇的旨趣来源于诗三百,传奇也应该以“警世易俗,辅王化”为目的,这其实就是“诗言志”在《桃花扇》中的表现。
综上所述,“言志”理论要求明清戏曲不能过多地强调个人的情感,戏曲所表达的主题也是要有益于风化,有益于国家统治。“言志”理论一旦运用不当就会沦为统治阶级宣扬教化、稳固统治的工具,丧失其文学性。
二、明清戏曲中的“诗缘情”理论
“诗缘情”强调的是诗歌的创作动机——情感,主张挣脱传统礼乐精神、政治教化对诗歌的束缚,确立情感在诗歌创作和诗歌内容中的主导地位。明清时期不少的戏曲主张及创作都强调情感的重要性。
徐渭的戏曲主张明显地表现出尚真的倾向。在徐渭看来,戏曲要表现“真我面目”“无一字不写其胸膈者”[9]103。徐渭认为,戏曲要最大程度地反映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不能矫揉造作地进行空洞的说教。
之后,汤显祖在发展徐渭所倡导的崇尚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著名的唯情说。唯情说认为,戏曲的本质在于表现情。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更是直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0]1“情不知所起”中的“情”是人的真情,只有真情才可以“一往而深”,进而达到“至情”,也只有“至情”才可以达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境界。在汤显祖看来,情可以将生死转化,而这种转化表现出作者对情感自由抒发的追求。汤显祖高举“唯情说”的大旗,让情感在戏曲作品中居首位,可见在其戏曲创作中“缘情”理论的重要性。
清代的传奇《长生殿》也反映了“诗缘情”的诗学主张。洪昇在《长生殿》剧本第一出《传概》中,通过剧中的曲词表达了他对情的认可:“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11]1
在《长生殿》中,洪昇不仅颂扬“精诚不散”的男女爱情,也赞扬“感金石,回天地”的忠孝之情,这些都表现出他对人世间真情的歌颂与赞美。在洪昇的眼中,这种真情在现实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在戏曲创作中将这种真情表现出来。虽然目前学界对《长生殿》的主题仍存在争议,但是作品中对李、杨之间真情的肯定与赞美是存在的。在笔者看来,《长生殿》的创作并不是以政治教化为目的。如果洪昇是为了政治教化而创作《长生殿》,清代的文人就不会发出“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感叹。
“缘情”理论在明清戏曲中的表现是作者大胆地抒发自己心中的真情实感,为文学而文学。但是,如果“缘情”理论被过度使用,则会导致滥情论的出现,使戏曲品格变得庸俗,甚至是低俗。
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做到“言志”与“缘情”并重,二者不可偏废,无论倾向于哪一方面,都会降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与审美性。“言志”与“缘情”孰优孰劣也不应该是探讨的重点,这两种诗学理论都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一旦超过了界限,就会导致教化论或者滥情论作品的出现。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做到两者兼顾,而不是走向极端。
戏曲由诗歌发展演变而来,自然会受到诗歌的影响,戏曲中所体现的“言志”与“缘情”理论让戏曲同样能发挥正统文学的作用,也让戏曲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