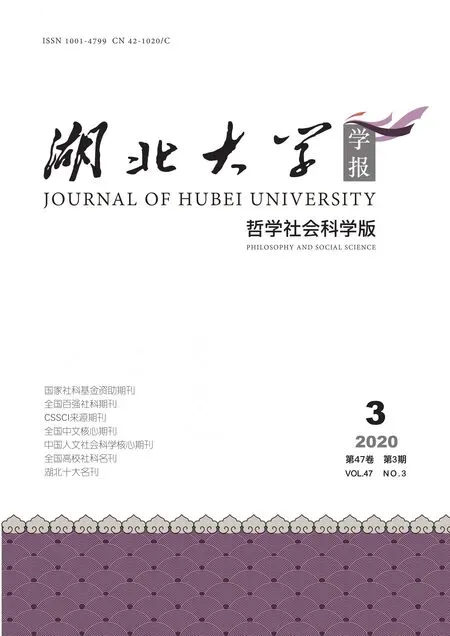和解与黑格尔的观念论体系
彭 超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和解与黑格尔观念论体系的现实性密切相关。和解的现实性需要观念论的体系提供支撑,观念论体系的现实性又需要和解的现实性来提供印证。黑格尔借助他的辩证逻辑较好地满足了前一种需要,却以一些应用逻辑学去应对后一种需要,以至于人们对黑格尔式的和解产生了十分不同的看法。黑格尔早年曾论及若干不同种类的和解,与《精神现象学》以及《逻辑学》最终达到的和解相比,它们往往过于简单,不能真正地实现和解本应起到的作用,反而提示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以及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巨大鸿沟。它们是黑格尔独特的观念论体系产生的背景。这个体系似乎包含着对那些对立状况的彻底解决方案,但在不同的人看来,黑格尔的和解观念及其所承载的现实的力量或是软弱无力的,或是任性暴力的。这两种看法的分裂已经是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挑战,但更大的挑战则来自它们之间可能的结合。毕竟让软弱者服从,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任性者的帮助。不过,要求易于和解的弱者与倾向不和解的强者和解,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和解的初衷。黑格尔关于和解的真正看法是什么,需要结合观念论体系产生前和形成中的状况予以澄清,这一看法有哪些问题,也需要结合观念论在现实中的落地情况进行审视。
一、黑格尔和解观的来源和发展
从词源上看,和解(Versöhnung,versöhnen)一词来自Sühne(赎罪),它与黑格尔所处的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黑格尔早年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那时他也曾以神学的角度审视和解问题。他在布道辞中谈到了和解性以及不和解性,并认为不和解的性情是使一个人堪称真正基督徒的行为(即爱)的反面,它源于自爱。不和解性不是完全不想和解,而是在和解中只想到自己,于是虽然倾向于调解(Aussöhnung),但由于自己的自负而做不到(1)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1.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9,S.60-62.。只有通过真诚的和解性,才能确保上帝对罪的赦免(2)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1. S.65.。和解性(Versöhnlichkeit)是形容词versöhnlich的名词化,黑格尔往往用它表达一种接受和解的倾向(3)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2014,S.129.或达成和解的乐意(4)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S.205.,它是人能够具有的一种特性。和解(Versöhnung)是动词versöhnen的名词化,它侧重于表达提供和解的行动及其结果。相互争执的普通人可以达成和解,但人与上帝的最终和解只能由上帝来完成(5)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1. S.237;Band 2. S.129.。
在黑格尔之前,康德也曾指出人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仅凭自己做不到和解,最多只能做到虔敬,但有能力并且应该符合义务地去生活。因此他认为德性教义要先于虔敬教义,虔敬教义只是加强德性意念的手段。和解的教义也是跟随在德性教义之后的,它能够加强德性带来的独立自主的勇气,因为它将人无法改变的东西设想为已被上帝解决的,从而缓解了人们对徒劳无功的惧怕(6)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187-188页。,并也有助于将人引向虔敬的良好生活方式(7)Kant,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XXIII.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55,S.124.。可以说,和解的教义在德性与虔敬之间,对这两者都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它本身仍然属于奥秘(8)Kant,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XIX.Berlin und Leipzig:Walter de Gruyter,1984,S.629.。另外,和解性一词在康德那里较少使用,并且也具有不同的意义。他将这种与复仇相对的和解性与拉丁文placabilitas(易宽慰)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人的义务(9)Kant,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XXIII. S.408.。
早年的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康德等人的主观宗教原则,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客观宗教接纳进来,发挥客观教义对主观原则的促进作用以建立一种民众宗教,避免主观原则成为私人宗教。他对和解问题的关注重点转到了人和神所共有的和解性上。神的和解性在于他对人的爱,他乐意与人和解,赦免人的罪。人的和解性也在于他对神以及他人的爱,他接受神提供的和解,乐意和他人达成和解。黑格尔认为,爱不仅能和解罪人和他的命运,它还能和解人与德性,甚至是德性的唯一原则,没有爱的原则,任何德性同样也是无德(10)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S.223.,这显然是针对着康德的德性学说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德性法则坚持着它的威严,不让自己被爱所克服,它是不和解性(11)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S.126.,而黑格尔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和解性是一种自爱和自负(12)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1. S.60.,律法主义奉行的就是不和解性。黑格尔认为一个想要恢复人性的全面性的人绝不可能选择康德那样的道路。他借耶稣的登山宝训强调了和解性的重要性(13)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S.157-158.,那里所提到的虚心的、温柔的、饥渴慕义、使人和睦的人,都是具有和解性的人。在黑格尔当时的理解中,和解性是爱的变形,它是一种天赋,而爱是对全体的感觉,它能避免人的本质的分裂。在这种和解性中,法则失去形式,概念被生命排除,这看似损失而实为无限的收获(14)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S.157-158,160-163.。
数年之后,黑格尔已经发现这种收获仍是有限的,想要获得无限的收获,还需要更进一步。在耶拿期间,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宗教,并在更多维度上思考和解问题。在《伦理体系·誊清草稿1802/03》中,他指出,“在君主制中,君主的旁边一定会兴起一种宗教;君主是全体的同一性,不过是在经验形态中的同一性;君主越是经验性的,民众越是未开化的,宗教就越具有强力并将自身建立得更加独立。民众愈是与自己本身、与自然和伦理同一,也就愈发多地将神性的东西纳入自身,并且愈是失去了这种与他作对的宗教;民众于是经由非宗教的、知性的无幻想性走过了与世界和自己本身的和解”(15)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5.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98,S.361.。这番表述将和解问题与政治、历史、伦理等领域联系起来,思考的出发点则不再是神学,而是转向了哲学。
黑格尔将和解个人的个别性与世界的普遍的东西当作了哲学的任务(16)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5. S.367.。这时的他已经认为理性与信仰的对立是哲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之前的哲学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种对立。他在与谢林共同创办并撰稿的《哲学评论》杂志中指出,与宗教达成和平的那种启蒙的理性其实只是知性,它仍然是信仰的婢女,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的哲学都有这个问题。这些哲学都是北方的、新教的主观性原则,它们意图保持与经验事物的不和解性,但最终所达到的仍然是与经验性的客观之物的和解,它们的主观性与经验性仍然脱不了干系。黑格尔认为这三种主观哲学无法达到真正的观念论,真正的观念论就在于它是客观的思维(17)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4.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68,S.315-322.。
不过,黑格尔在初步构思他的哲学体系时,并没有选用和解这个具有神学来源且与情感有关的词汇作为沟通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限的桥梁,而是开始使用一个原本存在于哲学中并且相当中性的词汇——中介(Vermittlung)。
在《耶拿体系草稿》中,对中介的讨论集中出现在逻辑学中关于“交互作用”的一节(18)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7.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71,S.67-73.,在黑格尔后来较为完整的逻辑学文本中,中介思想则已经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存在论中有隐秘的中介,它的开端虽然是直接性,但这恰恰是《精神现象学》的中介运动的结果,紧接着开端的“变易”也已经暗含了逻辑学本身的中介,而在质与量的互为依凭中,中介浮出了水面,存在论得以过渡到本质论。本质论中有发散的中介,它是从存在论所隐含的那种单纯的中介向完整的相互中介过渡的中间环节。这种中介的双方各自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有限的中介,并保持一个与这个中介不相干的另一部分向外发散。以这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只是非本质的本质性,只是可能性或偶然性,而那个发散出去的外在性作为直接的东西,又处于与内在的东西的有限中介之中。在种种相互中介的互相交替和补足之下,必然性和现实性就被建立起来了,相互中介成了交互作用,这种作用是相互成全而非相互制约。这就使得原本发散的中介成为概念论中的完整的自身中介。
黑格尔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逻辑学部分的本质论末尾指出“思维乃是自己在他物内与自身共进,亦即是解放。这种解放不是抽象式的逃遁”,并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补充说,这种解放是我,是自由精神,是爱,是极乐感(19)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这样的措辞是对他早年的所见所思的回应,它透露了中介思想所包含的新的和解作用,展示了他的和解观的转变。黑格尔早年谈及和解性时,“我”还是道德概念的对象(20)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2. S.5.,自由还与灵魂之美有关,爱也只是被动地去感觉全体并作出反应,极乐感也还只是一种幸福。那种和解性无法独自弥合各种分裂与对立,为此人们还需要其他的和解性,比如上帝的和解性、他人的和解性。而和解性的各不相同本身就是问题,就是分裂与对立的表现,就是它们的不和解性。这种和解性不仅无法自救,还由于它们自己的不和解性而面对着某种更高的不和解性(如康德的德性法则)的强制。那时的黑格尔虽然在不和解性面前重新主张和解性,但并没有提出和解的具体方案。离开关于和解性与不和解性的争论,是黑格尔哲学发展的第一步。但如果只有这一步,如果仅仅是避开那些不同而去追求同一,黑格尔的思想就难以与谢林的思想区分开来。谢林在写给黑格尔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一切事情的确都可以和解,除了一件事情”(21)Schelling,Aus Schellings Leben:in Briefen,zweiter Band.1803-1820.Leipzig:Verlag von S. Hirzel,1870,S.124.。与谢林对有限事物的和解性和无限者的不和解性的这种坚持不同,在黑格尔这里,一切事情可以相互和解,绝对者也可以与一切事情和解。它在那些他物中仍然与自身共进,它带着自己走进了它们,即使它们还不知道这一点。这种总体的和解性能将一切事情从不和解性中救赎出来,并且同时也是对不和解性本身的救赎。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不和解性失去了它的崇高地位,它不再具有超出有限的和解性的价值,而是变得和有限的和解性不相上下。坚持着那种不和解性的人或许会认为黑格尔的总体的和解性也是一种不和解性,是对不和解性的不和解,因此也包含着某种独断和暴力。但事实上,黑格尔的总体的和解性并不是不和解性的敌人,它是每一种不和解性的归宿,它包容了一切不和解性而不是驱逐和消灭它们,它就是那个在康德那里曾经被悬设而无法被认识的无限者所具有的和解性。
二、和解精神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形成
凭借着中介思想,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实现了对总体的和解性的概念把握。在此之前,《精神现象学》已经预先提供了意识向着这种和解性发展的经验。黑格尔在序言中指出了传统的和解性的局限、哲学家超越这种局限的尝试以及那些尝试的失败(2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建立在自身中介基础上的和解观(2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第12-13页。。这种和解观上的分别在正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精神现象学》始于意识的自在而单纯的和解性,完成于自在自为的无限的和解性,在这两种和解性之间,是各种各样的有限的和解性与不和解性。有限的和解性的变迁始终与意识对不和解性的经验以及作为不和解性的经验有关。在前一种经验中,意识保持着天真的和解性,在后一种经验中,意识开始观察到一种有目的的和解性,并将不和解性也变成了有目的的不和解性。当意识不再仅仅是和解性,也不再仅仅是不和解性,而是意识到自己同时拥有这两者于自身,它就开始走上了无限的和解之路。
(一)意识的天真的和解性
在《精神现象学》的正文中,和解一词直到自我意识一章的末尾才出现。意识部分的“感性”、“知觉”、“知性”三章并没有直接谈到和解,只在“知性”一章的末尾一处举例中提到了调解(Aussöhnung)(2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第102页。,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这三章与和解毫无关联。在它们展示的意识的未和解状态中就已经包含着意识的自在的和解性以及不和解性。感性确定性的接纳的态度首先显示为一种天真的和解性。但在对象面前保持天真,也可以被视为感性的不和解性,这意味着它将自己与对象区别开来,不对认识的方式与结果负责,只是确认了自己的无辜。但对象才是无辜的,它既没有邀请也没有拒绝感性对它的认识,没有特意针对意识去表现自己。它虽然在感性面前显得是一种不和解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责怪它。感性之所以没有真正认识到它,是因为感性只能获得有关对象的一些互不和解的个别性状,问题出在感性这边。由于意识是认知者,它就发展了它从一开始就抱有的和解性,承担起认知活动中求真的责任,成为了知觉。知觉扬弃了对象上各种个别的不和解性,使它们合在一起,和解为真实的事物。
然而,知觉的这种承担最初只是着眼于和解在对象上的各种不和解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和解性。它还是像在感性确定性中那样抱有一种在旁人看来自以为是的和解性,觉得自己不干涉对象,只是把对个别不和解性的接纳变成对诸多不和解性的统握就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这又是一种不和解性,它只想承担真,不想承担假。但对象仍是无辜的,因此如果在认知中产生了假象,那么这个责任也不得不由意识来承担。对真与假的双重承担使得意识反思到了自己,发现自己不仅仅出面和解了对象的各种属性的不和解性,还和解了作为实体的对象的不和解性与作为实体的意识的不和解性。在后一种和解中,意识达到了知性的层次。
知性在开始获取关于对象的观念时,再一次释放出天真的和解性,它退出了在知觉中它曾经有所承担、有所干涉的对象,重新保持一种不干涉、只统握的姿态。但这并不能使得对象直接地与它和解。知性获得的经验是对象本身的两个不和解的环节的和解性,是力和力的表现的和解性。这种和解性作为必然的规律是超感官的,也就是说,对于感性的意识而言是不和解的。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端,意识就是面对着对象的这种必然的不和解性表现出自己的和解性。和解性总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和解性,当我们谈到和解性的时候,已经从某一个真正的开端迈出一步了。如果要追溯那个开端,把第二个以及更多个事物都排除掉,回到对唯一一个事物的思考,那么我们就来到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在那里,作为开端的存在是一种不和解性。《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真正说来也是不和解性,不过这种不和解性不仅仅是对象的那种必然的不和解性。只要它开始认知对象,想与对象和解,它就同时也是自由的了。意识的不和解性其实是一种自由,但只有当意识成为了自我意识,它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二)自我意识以及理性的不和解性
经过意识部分的三章,意识已经能够发现,在它对待对象的那种天真的和解性背后有自在的不和解性。当意识还不知道这一点时,它还是无辜的,还是一种动物般的意识。一旦意识对这一点有所意识,发现自己既有和解性又有不和解性,它就成了自我意识。在对立的自我意识的斗争中,那些没有能力保持其不和解性但又不愿转而抱有和解性的自我意识被消灭掉了,留下的是有能力保持其不和解性的自我意识以及愿意与那些不和解性和解的自我意识,也就是主人与奴隶。主人需要奴隶对于主人的和解性,因为他需要奴隶为他消灭物的不和解性,而这使得奴隶在对物的加工改造中找回了自己的不和解性。在整个自我意识一章中,不和解性的对象是从外向内过渡的。意识的不和解性首先针对着外人,然后是针对着它与外人中间的物。从斯多葛主义到怀疑主义,是它对那些中间物的消极对待,最后在不幸的意识中,它成了完全对内的,成了自己对自己的不和解性。
对黑格尔而言,只有在出现这种不和解性之后,才值得谈和解问题。能和解自己对自己的不和解性的,才有可能是真的和解。和解是“不幸的意识之真正返回到自身”(2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第130页。,但不幸的意识本身并没有提高到一种和解的思维,黑格尔认为它只是一种无概念的默想,也就是说,它只是具有和解性,但并没有完成与自己的和解。它的和解性首先要向一个自身以外的中介者展示出来,借此它才能够回到自身,而回到了自身的它就成了理性。
理性的和解首先是唯心主义的和解。这种观念上的和解只是和解行动的开始,它仍然是一种和解性。但这种和解性既不是天真的,也不是被迫的,它具有一定的自信,可以容纳之前的和解性与不和解性了。理性作为和解性试图去容纳那对意识而言具有不和解性的事物,却观察到事物其实也有和解性,即有机物的目的性。理性对事物的和解性的这种认识,引起了它对自身所具有的和解性的现实性的观察,它最终发现那现实性就在它自己身上。
理性的自我意识在对象上拥有与自己的和解,而这直接就是对对象本身的不和解。从快乐的享受开始,自我意识在不和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它也不断地遭遇到别的不和解性。快乐遭遇到必然性,本心遭遇到现实,德行遭遇到世界进程。这些不和解性的对立运动揭示了自在的目的,达到了和解,但这种和解仍是虚假的、观念上的和解。要真正地把和解维持下来,就需要对虚假的和解保持不和解,需要一种比这种和解更高的普遍的不和解性来为它做保证。这种不和解性是康德哲学置于最高地位的绝对命令。黑格尔早年曾将这一法则与律法主义联系起来,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通过对立法以及审核法则的理性的批判,黑格尔揭露了普遍的不和解性并不现实,在现实中它并不是不和解,而是能与任何一种个别的不和解性和解,它的不和解性背后永远都有和解性。这种和解性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康德哲学之中,但它们的活动在黑格尔这里才真正地受到了重视。
(三)精神的三重和解
以不和解的方式去统领一切有限的和解性与不和解性是不现实的。要超越有限的和解性与不和解性,只能寄希望于和解。然而,任何在和解性与不和解性得到充分展开之前的貌似和解的状态都只是暂时的媾和,它难免带来新的不幸,但这也推进了不和解性的发展。当不和解性被推到极端,并且不仅具有最高的形式,还被付诸行动,形成了不和解性与不和解性针锋相对的状况,真正的和解就即将实现了。
1.世俗的和解
单纯理性范围内的不和解性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背后的和解性是现实的、活的伦理实体。但那些现实的和解性并不等于和解的实现,它们和意识最初的感性确定性一样天真。在“精神”一章中,黑格尔再一次展示了天真的失落和虚伪的形成。伦理从天真的和解性发展为抽象人格的不和解性,教化将不和解性发挥到极致,成为绝对自由的不和解性,道德将义务的不和解性现实化为良心的和解性,却难免再次落入虚伪的陷阱。然而,精神并不像立法和审核法则的理性那样虚伪而不自知。由于精神经验过理性的虚伪任性,并且起初就是那表面上绝对不和解而私下却具有特殊和解性的伦理实体,它就是从对法则的表里不一的认知中起步的,所以精神其实能够看到它自己的虚伪,看到和解性中也有不和解性。而理性起初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它只是对自身进行了一次同语反复的审核,根本没去看它实现出来会是怎样。不过,精神虽然能够看到自己的虚伪,却仍有可能视若无睹,这就是它更大的虚伪。但理性的那种只说不做也延续到了精神中并成为了进行道德评判的意识,它揭露了良心在行动中的虚伪,甚至不惜以袒露自己的虚伪来攻击那种虚伪,而这就将虚伪逼上了绝路。在这两个不和解性的遭遇中,有一种不和解性坚持着它直接的和解性,试图与不和解性切割,但这恰恰就体现了它的不和解性,说明它的坚持是无效的。继续顽抗下去也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不和解性迟早会放弃那种直接的坚持,转而对自己的不和解性有所担当,承认自己的和他人的不和解性都从属于某种普遍性。而既然意识已经一再经验到普遍的不和解性的虚伪,那么这种普遍性就只可能是普遍的和解性。在这里,和解第一次成为了现实。然而,从不和解性的对峙中抽身出来的和解还不是最终的、最全面的和解,它只是精神在遭遇自己的虚伪时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它只是接受现实。
2.超越的和解
精神的和解虽然是现实的,但它是在遭遇到自己的不和解性的不现实性之后才退回现实中的。这样达到的和解仍然依赖一些偶然的外在条件,它仍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和解性。如果精神没有遇到或没有发现其他的不和解性,或者其他的不和解性势单力薄无法与它抗衡,它就仍有可能心存侥幸,坚持不和解。这种尘世的精神还没有正面地去建构自己的现实性,没有从自己的和解性的方面出发进入到和解中。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它就成了超越的精神。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超越是通过宗教完成的。
精神首先仍从和解性出发。从对光明的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光的和解性与感光的和解性,而植物的感光的和解性会过渡到趋光、争光的不和解性,过渡到动物的不和解性,工匠则有意无意地将人的和解性注入到动物的形态中,于是工匠成为了艺术家,自然宗教过渡到了艺术宗教。艺术宗教从雕像的安静的和解性出发,在悲剧中再次展示了不同的不和解性的对立。与“精神”一章末尾的那次遭遇不同,由于走上绝路的不和解性是角色的而不是自己的,精神就没有退着回到一种有限的和解,而是在喜剧中看透了那些角色的不和解性,这也使得精神自己的超然的不和解性浮现出来。拯救这种不和解性是天启宗教的任务。和以往所尝试的和解不同,天启宗教并没有转向与不和解性对立的那种和解性。那种和解性是天真的而非善的,它不是不和解性的归宿,反而是不和解性的产生的背景。黑格尔早年曾认为不和解性是自爱,和解性是爱,这种区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这里,他已经发现“和解的第一环节”首先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去爱,而是如何对待这个“自”(2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第470页。。和解不是逃避自身而是返回自身,是认知到恶自在存在于定在之中,因此也可以说是认知到不和解性自在存在于定在之中。在宗教上,这体现为原罪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和解超越了那种受特殊条件限制的与他者的外在和解,成为一种普遍的、内在的和解。接下来,关于爱的问题也浮现出来了。在天启宗教中,意识只是暗自感觉到而非亲自直观到永恒的爱,于是黑格尔批评说,“它的和解只是在它的本心中,但同它的意识还是分裂为二的,并且它的现实性还是破碎的”(2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第474页。。彼岸的和解从直接的和解性出发,经过了中介并回到了直接性,但意识直接面对的仍是一个没有完成和解的此岸,它只能借助彼岸的和解表象将此岸的当下视为将得到和解的。
3.绝对的和解
在世俗中,意识最终经验到它向他人发出的不和解性是不现实的,于是它通过宽恕与和解扬弃了不和解性。在宗教中,意识最终获得了对彼岸的和解性的表象,但它在此岸的和解性又是暂未实现的,或者说此岸又被留给了不和解性。不和解性成了此岸或世俗所无法摆脱的枷锁。那么怎样使彼岸的和解在此岸生效呢?在天启宗教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仪式和程序被人为地设计出来作为中介,但它们始终都带有此岸的特征并仍然属于世俗的伦理,因此也难免陷入伪善。但人们已经通过向直接性的回归对天启宗教进行了更新,认识到在意识曾经看到的彼岸的和解中就已经包含了对和解如何来到此岸的表达,人们不再需要经过什么手续,仅凭对彼岸的信仰,就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来自彼岸的和解,而彼岸的和解方式也被此岸掌握,并把握为自己的和解方式。不过,这种新教的和解思想所强调的只是相对于那些有限的中介而言的直接性。如果说传统的天启宗教面临的问题是此岸的有限中介架空了彼岸,那么新教的问题就是彼岸的干瘪的直接性敷衍了此岸。黑格尔曾直言,新教模式的和解是“最新的,但也是最片面的”(2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7页。,因为它是主观性和它自身的和解。新教的苦痛“鄙弃一切与经验性的定在的和解”(29)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4.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68,S.319.。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将和解性与不和解性视为互相外在于对方的,时而坚持它们的对立,时而将它们混在一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做的是揭示这两者的内在关系。起初意识在对天真的和解性的坚持中不自觉地将自己区分为和解性与不和解性,并在对象的不和解性的引导下,意识到自己的不和解性,它将这种不和解性充分地发挥出来,最终在和解中超越了每一种不和解性。这种绝对和解是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并且经历了无数次的“不得已”之后被逼出来的,它是一种宝贵而脆弱的经验,需要被保持下来并传递给更多人。然而精神在保持和传播中面临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人们试图将它们保持起来,它们就僵化为陈规与教条,当人们试图去传播它们,它们就激化为压迫与入侵。在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的名下,人们曾经做了许多号称和解实则不和解的事情。这样的风险虽然也属于精神发展中的“不得已”,但人们不能总是宁愿去付出代价,以个体有限的生命去走精神的弯路,而是必须对这些“不得已”进行认识。绝对的和解是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而是包含了绝对认知的绝对精神,它扬弃了一般精神的弯路,是因为思想已经为它走过了弯路并找到了出路。
三、和解观念的建立与实行
和解精神所包含的绝对认知植根于辩证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概念的层次上解码了精神曾面临的“不得已”或不和解性,使绝对的和解上升为一种正面把握必然性并要求自身正面实行必然性的观念。
(一)和解作为观念论的终极形态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从个别意识的天真的和解性出发的,他的逻辑学则从所有事物的天然的不和解性出发,它关心的不是我们如何感受和应对事物的持存和变化,而是事物本身如何丝毫不受人们意谓的影响而独自持存与变化。这恰是引导意识发现自己的不和解性并最终同自身和解的关键因素。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第二版序言中,黑格尔指出只有在哲学中精神才能庆祝自己同自己的和解。这既表明精神的和解需要哲学的保证,也透露出在精神的和解中得到救赎的只有精神本身,而这还不够。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应对一般科学和教养的方式是与它们的内在矛盾(即不和解性)以及对矛盾的粉饰(即和解性)相矛盾(不和解),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独力达成与它们的和解,不能独力拯救它们。这个任务被交给哲学。哲学不仅要为精神自身的无限和解提供支持,还要为各种特殊的科学与教养的有限和解提供依据。因此,黑格尔认为哲学“进行和解,它朝着理性的东西去神化(verklärt)那显得不合道理(unrecht)的现实的东西,指出那在理念本身中有其根据的、理性借此将得以满足的东西本身”(30)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1.Band. Hamburg: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17,S.55.,这才是它的“最高的终极目的”(31)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第5页。。
黑格尔的这种哲学首先是逻辑学。在逻辑学的存在论中,存在可以被视为事物共同的不和解性,它没有与任何事物和解,甚至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与自己和解。但只有不和解性就等于无。无作为不和解性和存在这种不和解性统一于变易的不和解性中,因此变易是自己对自己的不和解性。这种对自己的不和解性首先表现为对他物的和解性,也就是定在的为他存在,但由于有了他物,它也就具备了与他物的区别,拥有了对他物的不和解性,成了自在存在。为他存在的和解性与自在存在的不和解性无法达成和解,它们在一种被黑格尔称为坏的无限性的不和解性中不断滑动。但在为他存在都有自在存在以及自在存在都有为他存在这一点上,它们的和解性与不和解性有了和解,存在也有了支点,成了自为存在。这种最初的自身和解被称为真的无限性,它的真是因为它在自身上带有和解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只是被发现,尚未被建立起来。在逻辑学接下来的部分,每一次和解同时都引出了新的不和解性,新的不和解性又参与到新的和解中。于是我们看到质的和解性(或不和解性)与量的不和解性(或和解性)统一于度的和解性,本质论则从这种和解性出发,通过和解性与不和解性的辩证进展,产生了作为和解性或不和解性的事物以及现象世界。不和解性与和解性同时存在于一个东西上,显示出的是和解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由此进入了思想中,并使得概念作为实体的真理性在原因与结果的交互作用中浮现出来。和精神的和解类似,概念的和解也曾暴露在风险之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概念的推理曾被用于论证上帝的存在。黑格尔指出了这种本体论证明的缺陷,即它只是一种抽象的、自在的同一性,差异或者不和解性仍然是与它对立的。只有让这些自为存在的有差异的东西与自在地被假定的同一性都过渡到一种它们在其中“得到和解”的同一中,才能解决概念的这种风险(32)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第137页。。这是黑格尔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逻辑学部分的正文中唯一一次提到和解,就是这种在绝对理念中才真正实现的和解使得黑格尔的观念论不同于过往的种种观念论,成为观念论的终极形态。
(二)观念论的落地姿态
从《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二版开始,黑格尔不仅在前言中强调了和解,还在导论中对他在法哲学中的和解进行了辩护。仅从法哲学本身的角度来看,这种辩护不无道理。黑格尔的重点不是要求我们与现实和解,而是希望在我们事实上已经与现实和解了的情况下,将这一和解公开出来,并认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和解。因为如果我们将事实上的和解隐藏起来,却在表面上坚持与现实的不和解,就会像其他各种各样的观念论那样陷入虚伪。《精神现象学》中曾经受到批评的那种立法和审核法则的理性就是如此,它事实上已经为各种内容大开方便之门,与各种内容都能和解,却还要假装自己在形式上的单纯,仿佛自己坚持着对不和解者的不和解。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指出柏拉图的空洞理想“只能作为一种腐败的东西表现出来”(33)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为了避免腐败的危险,这些观念最终都要寻求外来的援助,因此都是不完整的观念。由于那些援助也是些观念,它们最终就形成了一些表面上相互补足短板,实际却没有紧紧聚合在一起的观念群,在其中不和解性与和解性对立,现实与理想对立,有时这一个占上风,有时是另一个。身陷这些观念群的人也是这样来看待黑格尔的观念论的。他们在和解观念中也嗅到了某种腐败,但那或许是和他们自己身上的气味相似的气息。至少从完整性和公开性上看,黑格尔的观念论已经完成了对这些观念群的超越,他的逻辑学就能够单独地支持这一点。
然而,仅仅超越以往的观念论,并不能保证黑格尔和解观念的现实性。虽然绝对理念的和解性是不需要从外界获得援助就能自圆其说的,但它必须向外提供有效的援助才能真正地支撑起自己。黑格尔并没有彻底地满足观念论这种落地的需要,因为他另行安排了一系列一般观念作为现实性的代表,让它们在绝对观念真正落地之前就将它接走了。这样一来,绝对观念就只需要确保自己能显示在一般观念中,一般观念也只需要确保自己能承接绝对观念,理念和现实性的代表就能够达成和解。我们不能说这种相互肯定的安排一定是出于腐败的动机,但它确实难于避免腐败的结果,因为绝对观念用自己的绝对性掩护了一般观念的任意性,各种一般观念则联手衬托出绝对观念的完整性,这实际上陷入了另一种虚伪,即将现实层面的不和解隐藏起来,却在表面上显示出理念与现实的和解。这种和解不是绝对的和解,但不绝对也不可怕,在《精神现象学》就有许多次和解,除了最后一次之外,没有一次是绝对的,也没有一次不是朝向绝对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存在于和解精神与和解观念之间的一种区别:精神永远为否定保留了独立的一席之地,哪怕是绝对精神也不敢独占绝对,它在它的绝对性之外仍然看到了否定的东西,并因此向思想寻求支持,而绝对观念虽然在它的建立过程中包容了否定,但在它的终点上,所有否定都被安排在肯定中。
黑格尔的观念论体系在这种空前的肯定中达到了巅峰,它在不同科学中的实行颠覆了和解思想在《精神现象学》中从和解性到和解的上升的结构。从和解性到和解被视为绝对观念的落地,但这只是一种落地姿态。没有谁能够仅仅处于一般观念的境地而不面临着《精神现象学》中曾逼出和解精神的那些“不得已”,它们的现实性来自意识对必然性的经验。然而,虽然它们曾有力地支持了精神的提升并深刻地启发了思想,但自从思想成为了必然性的主人,它们的力量就成了思想能力的佐证,它们也沦为一般的现实。一般观念和一般现实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并不完美的和解,黑格尔没有强调其中的“不得已”,而是把这些和解的表现当成相互补充的(34)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第481页。,这看起来与逻辑学从本质论向概念论过渡时各种规定的相互交替与补足类似,但那些规定是在否定中得到了提升的,这里的各种和解则需要承接同一个肯定的东西,仿佛它们在各自范围内达到的自在自为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为绝对观念的,绝对观念也心满意足地收下了它们的礼物,并用理性的理念对它们各自的缺陷施以援助。这样一来,它实际上就将各种一般观念和一般现实以及它们的缺陷都包容在自身中,为它们提供了独家担保。因此,它显然要面对关于其连带责任的追问,这可以说是绝对观念论的“神正论”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末尾的表述不免让人想起以往神正论中关于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世界的说辞,他在声称尘世王国的粗鲁任性和精神王国的偶然暴力仅仅由于“同时根源于一种统一和理念”就达成了真实的和解时(35)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第481页。,也确实偏离了否定之否定的做法,试图祭出理念这种肯定的东西去打消否定,但凭借着黑格尔在辩证法上的突破,人们仍有机会为黑格尔的和解思想给出超越神正论的回答,那就是让绝对观念承认自己就是那不能脱离一般现实的一般观念,承认自己是必须在行动和否定中才能实现的和解精神,承认真正的和解不是对现实的神化,理念也不是神。
在黑格尔的框架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使和解观念向现实回归,而向现实回归就是向理性回归,向整个绝对理念回归。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已经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存在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的理性和作为现存的现实世界的理性之间的东西,把前一种理性与后一种理性分离并阻止其在后者中获得满足,是未被解放成为概念的所有抽象物的桎梏。在当下的十字架中认理性为玫瑰并以此享有当下,这种理性的洞察就是同现实的和解;哲学只把和解给予那些曾对和解有内在要求的人,这种要求驱使他们以概念来把握现实,并在实体性的东西中同样取得主体的自由,甚至不把主体的自由保持在特殊和偶然的东西中,而是保持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中”(36)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第13-14页。译文有改动。《法哲学原理》现有的两个中译本将“在当下的十字架中认理性为玫瑰并以此享有当下”译为“对现在感到乐观”或“对现在感到喜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解。该处原文是“Die Vernunft als die Rose im Kreuze der Gegenwart zu erkennen und damit dieser sich zu erfreuen”,其中sich+第二格+erfreuen是一个旧时的固定用法,如Duden词典的erfreuen词条所说,它指的是“欣然享有某物,幸而占有某物”,这与对某物持有乐观的(optimistisch)态度是极为不同的。。黑格尔意图表明,不管当下究竟是什么状况,我们都要欣然占有当下,享有当下,而不是忧心忡忡地逃避当下。这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粉饰,并不是让人们为现存的一切感到亢奋,而是为了消除人们对现存事物的灰心,它呼唤的是理性的自信,而不是对现存事物的轻信。虽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正文中最终偏离了这一要求,亲自将他所展望的和解做了降级的使用,使和解沦为了种种调和,但调和本来就不应被排除在和解理念之外,否则和解理念本身就不完整了。调和既可以调停,也可以调动。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及艺术宗教时,曾说对立与自身的和解(Versöhnung)不是作为对罪责(Schuld)的开脱,而是为罪行(Verbrechen)开脱,是意识的赎罪性的安慰(sühnende Beruhigung)(3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第445页。,这种在特定阶段上的局部的调停就不能被视为妨碍了整个辩证运动的进程,相反,调停就是调动的一部分。
关于现实中的和解,《精神现象学》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黑格尔和解思想的生命力就保持在和解精神之中。真正的和解精神能够将现实的认错机制和理性的除错机制汇集在一起。在这里,认错不仅仅是一种激情,除错也不仅仅是一种强制,两个方面都有机会放弃自己的一厢情愿与一意孤行,促成现实向理性的回归以及理性向现实的回归。黑格尔的和解精神做到了前一种回归,而把后一种回归交给了观念。观念在自身中解决了所有不和解性,并由此将两种回归都抓在自己的手中,将和解精神也纳入了观念论的科学体系。这种附属于观念的和解精神失去了独自与不和解性打交道的空间。和解观念是怎么对待不和解性的,它就得怎么对待不和解性。黑格尔对不和解性的这种态度是有缺陷的。虽然他曾不无道理地表明了不和解性最终是不能高于和解性的,但他对不和解性能够并且确实先于和解性、伴随着和解性以及后于和解性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也不承认不和解性能够与和解性平起平坐。不和解性所面对的和解观念没有和解精神曾具有的那种虚心,作为理性,它与黑格尔曾批判的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立法以及审核法则的理性有相似的任性。
在黑格尔之后,辩证的和解思想仍然有所发展,不和解性在和解思想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恩格斯曾提到“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同自己本身的和解(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9页。,这一表述是对黑格尔和解思想的延续和校正。阿多诺则对黑格尔的和解精神与和解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批评,将不和解性作为特殊的东西从黑格尔式的同一性的观念中解救出来。他认为黑格尔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委婉招认了弱者对强者的屈从并“不自觉地接近了不可和解性意识”(39)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66页。。同一性或和解性所面临的这种不得已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揭示的不同一性或不和解性的不得已在我们面前形成了对照。我们不可能还像黑格尔那样将它们安排在一个体系中,用唯一的和解观念来解决这些不得已,以至于抹杀了它们各自的自发性。我们从黑格尔的和解思想中能获取的积极的东西不是各种和解性在观念上的互补,而是不和解性在精神中的互鉴以及在现实中的互动,在这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