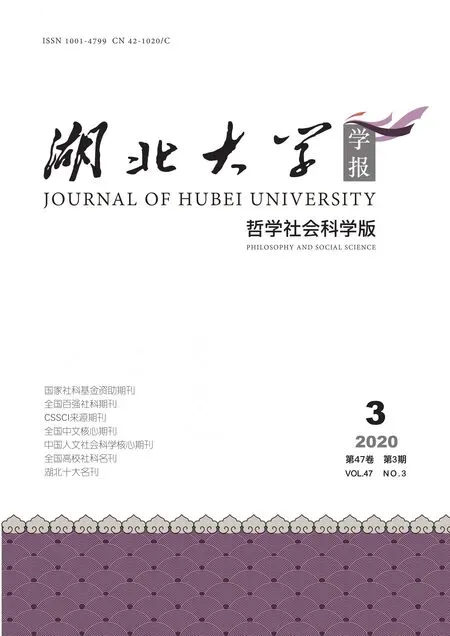“人兽之辨”可以休矣
刘清平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在以往中西哲学围绕人性展开的讨论中,“人兽之辨”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构成了评判人性优劣善恶的一条重要标准。不过,深入分析会发现,传统人兽之辨的核心理念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在实践中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人兽之辨的核心理念
哲学作为“人学”的特定身份,可以说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确立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以及苏格拉底反复引用的古希腊神谕“认识你自己”。如果说像“万物的本原”、“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样的“物性”问题只是一度吸引了哲学家们的强烈兴趣,那么,“人何以为人”的“人性”问题始终是哲学家们的关注焦点,直到今天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构成了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他分支的独特之处。毕竟,要是连自己为什么是“人”、怎样成为“人”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如何谈得上有了“认识自己”的“自知之明”呢?
按理说,哲学的使命既然在于认知人性,它就应当从“人本位”的视角出发,直接面对人自身,专注于探究人自身的各种属性、特性、品性、天性、本性等。但长期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哲学家们却似乎更倾向于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特别是两者之间的道德差异入手,考察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结果把所谓的“人兽之辨”(人禽之辨)放在了哲学人性观的首要位置上。究其理论根源,主要是因为早在进化论产生之前,哲学家们就注意到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紧密关联,所以才试图通过人兽之辨,发现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微妙异同,特别是根本区别,由此彰显人性的独特内容及其相对于兽性的优越地位。
先秦儒家就很重视人与禽兽的区别,并且其观点成为中国古代人兽之辨的主流见解。根据《论语·微子》的记载,孔子在谈到隐者时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特别强调人不可与鸟兽混在一起;接下来子路评论隐者时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彰显了君子与隐者在是否维系君臣长幼的伦理规范方面的本质差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见解,一方面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另一方面指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同样认为是否遵守忠君孝父的道德底线构成了人兽之辨的分水岭。荀子与孟子虽然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人兽之辨的问题上却是殊途同归,他明确主张“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同样将关注点放在了君臣父子的人伦礼义上,并且因此认为小人“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荀子·修身》)。在先秦儒家看来,人之为人的本性可以说就在于只有人才独有、禽兽所没有的某些伦理品性。
从古希腊起,西方主流哲学也流露出注重人兽之辨的鲜明倾向。在《政治学》里,亚里士多德曾凭借“属加种差”的方法,开宗明义地接连给出了几个有关人的定义:“与蜜蜂以及其他任何群居动物相比,人更是一种城邦(政治)的动物。……人是唯一具有逻各斯(语言)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具有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以及其他类似的感受。”(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引用西方译著时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注明。尽管在具体的关注点上存在某些难以否认的深刻区别,但在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入手、特别强调伦理道德这两个方面,他与先秦儒家的基本见解却是遥相呼应的,几乎可以说验证了“东哲西哲,心同理同”的格言。此后,“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五花八门的定义更是风起云涌,构成了西方主流人性观的基本模式:既然(其他)动物没有理性、不会说话、建不起城邦、造不出符号,那么,人就是理性、语言、政治、符号的动物;所以,人之为人的本性就在于只有人才独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某些特定属性。
有鉴于此,倘若着眼于两者的共同处,就可以说,先秦儒家和西方主流哲学的人兽之辨,实际上都遵循着“(其他)动物不是什么,人就是什么”的内在逻辑,结果把“人性之是”归结为“兽性之不是”,以致连人与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那些属性也没有资格算作“人性”了。例如,孟子和荀子虽然都承认人与禽兽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了差异点,但是他们认可的人性却主要在于两者的差异点(伦理品格),并不包括两者的相通点(食色本能)。再如,亚里士多德倡导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原本也有通过某些特定的“种差”把人之“种”与动物之“属”联结起来,便于人们通过“分析”对人做出清晰定位的意图;但是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们沿着人兽之辨的思路“分析”来“分析”去,却反倒把人性的各种定义弄得“分崩离析”了,只记住了那点特殊性的“种差”,而忘了人本身的一般性之“属”,认为人性仅仅在于“(其他)动物不是”的内容(理性、语言等),并不包含“(其他)动物也是”的因素(欲望、情感等),也就只是将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小部分特性单独抽离出来,当成了人之为人的本性来考察。
进一步看,引诱着西方哲学家们从分析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主要动机,在于“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人类中心主义信念(2)江山、胡爱国:《西方文化史中的人与动物关系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既然人是“万物之灵”,能够经天纬地、统率万物,我们就“应当”赋予那些种差独树一帜的重大意义,凭借它们把人这个种与动物这个属截然分离开来(虽然这些种差的原意是想把两者联结起来);否则,倘若将人与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属性也纳入到“人性”中,就会让人停留在冥顽不灵的动物界,难以彰显人对于其他动物的鹤立鸡群地位。主要就是由于这种规范性的价值信念隐隐作祟,在西方主流哲学的描述分析中,“人”越来越不像是一种“动物”,反倒单向度地“理性”、“语言”、“政治”、“符号”化了起来。拿理性主义者来说。他们总是把注意力聚焦在“理性”这种特定的“种差”或“本质”上,声称人只要有了逻辑思维的认知能力,就能摆脱其他动物摆脱不了的感性世界,跃升到“理性存在者”的超越层面,不仅在认知领域把其他动物甩在后头,在其他价值领域也比它们高出了许多,甚至有了可以和天使套近乎的资格。先秦儒家虽然没有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但它的人性定义同样充满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的优越感,所以才会宣布,唯独人才能具有忠君孝父的道德品格,其他动物在本性上就失去了拥有这些高尚品格的资格。因此毫不奇怪,这类人兽之辨大都潜含着“人性善兽性恶”的“天使本位”预设:人性像天使般纯洁善良,与低劣邪恶的兽性天壤有别。
从这个角度看,中西哲学有关人兽之辨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第一,片面关注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甚至主张“人性在于兽性所不是”;第二,特别强调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甚至主张“人性善兽性恶”。也正是以这两个核心理念为内涵的人兽之辨,长期以来在中西哲学的人性观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于人性内容及其善恶优劣的具体理论探讨。
中西哲学里也有另外一些人性观,不赞成把人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反倒大力强调两者的一致等同。如庄子就针对儒家的人兽之辨主张“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认为人与禽兽万物的“道通为一”才能造就“至德之世”。在西方,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不掩饰自己与狗的相通处,现代精神分析思潮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也指出:“在我看来,对人类现今发展阶段的解释似乎无需不同于对动物所作的解释。”(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5页。宽泛地说,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也能成立:只要接受了人属于动物的前提,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对人的解释其实也就是对动物的解释。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类潜含着“动物本位”预设的人性观不仅取消了人兽之辨,而且还会取消人性自身:人性与兽性没有差异,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是兽性。
从上面的讨论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性”是喜欢走极端的,所以人们常常在极端之间走来走去。但很可惜,这样在极端之间走来走去的结果是,人类哲学到现在已经探讨了两千多年的人性问题,却依然没能通过“认识自己”形成宝贵的“自知之明”,相反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程度上超过了两千年前。这种致命的失败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往中西哲学从人兽之辨的视角考察人性的做法,究竟在哪些地方陷入了误区?如果我们今天要是不对此拨乱反正,就会照旧在不知通向哪里的歧路迷途上越走越远。
二、人性之是与兽性之不是
导致中西哲学在人兽之辨中陷入误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把人性的“实然”与“应然”两个不同的层面混为一谈了,结果把自己认为人“应当”有的理想人性错误地当成了人“实际”有的现实人性。用这种特殊的“心想事成”方式考察人性,自然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扭曲了。
实然与应然两个词经常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语境里,却很少得到清晰的界定,显得有点神秘。其实,从休谟有关“是”与“应当”的质疑角度看(4)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9-510页。:“实然”主要涉及各种事实“是”怎样的层面,与人们对这些事实的认知性描述分析直接相关;“应然”主要涉及人们“应当”怎样对待各种价值的层面,与人们对这些价值的规范性评判诉求直接相关。至于两者的关联相当纠结,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以往人们对它们的理解:首先,事实一旦与人的需要—想要—意志(包括认知的需要与道德、功利、信仰、炫美等非认知需要两大类)形成关联,就会对人具有认知与非认知方面的价值;其次,价值一旦成为认知需要(求知欲或好奇心)的诉求对象,又能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认知行为加以描述分析的事实(5)刘清平:《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无论在休谟提出质疑之前还是之后,中西哲学人兽之辨的扭曲悖论都与它们没能厘清实然与应然的复杂关联直接相关。
本来,倘若从“认识自己”的“自知者明”视角看,中西哲学的人兽之辨也主要是基于好奇心或求知欲,试图通过辨析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探讨人性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因此理应位于实然性的认知层面。然而,它们在自觉不自觉地预设了人作为“万物之灵”比其他动物高超的独特地位后,却在认知需要外又引入了想要确立这种优越感的非认知需要,并在后者的驱使下,把“人们实际具有的人性是怎样的”问题改换成了“人们应当具有怎样的人性才能成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人”,用应然的人性取代了实然的人性,把理想化的人性愿景当成了实际有的人性事实。正是这种“心想事成”的思维模式,误导着传统人兽之辨的核心理念不是把关注点聚焦在“人性之是”上,而是聚焦在“兽性之不是”上。
这样转换关注点,会造成怎样的差别呢?要是探究人性的时候不受人兽之辨的误导,把关注点聚焦在“人性之是”上,那么,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具有的任何属性就都构成了人性的内容,没有任何理由被说成是“假人性”或“非人性”。当然,这种整全意义上的人性不会仅仅局限于所有人普遍具有的共同属性,还包含了只为某些人或某个人具有的特定属性,因此是十分丰富的;任何人性观只能探讨其中的某一部分这一点,非但不足以否定整全人性的这种丰富性,相反还向它们提出了“应当注意自己研究的人性内容与整全人性其他内容之间关联”的诉求。此外,这种认知性诉求正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纠结关系的一种表现:由于实然性描述分析来自好奇心或求知欲的认知需要,它们本身就内在包含着像“真理知识是可欲之善”、“应当全面考察事实”这一类的应然性评判诉求,结果生成了“实然里面有应然”的复杂局面。
可要是我们探究人性的时候遵循人兽之辨的思路,把关注点聚焦在“兽性之不是”上,悖论就会出现了,因为这时所有那些人与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属性,无论在人们的生活里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都将仅仅因为“人兽共有”这条单薄的理由,受到人兽之辨的扭曲而被拒之于“人性”的大门之外,不仅被说成是“假人性”或“非人性”,而且还可能被说成是“兽性”——尽管它们绝对真实地存在于人身上。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人们实际具有的整全人性内容的一小部分(只有人独有、其他动物不具有的那部分)才有资格算作“人性”,另外很大一部分(人与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那部分)要么被当成了没有意义甚至不存在的东西受到漠视,要么被当成了与人性截然相反甚至不共戴天的兽性受到贬抑。撇开“只有人独有、其他动物不具有”这个说法的笼统模糊、不知道何时能讲清楚的缺陷不谈(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其他动物是不是也有素朴推理、鸣叫呼喊、团体管治、兽伦关系的初生萌芽”的棘手问题就足够了),这种用应然替换实然的以偏概全肯定会扭曲现实人性的本来面目:人和其他动物实际上共同拥有的那些真实属性,何以就不“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而“应当”被视为兽性,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排除在人性观的视域之外呢?由此,这样以特定的“心想事成”方式被扭曲了的“人性”观,似乎更有理由叫做“兽性之不是”观。
怎样走出这种拿应然当实然的误区呢?说起来也容易,这就是把包括“确立人对其他动物的优越感”在内的所有非认知需要统统悬置起来,单纯基于认知需要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具有的人性本身,如其所是地描述分析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一心只想着证明:我们希望人们应当具有的那些属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毕竟,人首先是因为人自身成为人的,不是因为与其他动物有别或相似才成为人的。或者说,人首先是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野兽,也不是一半天使一半野兽的组合体。与之相应,人性是人所具有的属性,不是兽所没有的属性。或者说,人性首先在于“人之是(有、存在)”,在于所有人在现实中实际具有的所有属性,因此既不在于“兽性之是”,又不在于“兽性之不是”。诚然,就像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上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但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具体属性如何千差万别,它们都是人性而非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把理性、语言、符号、道德等等当成人性的时候,只是因为它们都是人自身所是的属性,并非因为它们是其他动物所不是的属性;而当我们把感性、嘟哝、涂鸦、残忍等等当成人性的时候,也是因为它们都是人自身所是的属性,无论其他动物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属性。
于是,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人性,就理应守住“人本位”而非“天使本位”或“野兽本位”的基点,直接从人自身而非人兽之辨出发,以“人所具有的无不具有”的方式,理直气壮地把所有人的所有属性都纳入最广泛意义上的整全“人性”,不管它们是否同时也为其他动物所具有。换言之,科学的人性观要克服人兽之辨的扭曲悖论,如其所是地揭示人性真相,至关紧要的就是直面人自身、回到人自身;相比之下,“其他动物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属性”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参照系,我们无需把它当成喧宾夺主的头号标准,而转移了我们对人自身的注意力。否则,倘若离开了人自身一味沉溺于人兽之辨,我们很容易受到前面谈到的两种先入之见的误导,要么把人等同于其他动物,要么把人与其他动物割裂开来,而忘了人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动物——后面这种先入之见更流行,危害也更大。不管怎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人与其他动物有着难以抹煞的深度差异,就凭借人兽之辨在两者之间挖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自信满满地以为人不再是动物了。无论人这个“种”有一天发展到了怎样高处不胜寒的地步,乃至从“新新人类”摇身一变转型成了“后后人类”,我们都只有踏踏实实地站在动物之“属”的土壤上,才能充分享受“自知之明”的种种好处;不然的话,等待我们的大概率是老子的另一句名言:“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考虑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了,而只是要求我们在全面了解人自身的基础上,再去全面了解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澄清人与其他动物在哪些方面一致相通,又在哪些方面泾渭分明——不必细说,这种实然性的事实辨析与应然性的人兽之辨存在着深刻的区别。无可否认,人性是从其他动物的兽性那里进化而来的,所以人性与兽性肯定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只要我们不用应然压倒实然,尤其是不在人兽之辨中以贬抑的方式曲解兽性,那么,无论是承认两者的关联,还是彰显两者的区别,都谈不上对人性的亵渎或推崇,而是仅仅旨在描述既成的人性事实——并且还是双重性的既成事实:不仅人们的理性、语言、符号、道德既有兽性的根源,又不同于兽性,而且人们的感性、嘟哝、涂鸦、残忍同样是既有兽性的根源,又不同于兽性。毕竟,当人是人的时候,人就不再是其他动物了(虽然人还是一种拥有特定种差的动物),因而人的属性也不会再是其他动物拥有的那类兽性。毋宁说,人性就是人的属性,哪怕再深层地植根于兽性,都不会因此变成兽性,而我们也不大可能再从中分辨出哪些是纯然的兽性,哪些是与兽性对立或无关的纯然人性。一言以蔽之,人们在现实中具有的所有属性都是如假包换的真实人性,无论我们怎样看不顺眼或深恶痛绝,都没有理由在实然性描述分析的层面上偷换概念、混淆语义,非要依据扭曲性的人兽之辨把它们说成是“假人性”或“真兽性”。
在这方面悬置应然、回归实然,能够让我们摆脱一些由于人性与兽性的纠缠不清所导致的理论麻烦和实践弊端。例如,在实践中坚持从整全人性而非特定种差的角度界定人,我们就能有效地纠正那种较常见的不正当态度,仅仅由于怀疑某些人缺少理性、语言、符号、道德这些特定的种差,就不再把他们当人看。再如,在理论上坚持从整全人性而非特定种差的角度界定人,我们就能很容易避开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空洞争论,如人与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食色本能,到底是人性还是兽性?在人兽之辨的语境里,它们大都被看成了兽性,理由是人兽共有,没法算作“人之为人的本性”;但麻烦在于,要是少了这些不可或缺的生理本能,其他任何“人之为人的本性”都将落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境地。相比之下,倘若坚持“回到现实中来,别沉迷于意愿”的实然性原则,我们就能在整全意义上快刀斩乱麻地宣布,既然人的食色本能真实地存在于人之中,那么,无论它们与禽兽的食色本能怎样地类同相似,也不管它们与人的理性、语言、符号、道德等种差怎样地天壤有别,它们都有资格构成“人之为人的本性”——理由很简单:一旦失去了它们,人就不再能够作为人存在下去了。
三、人性善与兽性恶
在人兽之辨中,用应然置换实然造成的另一个更严重的扭曲悖论是,“人性善兽性恶”被当成了不证自明的规范性标准,用来一刀切地比较人性与兽性的高低优劣:只有人的善良高贵属性才是真人性,邪恶卑鄙的属性则是“假人性”或“真兽性”。其实,上文的讨论已经表明,把“兽性之不是”当成“人性之是”的扭曲人性观的一个重要根源,正是人们拥有的这种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感,特别是其中包含的“人性比兽性善良高贵”的应然性预设。
要是只在善恶二字的非道德意义(宽泛性的好坏意义)上理解“人性善兽性恶”的命题,它应该说还是拥有某种实然性基础的,因为若从是否能够满足两者各自需要的角度看,人的理性思维、言语交流、社会管治等能力,的确要比其他动物的素朴推理、鸣叫呼喊、团体管治等能力更有效更强大,从而为人在这些方面不仅“自以为是”,而且“自以为优”的自信提供了一定依据。但在承认这类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人相对其他动物不那么优越的一面:人在某些方面(体力强度、奔跑速度、生理机能等)是赶不上许多动物甚至微生物的,所以人不仅会因为感染疾病而死亡,而且还会受到某些动物(所谓“野兽”)的侵袭而丧命(这也是人们主张兽性在道德上邪恶卑劣的一大理由)。这让人相对其他动物的非道德优越感也不得不打一些折扣。就此而言,我们在比较人性与兽性的非道德高低优劣时,同样应当悬置包括优越感在内的非认知需要,不可只盯着人类过五关斩六将的丰功伟绩做文章,却采取鸵鸟政策闭眼不看人类败走麦城的狼狈不堪——这类“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同样是拿应然遮蔽实然的“心想事成”的一种表现:对自己有利、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说成是存在的甚至必然的,对自己不利、自己讨厌的东西则说成是偶然的甚至不存在的。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善恶二字的狭义伦理意思上理解这个命题,主张人性在道德上就是善的,兽性在道德上就是恶的,那它的实然性基础就更是虚无缥缈、不堪一击的了,只能说主要体现了某种“天使本位”的应然性扭曲意愿,纯粹属于人们常说的“成见”、“偏见”、“先入之见”、“想当然之见”。
首先,在现代文明大大提高人的综合能力之前,的确经常发生豺狼虎豹吃人伤人的事件,并构成了人们斥责它们“凶恶残暴”、“兽性大发”的主要事实依据。但这个结论完全是人们从保全自己生命的规范性立场出发给出的道德评判,因此带有强烈的偏狭性。第一,豺狼虎豹吃人伤人大多是在饥饿驱使或遭受攻击的特定情况下展开的本能反应,即便看起来很残忍,也是出自它们行动的生理模式,几乎没有“有意害人”的自觉意图。第二,人们的这类“天使本位”的道德评判缺乏必要的反思,同样诉诸以应然遮蔽实然的方式,忘记了自己也经常对其他动物采取凶恶残暴的应对态度,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包含有意虐待的自觉意图,并没有因为自己拥有理性和道德等种差就变得更纯洁更善良。所以,如果其他动物也能从它们的规范性立场出发进行道德评判,肯定会宣布“人性才是凶恶残暴的”,甚至还能有不仅数量更大,而且也更难以反驳的事实依据。
其次,无论在种群内部还是种群之间,其他动物的凶恶残暴也大都出自本能反应的生理模式,因此在兽际关系中可以说并没有“有意害兽”的自觉意图。相比之下,人际关系中的凶恶残暴虽然包含本能反应的生理因素,但许多情况下却是出于“有意害人”的自觉意图,就连作为种差、常常让人引以为豪的理性能力,也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助纣为虐”(这个成语似乎要比“为虎作伥”更为精确)的工具效应。从这里看,将后面这类体现了人性之恶的现象说成是“禽兽不如”,哪怕在比附性的意思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是某些人干下了凶恶残暴的坏事,我们凭什么不从他们自己的人性那里找原因,反倒要平白无故地归咎于其他动物的兽性呢?即便某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恶棍,把他说成是“衣冠禽兽”,岂不是也有侮辱“禽格”、“兽格”的嫌疑吗?再以霍布斯将“每个人对每个人开战”类比成“人对人像狼”的说法为例(6)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3-97页。。今天中外学者们仍然津津乐道的这个著名比喻,不仅严重扭曲了人们在拥有利己动机的同时也有利他动机,因此在“许多人对许多人开战”的同时还会维系“许多人对许多人关爱”的人际事实,而且也遮蔽了狼群内部高度合作,甚至为了利它可以牺牲自己的狼际事实,所以这个比喻在双重性的意义上都无从成立。
毫不奇怪,“人性善兽性恶”的优越感包含的这些悖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也会带来扭曲的后果。宋儒朱熹就是理论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一方面继承了孟子的人兽之辨,明确宣称“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另一方面又基于天人合一的博大心态,大谈人兽之间的伦理相通:“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朱子语类》卷四)这就让原本还算界线分明的人兽之辨乱了套:“大体本清”而能“忠君孝父”的人,在什么意义上异于那些成“仁”成“义”的禽兽呢?如果说这些货真价实的禽兽都能因为遵守“君臣父子”的缘故具有道德上的“人性”,我们又如何能够逻辑一贯地斥责“无父无君”的乱臣贼子“是禽兽也”呢?简言之,倘若禽兽也有善良的“人性”,我们凭什么断言恶人只有“兽性”而无“人性”?撇开这种人性观在规范性层面的是非对错不谈,它在术语概念上的逻辑脉络已经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很难有厘清的希望(7)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3-95、232-233页。。对于目前仍很流行的那种自相矛盾——在把“野蛮”人的群婚杂合说成是“兽性”未泯的表现的同时,又借用鸳鸯蝴蝶来褒奖夫妇有别的文明“人性”,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
在实践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人对其他动物经常采取凶恶残暴的态度,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在理性意识中包含有意虐待的自觉意图。这样,一旦把某个人定位为道德上的禽兽,哪怕他没有干任何坑害他人的邪恶之事,而是仅仅倡导了某些标新立异的价值理念,或貌似缺乏理性和语言的发达能力,人们也很容易在人兽之辨的误导下,像对待禽兽那样对待他,这反倒是干下了凶恶残暴地坑害这个人的邪恶之事。事实上,把任何人说成是“禽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人格侮辱的因素了。因此,这类案例可以说最清晰地体现了人兽之辨在实践中的自败悖论:某些人强调人对于其他动物的道德优越感,其实只是为了确立自己对另一些人的道德优越感;更严重的是,某些自以为具有善良人性的人,还往往依据从人兽之辨中获得的道德优越感,在人伦关系中凶恶残暴地对待另一些被认为具有卑劣兽性的人,不把他们当人看,而是当成禽兽看。
有鉴于此,如果说在非道德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实然性理据指认人对于其他动物的部分优越性,那么在道德方面,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实然性理据炫耀人对于其他动物的任何优越性。换言之,凭借人兽之辨形成的人对于其他动物的道德优越感是一种纯属子虚乌有的幻觉,理论上背离事实荒诞无稽,实践上也有严重的负面效应,必须否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要坚持悬置所有非认知需要的价值中立原则,在贯彻实然性人本位立场的同时,明确反对应然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信念,不再去抢占让人性凌驾于兽性的道德高地,相反坦率地承认人性就是人的属性,不可一概而论地断言它一定就比兽性善良纯洁或邪恶肮脏,而只能从特定的规范性立场出发,具体评判哪些人性内容是善的,哪些人性内容是恶的。
有人会说,否定了人兽之辨,我们就无从彰显人对于其他动物的超越性特别是人格尊严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中西道德哲学里一种流行的先入之见,完全忽视了事情的关键:凭借人性善兽性恶的虚幻优越感,是无法真正揭示人在自然进化中实际形成的对于其他动物的非道德超越性的,相反还会以“心想事成”的方式将其扭曲变形,因为这种在自然进化中形成的超越性根本不可能超越自然进化本身,更不可能通过赋予人高于其他动物的道德优势的途径,让人享有人格的尊严。原因很简单,一旦跳出了人兽之辨的太虚幻境,立足于道德生活的日常土壤,我们会发现,人格尊严只能来自人在人伦关系中作为目的不受坑害的特定伦理地位,根本不可能来自人在人兽关系中极力抢占的道德制高点:一个人只有坚持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努力维护自己以及他人的应得权益,出于义愤反抗一切不义的侵权行为,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尊严。否则,倘若他只是对着鸡鸭猫狗、豺狼虎豹摆谱,宣布自己比这些“卑鄙邪恶”的禽兽们高出一等,以此来彰显自己人格的伟大高贵,听起来只会让人觉得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毕竟,在拒绝嗟来之食的“兽格尊严”方面,像麻雀这类禽兽的表现不见得就一定比人差到了哪里去。尤为反讽的是,如上所述,某些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时常打着人兽之辨的堂皇旗号,侮辱践踏那些被他们咒骂成“禽兽”的人的人格尊严。有鉴于此,我们又怎么可能诉诸人性善兽性恶的错谬预设来捍卫人格的尊严呢?归根到底,既然道德是在人伦关系中发生的,不是在人兽关系中发生的,那么,人格尊严也就只有在人伦关系中才能确立;试图从人兽之辨中寻找人格尊严,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这个问题上,先秦墨家的看法很值得注意和借鉴。一方面,墨家提出了某种独树一帜的“人兽之辨”:“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子在此既没有把人与禽兽等同起来,也没有凭借自以为优的道德制高点主张人性善兽性恶,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和反思指出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鲜明特征——只有凭借自觉的努力才能维系生存,因此非但没有流露出人凌驾于禽兽的优越感,反倒还向人提出了必须辛勤劳作以满足各种需要的诉求。另一方面,墨家依据“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的规范性原则,展开了人伦关系中的“是非利害之辨”,认为所有“亏人自利”的行为都是违反正义的邪恶,只有“兼爱交利”的行为才是合乎正义的良善。这种看法就是将人性的善恶是非完全归因于人以怎样的态度处理人伦关系,并且凭借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维护了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而不是诉诸人对于其他动物虚幻的道德优越感,所以更切近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8)刘清平:《论墨子“正义”理念的现代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相比之下,康德虽然明确主张“人是目的”,却同样由于混淆实然与应然的缘故走进了死胡同。他不仅在叠床架屋的概念体系里,区分了人的源于感性本能的“动物性”、感性和理性混合的“人性”、纯粹理性的“人格性”三种不同的禀赋,而且还特别赋予了纯粹理性凌驾于感性和动物性之上的道德优越地位,强调只有“理性存在者”才能拥有人格的尊严,所谓“理性在有关它自身尊严的意识中,蔑视所有那些来自经验领域的动机,并逐渐成为它们的主宰”(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也可参见刘静:《论康德“人是目的”的观念——对科尔斯戈德价值论回溯论证的反驳》,《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结果,康德强加给感性与理性、人与其他动物的实然性差异的应然性等级意蕴,就诱导着他将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仅仅指向了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一面,却把人作为动物也包含的“感性存在者”一面排除在外,最终让人格尊严陷入了只适用于人的理性存在,不适用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分裂状态。这样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悖论:难道人不是只有在作为理性与感性以及动物性的内在统一的整全意义上,才能充分享有道德上的人格尊严吗?比方说,要是人们在生命、财产、幸福这些感性意味相当浓郁的方面拥有的正当权益受到了其他人的不义侵害,我们怎么还有理由说他们的人格尊严在人伦关系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呢?(10)刘清平:《理性精神扭曲下的自由意志——康德自由意志观的悖论解析》,《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综上所述,几乎从任何方面看,中西哲学的传统人兽之辨可以说都缺乏积极的意义,相反还常常生成扭曲的效应,应当根本否定。事实上,如果我们无视传统人兽之辨的这些理论缺陷和现实危害,继续在实然与应然的混淆中坚持“人性在于兽性之不是”、“人性善兽性恶”的核心理念,就会在它们的诱导下深陷人性与兽性的二元断裂而无力自拔,照旧把关注点狭隘地聚焦在人性不同于和优越于兽性的一面之上,结果扭曲和遮蔽了现实人性的整全内容,在寻求“认识自己”的“自知之明”的道路上误入歧途并且越走越远。相反,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人兽之辨为什么陷入误区的致命症结,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地找到走出这座理论迷宫的正确道路:严格地把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区分开来,悬置所有的非认知需要,纯粹基于好奇心或求知欲如实地研究现实人性的整全内容,首先站在人本位的立场上直接关注人自身,然后进一步探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的复杂互动。也只有采取这种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我们才能如其所是、全面完整地揭示人性内容以及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关系的真相,最终建立起崭新的科学人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