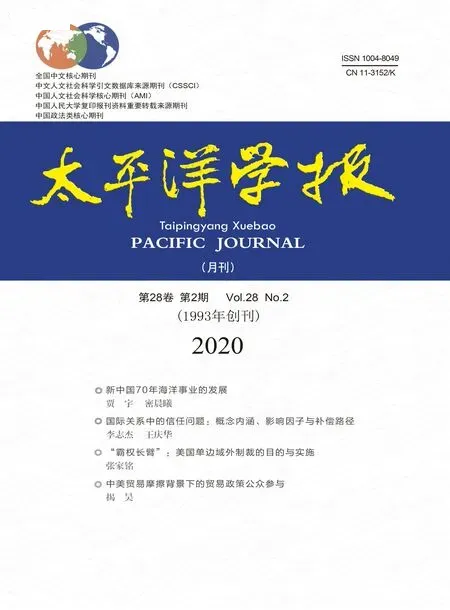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危机:表现、原因及发展
牛霞飞 郑易平
(1.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430070;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 南京210001)
2016 年注定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平凡的一年,从这一年起,美国政治进入特朗普时代并集中爆发了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崛起、否决政治大行其道、身份政治凸显和国民认同削弱等多重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互相缠绕,酿成了当前美国的政治危机。 所谓的政治危机,本文认为是由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矛盾或者国际冲突等因素所引发的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危险与转机并存的状态。①“危机”一般被认为是危险与转机并存的时刻、时机、状态,或者被认为是严重的冲突或冲突的转折点、关头。 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和冲突,但它们只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引起政治生活中的高度危险,但这种危险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本文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和政治灾难、政治崩溃有重大区别,后两者主要强调政治冲突的严重破坏性以及难以挽回的损失。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根源是什么? 特朗普的上台及其化解危机的举措又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本文不揣冒昧,对上述问题作出抛砖引玉的解析。
一、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治危机的表现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危机,本文认为,该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克里斯托弗·黑尔(Christopher Hare)与基思·普尔(Keith T.Poole)等学者对美国的政治极化作了长期的跟踪研究,他们认为,美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出现政治极化现象,所谓的政治极化,即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提高,民主党中的右派和共和党中的左派比例下降,同时在国会投票中,跨党投票现象越来越罕见,而按照党派路线投票的议员比例越来越高。①See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No. 4,1984,pp. 1061 - 1079; 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The MIT Press,2016; Adam Bonica,Nolan McCarty,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7,No. 3,2013, pp.103-124; Christopher Hare, Keith T. Poole, “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Polity, Vol. 46, No. 3,2014, pp.411-429.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日益严重,尤其到特朗普时代,政治极化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特别突出、显眼的难题。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治极化首先表现为价值观上的左右撕裂,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日益“左倾”,引起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弹,在税收、福利等经济议题以及移民、控枪、堕胎、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上,左右两派分歧越来越大。 受此影响,美国党派纷争更加严重,政党恶斗更加激烈,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攻讦、拆台,基于此,有学者指出,美国正日益变成民主党的国家和共和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相互反对,难以和谐相处。②Alan I. Abramowitz, “America Today Is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Don’t Get Along,” Washington Post,March 10,2016,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theory/wp/2016/03/10/america-today-is-two-different-countries-they-dont-get-along/?noredirect=on&utm_term=.38a058993404.
第二,民粹主义崛起。 民粹主义有三大核心特征,即推崇民众、贬低精英、诉诸直接民主。③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p. 19-20.虽然民粹主义在美国有悠久的传统,但由于在大部分时期中,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矛盾都不甚尖锐,特别是两党制建立以来,双方都力求使自己成为大多数选民的代表,都倾向于走中间路线,因此,走极端的民粹主义通常是被边缘化的。 然而,当美国政治社会出现严重的冲突或新问题时,民粹主义便会走向前台。 例如,1830 年代,在西进运动中,草根阶层强烈要求扩大选举权,他们与当时的统治精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民粹主义由此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时任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Andrew Jackson)顺应民粹主义的要求,推行了“杰克逊民主”;19 世纪90 年代,面对美国政治腐败、经济垄断等严重问题,民粹主义又一次崛起,他们组建人民党,震惊美国政坛,在大选中获得了100 多万张选票,并有多名骨干成为参议员和州长;在2011 年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民粹主义再次崛起,震动美国朝野。 当前,面对白人中下层经济地位下降、少数族裔在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增加这个美国主流社会前所未有也难以接受的挑战,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站在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以桑德斯为代表,同情弱势群体、关注经济平等、反对特权等的左翼民粹主义异军突起,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 双方之间互相角力,不仅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也对美国政党政治产生了较大冲击。
第三,否决政治盛行。 美国的政治传统崇尚以权力制衡来防止权力滥用,其政治体制以权力分散为特征,不仅有横向分权,还有纵向分权。 当社会同质性程度较高,价值观冲突不那么激烈时,这种复杂的分权制衡体制能够实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也能够对社会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回应。 然而,近年来,美国社会日益分化,族裔关系日益复杂化,这为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演变成“否决政治”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46-449 页。提供了温床。 正如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当前美国利益集团大行其道,他们分头“捕获”美国的各个权力中心(即行政、立法、司法及地方权力部门),只要它们能成功地“捕获”一个权力中心,就至少能达到保护自己特殊利益的目的。②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Prospect Magazine, December 13,2016, http:/ /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america-the-failed-state-donald-trump.但这样一来,就使美国政治体制效率降低,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越来越难以作出有益的变革,进而导致“政治衰败”的恶果。
第四,国民认同削弱,身份政治凸显。 二战后,美国合法和非法移民人数激增,伴随着人种结构的变化和对“政治正确”的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也日益兴起,对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忧心忡忡,直呼“我们是谁?”他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会降低“美国信念”对民众的凝聚力,导致美国出现国民认同危机。③[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前言第1-3 页。这种认同危机又使得福山等学者所关注的身份政治问题凸显出来,在他们眼中,当前美国左派日益强调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以及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等边缘群体的利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经济平等的关注,而右派则更重视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等相关的传统民族身份,同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自身基于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等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可④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7,No. 5, 2018, pp. 90-114.。 然而,身份政治由于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会进一步加深美国民众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使美国社会走向严重的“撕裂”,⑤Michael Thorburn,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by Mark Lilla,” Osgoode Hall Law Journal, Vol. 55, No. 1, 2018, pp.341-348; David Brooks,“The Retreat to Tribalism,”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 2018, https:/ /www. sacbee. com/opinion/op - ed/article192542484.html.例如,2017年7 月至8 月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决定移除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的雕像,爆发了“弗吉尼亚暴力事件”,其中,白人与非白人群体特别是与黑人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并引起了美国政坛的一场混战,特朗普也卷入其中。 更严重的是,身份政治反过来又会加深美国的国民认同危机,使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因为左派过于依赖身份政治,就会走向过分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而右派的身份政治走向极端,就容易再次陷入种族歧视的泥沼。
可以说,美国政治中的上述严重政治问题之间紧密联系并有叠加效应:首先,左右翼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发展不利于美国凝聚政治共识,因而也就会加大其左右撕裂的程度,使党派分歧与政党恶斗更加严重,进而加深美国的政治极化;而政治极化又是民粹主义的催化剂,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国民认同,加速美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越分化,特殊利益集团就越活跃,其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加,进而使美国“否决政治”的问题更加凸显。 简言之,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强化,甚至恶性循环,使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危机特征。
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爆发危机的原因
2.1 与社会进步相伴的社会矛盾引发其政治危机
二战后,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与此相伴而生的,还有诸多社会矛盾,进入21 世纪,这些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政治危机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到特朗普上台前后,政治危机终于爆发。
首先,在社会经济方面,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使各阶层财富水平提高,收入差距缩小,社会变得更为平等。 但20 世纪70 年代后,尽管民众的财富仍然在增长,但社会不平等程度也开始加大,中产阶级也逐渐萎缩。 地位下降的中产阶级将矛头对准华盛顿政客及华尔街精英,不管在左派还是在右派,民粹主义都纷纷崛起,桑德斯和特朗普所拥有的大批支持者体现了部分中产阶级对左右翼建制派的不满,也意味着大众和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其次,族裔冲突加剧。 从美国历史来看,尽管19 世纪30 年代至60 年代,美国爆发过排斥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一无所知运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又出现了“排华风潮”,但白人同黑人的矛盾一直是美国种族冲突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民权运动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推动了种族之间尤其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平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族裔冲突,但随着拉丁裔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的种族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而且,由于白人担心自己会由多数族裔变为少数族裔,种族问题又重新凸显。
最后,在社会价值观方面,民权运动的开展促进了不同种族和性别之间的权利平等,并进一步将这种政治上的平等推向文化价值观上的平等,达到了“政治正确”的高度,对此,多元文化主义者乐见其成。 而那些认为当前“政治正确”过分泛滥而限制了言论自由,进而威胁到了美国传统价值观以及白人主体地位的保守派人士,则与多元主义者针锋相对,使美国社会呈现出左右撕裂、国家认同削弱等混乱局面。
更严重的是,经济不平等、族裔冲突以及价值观等问题往往相互纠缠,互为因果。 中产阶级的衰落使民众更加不信任精英,而种族冲突大多数时候与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等问题缠绕在一起,又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 由于矛盾众多且难分难解,社会异质性程度也越来越高,导致不同阶层、族裔以及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越来越坚持自己的立场,难以达成妥协,而此前被公认为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共和两党发现自己愈加难以讨好大多数的选民,为了保住基本盘,只能向左或向右,使自己的观点极端化,在涉及左右两派各自最关心的政策议题上互不相让,由此造成政治极化的恶果。也因此,千头万绪的矛盾和日益极端化的左右阵营极力阻击对方的政策意图,使本身意在实现权力制衡、制造障碍以避免政策失误的美国分权制衡体制异化成了所谓的低效率、低能力的“否决制”。
然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进步的副产品。 民权运动的成功、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政治正确”的盛行乃至多元文化主义的备受推崇其实都显示了美国社会的进步、活力以及宽容,身份政治更是人们自我认识、自我尊严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可是,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文化进步的速度和广度却似乎逐渐超越了其政治体制所能容纳的范围。 例如,大规模移民的到来日益冲击着美国传统上以白人为主的社会,而“政治正确”也逐渐走向白人眼中的“反向歧视”,身份政治及多元文化主义日益挑战并削弱美国的政治共识,这些都使得价值观上相对保守的美国民众感到不适,甚至产生了一种“被围困心态”。①刘瑜:“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美国研究》,2018 年第6 期,第83-108 页。当崇尚进步主义理念的左派越走越远时,那些视保守主义为美国精神之根基的人自然难以容忍,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极度激化的矛盾就使美国政治一步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2.2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多重挑战加剧其政治危机
冷战后,美国以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积极推动了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在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挑战。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国债债台高筑。 众所周知,美国两党都需要迎合选民才能维持它们的执政地位。 共和党认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相信“涓滴效应”,②Merter Akinci,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rickledown Effect Revisited,”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36, 2018,pp. 1-24.因此,力主减税减福利;而民主党则更青睐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因此,主张增税增福利。 然而,当前共和党和民主党阵营中分别有68%和73%的民众反对减少社会福利,③Michael Lind,“This Is Wha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Looks Like,” Politico Magazine, May 22, 2016, https:/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5/2016-election-realignmentpartisan-political-party-policy-democrats-republicans-politics-213909.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取悦民意,赢得选举,共和党能减税却无法实质性地削减福利,民主党能加大福利却无法增加多少税收,两党政策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政府债务水平一路高升。 因此,奥巴马当政时期,美国国债债务上限被数度提高,仍然难以避免关门停摆的命运,特朗普上台至今,也已遭遇了债务上限危机。①张启迪:“美国债务上限危机的由来、发展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 年第2 期,第92-108 页。然而,两党政治并不足以构成美国背负巨额债务的全部原因,全球化也是其国债高涨的重要推手,根源就在于,全球化为美国提供了向其他国家借钱的便易渠道。 换句话说,没有今天的全球化,美国政府就难以向外大规模借债,借不到钱,无计可施,美国朝野就可能被迫削减债务规模。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20 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10 150 亿美元,比2019 年多出310 亿美元,从2019 年到2030 年,公众持有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从79%上升到98%,到2050 年,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至180%,②“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2020 to 2030,” CBO,January 2020, pp. 5-8, https:/ /www.cbo.gov/system/files/2020-01/56020-CBO-Outlook.pdf, 访问时间:2020 年2 月13 日。积重难返的巨额国债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隐患和风险。重债如山,任何大量增加政府开支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成为两党及其民众争执的焦点,艰难被通过又处在被废除边缘的“奥巴马医改”就是明显的例证。 故此,可以说,全球化之下美国的巨额国债成为其政党极化、左右撕裂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是,国内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空心化。 全球化使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为那些以逐利为本性、寻求低成本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出路。 后发国家则在全球化中借助这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工业,并转而向发达国家大量销售质优价廉的商品。 在后发国家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国内的制造业很快便失去竞争力,美国东北部的锈带曾经辉煌耀眼,而今空荡没落,成为美国制造业衰败的象征。③James Feyrer, Bruce Sacerdote,Ariel Dora Stern, Albert Saiz and William C. Strange, “Did the Rust Belt Become Shiny? A Study of Cities and Counties that Lost Steel and Auto Jobs in the 1980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2007, pp. 41-102.
传统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并加深了美国政治社会的两大问题:其一,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从业者、跨国企业中的资本家和高管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尽管美国普通民众因消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而降低了生活成本,但其所得的好处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大量低技能的白人蓝领因此失去工作,美国日益成为被“第三世界化”的“双层社会”,一个极其富裕且享有特权,一个极其痛苦且百无一用④[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季广茂译:《世界秩序的秘密——乔姆斯基论美国》,译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176-177 页。;其二,中产阶级萎缩。 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社会就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中产阶级在价值观上相对保守,在政治生活中相对理性,因此是美国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 然而,这个基石正日益遭到侵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6 年的报告显示,自2000 年起,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占比下降了5%,⑤“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 in OECD and Emerging Countries: Myth and Reality,” OECD, December 1, 2016, http:/ /perma.cc/C93R-59YY.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1971 年,美国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的成年人占比为61%,2016 年,这一比例降为52%,⑥“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Stable in Size, But Losing Ground Financially to Upper-income Families,” Pew Research Center,September 6, 2018, https:/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9/06/the-american-middle-class-is-stable-in-size-but-losing-ground-financially-to-upper-income-families/.到了2019 年,该比例持续下降为51%。⑦Juliana Menasce Horowitz, Ruth Igielnik, Rakesh Kochhar,“Trends in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January 9, 2020, https:/ /www. pewsocialtrends. org/2020/01/09/trends-in-income-and-wealth-inequality/.
在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中产阶级逐渐丧失主体地位的趋势,使美国社会中弥漫着焦虑和失望的情绪,普通民众尤其是白人中下层日益怀疑甚至敌视上层精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纷纷遭到选民的抛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美国的民粹主义。①Ronald F. Inglehart,Pippa Norris,“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pp. 10-12.因此,尽管美国主流社会和精英都反对声誉不佳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但渴望变革以改善自身地位的白人中下层还是将其推上了总统之位。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三个挑战是,移民大量涌入及其引起的政治认同、左右撕裂等问题。 先是欧洲,然后是亚洲和拉丁美洲、中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等地的移民进入美国,美国也由此成为多种族多民族的移民国家。 然而,隐藏在“移民国家”这副面具之后的,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导的美利坚民族国家。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民特性最初包括人种、民族、盎格鲁—新教文化和“美国信念”四个部分,随着早期移民融入美国社会以及民权运动的开展,人种和民族不再成为界定美国特性的因素。②[美]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29-38 页。但美国早期定居者所秉持的包括新教价值观、英语、法治传统等内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在这一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及私有财产制为原则的“美国信念”始终主导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因此,移民在美国逐渐被同化,白人也占人口绝大多数,所以美国政治社会虽问题不断,却未形成重大的认同危机。
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移民大规模涌入美国,这严重冲击了盎格鲁—新教文化,同时,双语主义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盛行,与美国主流文化相异甚至相悖的外来文化也要求得到美国社会的尊重和认同,从而降低了美国对移民的同化力度,甚至呈现出解构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倾向,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美国政治社会稳定运行的政治文化基础。
除了文化认同问题,移民还同上文提到的白人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等问题息息相关。 1970年,非西班牙裔的白人人口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3%,2015 年则降为62%,③Nancy Foner, Kay Deaux, Katharine M. Donato, “Introduction: Immigration and Changing Identities,”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5, 2018,pp. 1-25.到2018 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为60%,④Jens Manuel Krogstad,“Reflecting a Demographic Shift,109 U.S. Counties Have Become Majority Nonwhite since 2000,”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1, 2019, https:/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8/21/u-s-counties-majority-nonwhite/.美国白人对自身在将来可能不再占据人口多数的前景感到恐惧。 同时,移民确实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工资有某种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低技术移民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就下降0.2 个百分点。⑤William W. Olney, “ Offshoring,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ve Wage Distributio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Vol. 45, No.3,2012,pp. 830-856.白人蓝领认为移民不但不认同他们的政治价值观,还抢了他们饭碗,因此极度愤懑,催生了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疯狂举动。
另外,移民问题也是美国社会左右撕裂以及政治极化的根源之一。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移民问题既与文化认同有关,又与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相联系,因此,在两党的政策议题中,它既属于文化—族裔议题,又属于经济—阶层议题。 二战后,美国经济进入繁荣期,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因此,经济议题让位,而文化—族裔议题上位。 然而,进入21 世纪,全球化弊端日显,民众对经济和就业的关注与对文化—族裔的诉求并行,移民问题就成了美国政治中既危险又不能不被踩中的“雷点”。 民主党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的立场,强调身份政治,认为美国工人的福祉不足以成为反对移民及自由贸易的理由,而越来越倾向于民粹民族主义的共和党则与其针锋相对,⑥Michael Lind,“This Is Wha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Looks Like,” Politico Magazine, May 22, 2016, https:/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5/2016-election-realignmentpartisan-political-party-policy-democrats-republicans-politics-213909.由此,政治极化、左右撕裂、政党恶斗也就在所难免了。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四个挑战是,其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了新兴国家强有力的撼动。 美国朝野认为,二战后至今的全球化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全球化所依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美国建立的,美国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可以使其稳保全球霸主地位,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必将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所享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①Robert J. Antonio and Alessandro Bonanno, “A New Global Capitalism? From ‘Americanism and Fordism’ to ‘Americ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merican Studies, Vol. 41, No. 2/3, Summer/Fall,2000, pp. 33-77.
1959 年,美国学者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观点,此后,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Jackman)、迪特里希·鲁其梅尔(Dietrich Rueschemeyer),尤其是亨廷顿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响应,论证、补充并深化了“李普赛特命题”。 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其政治制度就会“自行演变为美国式的民主制”。 然而,大出美国决策者意料的是,“李普赛特命题”破产了,经济上崛起的新兴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上并未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向美国靠拢,反而更加自信、更加强调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严重威胁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实际上,美国并非第一次面对强大的、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竞争对手,然而在美国人眼里,尽管苏联很强大,但在冷战中,美国与苏联经济基本隔绝,且对苏联实施技术封锁,因此苏联的经济和技术鲜有可能实质性地超越美国。 中国则不同,如今的中国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未来还会有更大发展。 面对这种局面,两党一时手足无措,在焦虑之中互相指责,推诿责任,两党缠斗也就更加激烈。
2.3 信息技术革命对美国政治的冲击激化其政治危机
毋庸置疑,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创新在很多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创新也会对人类现有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秩序提出挑战,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所指出的,“创新可以导致制度的不稳定”。②Ron W. Coan,“Science,Technology,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 Spring 2014, pp.37-56.作为塞缪尔森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很早就认识到了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副作用。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从内部不断地打破旧经济结构并代之以新经济结构的过程,新的生产方法(即新技术的引入)是最为重要的创新方式。 创新可以增加利润,开拓新市场,形成新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然而创新最终会摧毁那些过时的产业、技术,在一定时期内造成大规模失业、低效率、贫富分化等现象,对政治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③张延、姜腾凯:“哈耶克与熊彼特——两派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介绍、对比与评价”,《经济学家》,2018 年第7 期,第96-104 页。
对于美国来讲,信息技术革命对其政治社会的破坏和冲击表现在:
第一,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至少在短期内减少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动摇了美国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 近年来的不少研究表明,生产和工作程序的自动化确实减少了某些行业以及某些类型的工作机会,例如,有学者指出,自动化持续且显著地减少了制造业中的就业岗位,1979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 950万,到1983 年,该数字下降到1 670 万,预计到2024 年,只有7.1%的美国人从事制造业。④V. Kumar and R.P. Sundarraj, “Glob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Value,” India Studi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pringer,New Delhi, Springer (India) Pvt. Ltd., 2018, pp.50-93.除了威胁蓝领工人的工作外,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影响了诸如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业的就业;⑤Eli Noam, “ Inequalit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n Lorenzo Pupillo et al. eds., Digitized Labor, 2018, pp.117-140.学者科恩(Deniel Cohen)认为,电子软件难以取代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工作,而那些以常规性、重复性为特征的工作则很可能被技术所取代;⑥See Stéphane Ciriani and Pascal Perin,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world Eco⁃nomic Journal, No. 100, 4th Q, 2015, pp. 145-163.学者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认为,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的47%都面临着被电脑取代的风险,①Carl Benedikt Frey,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Oxford Martin Programme on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September 17,2013, p. 38.等等。 在美国,由于工业自动化的快速发展,作为中下层阶级的蓝领工人失业问题严重,对这些工人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工人来说,学习新技能、适应新工作模式都是十分困难的。 而这些失业的或地位下降的人群就成为“愤怒的选民”,对美国政治社会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相结合,强化了美国经济社会的两极分化。 有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高技能职业和低技能职业数量都有所增长,而中等技能职业数量则表现出负增长趋势。②Stéphane Ciriani and Pascal Perin,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world Economic Journal, No. 100, 2015, pp. 145-163.1970—2014 年,美国劳动力占GDP 的比重有所下降,信息技术的使用增加了资本收入份额,加大了财富的集中程度,除小部分高技能工人外,其余工人的工资很难再有所增加。③Carl Benedikt Frey, Michael Osborne, “ Technology at Work: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Citi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 Solutions, February 2015, pp. 67-71.因此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使商业资本得以跨越国界,超越空间和时间,因此实际上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相结合,更强化了美国经济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和速度,甚至形成了一种“赢者通吃”的效应,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第三,信息技术革命中出现的社交媒体挑战了美国传统媒体的地位,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声誉,并加剧了美国的左右撕裂。 美国媒体一向被誉为“第四权”,在民众心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随着信息革命的开展,一方面,电视、网络等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媒体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诸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等新兴社交媒体也对传统媒体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后者逐渐失去了对新闻报道的垄断权,甚至有学者指出,面对网络时代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传统媒体将来很有可能被网络媒体完全取代④Ralph Schroeder, Social Theory after the Internet, UCL Press, 2018, pp. 28-59.。 传统媒体深感自身危机,开始积极采取措施迎接新兴社交媒体的挑战,但在激烈的竞争中,它们难免剑走偏锋。 一般来说,新闻报道尽管不可能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但应尽量保持客观中立,以事实为基准,然而为了赢回不断流失的受众,传统媒体越来越迎合民众的偏好,变得日益意识形态化。 例如,《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等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对特朗普大加鞭挞,而且确实在有些报道中有失事实,因此被特朗普回击为“假新闻”。 在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传统主流媒体也日趋极化,在涉及诸如移民、族裔、同性婚姻、控枪、堕胎以及对外贸易等新旧议题上,左翼媒体和右翼媒体针锋相对,争论不休,使美国左右争斗更加激烈。 此外,由于特朗普代表着美国白人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传统媒体特别是左翼媒体在特朗普问题上的不冷静使自身成了上述民众所诟病的“建制派”“精英”等的代名词,从而使自己的公信力受到了更大损害。
第四,信息技术革命使人们的交往、组织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运行及政府治理活动造成了明显挑战。 在信息社会中,人们能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更加直接、便利,因而可以说人们卷入政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但问题在于,网络媒体在带给人们更多信息的时候,也使其倾向于只接受符合自己口味与兴趣的信息,而对与自身不同的观点视而不见、大加批判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人们日益局限在封闭的世界中,不同观点之间缺乏有益的交流,结果就是群体内的同质性程度越来越高,而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政治极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利益集团、民间组织等参与政治,在信息社会中,这些组织尽管依然重要,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借助社交媒体来参与特定的政治议题,这种政治参与形式呈现出无中心、无领导的特征,人们因议题而聚,待热点一过,便消散无踪,政府无法寻找到可以与之进行协商的对象。 因此,面对信息社会中的大众政治参与,以不同群体、不同观点之间的理性交流、辩论、协商和妥协为要义的美式民主治理模式开始显得有些不适应。
总而言之,与社会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矛盾引发了美国的政治危机,另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放大并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强化了美国国内矛盾的复杂性、加剧了社会冲突的强度,而且还增加了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难度,终于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爆发了较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特朗普政府解决美国政治危机的措施以及危机的发展
3.1 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部分民众和精英化解政治危机的尝试
其实,2008 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结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以“改变”“是的,我们可以”的口号打动了那些期待变革、渴望革除美国政治社会弊端的民众的心。 奥巴马上台后,在经济、社会政策以及价值观等方面明显向左转,实施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图复苏美国经济,提高税收,通过“奥巴马医改”,推动有利于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政策,更加积极地推动有利于女性、LGBT 及少数族裔等群体利益的政策措施。 然而,客观而言,奥巴马八年执政,美国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不减反增,族裔冲突及左右撕裂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严重了。 例如,金融危机后,代表着白人中下层阶级以及价值观上更加保守的民众利益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茶党从“草根”中崛起,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①房广顺著:《美国茶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6 页。2011 年,美国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向政府表达了他们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的不满。 可以说,奥巴马解决美国当时初步显现的政治危机的努力失败了。
2016 年大选彻底暴露了美国政治社会的深刻危机,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势力更加壮大,在他们的支持下,民主党非建制派的代表桑德斯一度威胁到党内建制派领导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而属于共和党非建制派的特朗普却连连击败党内的建制派,不仅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还最终成了美国总统。 在这一过程中,草根阶层对精英的不信任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下层白人将希拉里看作是华尔街精英与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认为政治素人特朗普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呼声。
应该说,特朗普的上台正是美国部分民众和精英想要解决其国内政治危机的又一次尝试。在竞选中,特朗普打出了“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不仅赢得了白人蓝领的坚定支持,也赢得了一些意识相态相对温和的民众及精英的支持。②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 年第3 期,第9-21 页。在竞选中,特朗普一方面表现出了相对温和的立场,如反对奥巴马医改,但却不反对由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体系;反对女性堕胎,但认为女性也能够从计划生育项目中获益等。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表现出某种反共和党传统观念的立场,如他明确反对当前的全球化,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正是共和党长期坚持的主张;在外交上,特朗普最鲜明的主张是与俄罗斯缓和关系,而这又与共和党建制派的观念相悖。 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异常坚定,强烈反对非法移民,要求在美墨边境筑墙以及禁止外国穆斯林进入美国等。 另外,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大胆言辞也赢得了不少美国人的好感,他们认为,“特朗普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简单的解决办法”。③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9 期,第3-15 页。
3.2 特朗普化解政治危机的举措加深了危机的程度
然而,要解决美国政治危机的特朗普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特朗普上台本身就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危机。 先是蔓延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民众示威游行,然后是旷日持久的“通俄门”调查,以及特朗普与主流媒体的持续骂战。 另外,他的上台也给美国政坛搅起了一潭浑水,例如,美国中下层阶级特别是蓝领工人多年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拥护者,而共和党则被视作是跨国企业和华尔街精英的代言人,但在2016 年大选中,白人中下层阶级的很多人则抛弃了民主党而倒向共和党,民主党反而成了华尔街部分精英利益的捍卫者,因此,有学者指出,特朗普的上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政党政治“正步入一个重大调整与重新定位的阶段”。①刁大明:“美国两党政治走向及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10 期,第7-17 页。
其次,特朗普上台后所采取的化解政治危机的措施又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带来了新的冲突,使危机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特朗普与其执政团队坚信,全球化是加剧美国政治危机的重要根源,那些遵循着旧思路的简单的增税或减税、放松或加紧移民管控等化解危机的措施,似乎已是山穷水尽,因此,特朗普政府决定另辟蹊径,在“逆全球化”或“重新定义全球化”的思路下,以“美国优先”的策略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也就是说,在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大框架之下,在以下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缓解美国的政治危机。
其一,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尽管有学者认为,特朗普使“过度‘左倾’的美国回归正态”,因而“挽救”了美国,②林宏宇:“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12 期,第90 页。但实际上,特朗普复杂的意识形态立场使政治极化与党派斗争进一步恶化了。从总体上看,特朗普政府基本上持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自上台后,他领导下的行政分支及共和党就致力于纠正其所认为的近年来美国社会过于“左倾”的价值观。 例如,制定“特朗普医改”以努力使其取代“奥巴马医改”,提名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进入最高法院,使最高法院重新染上保守主义的色彩。 在特朗普以及保守主义者看来,只有使美国社会恢复传统价值观,才能应对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冲击。
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时而温和、时而“离经叛道”的意识形态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党派斗争。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当前美国共和党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特朗普化”的趋势,但共和党议员与特朗普的一致性更多体现在共和党的传统议题上,也即共和党是在“与本党一致,而非与特朗普一致”,③刁大明:“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10 期,第38-45 页。因此,当特朗普背离共和党的传统理念时,共和党的党派冲突就会发生。 一方面,就其较为温和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说,特朗普本人与共和党建制派时有龃龉。 例如,在医疗改革上,参议院共和党部分议员因“特朗普医改”保留了“奥巴马医改”中的重要条款而拒绝对其投赞成票,凸出了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的矛盾。另一方面,就其某些违背共和党传统观念的立场来看,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往往会加剧共和党内的分歧与斗争。 例如,特朗普自竞选时到现在都未放弃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想法,这不仅使他深陷“通俄门”的泥潭,还激起了共和党建制派的激烈反对,也因为此,特朗普与已去世的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John McCain)的关系一度变得水火不容。
对民主党来说,特朗普的保守化与某些极端化的立场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特朗普及共和党主导下的最高法院的保守化激起了左派的激烈反抗,后者认为,最高法院一旦保守化,将长期影响美国政治,在涉及移民、平权等方面的司法问题上,最高法院将做出有利于右派的决定,因此,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提名确认过程变得惊心动魄,甚至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④Ralph Ellis, “Anti - Kavanaugh Protesters Keep up the Fight, Even after He’ s Confirmed,” CNN, October 6, 2018,https:/ /www. cnn. com/2018/10/06/politics/kavanaugh - protests/index.html.另外,2018 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斩获众议院多数席位,这增加了他们反对特朗普的权力和信心,在“通俄门”问题上,尽管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要放弃弹劾特朗普,此后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又向司法部提交“通俄门”调查结果并建议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起诉,但为了防止特朗普出格的政策主张打击到自己的支持者,民主党仍然希望在“通俄门”及其他问题上找出特朗普的过错。 因此,2019 年9 月“通乌门”事件曝光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迅速发起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并于2019 年12 月18 日投票通过了针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即“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①“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新华网,2019 年12 月19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19-12/19/c_1125364158.htm。弹劾案送交参议院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前者竭力想抓住特朗普的弱点,掘出特朗普的罪行,在2020 年大选中将其击败。 两党斗争的白热化还体现在,2020 年2 月5 日,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时,拒绝和佩洛西握手,而佩洛西则公然撕碎了特朗普的国情咨文。
其二,在移民政策上,特朗普一上台就签署了被称为“禁穆令”的行政令,修建美墨边境墙,控制全球化下加速涌入的非法移民,希望以此为契机缓解美国紧张的种族关系、失业问题以及国家认同问题,但这同样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一方面,“禁穆令”三次颁布,都在全国各地掀起轩然大波,反对声浪此起彼伏,联邦地区法院三度阻击,特朗普不断上诉,最终,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判决。 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最高法院最终选择了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系却变得非常紧张。 同时,在对待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上,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也进一步加深,路透社和益普索对美国民众进行的联合调查表明,“高达49%的受访者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表示支持,反对者则有41%”。②郝亚明:“从‘禁穆令’看美国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人民日报》,2017 年3 月10 日,第18 版。
另一方面,在美墨边境筑墙的问题上,特朗普与民主党人在筑墙费用上难以达成共识,纵观特朗普以边境筑墙来解决美国政治危机的过程,不难发现危机程度的加深:从政府关门到特朗普颁布紧急状态令,从国会对紧急状态令的否决到总统对国会的否决,边境筑墙问题一波四折,特朗普与共和党部分议员也分歧重重,与民主党的对峙异常激烈,几乎达到顶点,尽显政治极化的恶果。
其三,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上,首先在经济方面,为了应对中产阶级衰落、贫富分化等问题,特朗普一方面放松金融管制、进行大规模减税,以吸引境外的美国资本回流,为白人中下层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则从贸易不平衡问题着手,“借‘公平贸易’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③刘均胜:“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中日韩自贸区”,《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12 期,第2 页。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一直宣称要进一步提高关税,以此胁迫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 另外,美国又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签订包含了“毒丸条款”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韩国签订贸易协定,与欧、日发表关于贸易的联合声明,意图以此降低美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使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被逐步边缘化”。④孔庆江、刘禹:“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及其应对”,《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10 期,第49 页。
在外交方面,为了达到“重新定义全球化”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举起单边主义大棒向全世界挥舞”,⑤张建辉、郑易平:“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调整、原因及其前景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 年第6 期,第27-45 页。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同时,迫使欧盟增加军费、日本多分摊驻日美军费用,意图通过节约开支的方式减轻美国的财政压力。 另外,特朗普及共和党强硬派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通过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方式崛起”,因此责难中国,将中国定位为“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并制定所谓的“印太战略”,意图遏制中国,挑起“新冷战”。⑥Michael Lind, “Welcome to Cold WarⅡ,”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8, pp. 9-21.特朗普还想通过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方式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只因受到共和党强硬派和民主党的强烈抵制而作罢。
然而,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上,特朗普针对其传统盟友及中国的做法同样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在对待传统盟友方面,美国与它们的新贸易协定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使盟友增加军费、退出部分国际组织等方面的举措虽然可能减轻美国的财政压力,也可能因此缓解美国国内矛盾,但特朗普不留情面的做法却伤害了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感情,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因此而损害了其自身的实力。①Lawrence Freeman, “A Subversive on a 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09, p. 39. 在该文中,作者明确指出,美国实力的基础是联盟,转引自[美]约瑟夫·奈著,[美]邵杜罔译:《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7 页。而且,民主党与部分共和党人也反对搞坏与其盟友的关系,因而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的做法又引起了党派矛盾。 在处理中国问题方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贸易摩擦等方式,迫使中国对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并试图使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球化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 然而,中美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给美国股市带来了不利因素,若美国民众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收益不能弥补其损失,则不仅不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还会引发民众对特朗普的强烈不满,加剧美国的国内矛盾,并且可能导致特朗普连任之梦破碎。 基于上述现实,特朗普近来也不得不降低姿态,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做出让步,以减少自身的损失,然而,可以预见,即使中美之间达成了贸易协议,由于特朗普仍然着眼于从反全球化入手来解决美国的政治危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时急时缓地持续下去。
四、结 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与欧洲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一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即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信念”,②[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景伟明译:《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新华出版社,2017 年版,第6-7 页。它是美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来源。 长久以来,这个信念与美国的政治体制之间都存在着裂痕,换句话说,也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裂痕,这个裂痕使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而且美国人还不断试图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这使得美国政治体制一直在恒久的冲突中不断地进行着变动与改革。
追溯美国的历史,不难发现,贫富分化、族裔冲突以及价值观冲突等引起当今美国政治危机的社会矛盾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例如,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贫富分化程度非常严重,外来移民、族裔冲突也时常刺激美国人的政治神经,二战后开展的民权运动中,族裔冲突更是异常激烈,但这些社会矛盾都没有颠覆美国的国家认同或“美国信念”。 实际上,阶层、种族乃至价值取向各异的美国人在其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所提供的弹性空间和纠错机制内,在对“美国信念”的坚守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政治博弈实现了能令各方基本满意的利益分配,从而较为成功地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 在这一过程中,理想和现实的裂痕虽未能得到弥合,但美国的国家认同在新的基础上得到确立,其政治体制也在博弈中得到修补。③牛霞飞、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 年第5 期,第44-64 页。正如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所言,只要不发生危及群体核心价值的破坏性冲突,一般性的、针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冲突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④郑易平著:《冷战的终结——20 世纪超级大国的政治体制特征、稳定性及对抗过程分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版,第246-247 页。它不仅不会动摇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还会促进社会的团结和整合。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前美国政治的危机程度还未达到南北战争时期的那种强度,围绕“美国信念”或科塞所言的核心价值而形成的共识虽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尚未越过警戒线,尽管它已经靠近了警戒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美国政治危机的烈度确实已经到了引发崩溃危险的峰值,但还是有可能渡过危险期,使危机得到缓和,并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更进一步来看,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同美国相似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的负面效应加剧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例如,在英国,为了摆脱欧洲债务危机与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英国选择“脱欧”,但这又反过来给英国社会造成了危机;在德国,超过200 万难民短期内无法顺利融入德国社会,反而给德国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使极右翼势力崛起;在法国,马克龙的当选打破了法国政治近40 年来“左右分野”的传统,同时,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逐渐崛起,此起彼伏的“黄马甲运动”也使法国政坛震荡不已。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融合的、复杂的、系统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具有强大的惯性,完全抛开这些规则而另起炉灶是极不现实的,因此对全球化规则体系的修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势头也难以阻挡,面对它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全新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可能经历痛苦且长期的适应过程,正如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人类需要“努力理解并掌握新兴信息社会的规则”。①Walter Russell Mead, “The Big Shift,” Huadson Institute,https:/ /www.hudson.org/research/14334-the-big-shift, 访问日期:2019 年3 月2 日。从上述意义上说,修正全球化以及应对信息革命的挑战非一日一功,也非一国之力,而是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和人类共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