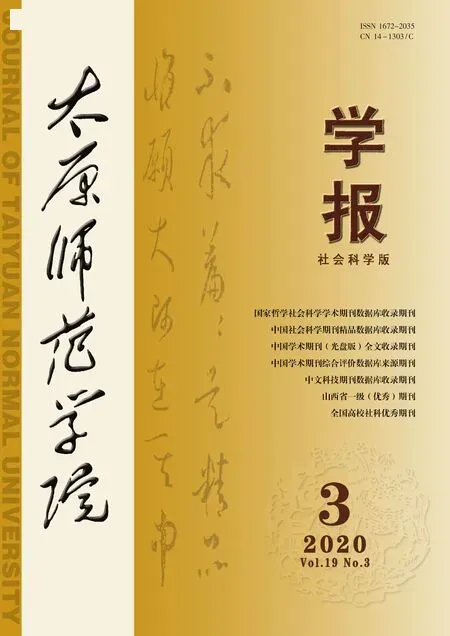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儿童伦理观念:自然、成人、承嗣
李 锐
(1.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2.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中国传统伦理中不但包括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阶级伦理,还包括关于老人、儿童等的群体身份伦理观念。就儿童伦理来说,儒道两家都有关于儿童的论述。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要从道的角度来看待婴儿;儒家鼻祖孔子则关注儿童学以“成人”,主张采用循序渐进的学习成长方法培养子弟;中国宗法社会则将承嗣作为家族核心伦理精神以延续家族、敬奉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儿童的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儒道两个维度,而具体体现为自然、成人、承嗣三种主要伦理观念。
一、自然
(一)儿童体现自然之道
在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世界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自然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实体的自然也是抽象的自然,是物质的自然也是自然的运行规律。道家将自然等同于道的承载者,自然是宇宙原初的状态,也是个体生命的原初状态。对个体来说,生命之初都会保持着自然的天性,这是最接近自然也就是道的本真阶段。因此,在道家文化观念中婴儿天然具有自然本真的状态,比起世俗化的成人更接近于天道。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提到了“婴儿”,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1]22,精神和形体合一而不分离,聚结精气以致柔和温顺,能像婴儿的无欲状态吗?婴儿是成人学习的榜样,可以从婴儿身上窥探天道;“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将所有世俗欲望放下,达到返璞归真的本真状态,就是婴儿尚没有意识的阶段;“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豁。为天下豁,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1]73。可见,老子推崇阴阳未分、阴阳合一的状态,也就是混沌境界,回到生命的源头体验生命原初的神秘智慧。老子对“赤子”再次给予了礼赞:“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1]145赤子就是刚出生、毫无心机的婴儿,颜师古注:“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发,其色赤”。其实,“赤”不仅有红色之意,还有纯粹之意。道家将婴儿视为天道体现者,与许多宗教认为儿童能够通达天意的认识是一致的。佛教“明心见性”,心性就是本真;基督教认为小孩方能进入天国,如《马太福音》中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入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到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受尊敬的”[2]187。这些宗教层面的论述具有相通性。
(二)童谣具有预言功能
童谣体现的是儒道融合以及人类纯朴的自然崇拜思想,“自然观”与童谣是相互联系的,“自然观”并未将自然神秘化,它是一种哲学思想,而童谣中有明显牵强附会的迷信色彩。在传统社会中,童谣对于政治具有巨大的预言功能,对于民众来说,童谣不但是民意的反映,更是上天借助儿童所传达的天意。在古人的观念里,儿童更贴近自然,也就是离“天”更近。儿童被看作能够传达天意、洞察神秘规律的群体。儿童无意唱出的歌谣,就是上天的意志。童谣一般比较简短,采用隐语形式表达一种预言,节奏轻快,琅琅上口,有利于迅速传播。中国传统童谣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背后的伦理原因即在于儿童与道合一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与西汉盛行的谶纬思想结合在一起,就会被许多权谋之人所利用,在政治斗争及历史进程中产生巨大功能。童谣天然适合于谶纬,还能保护制作者的安全,可谓一举两得。谶谣常常以童谣的面目出现,因而在《五行志》中,凡是预言后事的谶谣多被称作童谣。童谣的预言功能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舆论影响力,儿童就是舆论的媒介,通过儿童的传唱,童谣得以流传开来,营造出一种神秘的色彩,让接受者产生敬畏甚至恐慌心理,从而鼓动人心、引导民众情感意志。其实,作为民间诗歌的一种形式,许多童谣正是民众内心情绪和意志的表达和反映,本身具有舆论展现与导向功能。统治者历来注重收集民歌,以体察民俗民情,了解民间舆论导向。东汉以后,谶和纬基本合二为一,谶纬之学本来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童谣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谶谣由于其神秘性和‘应验’性,给人造成一种天意如此的印象,加上古代有荧惑星化为儿童传谣的说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上天垂象’,即上帝向人间降下的语言符号和预兆。《晋书》指出:‘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潜确类书》也说荧惑是执法之星,它的精灵化为儿童歌谣嬉戏。”[3]35
(三)儿童作为文学表现对象
受道家审美观影响,文人对自然始终具有独特的热情,自然始终是安放个体心灵的最佳处所,在描写自然的过程中,儿童成为文人笔下最重要的艺术描摹对象之一。在文人笔下,儿童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儿童成为自然的眼睛和心灵,儿童让孤寂苍凉的自然充满了生机和灵感,自然中若无儿童便少了许多灵动和谐舒缓的生活气息。诗人们以细腻的艺术眼光去发现童真童趣,描摹儿童形象,表现出淳朴的人文情怀。在唐代及以后的诗文图画中,有大量的关于儿童的诗句和形象,表达诗人、画家的情感和生活态度。唐代诗人中,杜甫关于儿童的诗句最多,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阆水歌》)其他诗人作品中也多有儿童形象出现,如:“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贾岛《寻隐者不遇》)“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黄庭坚《嘲小德》)“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黄庭坚《牧童诗》)“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宿新寺徐公店二首》)这些诗歌中有故乡的儿童、山中的童子、放牛的童子、牙牙学语的童子、游戏的童子,种种情态,生动自然。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代表新兴市民个性解放的思潮,李贽是这一思潮的代言人。他大力提倡恢复人类的自然情感和真实人格,对污染人们灵魂的假道学进行了尖锐批判。”[4]178此时整个社会思想压抑,理学盛行,道学独大,文人的自然伦理情怀受到极大压抑,在此背景下,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呼唤道家自然伦理精神。“童心说”认为,童子乃成人之初,童心是人心之初,童心就是纯真的本心,没有一点虚假伪作成分,因此,人如果失却童心,便是失却了真心,真心失却,就不是真人。为什么人们会失却童心呢?李贽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将外界的“闻见道理”作为内心主宰,最初一念的本心便被遮蔽住了,童心也便失却了,不是发自本心因而与本真相距遥远。“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童心说》)[5]96李贽的思想是对老子“赤子”思想的再次发扬,其中也融入了佛教的相关思想,以抨击当时教条的文风和令人窒息的伦理氛围。
二、成人
儒家儿童观认为人道更为切实,因而论人道重于论天道。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更重视人事,未知人焉知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6]112,因此,人道才是儒家的伦理核心。对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不同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儒道两家对于儿童所表现出的不同伦理态度。人道之要就是修身、齐家,即以修养良好品性、德性为根本,进而学习文化知识,“儿童”是一个“成人”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应当受到家庭社会、师长朋友的引导、帮助。在儒家看来,儿童尚为“小人”,不具备智慧和理性。与道家强调感性不同,儒家推崇理性精神、君子人格,儿童就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文质尚未彬彬,只有通过反省、学习、思考,方能获得成长,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6]64的层次。道家的感性与儒家的理性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两个源头,相当于尼采所区分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两个源头相伴相生、此起彼伏、相互交融,形成了内涵丰富、理念多元的伦理精神。
在儒家文化中,“学以成人”“约以成人”中“成”是动词,“人”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要脱离天地的母体成为一个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独立行动能力并且具有符合社会伦理要求的良善道德的个体。儿童就是“弟子”,相对于道家重视婴儿阶段,儒家更重视已经具备可塑性的童年阶段,这个阶段可以接受文化知识,进行社会化教育,这个阶段就是向社会化、成人化的过渡阶段。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7]2。文者,人文化成也。“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8]58“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62“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6]176教学就是化育成人的过程,“学”就是通过学文学礼习得文化,成为具有理性和责任感的社会人。由此可见,儒家重视后天的“习”而非先天之“性”,通过习来化性,以后天实践完善未圆满的天性。“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6]4儿童要接受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养成良好的品德,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成人”就是自强不息孜孜不倦,不断学习进行自我完善与提升的过程,就是“学以成人”“约以成人”的过程。学习的内容就是礼乐、道德、文化,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四科。儒家礼乐教育正是“成人”的一种重要教育内容,人需要经过文化的外在修饰,才能够文质彬彬。因此也可以说,“成人”的过程就是“学文”“习礼”的过程,即接受文化学习、教育熏陶的过程。
“约以成人”主要体现在礼乐教育中,通过礼乐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让人获得“成人”的身份与能力。《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9]9《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10]665“冠礼”便是“约以成人”的一种重要形式。“冠礼”是中国古代的成年礼,为男子冠礼,女子笄礼。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中国古代对成人和儿童的服饰发型有不同的标准。冠礼、笄礼都是社会化的成人仪式,《仪礼》《礼记》中有“冠礼”等仪式的记载。礼乐教育就是为“成人”服务,让个体不断趋向“仁”的理性主体。
三、承嗣
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及祖先崇拜文化中,儿童是家族延续以及民族发展的未来。商代甲骨文中不乏“多子孙”“多子女”的记载,这反映出商人对子孙的重视。《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的结合、生育源自天地阴阳化生之理,因而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神圣性。经学对生生之德的尊崇,深藏着对“生”之道、“化”之端的生命意识,因而充满神圣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所以“易基乾坤”;“妃匹之际,生民之始”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所以“诗始《关雎》”。[11]189《关雎》言夫妇之德,人伦之始。《诗经·大雅·假乐》中用“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的颂词来祝愿和歌颂周天子,将“千禄百福”与多子多孙相提并论,反映了典型的“多子多福”的婚姻与家庭伦理观。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记载:“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道也。”[12]27之后,《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中也有相关记载。家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延续后代,生育乃是自然之德、人伦之要。古人把生育后代看作接续香火和完成孝道的第一要义,认为传宗接代是缔结婚姻的首要目的,婚姻的功用在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13]270“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意为不孝的表现有三种,其中以断绝后嗣这种罪过最大。这一理念体现出中国人对家族的绵延与继嗣格外重视。孝的内容不仅有“生之以养”和“死之以葬”,还有重要的一点,即以后嗣的承继不绝来实现对先祖、父母的祭祀和家族的延续,如果没有后人,则家族生命不能延续,这是一种大不孝。孔子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6]7传统家族文化中将儿童作为继承者来培养,以延续家族生命,传承家族的家风与志向。
中国古代承嗣的儿童伦理观、生育观、文化观影响到了周边许多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对于承嗣普遍比较重视。承嗣观念至今仍然渗透在日本社会文化当中,“像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喜爱小孩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这在美国却不是那么重视。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是为了绵延家系,传宗接代,保持家门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14]230。由此可见,承嗣观念至今仍然有着极深的影响。
四、结语
自然、成人、承嗣三者并非各自孤立,而是具有一种内在关系,能相互联系在一起。“儿童”一词中,“儿”意味着天性、天道,“童”则意味着人道“化性”的学习。“儿”是无意识婴孩阶段,“童”是有意识开蒙过程。老子关注“婴儿”,孔子关注“童”。 道家视野中的儿童阴阳一体不分性别,儒家成人视角中的儿童,则承担家族使命,具有社会义务,是有性别倾向的。儒家并不认为天道包含在人的天赋中,要求人不断通过自己的求索与学习,达到接近天道的目的。至孟子时,儒道的儿童观念开始融合。孟子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13]282“赤子之心”即婴儿之心,婴儿之心当然纯洁无瑕,没有丝毫杂念,孟子已经将道家关于婴儿的观念融入儒家文化中,表现出儒道互补的特点。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13]412这里的“放心”为所丢失的本心,“放心”中“心”为本然之心,孟子认为此心就是仁,再次回到了对天道的体悟,而非孔子所谓“文”的学习,这与李贽的“童心说”有相通之处。孟子综合了道家的理念,因此受到了荀子的批评,认为他偏离了孔子思想。实际上,儒家“成人”思想并非与自然相对,而是寻求与自然造化相对应的个体的社会价值,并不丢失其本来的天性,涉及社会、家庭与个体人生价值;“承嗣”主要着眼于家族血缘传承,立足于种族延续以及宗法制下祖先崇拜文化的延续。中国古代的儿童伦理观念至今对中国社会的价值文化仍然有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注重家庭教育,将儿童作为审美对象,注重保护儿童天性,推崇自然纯朴活泼的状态,等等,这些思想融入了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对人类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