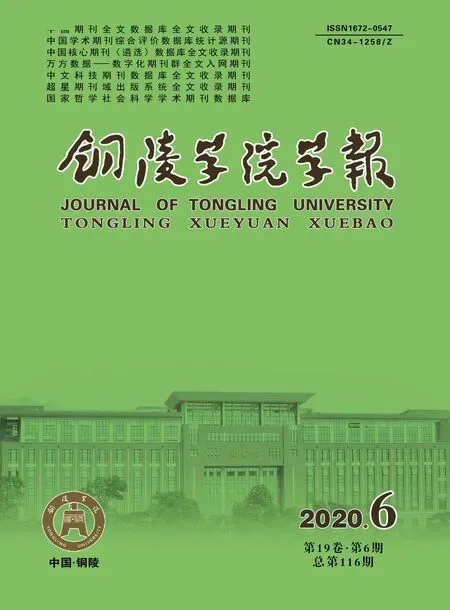汉字构形中审美意象的显现
陈 虹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汉字的创制与汉民族象思维方式的选择和形成几乎同时发生,作为民族思维集中体现,汉字与“象”一直存在着深厚执着的意绪与难分难解的情缘。我国古人给汉字最早的命名为“文”。许慎在《说文解字·叙》 中解释汉字创制过程时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文者,物象之本。”[1]形象地说明了汉字是天地万物和人情事理的凝固体,它用符号的形式记录了一个丰富而生动的生命世界。顾炎武说:“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那么又何所谓“文”呢?许慎解释道:“文,错画也,象交文”。也即,“文”是用以敷在器物、服饰、旗帜以致身体上的、用不同的线条与色彩交错而成的图案,“文”即“象”。可见,中国先民在创制文字的初始就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意识,汉字不仅作为记录语言传播讯息的工具而创造,还先天地带上了畅神怡情的审美性质。
与字母文字不同,汉字不是对汉语亦步亦趋的附庸,而是通过字形符号来表达观念意义。汉语依赖文本而存在,并且通过汉字来获得一种“雅正”的标准和超越于方言的规范化力量,汉字成为“言”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本源,甚而与“道”贯通。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出了“文”源出于“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立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在他看来,以汉字为主的“文”是“天地之心”,易象、八卦、河图、洛书、文字乃至“元首载歌”、“益稷陈谟”等等都是圣人用以垂显“道”的媒介。在宋代朱熹那里,“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2]。也即“文”与“道”同构,文与道一样的神圣。文本以汉字而构筑,汉字又以象寓道。因而当代画家石虎则干脆认为:“每个汉字是宇宙灵界的范畴图式概念。汉字以小寓大,以字寓道,是宇宙的内在本质之本元形式。”[3]汉字正是通过浸润了情感的图像来摹写世界、呈现意义,在对世界的呈现过程中因凝聚了“我”的意识情感而千变万化、意蕴重重,成为宇宙灵界的范畴图式,不仅显示了“为我之物”,甚而可以一并带出其身前身后的境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构形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意象”,是谓审美意象。
汉字具有鲜明的意象性,这在当今汉字研究领域几乎已成为定论,这里不再赘述。而强调汉字显现的意象是一种审美意象,因为审美意象既具有意象的一般特点:以象表意、形象生动,包合了主体经验,内涵模糊多变、不易确定等,同时又是一种特殊意象:它是人们审美活动的成果,是情变之所孕,是主体在融入某一种情感状态的情形下,对观照对象饱含情感的直观和体会,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意象世界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4]汉字意象正是这样一种带有艺术特质的可被审美感知的“意象”,它“将形、声、义合为一体,从而在一个汉字中,凝缩了我们丰富的感觉,就像一个‘集成电路’,以一种可以寻索却很难明示的方式,唤醒我们的感觉。”[5]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对汉字形体的审美观照中,调动起视听感觉,交融着理解、想象、情感、意志等一系列复杂的审美心理,在其千变万化的构形中去相遇一个完整的具有审美情趣的世界。
德国学者马丁·泽尔认为审美的对象即“显现”的对象:“事物的感性外观从来就不是审美的核心,审美的核心是当下的显现”[6]22,那么就汉字而言,当它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非实用或伦理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感性的外观也不能完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而是要“将文字变成‘直观’的场景,需要‘图像还原’”[7]另一方面,“尽管当下发生的‘显现’事件是审美活动的核心特征,但它不是审美可能性的全部。因为现实中发生的审美经验远不止专注于当下这么简单,它往往超出当下,引入了幻觉、想象、理解与反思。”[8][6]20当我们完全沉浸于某物的感性当下性中,它就是以一种“纯粹显现”的形式进入感知;当一个审美对象勾起我们对某种生活情境的联想,我们就可称之为“气氛式显现”;而当感知对象携带了感知者的想象,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表现,则可以看成一种“艺术性显现”形式。本文尝试以此三种显现形式来分析汉字的构形,以期对汉字构形中审美意象的生成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纯粹显现
马丁·泽尔认为,如果我们只关注对象同时和瞬时的出场方式,让对象仅仅停留在其感性显现中,而我们以“凝神性”的审美感知方式与其相遇,这种“显现”即为纯粹显现。汉字的意象性的创构方式,使我们在凝神直观中得以相遇一个个字象,这应该是汉字构形为我们审美感知提供的第一个维度:“纯粹显现”。
汉字的构形以“象形”为本。《汉书·艺文志》中把汉字创制的根本方法概括为六种: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前四种方法中都有个“象”字,而后两者则是由其派生出来的。宋郑樵说:“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通志》 卷三十一 《六书略·象形第一》),并将象形字具体地分为十形、六象,“六象犹嫡庶也。”①也就是说把六象当做象形的附属类。明代的杨慎在《六书索隐》中把六书的前四“象”当做经,后两书看做“纬”,也突出了“象”在汉字中的重要意义。从思维方式角度来看,象形字无论是“象”物、“象”形还是“象”态,都是人类原初思维的基本形式——实象思维(直观动作思维)的符号化和固定化。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用感性直观的方式实现象形字的图像还原,“将直观的目光朝向某物,变成了被思考的某个东西,通过目光交遇的方式在自悟中把握和达到本质。”[9]
前文已有所述:汉字虽来自自然人生,却不是现象界机械的模仿,而是经过了人心的过滤具有主观品格的符码。汉字中的图象也不是对天地万物的客观呈现,而是融入了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生命感觉与经验,成为人心营构之象。古汉字用线条表现万物的形态和神采,显现之象总是有最鲜明的特征。拿常见几种动物的名称来看,“牛”、“羊”、“鹿”形象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其两只角形态的刻画上,牛角是直指向上的,羊角是向下弯曲的,鹿角是分叉结节的。其他动物亦是特征鲜明:象有长鼻,豕具竭尾,犬为修体,虎有巨口,鸟有尖喙,凤有靓羽……还有蚕蝉黾兔、鱼龙蛇龟等等,莫不是叫人在直观的瞬间实现对其本质形象特征的顿悟。再如植物的形象刻画:“木”是挺拔的枝干,“帝”(甲七七九)是一枚挺直的承托花瓣的花萼,“果”(乙九六零)突出了枝干上的累累果实,“禾”(乙四八六七)是饱满的长穗低垂……自然现象:(佚三七四),显示一轮圆日,(甲三九四一《续甲骨文编》),直现一弯初月,(佚五五),如倾盆雨点从天而降,“申”(佚五九)象曲折流动的闪电当空划过,风云水火、山川田土,莫不尽显;摹画人体的:人(甲七九二),屈腰垂手、谦卑侧立;(乙七八二八)首,就是一动物头颅的简笔,齿(乙六一一),口(甲一一八一),舌(合22405)等等,都是触目可辨,直观立得。仰观俯察、远摹近取的物象就这样形神毕肖地凝定在视觉图像之中。
汉字构形中的“象”不仅摹仿客体对象的特征,还对其做符号化的综合概括,具有写意的性质,“我们认为:汉字的特点不在写实,不在具象,而在写意。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0]如“女”的甲骨文写作“”(甲二三五六),如同一个柔顺拘谨的女子屈身静坐的样子,既有“象”——反映了女人的形体姿态特征(象),但也有“意”——其“拘敛”形象又包含着造字者对女人的主观意识。我们在意识中还原了眼见事物的具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并且将其用形式显示出来。我们意识到某个对象也就是一个构成对象、显现对象的过程,也即“意象”生成的过程。这与胡塞尔的“意向”概念便似有了相通之处,“意向”这个概念包括了“意象性行为”和“意象对象”的融合,意向之物既呈现物的真实形象,又有意识虚构的结果,使万物皆着我之情感,字象尽显我之个性。
指事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另一种“象形”,不过是将心中的意象用线条表达成符号,来表明意义的一种造字方法。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依类象形谓指事、象形二者也”,并认为“象形者,实有其物,日月是也。指事者,不泥其物而言其事,上下是也。”也就是说,象形字所“象”的是实在的物象,而“上”“下”等指事字所“象”的是囊括众物的物象,是一种共相②。指事字有的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抽象的符号构成,如:“本”、“末”就是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各加一划以示根部与树梢,“自”本是指鼻子,以手指鼻成为“自己”的代称。而“旦”,则以一横表示地面,上面一轮旭日升起,是谓早晨。这些意象虽涉抽象事理,但仍是触目可及,瞬间顿悟。
要之,由于汉字象形表意的基本构造方式,我们相对容易去注意象“形”字的感性形态,沉浸于这种“纯粹当下”中。然而这种“纯粹”的显现可能并不“纯粹”,因为它无可避免地被各种当下所共存并互渗的显象所介入,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意味。
二、气氛式显现
如果说纯粹显现是“显现”的当下化,是观照者迷失在对当下的直观中,没有想象也没有反思,不寻求也不去发现意义的话。气氛式显现则是“某物通过生存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呈现在感知者的面前。”[6]172显现对象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形态,来赋予所属的情境一种独特的形态,从而实现对一种生活情境或生存意义的表达。这种“气氛”可以理解为对“生存交互性”的一种感性——情感觉悟。换句话说,人们通过一种交往性的审美感知去逾越他所处的时空位置,使得我们与更大的生存性现实发生交往。
独体的象形字和会意字显然并不能满足指称纷繁的物象世界、表现丰富的生活与情感的需要,形体千变万化的组合成为汉字创制的重要方式。通过字象的并举配合,对立穿插,诸显象之间仿佛进行着一场通感游戏,从而在一种气氛式显现中生成新的意象。
会意字是指在象形基础上通过形体的重新组合而形成新字,具有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感性形态。人们在组合字象的基础上通过联想和想象创建出新的审美意象。这种组合有同体会意字和异体会意字两种。同体会意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部件组成而成,相同意象并置构建一种特定的情境。如两人相随为“从”,两人相背为“北”,三人并置为“众”,两火相加为“炎”,二木为林,三木为森。这里“木”、“人”、“火”都是相对应字的意义之象。而将三个相同字象呈“品”字形排列,是汉字构形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如:淼、磊、犇、猋、骉、森、晶、众、品等字,这种字象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结构稳定之感,同时还传达出强调渲染的意味,激发人们的联想。如“犇”的三牛齐驱,显示的是一群野牛在原野狂奔的情境,类似的还有“猋”、“骉”等。再如“晶”字三“日”相叠,我们可以极力想象其璀璨美丽;而“品”三“口”相续,强调其回味无穷。如此,每一个貌似相同的字象都有了丰富的表现力,也就是说在它自身所固有的领域得到了充分的感知,从而让一种有感染力的气氛变得醒目,产生了以少状多,以有限象征无限,超越了图形有限表达力的效果。异体会意字中几个意义之象各不相同,在并置组合中进行象征性的图示。以甲骨文中的“目”字为例:有“目”为见(甲二零四零),是人以目平视前方;(佚五三三)而“望”的眼睛则有了后仰的角度,极目远眺之态毕现;(765)“省”则似睁大目观草,有省视之意;“相”(前五·二五·五),犹如俯身仔细地观察树木,也有探视的意义。显然,以“目”符同其他形符组合而成的会意字,都有以目视之意。同样,以耳为核心的甲骨文会意字:如闻(甲一二八九),象人跪坐仔细谛听的样子,聴(一期前六、五四),从耳从口,以耳感知声音为聴;这里“耳”的形象特别突出醒目,也渲染了一种静听的情态和气氛。还有一些会意字是由象形组成的一幅画面。如(粹四八五),一个人坐在煮饭的锅前,把头扭向相反的方向,表示饭已经吃完了,就是“结束”,就是“既”;(323),而一个人跪在锅前,则是要开饭了,就是“即”,(后一·一七·三)“伐”,戈架在人的脖子上,可见征伐时杀气腾腾之情境。这些字的每一部件都参与了字象的构成,而创造的意义又远大于各部分形体意象所表达的综合。在这些审美意象的显现中,类比和联想并重的交互性审美直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字还常常有意将所取之“象”在时间维度上的意义流转,化为空间维度上发散的意义,以富有意蕴的视觉图像来实现作为概念单位的空间性和声音时间性的有机统一。如“咺”字,从“亘”,意为婴儿哭泣不止,“不止”本属时间的范畴,但是“亘”用一圈圈回环的意象表达时间连绵不断的含义。再拿“时”字初文来看(2463),画中一只正在走动的人脚加上太阳,意为“太阳在行走。”比喻时间的流逝。甲骨文“昃”(燕三·九四背)字的形态也颇令人玩味:“日”下是“仄”,本义为日光下侧偏之人体投影。古代先民用日照与偏斜之人影这一空间距离所生成的现象,表示太阳偏斜这个时段。直观斜阳旁边的一抹人影,我们感受到的是夕阳西下白日将尽的落寞。类似的还有黄昏的“昏”(京津四四五),以日在俯身的人形之下,会日落意。“暮”,日落草丛中,以示夜色降临,等等。
占汉字绝大部分的形声字,是以其形体之象与声音之象来共同参与气氛式显现。因形声字的形旁是由独体的象形字演变而来。虽然其象形的程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降低,形体与意义建立联系的理据性也逐渐模糊,但是在长期的使用中经过循序渐进的演变,形体和意义之间又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理据性。因此形体往往较稳定地代表某种意义。比如表示草本植物,凡以艹为形旁的字大多属于草本植物,像葫、芦、蘑、菇、蒹、葭等;又如,表示与刀有关。有字:割、刮、划、刻等等。“土”(1188)则与土地、建筑有关,如坡、块、坑、寺、垃、圾、城、场等等。在这些字中,形旁成为意义的载体,成为整个字的意义之象。
另值一提的是:形声字中声符有时也参与审美意象的构成。汉族的先民们在生活中不仅常用自身的感叹呼叫来表达情感,还在倾听自然界的声响时产生灵感。他们把捉了大自然中最能触动感官、触动心灵的声响并以之为事物命名。章太炎先生在《国语论衡·语言缘起说》 中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语言现象:“何以言雀?为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何以言鸳鸯?谓其音加我也。”其实不仅鸟禽,许多事物的命名皆可以此寻迹,如牛鸣为牟生而叫牛,猫叫似喵则呼猫,铃声叮铃名为铃,钟声叮咚名为钟,树木果实成熟,“骨碌”一声落地,即成为“果裸”,简称为果。江、河二字的构形也是来自对长江、黄河惊涛拍岸声响的摹拟。因“江”的声旁“工”的孳乳字里有一“碽”音gong,《集韵》中解释“击石声”,长江之中多悬崖巨石,激流冲击时发出gong-gong 的声响,所以人们就专门叫这条大河gong,并且专门用gong 声的“工”加个“水”旁造成了“江”字[12]。同样,“河”也是为黄河而专造的字。“可”本发ha 之声,形容黄河之水奔流的声音,加上“水”旁构成“河”字。可见,“江”、“河”之声旁之所以用“工”、“可”二字之读音,是源于同长江、黄河的水声相似,因此取以读此音的汉字加上形旁以喻之,是谓声象。声音之象虽然不能直接被人的视觉捕捉,但因为审美感知的相通性,富有特征性的音响可以把人带入特定的情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参与了汉字审美意象的生成和显现。
三、艺术式显现
泽尔认为:艺术是一种表现,这是它们与其他显现对象最根本的不同。“而若我们面对的显现,在自身显现之外另有所表现,牵涉到想象和解读,从当下拓展到人类文化的广阔空间,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艺术式显现。”[6]20同时泽尔强调,“艺术作品区别于新闻照片、交通信号、象形文字等,是一种精确的、独特的符号元素的排列,是一种布局性的表现。……显然,他对中国的象形文字——汉字的诗性特质并未有足够深入的了解。钱穆先生就曾指出,汉字是“别具风格的一种代表中国性的艺术品。我们只有把看艺术的眼光来看中国字,才能了解其趣味。”[14]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也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一文中认为,汉字远不是任意的符号,汉字的思维图画由符号唤起,但又比符号生动具体得多。同时汉字中包含了诗的品质,即将“大自然的真理一大部分隐藏在细微得看不见的过程之中”[15]因此,笔者认为,汉字也可以作为一种能表达的显现构造物而存在,它以特殊的形制召唤着形而上的意味。我们通过与其在艺术式显现中的遭遇,去感受其在感性形态之外的深不可测的内蕴,并获得对我们生活不可控制的当下的直观。
譬如甲骨文中的“日”和“月”,分别是对太阳和月亮形状的摹拟。月亮有圆有缺,但以缺月居多,因而示之为“一弯明月悬中天”之形,而“月”的声训也正为“阙也”,与之吻合。人们由“阙也”的月亮意象,联想到它的宁静柔美的阴性特质,甚至可以联想到人臣之相、妇女之象;而“日”字,《说文》解释:“时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其圆满灿烂、热情四溢使人联想到天、父、夫、兄等一切阳性物象。《说文义证·卷二十》引《洪范传》云:“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纪,群阳之精,众贵之象也。……故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应也。”人们还可以从甲骨文“”中产生神话的想象,如唐代的李阳冰认为“古人正圜象日形,其中一点象乌”;段玉裁也把《说文》中“日”的古文形象当做日中有乌,因为中国古代有后羿射杀太阳金乌的传说,因而我们似乎并不难接受这样的联想。再如(大),象人两臂左右平举、两腿张开正立之形。《说文》解释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王筠在《说文释例》中道:“此为天地之大,无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非谓大字即是人也。”由字形想到人体正立之“象”,并进而想到人为至贵而为天地之大,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进行思考。可见,当我们的视觉与汉字构形中字“象”遭遇,就会以线条的抽象框架形象所激发的意象思维与字所对应的物象复合,于是有了“意”的绵延,这种绵延使汉字具有了诗意般的不可言说性。汉字的构形达到了一种超然的意义美感和建筑美感同享的境界[16]。这不正是一种艺术式的显现吗?
总之,汉字构形中空间组合的丰富变化带来的是审美意象的蕴藉多义,而审美意象的显现方式也绝非静止的、固定与单向度的。正如泽尔自己所认为:“这三种显现所描述的只是三种遭遇的可能性,而不是三种固定的对象或者态度。在同一种对象身上,三种显现都有可能发生。而且三者之间也完全可能相互交叉、重叠。它们进一步展示了审美的开放性。”[6]20或许正因为此,生成了汉字书写无限丰富的意义表现空间,最终成为“穷变态于毫端”的书法艺术,“完成了从民族共同体的共性符号到展示个体生命的个性符号的转换。”[18]
注释:
①《六书略·六书序》中所谓十形分别是:“天地之形,山川之形,井邑之形,草木之形,人物之形,鸟兽之形,虫鱼之形,鬼物之形,器用之形,服饰之形,都是具体物象之形;六象指的是:象貌(爻、文、非、小、生、凶、至、垒等),象数(数目字),象位(方位字),象气(语气词),象声(拟声字),象属(乙亥)。
②一、二、三等字找不出所象之物的形状,但确实又是以形来表意的,陈梦家将其看成抽象象形,认为它们的形体是从许多的个别的具体中抽绎出来的共相。见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 版,第32 页。